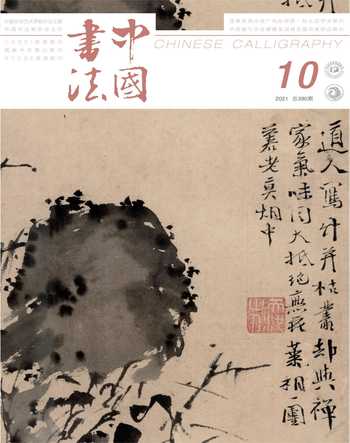不破不立有新法:徐渭對掛軸書法的視覺形式創造
劉正成











關鍵詞:徐渭 形式 掛軸 以畫入書 墨法
筆者在《掛軸:藝術書寫成為書法主流》[1]中論述了掛軸書法的流行對明代書法創作和審美的巨大沖擊。讓我們簡略回顧一下此前的歷史。
漢晉以前,即書法藝術的前自覺時期,書法大多用于實用藝術的裝飾。例如:巖畫符號、甲骨文占卜、青銅禮器、兵器、詔版、帛書、宮殿文字、紀功碑銘、祭祀碑銘、造像題字、摩崖刻經、抄書、抄經等。
中古時期,書法在文字的實用過程中審美作用逐漸提高,在文獻的抄寫和閱讀過程中,在紀念性建筑的記事和展示過程中,文字成了關注的中心,其書法的審美創造與觀賞性變得越來越重要。在這個過程中,專業性的抄書手、抄經手、書寫祭祀碑銘的書手,是最早的一批不記名的書法家。而個別經卷、碑銘的書寫者署名,是書法家在審美創造中主體身份認同的濫觴。
晉唐以后,由于紙張的普遍使用,除了抄寫、抄經等職業性書寫行為外,文件與詩文書寫成了所有文人的日常行為。于是,書法的藝術自覺性萌發并高漲,文人書法成為藝術主流。晉唐以后傳世書法墨跡均為文人書寫作品。例如:翰札、詩文手卷、冊頁、扇面等。除了文人實用書寫后進入審美欣賞功能外,也有部分純藝術書寫作品,如唐代書法家的書壁和屏風陳設書法。南宋施宿《嘉泰會稽志》云:『(賀知章)嘗與張旭游于人間,見人家好廳館、好墻壁及屏障,或忘機興發,落筆數行,如蟲篆飛走,雖古之張(芝)、索(靖)不如也。』[2]這是純藝術書法的濫觴期。但是,這種純藝術書寫的作品傳播和流傳范圍受到局限,純藝術書寫的作品并未大規模進入社會大眾的審美視野,這一時期的純藝術書寫只是書法藝術活動的支流。
明代中、晚期, 即嘉靖元年— 崇禎十七年(一五二二—一六四四),并后延至清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傅山逝世,是掛軸書法出現和流行的時期。前此時期,即元末和明初有少量小掛軸在居室中出現。文震亨(一五八五—一六四五)在所著《長物志卷五·書畫十一·單條》中云:『宋元古畫斷無此式,蓋今時俗制,而人絕好之。齋中懸掛,俗氣逼人眉睫,即果真跡,亦當減價。』[3]明代自永樂(一四○三—一四二四)以來,一方面王朝制度松馳,另一方面蘇州地區造磚業的發達,民居建筑的土木結構技術提高,高堂大屋在民間實現了普及。廳堂升高后,原先用于分隔廳堂內空間的屏風便相對顯得矮小了,于是長條形的中堂、條幅經過裱褙后,直接掛在固定通頂屏風——通屏上了。明代萬歷時期,蘇州、揚州一帶商品經濟發達,徽商、揚商、晉商匯聚于此,因其并不與文人藝術家打交道,只有通過書畫商收藏字畫,以附庸風雅、裝點廳堂門面,同時也為交際官場、培養子女求學入仕而賄賂,于是,畫商經營書畫市場的主要商品便是這種純藝術書寫的掛軸。畫店老板向書法家訂貨,向客戶供貨,或者按客戶的要求向書法家訂貨,書法家按需創作藝術產品。文震亨《長物志》對明代中、晚期書畫與市場、書畫鑒賞與收藏等社會狀態,做了很全面細致的古今比較研究和記錄。柯律格《雅債——文徵明的社交性藝術》一書所引證和羅列的書畫藝術作品在社會流轉的情況,正是掛軸書畫作品流行的某種藝術人類學背景。
掛軸書法作品特別是高堂大軸的幅面巨量增大,這一平面空間的改變首先導致了書寫載體與書寫工具的大變化,同時因長鋒羊毫與產生巨大浸潤效果的涇縣青檀皮宣紙的運用,進而使書法創作在筆法、墨法、章法這三大技法上發生了適應性大變化。徐渭書法創作正是在這個變化過程中發生了獨特的改變和關鍵性的推進作用。
徐渭棄唐取宋對筆法進行了破壞性的改革
掛軸書法的作品幅面的字形與點畫呈數十倍以上增加,自晉唐以來王羲之、蘇東坡、趙孟頫們所使用的鼠、兔、狼等硬毫短鋒難以操作,于是使用羊毫、石獾、茅草等原料制筆便直接導致了書法點畫與線質的視覺審美效果的改變,用一種通俗的說法是筆法變精致為粗糙。
吳門書家面臨這種改變的基本態度是從唐人筆法的保守中討生活,這種唐人筆法基本上就是由唐人所闡發和運用的王羲之『永字八法』。通過祝允明、文徵明、陳淳等吳門書家的作品來觀察,他們的翰札、手卷等作品與趙孟頫傳承『二王』法則是一脈相承的。但是,在掛軸作品特別是高堂大軸作品,唐人筆法顯得非常拘謹,尤其是文徵明的大軸行書書寫,非常小心謹慎,字字皆無放逸之筆,生怕越雷池半步。這些作品的用筆不僅充分體現了作品和單字由小變大后的掌控難度,亦是筆法點畫視覺形態規范的束縛所致。祝允明無大軸,此可以上海博物館所藏文徵明的高堂大軸《進春朝賀詩軸》,縱348.4c m,橫105.1c m為例。以祝允明、文徵明為首的吳門書家,以高舉趙孟頫復古主義的大旗,棄宋取唐,以唐人法則為圭臬,所以無法適應掛軸大字的新局面的狀態。對唐對宋的筆法取舍區分,可以從文徵明和徐渭大量的論書言論中看得出來。文徵明論宋人書較少,論唐人書較多且贊亦多,而所贊多在筆法,最為重要的在正德三年(一五○八)端陽前二日書于玉磬山房的《跋趙鷗波書唐人授筆要說》。云:
昔趙鷗波嘗言:『學書之法,先由執筆,點畫形似,鉤環戈磔之間,心摹手追,然后筋骨風神可得而見。不則,是不知而作者也。』今觀所書唐人授筆要說,則益信然。至于筆法次第,非深知者未易言也。把玩之余,為之三嘆![4]
陳獻章(一四二八—一五○○)甚至用廣東老家圭峰山的白茅草制筆,自稱『茅龍飛出右軍窩』,故號稱『茅龍筆』[5],其字跡點畫粗糙可想而知。然而,文徵明所貶低的『狂怪怒張之態』,又恰恰是徐渭別具只眼而取法的。他在《玄抄類摘序》中則幾乎是針對文徵明所推崇的『唐人授筆要說』來了一個全新而透徹的撥亂反正。曰:
自執筆至書功,手也;自書致至書丹法,心也;書原,目也;書評,口也;心為上,手次之,目口末矣。余玩古人書旨,云『有自蛇斗若舞劍器,若擔夫爭道而得者』,初不甚解,及觀雷太簡云『聽江聲而筆法進』,然后知向所云『蛇斗』等,非點畫字形,乃是運筆。知此則『孤蓬自振,驚沙坐飛』,『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可一以貫之而無疑矣!惟壁坼路、屋漏痕、折釵股、印印泥、錐畫沙,是點畫形象,然非妙于手運,亦無從臻此。手之運筆是形,書之點畫是影,故手有驚蛇入草之形,而后書有驚蛇入草之影。手有飛鳥出林之形,而后書有飛鳥出林之影。其他蛇斗劍影,莫不皆然。[6]
顯然,這種對『點畫字形』與『運筆』的不同界定,自非一般書論家對筆法的解讀,更近于創作實踐真實。文徵明所謂的『態』即『點畫字形』在徐渭看來只是『口目之末』,而非他所指出『運筆』則是『心為上,手次之』的『古人書旨』。換一句話說,徐渭用王陽明心學原理,闡述對『法』從『心』出的道理。這段書論序言,是徐渭棄吳門文、祝所尊的『唐法』,而進入蘇、黃所尊的『宋意』的筆法論總綱。而徐渭論唐人書較少,議宋人書較多贊亦多,最典型的是收入《徐文長逸稿》卷二十四的《評字》。云:
黃山谷書如劍戟,構密是其所長,瀟散是其所短。蘇長公書專以老樸勝,不似其人之瀟灑,何耶?米南宮書一種出塵,人所難及,但有生熟,差不及黃之勻耳。蔡書近二王,其短者略俗耳,勁凈而勻,乃其所長。趙孟頫雖媚,猶可言也。其似操作數率俗書不可言也![7]
被吳門諸家所尊崇傳授『二王』筆法的蔡襄和趙孟頫,徐渭則直言為『俗書』。《中國書法全集·徐渭》卷總計收入五十四件作品,有『四體』『五體』書長卷八件。在這些多體長卷中,尤以隆慶和萬歷初年之間(一五六七—一五七八)的六件多體卷,皆以宋人蘇東坡、黃山谷、米芾三人為主,幾乎未有唐名家體。除了偶有一二處顏真卿和《閣帖》中的魏晉人章草意思外,罕有唐人身影。其中尤以香港虛白齋所藏書于萬歷元年(一五七三)的徐渭早、中期之作《天瓦庵等四首四體卷》為例,基本上是對黃山谷和米芾的亦步亦趨。正是這些解構唐人筆法的長期努力,才促成了他在掛軸尤其是高堂大軸中具有原創價值的徐渭筆法。徐渭雖狂,但仍是一個具有自我批評精神的真人真性情。他在《題楷書楚辭后》對自己的楷書采取了否定的態度。曰:
慕子蘭深博古器,而法書圖畫尤其專長。余書多草草,而尤劣者楷,不知何以入其目也?古語曰:『心誠憐,白發玄。』其斯之謂歟?
徐渭這種解構不僅是對唐人筆法的破壞,甚至也是對宋人筆法的破壞——應該有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創造性破壞的矛盾心理。所謂『楷劣』應該用一種分析的方法去判斷,試以原藏于紹興市青藤書屋的《初進白鹿表小楷冊拓本》、現藏于故宮博物院的《禮部明公小楷冊》來看,這種不取『二王』館閣體而取鍾繇的楷則也許是其科場屢北的原因之一,但卻是一種非唐楷的新風氣。祝允明也取鍾繇《薦季直表》作小楷多得其形,而徐渭取鍾繇則多得于意,并成功地引入他的大字行楷之中而自創新格。也許,這種創造連徐渭自己也未必具有其自覺意識,故留下『楷劣』之論。如果我們當下對這種藝術史進程缺乏客觀而入微的觀察和認知,你也會難以理解徐渭筆法的這種破壞唐法傳統的必要性和創造的價值。
使用筆鋒很長的羊毫筆是解決書寫大字的主要辦法,但是羊毫柔而軟,給使轉筆毫書寫各種形態的點畫造成極大困難。直到清代書法家也一直為使用羊毫書寫大字頭疼。書法家包世臣《藝舟雙楫》中十分感嘆。云:
古人用兔毫,故書有中線;今用羊毫,其精者乃成雙鉤。吾耽此垂五十年,才什得三四耳。[9]
舉凡徐渭的掛軸作品上海博物館藏《一篙春水詩草書軸》,紙本,縱123.4c m,橫59c m。掛軸中『抱月懷中』的『中』字長豎以幾個頓點延續完成,占據整紙三分之一即同幅三個字的尺寸即超過40c m,從大小和點畫形態來說絕對是書法史紙張書寫上空前未有之筆法。其中絕大部分字的點畫絕對遠離王羲之的『永』字八法,在懷素、黃庭堅、祝允明草書絕對找不到的點畫和側鋒使轉方法,其中尤以『水』『眠』『傍』『神』『仙』等諸字離譜,如以唐法來論定皆為紊絲亂法的敗筆。但是以這個中堂幅面視覺空間的構成關系來看,它又是合理的,它明顯有節奏的快慢緩急,有力量的輕重虛實、有旋律快慢頓挫。這顯然比我們前面提到的文徵明《進春朝賀詩軸》的視覺審美更富有變化。
徐渭在他的前期創作中掛軸較少,即使有也是幅面較小,如約書于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的《十六夕詩草書軸》,也高不足四尺。到萬歷八年(一五八○)六十歲以后的晚年,書寫高堂大軸驟然增多,這應該就是他對筆法創造更為成熟的時期。如現藏寧波天一閣的幅高八尺的《白燕詩軸》和現藏青島市博物館的幅高丈二的《群望詩軸》,其行書的點畫變輕逸為沉厚,他的點、橫、撇、捺形態雖完全偏離唐法,甚至與善寫大字行書的黃庭堅精致點畫形態相去甚遠,他卻在高大的紙幅上用中鋒行筆,筆實墨沉,字字雄峙,震撼而立,又如鐵錘敲擊,鏗鏘有力。這種筆法創造在吳門諸家眼中即是大逆不道,但他卻是張瑞圖、王鐸、傅山、何紹基、沙孟海等一路掛軸新書風的開山祖師。
從傳統筆法的開拓上來觀察,現藏于無錫博物院書于萬歷十年(一五八二)左右的《李白橫江詞草書軸》,則是將王獻之、張旭『一筆書』和傳為創于蔡邕、成于王獻之、唐太宗和武則天所愛的『飛白書』在一幅作品中融合一體繼承改造,筆筆連屬、筆筆飛白,蔚為大觀。后繼者王鐸或有飛白,或有一筆書,皆未一統而成。
作品平面空間擴張后,書寫工具毛筆的材質、大小及其使用方法均發生適應性改變,因此要用一種新的技法觀和審美觀來創作和審視書法作品點畫與結字的視覺形態,這樣才能更為深刻地理解徐渭在筆法和結字改造上所作出的巨大貢獻。
徐渭變亂勻整行列開創了掛軸多種章法結構
掛軸書在明代中期流行以來,雖然作品幅面變高變大,書法大多仍然沿襲千年以來翰札簡冊書的豎成列、橫成行的閱讀式的章法結構進行書寫。徐渭自己的一些小楷作品就是這種章法構成的典型。現藏于故宮博物院的兩件一早一晚小楷書軸,分別是無記年而應歸屬于早期的《蘇軾黠鼠賦行楷軸》,縱111c m,橫30.5c m,計二百九十八字;款署壬辰即萬歷二十年(一五九二)的《歐陽修晝錦堂記行楷軸》,縱183c m,橫48.5c m,計五百一十二字。一般的行楷小字通常會按卷、冊幅式書寫,這兩件多字作品卻寫成掛軸,尤其是《歐陽修晝錦堂記行楷軸》高五尺多的掛軸,想必是應囑點文的書寫,徐渭只能按傳統章法模式完成。盡管他有高超的點畫書寫技法和通篇行列的視覺處理能力,在不用打格的廣大幅面上字字精整,氣息連貫,行行端正,全幅無一氣弱處,堪稱精品。如果兩幅作品并列置之廳堂展示,遠距離觀賞,不僅閱讀困難,章法平面構成雷同且平淡無奇,久視之則有視覺疲勞感。
從晉唐宋元以來,傳統的翰札、手卷紙張幅面很小,橫平豎直的行列章法自然便于在手中閱讀把玩。中、晚明掛軸書法出現后,特別是高堂大軸在當時蘇州庭園居室中甚為流行。掛軸作品平面空間擴張數十倍以上后,橫平豎直的這種翰札簡冊式章法排列在視覺審美上顯得十分呆板。因此書法家都面臨作品幅面變大以后,如何將晉唐以來經典作品創作中的經驗進行轉換,來處理大作品的章法構成問題,而徐渭無疑是屬于第一個吃螃蟹者。徐渭毅然變亂文徵明式的掛軸章法結構,即打亂字與字、行與行的等距空間關系,使作品的視覺空間出現了如同繪畫一般的奇異變化。
徐渭處理高堂大軸章法構成的第一種方法是以密破疏。這以均收藏于蘇州博物館的《代應制詠劍詞草書軸》,紙本,縱352c m,橫102.6c m和《代應制詠墨詞草書軸》,紙本,縱353c m,橫102.6c m為例。兩件作品尺寸只差1c m,可謂相同大小的超級高堂大軸。沈偉考證:這兩件尺幅幾乎完全相同的作品均系代翰林院張元汴而作。萬歷九年(一五八一),張元汴在京翰林任上,徐渭去年因張元汴邀請赴京客其幕中,多有代作。所謂應制,即是如同當年代胡宗憲上的《白鹿表》一樣,奉皇帝命令而作。兩軸所收詞皆出于《徐文長三集》卷十二,可見詞是徐渭的、書是徐渭的,紙是太史張元汴的(徐渭哪里買得起這種丈二巨幅宮廷用宣紙),獻給皇上的名義是太史張元汴的。這兩首獻給皇上應制歌功頌德的詞,卻全然沒有阿諛奉承皇上之嫌,如同李白獻給唐明皇楊貴妃的《清平調三首》一樣,在歌頌一種美,即鑄劍之美和造墨之美,堪稱絕妙好詞。所以這兩件筆酣墨暢、美輪美奐的杰作傳世于今,堪稱一對翰墨國寶。這兩件書作的藝術特色首稱章法之美。徐渭之前,未見任何書家寫如此大幅面如此密集的行草書條幅。這種章法的最大特點,不是讓觀賞者像傳統審美那樣觸眼先去閱讀它的詩文,而是像觀賞范寬的《溪山行旅圖》或董源的《溪岸圖》或巨然的《萬壑松風圖》一樣,是首先接受它無比密集而回環奇妙圖式的視覺震撼力。徐渭用姿態萬方、若霧若煙、飄飄欲仙的行草筆意,整幅密不透風,但又字字點畫舒展優游,編織了一只巨大的具有魔力的線條之網,讓你驚嘆莫名。筆者曾三次專程去蘇州博物館才得以一見此二軸,但因當時并無高墻可以懸掛而窺全豹,只能手把軸頭,心生云龍見首不見尾之嘆。這種審美感受和在博物館玻璃展柜燈光下觀賞王羲之《蘭亭序》、顏真卿《祭侄稿》和蘇東坡《寒食帖》時所完全不同的。以視覺感受為先導,再以閱讀認知為深入,讓你從視覺上、精神上,進而文化上完成復合型的書法藝術作品的審美。
再以《中國書法全集·徐渭》卷所收《春園暮雨詩》三軸,其實是同一詩文內容的三件作品為例,進一步談談徐渭章法創造。這三件作品幅式相近而大小不同,現分別在兩家公藏和一家私藏。沈偉根據詩文和作品的款字分析考證,此三件掛軸皆略書于萬歷十八年(一五九○)春之同一天,徐渭應邀在他的學生陳守經家里吃飯前后書寫。《徐文長三集》卷七收有幾首同一時間段與陳守經飲酒并書畫的詩。其中,蘇州蔣風白舊藏本尺寸相對較小,縱166c m,橫68c m,應是五尺中堂,款署『病起,過陳守經』云云,應是飯前即興賦詩時所作行楷書。上博藏本最大,縱306.6c m,橫104c m,這幅是一丈巨軸,款署『春初,飲陳守經海棠下時』,應是酒興起時所作行書。故宮藏本大小居中,縱209.8c m,橫64.3c m,亦屬六尺大軸,款署『醉守經海棠樹下時,夜禁頗嚴』云云,應是深夜醉后所作大草書。這三個大軸雖在同一天晚上書寫,書寫的又是同一首詩,卻絕不雷同。首先是書體不同,飯前先寫的行楷結構扁長,點畫精細飄逸,字距行距均較寬松;飲中所寫的行書結構變長,點畫重拙樸厚,字距極度縮小,行距略顯,如傾瀉而下;醉后所寫的大草字距行距幾無空隙,用筆疾速,左盤右旋,多字連綿如一筆書,點畫粗時多飛白,細時如游絲,通篇無字距、無行矩、無空白,卻通透灑脫,如金花遍地。
三件相同文字,相近幅式,并幾乎同時書寫的大軸,作者運用不同的書體和字形長短結構、不同的點畫粗細輕重、不同的行筆速度和墨法,創造了三個截然不同的平面空間構成即章法,創造出非凡的視覺張力和藝術感染力。這三件高堂大軸作品的謀篇布局,章法結構,可以說在祝允明、文徵明等吳門諸家作品中未見的,即使在徐渭之后的董其昌、張瑞圖、黃道周、倪元璐的作品中也罕見。如果說徐渭的兩件應制詠劍、詠墨大軸作品密不透風形章法啟迪了傅山的話,這三件春園詩大軸以及北京辛氏舊藏《李白永王詩草書軸》的疏密對比章法無疑影響了王鐸。這兩位偉大的繼承者王鐸和傅山成功繼踵了徐渭近于破壞性的章法開拓之路,并由王鐸推進到一個空前絕后的高峰。
徐渭以畫入書、由濃入焦創五色墨法
明代以前書畫用紙皆用楮皮、桑皮纖維做的皮紙吸水功能較弱,沒有一筆落紙見濃淡的功能。因青檀樹是安徽宣州涇縣當地主要的樹種之一,而青檀樹皮纖維粗壯而長,與當地的沙田稻草按四比六混合后能飽含水分,便使水墨因浸潤而出現濃淡效果。與明以前的所有紙張都不同,為書畫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創新條件。文震亨(一五八五—一六四五)《長物志》卷七《論紙》:『涇縣連四最佳。』[10]沈德符(一五七八—一六四二)《飛鳧語略》:『此外,則涇縣紙,粘之齋壁,閱歲亦堪入用。以灰氣且盡,不復沁墨。往時吳中文、沈諸公又喜用。』[11]『文、沈諸公』喜用的涇縣這種『連四』紙,就是沿用至今的宣紙。
明代以前,基于翰札、手卷這種小幅面作品使用的吸水怪不強的皮紙,自王羲之時代以來千年時間,書法的經典用墨理論以蘇東坡《仇池筆記·論用墨》為概括,既黑又光,是書法用墨的準繩。云:
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為棄物;若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晴,乃為佳也。[12]
掛軸書法流行的早期,即使流行了吳門『文、沈諸公』喜歡使用的吸水性強的涇縣宣紙,但在墨法上仍然沿用晉、唐、宋的既黑又光的古法。這樣,在凸現視覺刺激性的大幅面掛軸書法的無差別濃墨運用,就缺乏觀賞中色彩的節奏感,顯得十分呆板乏味。于是,稍后時代兩位偉大的畫家徐渭和董其昌則破壞墨古法,董其昌用淡墨入書,徐渭則用焦墨入書,創造性地打開書法用墨的新時代。
唐代杰出的藝術理論家張彥遠(八一五—九○六)在《歷代名畫記·論畫體工用拓寫》專門闡發了繪畫中的墨法,即著名的『墨分五色』論。曰:
夫陰陰陶蒸,萬象錯布。玄化忘言,神工獨運。草木敷榮,不待丹碌之采;云雪飄飏,不待鉛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鳳不待五色而綷,是故運墨而五色具,謂之得意。意在五色,則物象乖矣。[13]
這種『運墨而五色具』之法,不僅是畫法,亦通于書法。運墨不是『意在五色』,在『得意』而已。這種『得意』應該就是運用墨的深淺濃淡的變化,使之有『五色具』的藝術效果。時至今日,幾乎所有西方的中國美術史論家,包括一直生活在西方文化環境中的華裔美術史論家,均因缺乏張彥遠這個『墨分五色』的精論,無法感受和進入中國宋以后的文人寫意畫的審美境界,對書法審美,更是有感覺而無法跨進其審美門墻予以理性認知的主要原因之一。
宣城涇縣青檀樹皮和沙田稻草制造的宣紙出現,使書法作品的濃淡墨在視覺空間出現更多的節奏和韻律變化,于是,便有了唐以來繪畫中『焦、濃、重、淡、清』這種『墨分五色』的新技法。用繪畫形式手段處理作品變大后的書法墨法問題,這就是筆者曾經研究過中國書法美術化傾向在明清時代發生的重要變化之一。[14]可以這樣說,畫家徐渭是把張彥運『墨分五色』的理論運用于書法的先行者,他的『焦墨入書』破壞了蘇東坡總結的『小兒目晴』的古典墨法,開啟了掛軸時代純藝術書法的一個視覺形式技法創造的新天地。
試以徐渭與董其昌草書用墨的比較來分析,他們有顯然不同的墨法來創造『虛』的點畫視覺形態。收入《中國書法全集·董其昌》卷的美國底特律美術館所藏董其昌《張旭郎官壁石記草書卷》,幾乎均用輕柔如禪翼的虛筆所書,其視覺效果如同飛白,然而并非飛白,是用含水較多的淡墨書寫而成。沒見徐渭明顯用淡墨作書,而是用不滲水的濃墨、焦墨作狂草,從而創造出奇妙的飛白來。
如果說《春雨楊妃二首草書卷》的卷首開筆時還有一點淡墨的痕跡,十行以后皆用濃墨,后半幅基本是焦墨寫成。后半幅三十行左右用濃墨、焦墨所寫出的飛白書,真有云龍霧豹,天泉飛花的境界。徐渭的飛白不是淡墨書成的,恰恰相反是用濃墨、焦墨和渴筆以疾速的行筆書寫的,達到高潮處行行皆是『一筆書』,左飛右挪騰蛟起鳳。《白燕詩三首草書卷》落筆便是焦墨,第一個字就出現飛白,第二行開始,通篇皆以焦墨飛白書完成。有漢武帝《秋風辭》『秋風起兮白云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的畫面疊印,又有魏文帝《燕歌行》『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的色彩幻化。這種以濃入焦的墨法還有秋風撕裂時而山谷盤旋,時而平野回蕩的音響效果,堪稱變幻莫測氣家萬千。最近有幾位善于草書的名家在公眾場合聲稱『已經超越古人』引起一片嘩然,也令人費解。這句話沒有全部錯,從事書法的人數和寫出作品的件數,的確是今非昔比;如果從經典書家和經典作品的高度與深度,也許是今不如昔?但是,分析藝術作品不能打包稱斤兩,而要一件一件具體分析。就在今日鼓吹『形式至上』的時尚中,參加『國展』作品大多以設計代替書卷的自然天機,有幾件作品從視覺形式上超越徐渭的上述飛白狂草?也許你人狂、心狂、動作狂,但你詩不狂、文不狂、筆不狂、墨不狂,何來書狂?更何來狂草?
就徐渭的高堂大軸的草書作品來看,運用焦墨飛白的作品有現藏上海博物館的《杜甫懷西郭茅舍詩草書軸》和現藏西泠印社的《岑參和賈至詩草書軸》,前者通篇飛白,如風吹白云霞光萬道,如蓮臺花落目不暇接。后者是丈二巨幅的焦墨行草書,字大者徑尺,字小者四五寸,縱筆揮寫,大小差落,重者如鐵柱撐天,輕者如浮云掠空。如果說到視覺沖擊力,這種畫如滿架葡萄飄香,又如萬歲枯藤掛崖,確實是既非晉唐、又非宋元的『真我面目』。這種墨法的繼承者是傅山和齊白石。
作為畫家的徐渭,他眼前的畫會變成書,而眼前的書會變成畫。幅面從翰札書寫成幾十倍擴大的幅面后,繪畫的視覺創造無疑經過畫家手與腦的轉換,為掛軸書法的墨法創造出一些新的審美觀念去適應它。如果說董其昌用濃與淡的墨法變化中尋求掛軸書的墨法輕逸空靈,徐渭即用潤與枯的墨法變化中尋求其墨法的蒼勁沉雄。徐渭這種用焦墨渴筆所創造的新墨法不是否定晉唐經典墨法的技巧,是掛軸書法大幅面作品空間視覺形式的適應性改變。這種墨法改變又是基于審美功能的變化而產生的,這就是書法作品從坐在書房拿在手里把玩的近距離審美,變成掛在廳堂的遠距離審美感知所左右的。也可以這樣說,正是重視墨法變化的視覺審美,才有了徐渭開創的沒骨花鳥畫一筆見濃淡的水墨大寫意,從而受到石濤、鄭板橋、吳昌碩、齊白石這些晚輩巨匠的頂禮膜拜。
一個簡短結論:徐渭和晚明六家是明代書法的高峰
王世貞曾有所謂『天下法書歸吾吳』[15]的論斷,他是否看見過徐渭的書法,或是看過了并不予認同?不管處于哪種狀態,有一點是肯定的,即徐渭及其書畫藝術并不屬于吳門時代。徐渭書法與文徵明所代表的吳門書法確實有相當大的不同,這種不同不僅在于藝術創作主體身份未經察覺的差異,而且在于掛軸作品純藝術書寫成為主流以后的視覺形式的破壞性、適應性的大改變。
明代以前,書法作品傳統的審美方式是閱讀把玩式,廳堂中的掛軸變成繪畫作品視覺掃描加閱讀把玩的審美模式,前者的要點在筆墨與神采的意境把玩,后者的要點在平面空間視覺形式的感知。掛軸書法使書法家的創作不再僅僅是自娛自樂的書房文玩和文人圈里的風雅事,為他人、為大眾需要所創作的作品不僅在文字內容、作品幅式大小、特別是創作心理與審美模式上,都與宋元以前的傳統極為不同。以文徵明為首的吳門書家為掛軸書法的視覺審美也傾盡全力去適應,但是囿于唐法終究沒有跨出決定性的一步,這一步是由徐渭跨出去的。
徐渭在筆法、章法、墨法的視覺形式的新創造,開啟了近古五百年來的書法大改變。如果可以說黃帝之史倉頡創造文字結構之美成為書法史開山之祖的話,王羲之『永字八法』和文人書法是書法史的第一次大變革,那么徐渭所領軍的晚明六家掛軸書法的純藝術書寫是書法史的第二次大變革。鑒于晚明書法潮流延至清初的史實,近古書法史上概稱『晚明六家』是大家熟知的(以年齡為序)董其昌、張瑞圖、黃道周、倪元璐、王鐸和傅山。所以,明代書法的高峰不是以文徵明為代表的吳門書法,而是以徐渭及其『晚明六家』為代表的劃時代創造成為高峰。當代書法則是這個近古五百年新時代的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