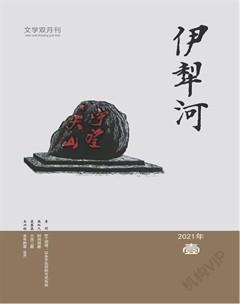阿熱買里撿秋
1
我在阿熱買里住過整整一個月,一開始常陷入焦灼,從熟悉的地方到陌生的地方去,總要適應幾天。此時秋收已近尾聲,豐饒過后的微涼,一層層彌漫上來,逼得自己鼻尖發酸。
這一片果林,黃香蕉正值好年華,他們都很喜歡,尖叫著搖晃樹枝,頂端的艷麗落下,又尖叫著從綠油油的苜蓿地撿起來,象征性地用手掌擦兩下,吃起來。在阿熱買里,我見到了所有成長在記憶里的老品種蘋果。我喜歡二秋子,吃夠了,放兩個在包里,拿出來聞一聞,味蕾積累多年的愛意在鼻息間歡呼雀躍。海棠果也令人歡喜,小而金黃的,擠在一起,和秋葉一樣身披風塵,并不顯眼。待到霜降,方知人間美味也如人生,需要櫛風沐雨,寒霜淬煉。
這片果林是亞哥家的,他是一個真正的農人,整個夏季奔忙于田地間,臉色默黑。他很固執,不肯用農藥。植物并不都聽話,果林里套種的蔬菜,品相一般,尤其是西紅柿,遠看紅艷艷一片,腐敗者近半,能入口者甚少。完整美好的則口感極佳,我一次能吃七八個,中午回去不吃飯。土毛桃亦如此。果蒂處往往生蟲,蟲蛀后生出結晶狀傷痕,色澤暗昧不清,介于綠和黃之問,個頭小又有毛。和亞哥一樣的人,在阿熱買里并不少見,他們的植物大部分靠取天地精華長成。以相貌取之的思維,在阿熱買里果蔬界大錯特錯,會失去很多機會。我提著一袋核桃般大小的毛桃去水渠邊洗,又坐在田埂邊大吃大嚼,整個過程得意洋洋。和我一樣得意的還有云,在廣袤而空闊的地帶看云,云才是云,有恣意妄為之態,潑出巨幅華美的形象,也扯出若有若無的一抹,云淡風輕。
恣意年華,不問收獲,佛系種植。包括自己人生的大事,譬如做一份什么樣的工作,該在一個怎樣的城市生活,嫁給什么樣的人,并無精準的規劃和經營。游牧風韻,浪子情懷,有些美,最終,也有些落寞。我在這里捕獲一些被農人遺忘的東西,覺得自己和阿熱買里的某株植物很像,一棵豇豆、一株杏樹或者一根狗尾巴草。
2
天黑之前,一直在幫不知姓名的女人掰苞米。她戴口罩和粉色紗巾,只露出睫毛長長的一雙黑眼睛。總共17畝地,我們在各自的角落里,像是幾只埋頭苦吃的蠶圍著一大片桑葉。鐮刀悄無聲息,在身后留下大片躺倒的玉米。日頭漸漸灼熱,她家里的人都躲進棚子下吃西瓜,她沒有去。在大片砍倒的秸稈里,一小團的粉色,仿佛未動過地方,卻從這頭倒在了那頭,又開辟了一片新領地。我對著她喊,我們從兩頭開始,會師啊。地頭太遠,我們都沒聽清對方說的話,卻都知道說的什么意思。日頭略斜,一層云上來,帶來清風,心里舒爽,提高了調子唱歌,《我和我的祖國》,反復唱,停不下來,她在那頭唱,比我唱得好。
她讓小女兒送西瓜給我吃,我要她吃,推讓得面紅耳赤。在玉米地里一下午,只有唱歌時,我的腰痛得不明顯。勞動最光榮,唱歌與勞動最相配。
有一天我們去了瓜地,只帶了拳頭。瓜們大大小小橫在地里,外皮蒙了一層白膜。逡巡期間,捕捉到一個飽滿的瓜,摘下拿到水閘上砸開,我親手干的。皮薄,略微過了時間,口感稍差,尚有夏日余味。但環境不錯,渠里的水半清半渾,蟲鳴和水流聲和鳴。這片瓜地的主人我們也認識。今年的西瓜不如去年的好。去年瓜賣了好價錢,嘗了甜頭的人,以為會繼續下去。夏天見時,他連連搖頭,好像損失了一個億。瓜地后期疏于管理,成了一群無主之瓜。有人口渴進去翻找一番。不口渴也很想去尋寶,比如我們。主人的遺棄,成就了路人的驚喜。
教師節的前后幾天,我們都在田邊找“紅姑娘”。“紅姑娘”是一種藥材,樣貌俊美,外罩似燈籠,艷艷的桔色,內里裹著潤盈光潔的同色果實。咳嗽是現代人流行的病癥,我有一次在偌大的辦公室見到4個人帶著各種品類的糖漿,都是干咳,夜咳,像老頭一樣。“紅姑娘”治咳嗽,幾個男人在做一件大事,往往是給他們的妻子或者老母親。他們長了肚脯,彎腰時看上去吃力。“紅姑娘”并不只長在路邊,容易采摘的早被人先行下手,但可以順著這種草本植物的軌跡前行,灌木叢里會多些,他們巧妙而為難地鉆進去,不久,粘一身刺球出來。表情得意或者黯然,與“紅姑娘”的數量多少有關。
3
阿熱買里有兩個巴扎日,周五和周一。要是有王哥在,我們就會買牛肉。他是老江湖,老牛或者小牛,哪塊肉好,他都知道賣肉的人并不以要把肉賣給我們為目的,他連看都不看我們一下,只認真和王哥對視。王哥的手指頭一指,刀子就按著王哥手指頭畫出的圓或者半圓割下一塊肉來。
買完東西吃東西,老三樣,先來一碗涼粉。隔壁烤肉師傅是整個巴扎最像樣子的,穿廚師的制服,廚師帽也規規矩矩扣在腦袋上。王哥愛吃烤腸子,香,油多,我們勸他,三高越高,肚子越胖,他根本不聽。我一般吃兩串烤肝子。正吃著,過來一個熟人,非得請客,我們起身相勸,聲音大起來,那也勸不住,只好多吃。吃多了燒烤,趕緊去刨冰攤子上解解膩,一人一碗,酸酸甜甜,冰涼爽快。有兩個同事合伙買了一箱子黃色棒棒冰糖,一個說,過年的時候家里來客人泡一根到茶碗里去,熱情,有年味道。另一個也很高興,說比超市便宜許多。
他們又去菜攤子上買菜。我等得著急,四下亂看,腳下的蛇皮袋子露出紅紫洋蔥。天吶,怎么可以這么好看!小,圓,齊整。我買了一大袋子回家。放在小竹筐子里,送給老公當茶寵。他有些為難,好看,也有趣,不過,好像奇奇怪怪的,茶配洋蔥?我只好把它們端到臥室的飄窗上。后來他們長出了芽,嫩綠有趣。再后來用它們做抓飯,炒雞蛋,吃了好幾頓。
阿熱買里的村干部和村民很高興我們去巴扎買東西,甚至在一天早派工會議結束時,有人極為認真地安排,今天是巴扎日,你們等下都去逛逛,買點吃點什么的。一來嘛,搞好干群關系;二來嘛,拉動一下消費。原話不是這么說的,就這么個意思。我記得是羅書記說的,他不一定肯認賬。他現在有阿熱買里情結,我們為這個村多付出一點,他覺得很應當,也很有成就感,并且露出了得意的微笑。冬天的巴扎怎么辦呢?有人趕緊說,他們鄰居家計劃冬天賣烤紅薯。
4
9月下旬最暖和的一天,我們在大桑樹下舉辦了一場小小的宴會。戶外餐桌和所有的地墊都從車里拿了出來。每個人都帶了吃的,烤雞和小紅蝦,幾種水果,瓜子和花生,馕和辣子醬。大家席地而坐,亮哥用爐子煮了兩包方便面,再把蝦和玉米粒剝好放進去,一人分配了一杯(餐具是一次性紙杯),玉米濃湯海鮮面哪。過往的車輛有意停滯,副駕駛轉臉看我們。有人還從車窗里伸大拇指給我們。一只松鼠從頭頂的枝丫間現身,散步,像孩子在家門口玩耍,并不理會占用了它家領地的我們。
夜晚我們組織一個暴走小分隊。村莊很方正,周圍是農田,我們在最外圍的方框里重復路線三遍。手機里放一點音樂,天邊的云從粉紅色慢慢變成了暗灰色,樹和苞米地的影子濃重起來,每一片地的氣味都不相同,我們像狗一樣吸鼻子,判斷植物的種類。植物充滿個性,連氣味都是。可如果不在夜晚出來走一遭,鼻子的功能會被浪費。
走最后一圈時,有人指著天上的星星問,那是不是北斗?無人回答,有人拿出手機問“度娘”,指著最亮的星星說,看那,那就是啟明星。我們小的時候,父母會教給我們星星和云的知識。云是會左右天氣的。現在的孩子,在手機和電腦上有更豐富更智慧的世界。月亮藏在樓背后,他們也看,并不暢想月亮里的嫦娥和月桂樹,而那些典故,早就從現實又不現實的網絡世界獲知了。他們更豐富,所以并不抱殘守缺。可是月亮并不殘缺,比如今天是中秋,那么圓,那么溫柔,又那么堅定。
再好的日子和再壞的日子,都在指縫間溜走。情懷、友情的變遷,孩子長大的步伐,包括阿熱買里的那段日子,都讓我憂傷。我想擁有一些東西,可擁有后一樣孤單。我以為走入陌生會孤單,可那孤單竟然如此豐美,到最后一點也不孤單。
·作者簡介·
李昱慶,現居伊寧市,伊犁州作家協會會員,就職于伊寧市人民政府辦公室。作品散見《伊犁河》《詩選刊》《南方日報》《新疆日報》等多家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