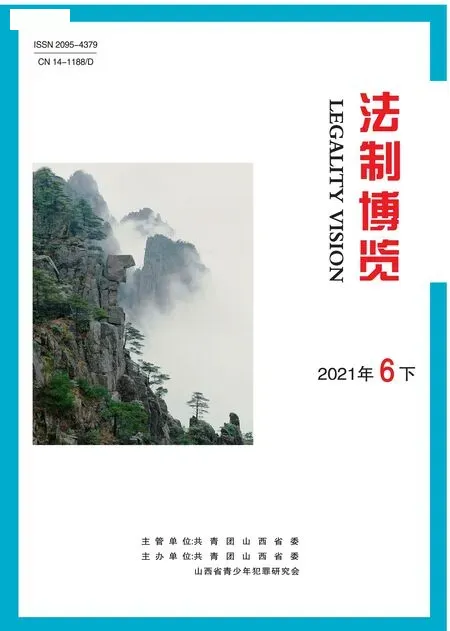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理論及實踐出現的若干問題研究
明 溪
(北京交通大學法學院,北京 100044)
一、理論探討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各國立法中均有體現,下面將從定義“非法”“證據”“排除”三個詞語出發定義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具體概念。
(一)非法
顧名思義,“非法”即指的是違反違背法律法規。那么在我國,“非法”中的“法”涵蓋了哪些法律法規和法律文件?隨著201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下稱《刑事訴訟法》)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進一步細化,雖然公檢法等相關主體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解釋上仍未能達成基本共識,但我國理論和實踐中有關這一點已經趨同一致,即“非法”中的“法”應僅限于符合《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中明文規定的及以其為基礎的《嚴格排除非法證據規定》《排除非法證據規程》等法律法規明文規定內容。
之所以不能將“非法”的“法”擴大到包括一切實體法和程序法,是因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以保護人權和維護結果正義之間的平衡為目的,驟然擴張很容易打破這個平衡;且從我國國情來看,我國目前司法資源不足、偵查人員素質、偵查技術等均需不斷發展,貿然擴張,反而容易欲速不達,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健康穩定發展和順利運行造成影響。因此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固然能夠發揮保護人權、維護程序正義等作用,但目前仍有必要加以限制,以在打擊犯罪和保護人權之間尋找平衡。
(二)證據
非法證據包括兩類,一為非法所得言詞證據,一為非法所得實物證據。對有關非法證據的爭議主要存在于“毒樹之果”、二次自白問題中。對“毒樹之果”問題,即使是在確立該規則的代表國家美國,其判例法中也多有例外;針對該規則國際也都普遍采取保守態度;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體系中也是如此,采取保守態度,并不存在關于“毒樹之果”規則的認定。
關于二次自白問題,一般認為其屬于廣義上的“毒樹之果”,我國有關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對該問題并無明確規定。但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已有案件表明排除的態度,即浙江寧波章國錫受賄案。此問題在立法和實踐中都較新穎,缺乏比較有公信力的結論,實務中一般不主張一排到底。
(三)排除
證據法理論中,對非法證據一般有兩種排除方法,“強制性的排除”和“自由裁量的排除”,區別在于確認某一證據為非法證據后[1],法院是否具有決定排除的自由裁量權。
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為兩者結合,在立法中分別體現為“應當予以排除”和“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即法庭擁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權,要求對非法證據做出補正或合理解釋,否則排除。
此外,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還包括由我國獨創確立的“可補正的排除”規則,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創舉,跳出了西方證據法理論“All or nothing”的極端規則,充分考慮到司法現狀,對非法取證情節較輕的程序瑕疵不是一律排除,而是給予了補救機會,避免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適用過于嚴格對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帶來較大的沖擊,維護了司法公正。
二、適用現狀
(一)立法發展
我國對有關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法律法規自1994年出臺,2010年正式確立,此后數年數次規定、規程出臺,健全完善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最新法律法規為2018年對《刑事訴訟法》進行的第三次修改,于第五章第五十六到第六十條詳細規定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配合其后陸續出臺的配套司法解釋,更進一步完善了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二)司法實踐現狀
1.應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案件數量年際變化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經歷了近十年發展后逐漸深入人心,在實踐中應用也逐步上升,在諸多實證研究文章中都體現出這一觀點,表明有關非法證據排除的案件數量、應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案件數量均處于上升態勢。這符合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相關立法情況,說明在司法實踐中越來越重視保障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權,重視證據來源的合法性[2],重視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應用。
2.應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案件普遍困境
雖然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逐步普及深入,但在司法實踐中,成功運用該規則進行非法證據排除仍然面臨困境,非法證據排除“難”已經成為被告人、律師和法官的共識。在學者易延友的一篇實證分析文章中,1459個有關非法證據的刑事案例中提出非法證據排除申請能獲得支持從而排除非法證據的案例僅有一成[3]。
分析其原因,可能有如下影響因素:
(1)提出排除非法證據的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是否有辯護律師。非法證據排除問題是專業法律問題,我國重刑傳統加之普法程度不足,大多數刑事案件被告人并不具有專業法律知識,因此必須由律師幫助提出。
(2)“毒樹之果”原理的缺失。“毒樹之果”原理在其發源地美國受到極高重視,而我國在立法上回避了“毒樹之果”問題,并未確立毒樹之果原理,導致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實際應用困難,尤其是在二次自白、多次自白語境下。
二次自白問題作為“毒樹之果”原理的派生,在我國司法實踐中解決情況如何?在針對律師的調查問卷中顯示,二次自白被排除的可能性“非常小”的超六成,“比較小”的近三成,兩種情況共占比91%[4]。易延友教授的研究則顯示有的法院存在“以二證一”“二三證一”現象,即以之后的取證程序合法倒推之前的程序合法,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此類案件中失去震懾效果。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如果不排除“重復自白”,排除規則就會在事實層面被規避,無異于縱容偵查機關“曲徑”規避法律,排除規則喪失其效用,不能起到震懾作用,不能保護基本人權。
(3)其他因素導致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失效。有的法院表現出“真實故合法”“印證故合法”“穩定故合法”的論證模式,毫無道理地曲解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針對的應該是取證程序的合法、取證主體的適格,而從來不針對所獲得證據是否真實。
有的被告人遭受過刑訊逼供但表示不需要提起非法證據排除,因此受理法院也拒絕提起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不符合我國法律對嚴重違法所得證據所本應采取的強制性排除規則,法院以被告人拒絕而不提起排除程序是明顯不符合法院履行職責的表現。
此外還有被告人與辯護律師意見不一致,辯護律師認為“贏面小”因而不提起排除程序;混淆瑕疵證據與非法證據;控訴方證明責任過輕、辯護方申請過難等原因導致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失效。
三、改進路徑
針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所展現出的問題,筆者認為可能有如下改進路徑:
第一,加強普法教育,樹立依法取證的法治理念。使各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都有非法證據應予排除的意識的同時,也應提高偵查人員、司法工作人員法治意識,明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內涵,杜絕“真實故合法”“印證故合法”“穩定故合法”等對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曲解,加強裁判文書說理,使論證符合事理邏輯,符合法律規定,而非“真實故合法”式的強詞奪理。
第二,確立“毒樹之果”原理,重視程序層面的完善和落實。我國法制建設尚未完善,司法現狀不容樂觀,也素有重實體正義而輕程序正義的傳統,確立“毒樹之果”原理較困難,但至少在二次自白這樣較典型、較特色的情境中,應能明確否定其后續重復自白的證據能力,避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被架空。
第三,強化律師的參與權和辯護權,調整公檢法三機關的權力關系,完善相關的配套制度。通過建立律師訊問在場制度、落實沉默權,建立完善公檢法三機關監督體制等措施,盡可能使司法機關保持獨立性,敦促法院盡職盡責履行職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