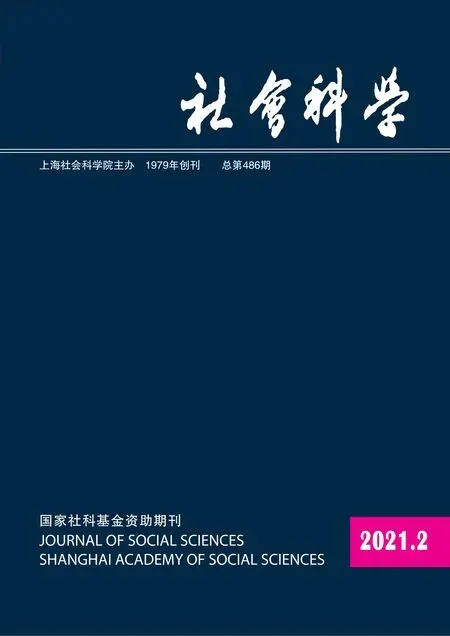“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命題之反思
劉林平 任美娜 楊阿諾
1847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影響深遠的《共產黨宣言》中斷言,工業革命和世界市場塑造了現代資產階級:“現代資產階級本身是一個長期發展過程的產物,是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一系列變革的產物。”(1)[德]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2頁。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從宏觀社會歷史角度來談論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產生與發展的,他們的論斷精辟并富有啟發性,但略顯籠統。在《共產黨宣言》中,他們還認為,資產階級把“宗教的虔誠”這一類東西“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2)[德]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第252頁。他們的這一觀點對于后來的馬克斯·韋伯是否有啟發,我們很難判斷。57年之后,與宏大敘事的《共產黨宣言》不同,馬克斯·韋伯發表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對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的產生與發展做了細微而具體的討論。他提出了與“幼稚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3)[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林南譯,譯林出版社2020年版,第27頁。相反的思路,將資本主義產生的關鍵因素或變量歸之于一種從新教倫理發展而來的精神——資本主義精神。韋伯關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命題為解釋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和視角。但是,學界關于這一命題本身的研究并不深入。在面臨新的歷史轉折關頭的現在,對于一個具有理論張力的經典命題重新進行反思與討論也許不無意義。
一、韋伯命題的基本含義和理論模型
在談論資本主義精神之前,先要弄清楚什么是資本主義。韋伯首先否定了資本主義就是追求獲利的庸俗化看法,他說:“對財富的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資本主義,更不是資本主義精神。倒不如說,資本主義更多地是對這種非理性(irrational) 欲望的一種抑制或至少是一種理性的緩解。”(4)[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修訂版)》,于曉、陳維綱等譯,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頁。后文引文皆引自該版本。韋伯認為,資本主義具有如下特征:其一,資本主義的經濟行為依賴于利用交換機會來謀取利潤的行為,這是一種和平的獲利行為;其二,資本主義的經濟行為是持續的、理性的,利用企業活動來生產和再生產利潤;其三,資本主義的經濟行為要根據資本核算來調節,要以貨幣形式進行資本核算,要計算收支,要盈利;其四,資本主義生產要利用商品或人員勞務作為獲利手段。(5)[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4-5頁。將上述論述概括一下,資本主義的經濟行為具有和平、持續、理性的特征,它是以企業為主體、以出售商品或勞務為手段的盈利行為。這也就是說,資本主義不是強盜搶劫或軍事掠奪,也不是一時興起的暴發戶,它是企業的市場獲利行為,主要依賴理性核算和管理。韋伯認為,資本主義企業是“自由勞動之理性的資本主義組織方式”。它具有兩個重要特質:“把事務與家庭分離開來,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合乎理性的簿記方式。”(6)[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7頁。
在界定了資本主義的基本概念之后,韋伯從世界文化史的角度提出了他的中心問題——“以其自由勞動的理性組織方式為特征的這種有節制的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起源問題,或從文化史來說就是:西方資產階級的起源及其特點的問題”。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需要兩個重要的社會條件:其一,科學技術。資本主義根本上依賴于現代科學,特別是以數學和精確的理性實驗為基礎的自然科學。其二,法律制度與理性的行政體系。近代資本主義不僅需要生產的技術手段,而且需要一個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規章辦事的行政機關。(7)[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9-10頁。
但是,僅有“理性的技術和理性的法律”還是遠遠不夠的。“與此同時,采取某些類型的實際的理性行為卻要取決于人的能力和氣質。如果這些理性行為的類型受到妨害,那么,理性的經濟行為的發展勢必會遭到嚴重的、內在的阻滯。各種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們為基礎的關于責任的倫理觀念,在以往一直都對行為發生著至關重要的和決定性的影響。……我們將討論這些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8)[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11頁。這樣,通過以上敘述,韋伯進入了他的正題,也就是他在該書中要討論的核心議題或問題:“近代經濟生活的精神與禁欲的新教之理性倫理觀念之間的關系問題。”(9)[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11頁
韋伯首先界定了資本主義精神的界限與范圍:其一,個體性。“資本主義精神這一術語……所適用的任何對象都只能是一種歷史個體。”(10)[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11頁其二,近代性。“資本主義精神這一概念,就是指……近代資本主義精神。”(11)[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14頁。其三,地域性。“我們這里所論述的只是西歐和美國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在中國、印度、巴比倫,在古代的希臘和羅馬、在中世紀都曾存在過。但我們將會看到,那里的資本主義缺乏這種獨特的精神氣質。”(12)[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14頁。
資本主義精神是個體的、近代的和歐美的。它具體的代表者是工業中產階級。工業中產階級的典型代表“不是利物浦和漢堡的那些風度翩翩的紳士(其商業財產是世襲而來的),而是曼徹斯特和西法利亞的那些多在非常普通的環境中靠個人奮斗而發財致富的暴發戶。”(13)[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23頁。他們精打細算又敢想敢為、節制有度、講究信用、精明強干、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事業中,并且固守著嚴格的資產階級觀點和原則。(14)[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26頁。資本主義精神完全不同于傳統主義,傳統主義甚至是資本主義精神的對立面。
在前資本主義時代,“合乎理性地使用資本和按照資本主義方式合乎理性地組織勞動尚未成為決定經濟活動的主導力量。而各個地方的人們在適應一種有秩序的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經濟狀況時,他們所遇到的最頑固的心理障礙之一恰恰正是這種態度”。傳統主義的“勞動者缺乏自覺性……信奉無紀律的自由自在……不講道德”(15)[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18-19頁。。韋伯著重闡述了資本主義精神的兩個內涵:
第一,理性地追求利潤。“資本主義經濟的根本特征之一就是:這種經濟是以嚴格的核算為基礎而理性化的,以富有遠見和小心謹慎來追求它所欲達的經濟成功,這與農民追求勉強糊口的生存是截然相反的,與行會師傅以及冒險家式的資本主義的那種享受特權的傳統主義也是截然相反的,因為這種傳統主義趨向于利用各種政治機會和非理性的投機活動來追求經濟成功。”(16)[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31頁。
第二,“天職”觀念——職業精神。“一個人對天職負有責任——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社會倫理中最具代表性的東西,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根本基礎。它是一種對職業活動內容的義務,每個人都應感到、而且確實也感到了這種義務。”(17)[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16頁。“把勞動視為一種天職成為現代工人的特征,如同相應的對獲利的態度成為商人的特征一樣。”(18)[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103頁。
馬克斯·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精神對于企業和社會的變革是基礎性的和關鍵性的。如果企業的組織形式是資本主義的,但企業家的精神是傳統的,那就還不是一個真正的資本主義企業。資本主義精神的作用遠遠超出資本。“近代資本主義擴張的動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資本主義活動的資本額的來源問題,更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問題。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資本主義精神出現并表現出來,它就會創造出自己的資本和貨幣供給來作為達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況則是違背事實的。”(19)[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25頁。
資本主義精神是怎么發展出來的呢?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新教倫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聯系,韋伯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說明:
其一,禁欲主義導致理性。韋伯認為,禁欲主義有一種明確的理性特征。西方修行生活試圖使人服從一個至高無上的、帶有某種目的的意愿,使他的行動得到經常的自我控制,并且讓他認真考慮自己行為的倫理后果。清教徒就像所有理性類型的禁欲主義一樣,力求使人能夠堅持并按照他的經常性動機行事,特別是按照清教教給他的動機行事,而不依賴感情沖動。“禁欲主義的目的是使人可能過一種機敏、明智的生活:最迫切的任務是摧毀自發的沖動性享樂,最重要的方法是使教徒的行為有秩序。”(20)[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62-63頁。
其二,神意給予了追逐利潤行為以正當性和合法性。韋伯認為,以神意來解釋追逐利潤為實業家們的行為提供了正當理由(21)[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93頁。。新教禁欲主義與自發的財產享受強烈地對抗著;它束縛著消費,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費。而另一方面,它又有著把獲取財產從傳統倫理的禁錮中解脫出來的心理效果,它不僅使獲利沖動合法化,而且把它看作上帝的直接意愿。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它打破了獲利沖動的束縛。(22)[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98頁。禁欲主義還給資產階級一種令其安慰的信念:現世財富分配的不均本是神意天命。(23)[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102頁。
其三,禁欲主義的節儉導致資本積累。“禁欲主義的節儉必然要導致資本的積累。強加在財富消費上的種種限制使資本用于生產性投資成為可能,從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財富。”(24)[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99頁。
理性、資本積累和盈利行為的合法性都是從新教倫理中發展出來的,這主要是針對資本家或企業家來說的。韋伯總結道:“一種特殊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倫理形成了。資產階級商人意識到自己充分受到上帝的恩寵,實實在在受到上帝的祝福。他們覺得,只要他們注意外表上正確得體,只要他們的道德行為沒有污點,只要財產的使用不致遭到非議,他們就盡可以隨心所欲地聽從自己金錢利益的支配,同時還感到自己這么做是在盡一種責任。”(25)[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102頁。
在韋伯看來,新教倫理導致的資本主義精神不僅體現在資本家身上,還塑造了與資本配合的近現代工人。這主要表現為:
其四,現世的禁欲主義導致職業精神。韋伯認為,在構成近代資本主義精神乃至整個近代文化精神的諸基本要素之中,以職業概念為基礎的理性行為這一要素,正是從基督教禁欲主義中產生出來的。(26)[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104頁。強調固定職業的禁欲意義為近代的專業化勞動分工提供了道德依據。(27)[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93頁。“宗教禁欲主義的力量還給他們提供了有節制的、態度認真、工作異常勤勉的勞動者,他們對待自己的工作如同對待上帝賜予的畢生目標一般。”(28)[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102頁。職業精神最核心的內容是“以勞動為自身目的和視勞動為天職的觀念”,(29)[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22頁。這是傳統主義難以提供的。
韋伯帶有總結性地說:新教禁欲主義認為,勞動是一種天職,雇主的商業活動也是一種天職。“把勞動視為一種天職成為現代工人的特征,如同相應的對獲利的態度成為商人的特征一樣。”(30)[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103頁。
韋伯在《儒教與道教》一書中總結了資本主義企業家的倫理特質:“極端專注于上帝愿望的目的;禁欲倫理制約下的沒有顧忌的實踐理性主義;務實的企業經營方法;憎惡非法的、政治的、殖民的、掠奪的、壟斷的資本主義。……肯定日常經營的冷靜、嚴格的合法性與有節制的理性動力;理性地評估技術上的最佳辦法,以及實踐上的可靠性和目的性。”工人的特質則表現為“勞動意愿”。(31)[德]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洪天富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頁。企業家和職業工人就是資本主義精神的代表。
資本主義精神是一個價值觀念和倫理觀念體系,其目標是塑造出一種理性地追求利潤的態度。它的核心是追求財富的合法性和義務感,還包括“時間就是金錢”、誠信、勤勞、節儉、守時、公正等觀念或品格。對于工人來說,它表現為一種高度的職業精神。
韋伯的論述實際上提出了一個解釋資本主義起源與發展的理論模型。他的基本思路是:新教倫理導致了資本主義精神,資本主義精神是資本主義起源與發展最重要的動力與影響因素。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科技、法制和理性的行政體系都很重要,“經濟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32)[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11頁。,但精神是最為關鍵的因素。
二、模型:變量遺漏、內生性和數據檢驗
韋伯提出了一個關于“新教倫理-資本主義精神-資本主義起源與發展”的理論解釋模型。顯然,資本主義是一個復雜的體系。它可以從多個層次來分析:在個人層次上,有資本家和具有職業精神的工人;在組織層次上,有資本主義企業(公司、工廠);在社會和國家的層次上,有市場(資本主義的經濟生態體系)、國家與社會(資本主義的法律體系和社會體系);在全球層次上,有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國際市場和相應機構)。韋伯沒有對資本主義體系的層次作出細致的分類,這一點受到科爾曼的批評。科爾曼認為,韋伯的命題可以用下圖的模型(33)[美]詹姆斯·S.科爾曼:《社會理論的基礎(上)》,鄧方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頁。來表示。
在科爾曼看來,新教教義和資本主義是宏觀層次的變量,而價值觀念和經濟行為是微觀個體層次的變量。新教教義塑造了個人的價值觀念,個人的價值觀念影響了其經濟行為,“促成資本主義發展的是眾多個人經濟行為的結合”。(34)[美]詹姆斯·S.科爾曼:《社會理論的基礎(上)》,第10頁。韋伯的模型如果要成立的話,涉及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概念理解。韋伯模型最基本的概念無疑是資本主義。與韋伯對資本主義的理解不同,布羅代爾區分了市場經濟的兩種形式:一是“集市貿易和地方性的短途貿易”;二是“長途貿易”(35)[法]布羅代爾:《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一卷)》,顧良、施康強譯,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xxiii,xxv頁。。布羅代爾指出:“概括說來,有兩種不同的交換:一種是普通的交換,帶有競爭性,因為是公開的;另一種是高級的交換,帶有欺騙性和獨占性。兩種交換的活動方式和經紀人各不相同。資本主義不屬于第一種交換,而屬于第二種。”(36)[法]布羅代爾:《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一卷)》,第xxix頁。“資本是可以捉摸的實體,是不斷運動著的和容易辨認的手段;資本家是把資本投入到生產過程中去的主持人,而在所有的社會里,資本注定要投入到生產過程中去。……資本主義就是通常為著利己目的且把資本投入到生產過程中去的方式。”(37)[法]布羅代爾:《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一卷)》,第xxii頁。
從資本主義的概念到資本家,布羅代爾認為,資本家不是普通的市場(集市貿易和地方性的短途貿易)交易者,而是跨地區、跨國或海外貿易(長途貿易)的交易者。長途交易需要巨額資本,會發展信貸與金融手段。海外貿易還會使得資本國際化,不同民族的資本家會相互交流。所以,資本家是企業家,他們“擁有信息、智慧、文化等優越條件”。
在布羅代爾對資本家特質的描述中,他強調了資本家的人力資本。而且,他認為,資本家是企業家,需要承擔風險,比如在信貸和大規模海外貿易中就存在巨大風險。而韋伯強調的則是資本家的理性,其中內含著謹慎。
在傳統的社會結構方面,布羅代爾認為,資本主義或資本家的積累是長期的、緩慢的過程,它依賴于家族制和等級制。“個人的成就幾乎始終應歸功于到處鉆營、力圖逐漸擴大其財產和影響的家族。……孕育著資本主義過程的資產階級創造了或利用了堅固的等級制,后者將成為資本主義的支柱。為了鞏固財富和實力,資本主義同時或先后依靠了貿易、高利貸、長途貿易、行政官職和土地;土地是尤其可靠的價值,土地擁有者在社會享有的聲望比人們所能想象的更高。如果注意到了名門世家的代代相傳以及祖產的緩慢積累,歐洲從封建制向資本主義的過渡就變得不難理解。……資產階級的上升是長期的和緩慢的,父輩的野心傳給兒子,再傳給孫子,子子孫孫地往下傳,永無窮盡。”(38)[法]布羅代爾:《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一卷)》,第xxxiii頁。布羅代爾關于家族制的說法,是從資本積累的角度說的,盡管不一定與韋伯的說法相矛盾,但顯然,在韋伯那里,家族制、等級制都屬于傳統主義的東西。
不僅僅是布羅代爾,其他學者在關于資本主義及其起源的解釋中,也有與韋伯明顯不同的理解。貝爾這樣說道:“關于資本主義的流行理論……主要是在馬克斯·韋伯的影響下形成的。韋伯強調加爾文教義和清教倫理——具體指嚴謹工作習慣和對財富的合法追求——是促使以理性生產與交換為特征的西方文明興起的基本原則。然而資本主義有著雙重的起源。假如韋伯突出說明了其中的一面:禁欲苦行主義,它的另一面則是韋爾納·桑姆巴特長期遭到忽視的著作中闡述的中心命題:貪婪攫取性。”(39)[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蒲隆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27頁。
第二,變量遺漏。(40)所謂遺漏變量是指在統計模型中,有變量對因變量有影響、對解釋變量也有影響而未被列入模型,這樣會造成“遺漏變量偏倚”([美]米歇爾·劉易斯-伯克、艾倫·布里曼、廖福挺主編:《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百科全書(第二卷)》,高勇等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926頁)。本文并不是通過嚴格的數據分析來說明韋伯模型的遺漏變量問題,而是依據統計原理來分析的。就資本主義的起源與發展的影響因素來說,如前所述,韋伯并不反對經濟因素的作用,他也考慮到了科技應用帶來的工業革命和法制以及理性的行政管理的重要性,這也就是說,他其實考慮到了馬克思的生產力、上層建筑等因素,也知道資本積累在資本主義發展中的重要性,只不過,他強調的關鍵因素與馬克思不同,是精神的力量。但是,在馬克思和布羅代爾那里特別強調世界市場對資本主義發展的作用,這一點,韋伯似乎是忽視了。
布羅代爾認為,資本家很早就超出了本民族的界限。他們依靠雄厚的資本,才能保住優勢,獨占當時的國際貿易。(41)[法]布羅代爾:《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一卷)》,第xxvi-xxvii頁。就新教倫理對資本主義精神的作用來說,韋伯強調的只是宗教的影響,很顯然,他忽視了其他精神或文化因素的影響,比如地方文化的影響。或者換句話來說,他應該在控制了其他文化因素(比如家族傳統、地方文化和官方意識形態)的條件下來說明新教倫理的關鍵作用。顯然,地方文化等因素既與宗教信仰相關,也對資本主義精神的形成有一定影響。
第三,內生性問題。所謂內生性問題,是指“在一些情況下出現反向因果問題:解釋變量受到被解釋變量影響,而不是我們假設的影響被解釋變量。……對于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來說,內生性是一個普遍且嚴重的問題”。(42)[美]加里·金、羅伯特·基歐漢、悉尼·維巴:《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陳碩譯,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80頁。
就資本主義精神影響資本主義起源與發展來說,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馬克思顯然不能同意韋伯的見解。“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43)[德]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載梁寒冰編《歷史學理論輯要》,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43頁。恩格斯發現了新教與資產階級的聯系,“新教異端的不可根絕是同正在興起的市民階級的不可戰勝相適應的,……加爾文教是當時資產階級利益的真正的宗教外衣”。(44)[德]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1-252頁。但是,恩格斯認為,“歷史上的偉大轉折點有宗教變遷相伴隨”。(45)[德]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第231頁。不是宗教精神推動了資產階級的產生,而宗教(新教)是資產階級的伴生物或外衣。
和馬克思、恩格斯一樣,布羅代爾也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是由精神力量推動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條件是物質生活的膨脹,以及由此帶來的與外界聯系的擴展。物質生活是一切的基礎:一切進步取決于物質生活的膨脹,市場經濟本身也依賴物質生活而迅速膨脹,并擴展與外界的聯系。在這一擴展中,得益的始終是資本主義。……任何資本主義首先是以其經濟基礎為尺度的。”(46)[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22頁。為什么呢?因為在布羅代爾看來,“代表傳統勢力的宗教一般反對市場、金錢、投機、高利貸等新興力量。但這里也有妥協。宗教雖然不斷反對,但它終將接受時代的迫切要求。總之,它將同意實行某種現代化”。(47)[法]布羅代爾:《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一卷)》,第xxxi頁。布羅代爾認為,韋伯顛倒了宗教精神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關系:“在馬克斯·韋伯看來,現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不折不扣地是基督教甚至清教的產物。”(48)[法]布羅代爾:《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一卷)》,第xxxi頁。布羅代爾實際上認為,宗教是同市場相對立的力量,它不可能推動資本主義市場行為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但是它會適應市場的發展而改變自身。
不僅僅是布羅代爾,戴維·萊廷也認為韋伯的命題存在反向因果的內生性問題:“韋伯試圖證明作為特定經濟行為的資本主義精神是新教教義和教旨的意外產物。但作者和他的追隨者都無法回答如下質疑:也許正是那些突破前資本主義藩籬的歐洲人才希望擺脫天主教會的束縛。也就是說,特定群體的經濟利益也許是導致新教倫理發展的原因。”(49)[美]加里·金、羅伯特·基歐漢、悉尼·維巴:《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第181頁。
其實,韋伯在一定程度上也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他認為,資本家、企業家和高級工人中新教徒較多的事實,可以部分地歸之于歷史因素:“這些歷史因素可以追溯到遙遠的過去,而在那里,宗教派別并非是經濟狀況的原因,它在某種程度上倒似乎是經濟狀況的后果。”(50)[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3頁。當然,在資本主義的起源和發展的問題上,韋伯是堅持精神力量的決定性影響的。
第四,實證結果。布羅代爾認為,韋伯的錯誤主要在于一開始就夸大了資本主義對現代世界的催化作用。根據他的理論邏輯推斷,新教徒集中的地區應該資本主義發達。但是,這并不符合歷史事實。“所有的歷史學家全都反對這個精巧的論斷,雖然他們無法徹底拋棄它:它不斷改頭換面地重現在他們的面前。然而,這個論斷畢竟是錯誤的。北歐國家只是取代了長期由地中海占有的資本主義中心的地位。無論在技術方面或在商業方面,它們沒有任何創新。……世界經濟中心的每次轉移都是由于經濟方面的原因,并不觸及資本主義內在的或隱秘的本質。”(51)[法]布羅代爾:《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一卷)》,第xxxi- xxxii頁。
根據韋伯的邏輯,新教倫理促進了資本主義發展,也意味著促進了經濟發展。兩位德國學者利用19世紀普魯士的人口普查數據發現,這一假設的確可以成立:某地區新教徒密度較高,就會有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人均所得稅收入)。甚至在現在的德國依然如此。但是,如果控制地區平均識字率差別,新教徒密度對于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就消失了。他們認為,宗教改革往往會推動于教育事業發展。因為進入教會,為了閱讀圣經,就得認字。這樣,新教徒較多的地區人均教育水平普遍更高。所以,并不是“新教倫理”這一變量直接促進了“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而是教育(人力資本)這一變量促進了“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52)Becker, S.O., Woessmann, L.,“Was Weber Wrong? A Human Capital Theory of Protestant Economic Histo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24,No.2, 2009,pp.531-596.后續的研究支持了這一結論。D.Cantoni使用1300-1900年間羅馬帝國境內272座城市的人口數據發現,在奧格斯堡和約簽訂之后,新教城市并不比天主教城市發展得更好。(53)Cantoni, D.,“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Testing the Weber Hypothesis in the German Lands”,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13,No.4, 2015,pp.561-598.因為到19世紀上半葉第二次工業革命后,人力資本的作用才能顯現出來。這可能說明“新教倫理”對經濟增長并沒有顯著作用。
從統計的角度來說,如果一個模型遺漏了重要的變量,存在著自變量與因變量反向因果的內生性問題,而且解釋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關系忽視了中介變量的作用而導致對數據的誤讀,那這個模型就會產生嚴重的偏誤。
當然,完全用現在的統計模型的思維方式來責備韋伯是不公平的,將一個理論模型轉化為實證的統計模型并借助數據分析來證偽理論,有一個前提條件,那就是統計模型的設置正確無誤,并且所使用的數據質量非常好。顯然,就像韋伯的模型并非絕對正確一樣,對這個模型的實證檢驗也并不完美無缺。因為,就數據基礎來說,通過歷史資料收集的數據往往有較大的局限性。從理論和實證結合的角度來說,韋伯的模型提供了一種思路,具有理論張力,對它的批評、質疑和證偽還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三、韋伯命題的中國意義
毫無疑問,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命題已經成為了經典。“自1905年問世以來,《新教倫理》竟成為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爭論不止的一個中心問題。”(54)余英時:《儒家倫理與商人精神》,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18頁。幾乎所有的社會學教科書都會提到韋伯的這一命題。那么它到底有什么意義呢?
其一,韋伯提出了與馬克思不同的關于資本主義起源和發展的因果解釋。(55)吉登斯說:“《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顯著特點在于它要說明,作為現代資本主義特征的經濟生活理性化與非理性的價值約束有關。這是一項對因果關系作出評估的初期工作。”([英]安東尼·吉登斯:《資本主義與現代理論——對馬克思、涂爾干和韋伯著作的分析》,郭忠華、潘華凌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頁)這一因果解釋找到的關鍵因素或解釋變量是“新教倫理”及其塑造的“資本主義精神”,而不是物質條件、經濟狀況或生產方式。“這里的因果關系正好與按唯物主義觀點得出的因果關系相反。”(56)[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17頁。盡管韋伯并不認為資本主義是單一因素的產物,但他的確將“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作為最為重要的因素。如果在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過程中,物質資源和精神資源缺一不可,那么韋伯命題就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從精神的角度來研究、說明、理解資本主義的起源與發展,避免了對資本主義機械和庸俗化的解釋,也避免了對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夸大和以此為基礎的預期。
其二,韋伯命題與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思路不同,它強調觀念、意識、倫理和精神的作用。與歷史唯物主義強調物質因素的作用一樣,關于精神作用的理論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歷史和社會本來就是多層面、多維度的立體結構,所以,對它的觀察與研究就不能是單一的視角或理論。從觀念的角度出發,將精神作為關鍵解釋變量,開辟了新的思路。在一定意義上,韋伯命題是現代新制度主義的一個古典起點。韋伯的理論給后來者以啟發,成了研究者必須面對的一個思想存在。“默頓認為,苦行的新教教義(不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觀念、準則和價值為現代科學的發展產生出了適當的文化上的先決條件。”(57)[美]D.韋德·漢茲:《開放的經濟學方法論》,段文輝譯,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頁。《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提出了“文化的原因論以及現代資本主義的文化意義”。(58)[英]山姆·威姆斯特:《理解韋伯》,童慶平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頁。因而,韋伯的理論有“持久性意義”(59)[美]喬治·瑞澤爾:《古典社會學理論》,王建民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249頁。。
其三,韋伯命題重要的不僅僅在于它是否正確,而在于它提出了新的問題。新的觀察視角可以發現“新穎的事實”并提出新的問題。韋伯的模型講述了古老而新穎的故事,甚至給出了“隱喻”。他的命題具有理論張力,引發了一系列問題,形成了一個“問題家族”。以韋伯的命題對中國歷史而言,可以提出一系列的問題:為什么在中國沒有發展出近代資本主義?“為什么科學的、藝術的、政治的、或經濟的發展沒有……在中國也走上西方現今所特有的這條理性化道路呢?”(60)[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10頁。儒教、道教與清教有什么重大的差異?為什么儒教和道教會阻礙資本主義的發展?如果再擴展一點,還可以提出的類似問題是:“為什么中國發展不出近代的科學技術?”(61)[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 導論)》,袁翰青等譯,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頁。“為什么中國不能出現工業革命?”(62)當然,也有人認為,提出這樣的問題是一種西方中心主義觀念。比如,柯文在講到對中國歷史進行研究的思想框架時說:“近代化或傳統-近代取向……的基礎可上溯至19世紀西方人對文化、變化、中國與西方本身所持的看法。這一取向的錯誤在于把一種來自外界的——同時也是狹隘的——西方觀點,即關于什么是變化,哪種變化才是重要的界說,強加在中國歷史上。這種取向如果不是明顯地,也是隱含地側重于從西方近代史角度就中國歷史提出問題——例如,中國能否獨立產生近代的科學傳統和工業革命呢?如果不能,為什么?”([美]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林同奇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109-110頁。)等等。
韋伯的命題與理論在中國產生了巨大影響。他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在中文世界就出版了21個漢語譯本。韋伯已經成為中國社會學和社會科學言必稱之的人物。韋伯在《儒教與道教》一書中具體討論了中國的社會結構、階層和儒教與道教的基本內容與特征,并將儒教、道教與清教進行了對比。他認為,在儒教和道教的精神傳統下,“具有現代西方特色的理性的經濟與技術是不可能產生的”;“中國盡管具有各種有利于資本主義產生的外在條件,但……在中國發展不出資本主義。”(63)[德]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第257、277頁。
總體上,中國產生不了資本主義精神,但這并不排斥在局部地區產生或出現資本主義精神。韋伯也認為,中國的“實利主義”并沒有發展出“理性的經營觀念,而這些觀念,至少在經濟領域里,曾是現代資本主義的先決條件。這樣的觀念對中國人來說是陌生的,只有廣東人是個例外,在他們那兒,由于過去外來的影響,加之現在有西方資本主義的不斷進逼,才學會了這些觀念”。(64)[德]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第271頁。據此可以認為,中國的地方文化比之傳統的意識形態(如儒教與道教)更有可能產生、催生或塑造出商人精神或資本主義精神,比如明代徽商的誠信與節儉,(65)傅衣凌:《明代徽州商人》,載江淮論壇編輯部編《徽商研究論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23頁。清初山西的地方風氣“向往經商”和山西商人的勤儉、不欺,(66)[日]寺田隆信:《山西商人研究》,張正明等譯,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1-275頁。明清福建商幫的開放(面向海洋)、流動和進取,(67)林楓:《明清福建商幫的性格與歸宿——兼論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延續》,《中國經濟史研究》2008年第2期。清末民初廣東商人的“商業至上”觀念,(68)敖光旭:《“商人政府”之夢——廣東商團及“大商團主義”的歷史考查》,《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等等。當然,地方文化所產生的資本主義精神并不完整,不能形成完整、普遍的價值與倫理體系。
韋伯對中國宗教的批評并不完全正確,但他對中國近代歷史研究的重要貢獻是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中國為什么發展不出資本主義?進而言之,在傳統社會向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中國有什么樣的文化精神缺失?在近代中國發展不出資本主義,這是一個歷史的問題。但是,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把問題轉換一下,在當代中國,市場經濟改革已經進行了四十多年,鍛造出了真正的市場精神(69)米塞斯認為,“市場是自由的;沒有市場以外的因素干擾到物價、工資率和利率”。政府“只專心市場運作的維持,而不妨害它的功能,并且還要保護它,不許別人侵害”。( [奧]路德維希·米塞斯:《人的行為》,夏道平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234頁)很難對市場精神做一個準確定義,但它應該包含主體平等、公平競爭、自由選擇、敬業守信、法制約束等基本理念。嗎?為此,我們可以提出如下具體問題:制造假冒偽劣、山寨、做假賬是否符合真正的市場精神?不遵守契約、缺乏契約精神是否符合真正的市場精神?壟斷是不是資本主義、是否符合真正的市場精神?在韋伯看來,資本主義精神作用于資本家和工人:對于前者形成企業家精神(70)企業家被定義為“專門就稀缺資源的配置做出判斷性決策的人”。([英]約翰·伊特韋爾等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二卷)》,陳悅譯,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頁)實際上,韋伯只揭示了企業家精神中的“天職”和敬業勤奮的一面,而企業家精神還包含創新、承擔風險等方面。([美]約瑟夫·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郭武軍等譯,華夏出版社2015年版,第72-77頁),對于后者塑造了職業精神。那么,進一步的問題是: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是否塑造了企業家精神?它有哪些主要表現?中國的工人(其主體為農民工)是否具有職業精神、工匠精神?如果缺乏,是什么原因?
改革開放之初,深圳蛇口掛起了巨大的標語牌:“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四十年來,中國的農民工表現出了世所罕見的勤勞、刻苦和節儉的精神,但也有研究者認為其職業精神仍有待提升。四十年來,最初的一批個體戶和倒爺大多倒下了,后來,一批又一批企業家出現了,現在風頭最勁的是房地產大亨和電商巨頭,他們究竟具有何種精神和倫理品格?四十年過去了,中國的經濟取得了偉大的成就,成了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人們對中國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做了很多總結,比如,在《偉大的中國經濟轉型》一書中,學者們討論了人口、勞動力市場、教育、環境、科技、民營經濟、法律、財政、農業、金融、工業、全球化以及經濟增長、結構轉型、收入不平等等諸多方面,但是,卻沒有論及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塑造了什么樣的精神理念和倫理品格。(71)[美]勞倫·勃蘭特、托馬斯·羅斯基:《偉大的中國經濟轉型》,方穎等譯,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科斯的《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一書也詳細回顧了中國的改革歷程,論及了中國改革的性質、特點、步驟、動力、方式、成就、阻礙和缺陷,等等,(72)[英]羅納德·哈里·科斯、王寧:《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徐堯等譯,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但也沒有從精神層面很好地進行總結。不過,科斯在該書中提出了一個值得關注的論斷:“當中國市場化轉型催生了蓬勃發展的商品與服務市場,并讓中國成為全球生產領域的領頭羊時,卻沒有為思想創造一個活躍市場。”(73)[英]羅納德·哈里·科斯、王寧:《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第250頁。倪志偉等人對長三角地區的民營企業家進行了訪談、問卷調查,以這些數據為基礎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并得出一些有價值的觀點。但是,他們的問卷幾乎沒有收集企業家的價值和倫理觀念等精神層面的數據。(74)[美]倪志偉、歐索菲:《自下而上的變革:中國的市場化轉型》,閻海峰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
顯而易見,壟斷、官商勾結、唯利是圖、山寨、假冒偽劣、不誠信、不遵守規則等等現象在中國的市場經濟活動中并不鮮見。對于這些現象要盡可能地深入探討,而韋伯可能是我們的一個出發點。從韋伯的理論出發,可以認為,精神要素既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原動力,也是資本主義體系價值的精神凝聚和表現。那么,總而言之,我們最終的問題是: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應該塑造何種精神?在改革開放的歷史過程中,鄧小平同志始終強調要搞清“什么是社會主義”(75)鄧小平:《計劃和市場都是發展生產力的方法》,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3頁。。貫穿改革開放全過程的一個基本事實是,中國都在摸索建設社會主義,并進行了“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前提條件是搞清楚什么是資本主義。韋伯給我們的啟示也許是:如果我們只是從物質條件、生產、市場交換等角度認識資本主義,這可能是遠遠不夠的。就像一個人,如果我們只知道他的軀體存在,而不能深入其靈魂,我們實際上對他并不了解。韋伯命題在今天中國的重要意義就是,我們要從精神層面去認識資本主義,從而認識市場經濟的靈魂,進而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