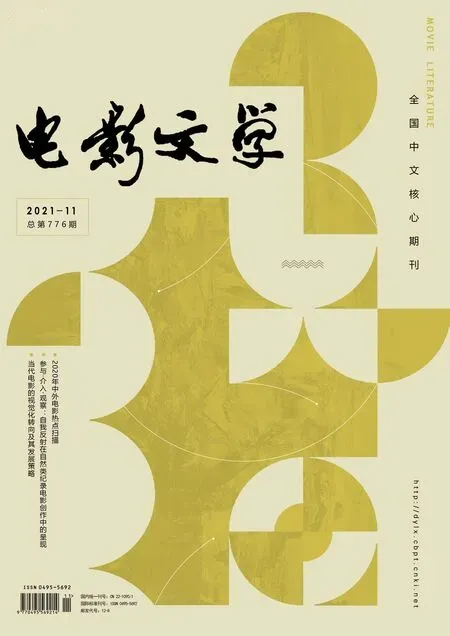引領與推進:《明星月報》在左翼電影運動初期的影響
趙博翀 劉盼紅
(1.東華大學人文學院,上海 200051;2.東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上海 201620)
20世紀30年代是中國電影發展史的重要時期,亦是近代報刊勃興與繁榮的階段。電影刊物作為接駁二者的橋梁,其發展依托于報業長久以來的繁榮與穩定,同時對電影行業產生重要影響。前人關于電影刊物的研究已不勝枚舉,但多拘泥于報刊文本,或將報刊作為史料以電影學為視角探討近代中國電影的發展,較少采用報刊史和電影史的交叉視角。然而電影刊物研究還應注意到文化思潮的影響、刊物與電影創作的互動以及其對于電影理論的推進。
1933年5月1日由明星影片公司(以下簡稱明星公司)編輯發行的《明星月報》為這項研究提供了典型案例。該報創刊于上海,1935年1月1日停刊,共發行12期。時值左翼電影運動發展初期,作為明星公司的附屬刊物,《明星月報》在1933—1935年記載了明星公司的主要電影活動。更值得關注的是,該報對左翼電影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然而目前學界關于該報的研究以描述性文字居多,缺乏詳細、深入的探討。本文以《明星月報》為研究對象,主要考察該報的政治態度,以及該報在左翼電影運動中的地位與影響。
一、偶然與必然:《明星月報》的政治態度考論
《明星月報》是左翼電影運動中具有影響力的電影刊物,亦是中國電影發展史中毋庸置喙的重要內容。然而回溯其發展,左翼文化的推進、時勢環境的變化、明星公司及電影藝術本身等諸多偶然因素,對于《明星月報》中左翼文化傾向的培育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些看似偶然的背后其實蘊含著無數必然。
1930年3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以下簡稱左聯),左翼電影運動由此迸發。1931年1月,在左翼作家聯盟基礎上,戲劇界左翼人士建立左翼戲劇家聯盟(以下簡稱左翼劇聯),并發布《最近行動綱領》,對左翼電影運動提出明確指導意見。要求左翼劇聯成員加入制片公司,供給左翼電影劇本;組織電影研究會,吸收進步演員和技術人才;同時注意加強左翼創作理念,揭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斗爭過程。《最近行動綱領》給予左翼電影運動路標式的指引,然而電影藝術的發展需要平臺與媒介支撐。20世紀30年代,上海有16家電影院放映國產影片,明星公司占12家之多。強大的市場占有率使明星公司成為左翼電影運動必須爭取的對象。
其時,明星公司正經歷著嚴重危機,急需符合觀眾審美志趣的電影工作者加盟,以改變公司頹勢。總的來說,該公司面臨經濟危機和創作理念更迭兩方面的困境。首先,明星公司對有聲設備的采購所耗甚糜,收效甚微。明星公司為制作有聲電影,派導演洪深赴美。然而對先進電影技術缺乏了解,導致明星公司購辦失策,陷入財政危機。《電聲雜志》曾在《電影界陣線大變動》中報道此次事件,文章認為,洪深奉命赴美購辦有聲機器,使明星公司蒙受巨大損失,該公司在經濟層面已陷入絕境。其次,電影觀眾的觀影需求發生根本變化。受眾心理根源于社會和政治。一·二八事變后,傳統鴛鴦蝴蝶派和武俠神怪片已難滿足觀眾對于中國社會的焦慮和制度的反思。脫離現實的劇情與當下受眾審美背離,現實主義電影逐漸成為電影市場主流。然而明星公司并未在這一思潮中及時轉向,1932年明星公司制作影片《啼笑因緣》,這部寄予厚望的巨制卻并沒有受到觀眾的喜愛。票房失利讓明星公司對電影創作理念有了新的思考。
此時左翼文化已露萌芽,各個左翼聯盟在黨的地下組織領導下開展左翼文化運動,擴大影響力。左翼劇聯成員進入明星公司的視野。明星公司創辦人之一周劍云邀請夏衍、阿英、鄭伯奇等人加盟明星公司,參與影片制作。1933年,夏衍、阿英、王塵無、石凌鶴、司徒慧敏組成黨的電影小組。在夏衍的主持下,電影小組接受明星公司的邀請,領導左翼電影運動。左翼人士在電影小組的指導下陸續進入明星、聯華、藝華等各大電影公司進行電影創作,并通過各類報刊開展電影批評工作,以擴大左翼電影運動影響。
同年,《明星月報》正式發行。該報否定明星公司之前的創作理念,宣傳左翼電影,嘗試為觀眾和讀者建構新的公司形象。該報將電影批評、理論探討、記錄電影創作情況,作為刊行內容,并在其發刊詞中稱:“本刊的誕生是打算來替電影文化盡一部分吶喊的力量。”該報認為,電影屬于大眾,因此電影人應通過報刊向大眾做誠摯的自白。《明星月報》將大眾讀者作為其受眾群體,體現了明星公司創作理念的變化,亦可看出左翼電影工作者在此時已對明星公司的電影價值體系產生影響。
左翼人士大量介入《明星月報》,使該報成為左翼電影運動重要傳播陣地。《明星月報》直接勾連明星公司的電影生產,其撰稿群體亦是電影制作中的主要創作者。總體來說,《明星月報》的撰稿群體大致分為兩類:一類為左翼成員和左傾工作者,包括夏衍、鄭伯奇、阿英、王塵無、司徒慧敏、沈西苓等;另一類則來自明星公司的電影制作群體,主要由導演和演員組成,如鄭正秋、舒湮、張石川、王乾白、程步高、姚蘇鳳、柯靈、陳凝秋、唐納、艾霞等。1933年5月,國民黨文教特務潘公展曾以銀行貸款來威脅周劍云,逼迫其將姚蘇鳳安插進明星公司編劇顧問中。電影小組對此反應強烈,致使明星公司編劇會議兩度停開,阿英曾言:“他來我們就走。”最終經中國共產黨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黨團書記陽翰生的授意,夏衍等人向明星公司提出:“假如姚在編劇會議中反對乃至否定我們的劇本,我們三個人就集體辭職。”由此可見,左翼團體在20世紀30年代的明星公司和《明星月報》中均具有較大話語權,他們所挾帶的電影創作理念被《明星月報》繼承。
《明星月報》始終與左翼電影運動緊密聯系。1933年9月國民黨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成立,電影限制和審查制度愈加嚴格。同年11月,藝華影片公司因攝制左傾影片被搗毀,左翼電影運動進入低潮。明星公司成為僅存的左翼電影陣地。不久明星公司也受到來自政治和經濟各個方面的壓力,被迫調整制作方向。《明星月報》暫停發刊。1934年10月,夏衍等左翼人士退出明星公司。該年11月,《明星月報》重新刊發,但已鮮有左傾文章出現。《明星月報》雖非左翼人士創辦,卻與左翼電影運動亦步亦趨,誕生于運動高漲之際,偃旗于運動低迷之時,成為左翼電影運動重要的理論探討平臺。
二、組織確立:“中國電影文化協會”的合理性宣傳
李少白認為,中國電影文化協會的成立是左翼電影運動的標志。左翼電影運動的發展和早期中國電影創作觀念的變革都與左聯的領導密切相關。1933年,左聯在電影小組的基礎上成立中國電影文化協會,提出了促進新興電影發展的口號。這標志著一種新的文化觀念和意識形態的崛起。實質是對固有創作理念的顛覆和修正。
不同的行業群體都有與其自身相適應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準則,成立裹挾新思想的行業組織可以看作是對原行業固有文化準則的挑戰,中國電影文化協會需要對其建立的合理性進行宣傳。其時,左聯成員通過各種渠道進入電影公司、唱片公司和出版發行機構中,不斷占領和擴大革命文化宣傳陣地。而報刊作為20世紀30年代主流傳播媒介,則成為其合理性宣傳的重要推力。魯迅曾將報刊陣地視作左翼文化運動發展的重要事宜。他認為,社會烏煙瘴氣,報紙不可能干干凈凈,左翼文化工作者只需利用它的一角,說自己的話,不作原則性的遷就即可。
左翼人士將報刊作為確立電影文化協會合理地位的主要途徑。得益于明星公司與左翼人士的密切往來,更依賴于明星公司在電影界的影響力,這一任務自然地落在了《明星月報》上。
1933年《明星月報》在其創刊號中利用大幅版面刊發阿英所著《論中國電影文化運動》,他以鳳吾為筆名論證了成立電影文化協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一方面,明確指出建立中國電影文化協會組織是中國電影界發展的客觀要求,“要開展中國的電影文化運動,若果沒有一個堅強的統一領導機關,是絕對不可能的事”,鼓勵電影界和廣大群眾擁護和支持中國電影文化協會的成立。另一方面,具體指導中國電影文化協會如何攝制左翼電影,認為應撰寫現實主義劇本,跳出“咖啡館、跳舞場、戀愛或瑣事”的固有創作范圍,使民眾從本質上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有深刻充分的理解。但該報對中國電影文化協會的成立并非完全樂觀,只是將其作為電影文化運動組織上春天到來的信號。
同樣持此觀點的還有明星公司電影制作群體。創始人張石川和鄭正秋,皆在《明星月報》上發文論述電影文化協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鄭正秋解釋道,中國電影從業人員智識不足,無法通過自身提升思想認識。所以,進步文藝工作者需要聯合起來,做電影從業者的戰友,促進電影界前進。他還建議電影文化協會應積極組織刊物、學堂、演講和研討會,以聯合文藝界進步人士,走上前進之路。張石川亦對電影文化協會滿懷期望,他認為,該協會的成立打破了電影與新文化的藩籬,使二者有機結合,共同推進電影藝術發展。從二人上述表述可看出,電影文化協會得到了明星公司制作群體的廣泛贊同,明星公司將其視作改變中國電影發展狀態的關鍵行為。
綜上所述,左翼作家和明星公司對于電影文化協會的集體背書使電影文化協會的成立具備了合理性。此后,電影文化協會擬定的方針路線被電影界接受,如明星、聯華、藝華等電影公司,均有左翼電影產生。上海各大報刊的電影副刊和電影專門刊物亦發表大量諸如左翼電影理論及電影批評的文章。左翼電影運動因電影文化協會而勃興,20世紀30年代初期繁榮的左翼文化亦離不開《明星月報》的宣傳。
三、路線引領:確定左翼創作理念
左翼電影運動的目的是與電影界及受眾形成共同的電影審美志趣,對中國電影創作理念進行路線引領。《明星月報》一直支持左翼電影創作路線,認為電影創作應遵從反帝反封建的現實主義道路。其時,關于電影創作路線的選擇一直是電影界爭論的焦點。左聯成員和左傾文化工作者根據電影小組的領導,經集體討論后,分別執筆,在《明星月報》發文闡述左翼電影創作理念,并通過交流研討、電影批評、翻譯蘇聯電影理論等傾向性傳播行為進行創作路線的引導,建立具有共同意識的左翼電影創作理念。
然而,電影文化運動正如火如荼之時,南京國民政府也時刻嘗試插手電影界。他們希望把電影納入他們的意識形態軌道,與新興電影文化運動相對抗。黃嘉謨、劉吶鷗等人于《現代電影》上提出軟性電影理論,反對左翼電影反帝反封建的大眾化路線。他們認為走大眾化路線的左翼電影其實是復制蘇聯電影,千篇一律地重復工人生活。他們主張藝術純粹論,認為電影必須重新恢復第八藝術的純真,并抨擊左翼影評人淺學無識。
對于此種論調,左翼作家在各類報刊中給予了嚴厲駁斥,然而將左翼電影理念蓋棺定論成為中國電影創作路線的一系列文章則來自《明星月報》。在該報創刊號中,鄭伯奇以席耐芳為筆名對現實主義創作路線做了解釋。他指出,左翼電影應直接展示現實矛盾,為民眾尋找出路,使觀眾深刻感受到社會變革的必要性。在此基礎上,阿英不惜筆墨詳細論述了反帝反封建的電影主題和今后左翼電影運動的發展方向。王塵無則在《中國電影之路》一文中,具體列舉了目前中國電影應抓取的題材。他認為,左翼電影創作重點是反對宗教、地主、軍閥和帝國主義,應著重描寫廣大人民群眾的反帝反封建運動和在帝國主義、封建軍閥統治下人們的艱難生活。他寫道,要盡量將電影大眾化,摒棄夸張和裝飾,用樸實的記錄鏡頭將偉大有意義的史實展現給大眾。此外,對于左翼電影發展和擴大,他也指出,工人大眾有12小時以上的工作時間,很難抽出時間進行影片觀賞,而勞苦大眾更沒有機會看到電影。因此,左翼電影應多制作短片,增加露天電影放映。其余如《中國電影的新使命》《中國電影檢討》《對于新興電影的意見》等“左”傾文章也均在《明星月報》發表,使該報成為左翼電影運動時期的重要理論傳播平臺。
左翼人士對電影創作路線的宣傳,使明星公司的制作團體對其創作理念產生共識。鄭正秋在《明星月報》中公開表明反帝反資反封建的“三反”立場。明星公司成員張石川、程步高、梅熹、高倩蘋、胡萍等人也在《明星月報》發文對電影的創作方向發表看法。如《傳聲筒里》《如何走上前進之路》《我們的戰場》《中國電影的本質問題》等探討電影理念的“左”傾文章均在《明星月報》刊發。這些文章是對左翼創作路線的肯定與支持,表明了明星公司與以往電影創作觀念割席的決心,也顯示出明星公司內部對電影創作路線已有共識。
左翼人士和明星公司成員在《明星月報》中連續發文,使該報無形中引領了20世紀30年代的電影創作路線。《中國電影發展史》認為,該報所刊文章推動了近代電影公司的現實主義創作路線,影響了“明星”“藝華”“聯華”“天一”等諸多電影公司的電影生產。更重要的是,這些文章正面回答了電影界關心卻迷惑的問題,回擊了“讓眼睛吃冰激凌”“藝術純粹電影”“美的觀照態度”等軟性電影理論,也增強了電影界制作左翼電影的信心。程季華稱,《明星月報》關于電影創作路線的探討對左翼電影運動的理論建設和創作實踐都有重大意義。該報的刊載內容,擴大了電影界的團結和對于反帝反封建統一戰線的認識,更確定了左翼電影文化運動的方向、任務和方法。尤其是在國民黨企圖瓦解左翼電影創作理念之時,《明星月報》給予了這場運動明確的支持和清晰的路線引導,使左翼電影陣地更為牢固。該報刊載內容完善了左翼電影運動的思想內涵,確認了左翼電影路線作為中國電影創作理念的思想共識。因此,《明星月報》對左翼電影運動的引領和建設是其在中國電影史中的重要貢獻。
四、內涵提升:推進左翼電影發展
左翼電影運動的開展離不開左翼人士以及“左”傾文藝工作者的呼吁和探討,此時的《明星月報》成為左翼電影發展的重要平臺。該報通過宣傳左翼電影、探討創作經驗、刊載影評文章、介紹西方電影藝術發展狀況等方式,引導讀者視點,加深了受眾對左翼電影的理解,客觀上促進了左翼電影的發展。
(一)關注電影生產
作為專業性電影刊物,《明星月報》重點報道電影生產方面內容。尤為重要的是,該報具有前瞻性思維,積極接收西方先進電影思想,通過翻譯和調查等方式對西方電影發展予以分析,以此為參照對中國電影發展貢獻策略。
首先,《明星月報》十分關注有聲電影發展。20世紀30年代正值無聲電影向有聲電影過渡的重要時期。《明星月報》陸續刊發《有聲電影的研究與發展史跡》《有聲電影上的音響整理法》《睹影聞聲與有聲電影》《有聲電影在將來》《有聲電影的發明及進展》等文章,從歷史脈絡、未來發展和應用技術等方面對有聲電影進行研討,并翻譯《有聲電影的劇本》《卡通聲片的繪制》等文章,促進有聲電影發展。其次,《明星月報》注重蘇聯電影理論的傳播。該報翻譯《時間的“特寫”》《蘇聯電影之創作的諸問題》《影場進化史的一頁——機械化攝影場》等文章。夏衍也曾在《明星月報》以丁謙平為筆名翻譯蘇聯電影《生路》的劇本。該報對《生路》的刊載使其成中國電影史上第一個被翻譯的蘇聯劇本。再次,《明星月報》關注世界電影發展趨勢。沈西岑所著《世界各國電影界最近之趨勢》,張常人所著《從游戲場的衰落說到電影業的發展》,國外電影研究文章《電影與資本主義》均在該報發表。除此之外,《明星月報》還開展電影發展調查,發布《各國電影雜志一覽表》《各國制片公司總調查》等調查報告,并于第二卷第一期和第二期發布《電影在各埠》詳細論述了各地的電影市場發展情況。最后,《明星月報》積極探尋擴大和發展中國電影的新思路。該報曾刊發《論電影宣傳》《應用卡通為活動教材之芻議》《怎樣啟發新人才》《關于影評問題》《電影批評上的二元論傾向問題》等文章積極為中國電影獻計獻策。柯靈、阿英、李萍倩等電影一線編劇、導演、影評人均為該刊供稿,闡述創作理念的同時,對中國電影發展提出意見。
(二)注重電影宣傳
于明星公司而言,《明星月報》所承擔的不僅是商業化宣傳,更是影片制作公司對于左翼電影“投石問路”式的試水。因此,該報注重電影宣傳,將明星公司出品影片作為刊載重點。《春蠶》《前程》《鐵板紅淚錄》《脂粉市場》《女性的吶喊》《母與子》《生路》等影片均在該報上進行大幅宣傳。在《明星月報》中,大量篇幅被用于介紹電影劇照、攝影臺本、文學本事、演職員表、插曲歌譜,并通過介紹影片拍攝時的奇聞逸事及工作記錄來增加報刊的趣味性。
《明星月報》注重刊載內容與電影市場的互動。首先,該報通常在電影上映前發布影片宣傳海報、劇情照片以及攝制照片,并重點刊發與主創相關的文學創作。如左翼經典《春蠶》上映之前,該報于第2期發布上映公告,第3期即公布《春蠶》海報和劇情照片,并選登文章《〈春蠶〉絲未盡》。該文章論述了《春蠶》的制作意義、描繪攝制過程,并對程步高導演進行采訪。其次,在影片上映后,該刊主要刊發電影創作者的創作體悟和電影本事。如《現代女性》上映后,《明星月報》隨即刊發主創艾霞所著《我的戀愛觀——編現代女性后感》并將該片本事作為刊載內容。
《明星月報》發行與明星公司電影制作高度結合,這樣的內容特質,使該報的受眾群體與明星公司的電影觀眾類同。同質化的受眾群體使《明星月報》的發行成為電影票房的前奏和預演。明星公司可以通過《明星月報》宣傳即將上映的電影,而電影上映后,《明星月報》亦可利用電影的成功延續其品牌效應,通過電影刊載電影文本、主創體悟,發表相關文學作品、片場逸事等方式攫取其“剩余價值”以擴大讀者群體及購買量。而正如前文所述,在20世紀30年代的明星公司,左翼電影成為其攝制重點,左翼人士也成為《明星月報》的主要撰稿群體。明星公司的商業運作中,電影和報刊二者相互影響、互為促進,無形中擴大了左翼電影的傳播。至1934年《明星月報》已成為中國廣為傳播的電影刊物之一。而大量左翼電影亦通過《明星月報》被世人所熟知。于讀者而言,《明星月報》的傳播過程,亦是對受眾認知行為的影響過程。因此,雖然《明星月報》的刊行仍以商業需求為主,但卻對左翼電影運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電影宣傳和電影生產貫穿《明星月報》發行始終,是該報重要版塊。《明星月報》對電影宣傳和電影生產的重視,提升了左翼電影內涵,更推進了20世紀30年代中國電影發展。
結 語
以上部分,大致對應《明星月報》在左翼電影運動中的歷史貢獻。該報雖非左翼人士創辦,但卻成為左翼電影運動的重要輿論陣地。《明星月報》在左翼電影運動的組織確立、路線引領和內涵提升等方面產生關鍵影響,宣傳了中國電影文化協會的合理性,確定了反帝反封建的現實主義電影創作路線,推進了20世紀30年代乃至之后更長時間里中國電影事業的發展。
電影和報刊皆為傳播媒介,傳播形式又有明顯區分,在各自領域平行獨立發展,電影刊物使二者在歷史長河中交匯。作為電影的附屬性產品,電影刊物是研究中國電影發展的重要史料。它的產生和發展伴隨著電影產業和近代報業的跌宕與起伏,成為電影史與報刊史的交叉研究方向。
如果從當代立場來檢視,《明星月報》對中國電影發展乃至中國電影史的書寫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20世紀30年代,正逢國難之際,媒介成為開啟民智的重要手段。在左翼文化運動中,《明星月報》成為左翼電影宣傳的捷徑。而更為重要的是,該報刊載內容中無處不在的左翼文化理念,它們時而存在于電影宣傳和影評中,時而又隨著創作探討而浮現,甚至在創作體悟中也能有所體現。必須說的是,《明星月報》并沒有明確的斗爭精神和堅定信念,該報的內容以及刊行始終遵循商業行為,服務于電影市場。然而20世紀30年代有其獨特性,任何機構和團體都不能在民族意識覺醒之際獨善其身。《明星月報》對于左翼電影運動的促進亦說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