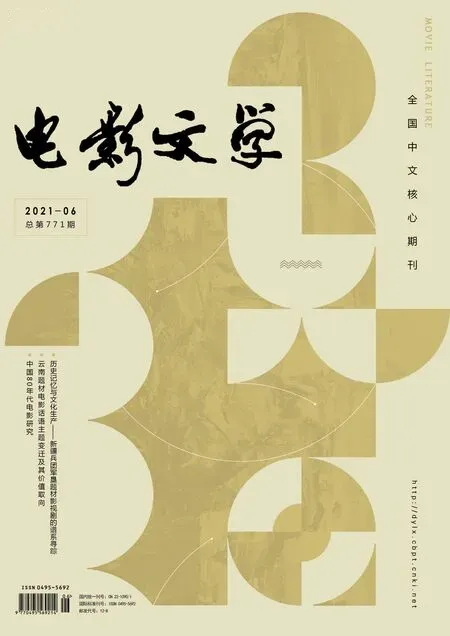紀錄片《鄉村里的中國》的四重敘事機制探析
楊曉軍(樂山師范學院 文學與新聞學院,四川 樂山 614000)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開篇即指出:“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數千年的傳統農耕社會的確奠定了鄉土社會在中國社會的重要地位,鄉村實際上是每一個中國人的根,是中國人寄托無憂無慮生活的原野,是我們想象中的精神家園。隨著我國社會變遷和城市化進程的推進,我國的鄉村,成為一個“衰落”的文化意指和想象空間。鄉村的衰落導致村莊正在退出歷史舞臺,社會學領域的學者將這種現象稱為“村落終結”(周銳波等,2009;劉夢琴,2011;田毅鵬等,2011)。在此背景下,鄉村再一次成為影視關注的焦點。
《鄉村里的中國》是2013年由中央新影集團出品,焦波導演的紀錄片。影片獲得了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最佳中國紀錄片”、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紀錄片”、中國電影“華表獎”“優秀紀錄片”、中國(廣州)國際紀錄片節“金紅棉”獎“最佳長紀錄片”等諸多獎項。可以說,《鄉村里的中國》是近年來我國鄉村題材紀錄片中較為成功的案例。值得一提的是,學界對影片的學術探討,從2014年開始便熱度不減,僅2020年(截至11月中旬)就有6篇相關研究文章發表,其他年份的發表情況分別是:2019年3篇;2018年5篇;2017年6篇,2016年10篇,2015年1篇,2014年兩篇。相關研究主要聚焦在鄉村影像與國家形象建構(胡滿江,2020)、鄉村記憶與影像表達(陳新民、楊超凡,2020)、影片所反映的農民問題(鐘凱,2018)、影片的敘事策略(代輝,2018;張端霞,2017;陳曉波等,2016)、影片中的農民生命觀(褚興彪,2016)等。不得不說,《鄉村里的中國》得以被學術界持續關注的原因,除了影片作為“鄉村”題材紀錄片具有一定典型性,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其敘事手法和敘事策略的獨特性。《鄉村里的中國》通過多線穿插并行的鎖鏈型結構、二十四節氣所創設的時空節奏、人文關懷下的平民敘事視角、矛盾沖突與細節呈現結合的敘事手法,構建了一個立體的、鮮活的、真實的、充滿張力的中國“三農”景象。
一、敘事結構:多線穿插并行的鎖鏈型敘事
素材是一部紀錄片的血肉,而敘事結構則是一部紀錄片的骨架。只有搭起了影片的整體“骨架”,將“血肉”合理分布,紀錄片的結構布局才能精巧,內容才能始終對準主題,敘事才能清晰準確。《鄉村里的中國》采取了三線穿插交織、順序并行的“鎖鏈型敘事結構模式”,將家長里短、婚喪嫁娶、夫妻相處和鄰里矛盾通過農民杜深忠一家的家庭生活線,村主任張自恩的基層工作線和大學生杜濱才與父親杜洪法的代際相處線組合延伸展現出來。三線相互關聯,不可分割,不同人物的生活交織對照緊密呼應著紀錄片的鄉村主題,形成了統一的邏輯情感。
(一)農民杜深忠的家庭生活主線
農民杜深忠在年輕時拿過槍當過兵,在魯迅文學院培訓過寫作,早年就愛潑墨揮筆、寫寫小說,鏡頭下的他閑暇常常拿著毛筆寫寫畫畫,或者拉著一把走音的二胡,心心念念地想買把琵琶,長年讀報看新聞關注國家大事。雖然是村里難得的文化人,卻很少花心思在農活兒上。因此家中生活清貧,女兒小梅也只能輟學打工負擔起家庭重擔,杜深忠的這些想法在大字不識幾個的妻子張兆珍眼里,自然是“頭頂火炭不覺熱”,尤為不切實際,不務正業,為此,夫妻間總有唇舌之爭。杜深忠和其他鄉民生活方式的大相徑庭,以及對精神的追求,一改大眾心中的農民形象。他的精神哺養追求在貧瘠的物質現實面前幾乎潰不成軍,杜深忠的遭遇是不少農民正在經歷或即將經歷的命運,作為貫穿全片的主線索,串聯起另外兩條線,讓受眾跟著杜深忠同呼吸,共命運,直擊人文主題。
(二)村主任張自恩的基層工作輔線
村主任張自恩主持日常村務,忙著調解鄰里矛盾,還在為招商引資奔波,為杓峪村做了不少好事,卻仍有各種反對和不解。為了改變村容村貌修建小廣場,張自恩安排施工隊砍樹時和村民發生沖突;為了讓村里脫貧,張自恩多次去旅游開發公司洽談,村民卻懷疑其貪腐,不斷上訪要求查賬;直到后來他家的秧苗都遭到“有意殘害”。村民對張自恩的這種反對與不解,更多是由于老百姓對官員固有的、根深蒂固的偏見。張自恩在總結自己一年的工作時,在醉酒與反思中不無心酸地說出了“干一年支部書記,也就是賺了一肚子酒”的話。這條線衍生出了其他村民的柴米油鹽、大事小情,極大地豐富了敘事,讓整個村子的民風民俗立體起來,使得農民的性格形象也更為真實,既不高大也不卑微,有深明大義的一面,也偶爾嶄露一角人性弱點。
(三)大學生杜濱才和父親的情感輔線
大學生杜濱才一線揪出了中國人隱秘的、不容宣之于口的、心口不一的情感表現。杜濱才的父親杜洪法多來年一直罹患精神疾病,有時候控制不了沖動,因此母親離開了父親,也離開了這個家。雖然父親對他竭盡所能付出,但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杜濱才,怨恨又想念母親,和患病父親的相處充滿著情緒的宣泄。而紀錄片記錄下了杜濱才對母親的和解,與父親相處的軟化,把深藏多年的感激和愛最終用正面的方式表達出來。這一條線承擔著全片的感情線,得到了觀眾的一致情感認同,填充著紀錄片的淚點。
這三條線索穿插并行,形成鎖鏈型的敘事結構,加強了敘事情節的故事化,適應了觀者的觀看要求,三線結構互為補充,將各個小敘事串聯成最終指向主題的完整敘事。
二、敘事節奏:二十四節氣創設自然時空節奏
電影可以用色彩、線條、構圖等種種可捕捉的表達方式來傳達可見的、直接的內容。但還有一部分暗流涌動、隱藏著的意境無法直接表現,言語會曲解,書寫也不足夠,是一個難以越過的障礙。對于這部分不可直言的意境,在電影中通常體現為情節轉變帶動人物情緒和動作的變化,或者使用不同景別、不同快慢的鏡頭組接,在一動一靜的規律剪輯中,在鏡頭的推拉搖移里,在光影色彩的變化里,形成獨特的敘事節奏。節奏是電影藝術的個性,“把握好敘事節奏,可以增強紀錄片的可視性和趣味性。”《鄉村里的中國》對總體節奏和基調把握自然得當,敘事的起承轉合、急緩疏密往往都依據線索人物的生活際遇發展,呈現一種和日常生活節奏協同的敘事節奏。
影片按農歷二十四節氣劃分,用遠景、中景、近景鏡頭組接,表現不同歲時節令杓峪村的不同風景人事,構成了一種自然的時間節奏。影片從“立春”開始,翻開就是沂蒙的山水遠景,冰雪消融,河灘上群鴨嬉水,村民們在羊身上刷紅漆“打記號”,撰寫大大的“春”字,一派歡欣景象;“驚蟄”開篇,是旭日初升的山景,杜深忠為蘋果樹修剪著枝條;谷雨則配以山花爛漫、鳥在繁枝筑巢的盎然風景,村民們忙著“點蘋果花”;小滿時,巢中鳥蛋特寫,野刺猬爬行在草叢里,蘋果到了“套袋”的時候;大暑,山中雷雨馳行的遠景,張自恩的工作也迎來了更大的矛盾;寒露,火紅流云在群山蔓延,蘋果也迎來了豐收,卻遲遲賣不出去;冬至,小山村銀裝素裹的大遠景,村民在雪地里逮兔子,孩子們玩雪玩得不亦樂乎,杜深忠喜迎嫁女……全片用明麗的風景把村里的大事小情鏈接對照起來,將敘事推進寓于時空表現,四季變換,三條敘事線索也在循序展開。除此之外,影片主角杜深忠家里的那臺電視里出現的神九發射、奧運會舉辦、習總書記講話以及春晚的新聞畫面,也是影片節奏的另一個體現。電視里的“重大事件”將這個看似封閉的小山村和國家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形成了“家國一體”的政治隱喻。
瑞典電影大師英格瑪·伯格曼指出:“節奏是至關重要的,永遠是至關重要的。”節奏有遲速之辨,吟猱有緩急之別。《鄉村里的中國》敘事節奏是順其自然的,人景和諧統一,更是勻速的。三分鐘一個情節,五分鐘一個節氣,無痕過渡。每個段落下的家長里短、雞毛蒜皮都敘述得清楚詳盡,一氣呵成,節奏均勻。這種緩緩的時序節奏,讓觀者擁有了一種平靜和輕快的觀感。它將小村里瑣碎冗雜的事與情,隱藏在舒緩如水的節奏中,余音回響在觀者的腦海里。
三、敘事視角:人文關懷下的平民視角
(一)客觀視角與鄉村里的真實中國
紀錄片的敘述視角是指對記錄對象采取的觀察和講述角度。法國文藝理論家茨維坦·托多羅夫將其分為“全知視角、內視角和外視角”。著名敘事學家熱拉爾·熱奈特則將其分為“零聚焦、內聚焦和外聚焦”。而我國學者陳平原把敘事視角分為“全知視角、限知視角以及純客觀視角”。這幾種分類實質上是大同小異的,我國紀錄片在這幾十年里經歷了由傾向全知到限知,再到純客觀的轉變。全知視角又稱云端視角,開創英國紀錄片學派的格里爾遜把紀錄片中的解說詞形容為“上帝之聲”,生動地為紀錄片的全知視角做了注解。這種視角固然自由靈活,卻缺少對人內心世界的關注,顯得高高在上,太過冷漠。
《鄉村里的中國》拍攝時間長達373天,在一年有余的拍攝中,攝制組進村成了這里的第168戶村民,像農民一樣種地、生活。這種弗拉哈迪式的全程參與拍攝方式,消除了與村民之間的距離感,讓人們對鏡頭習以為常,大事小情都納入鏡頭,確保了紀錄片的真實性。因此《鄉村里的中國》有了無限接近真實生活的客觀視角,敘述代替說教,攝像機直接將人們的生活場景和對話純粹地展現給觀眾,不加任何干擾。并和觀眾一起探索未知,最大限度融入了鄉民集體,呈現了鄉村生活原貌,還原了質樸本真的村風民俗。比如呈現村里過年咬春的游戲,老人“給小孩頭上縫豆子,小孩不生痘子”,小梅出嫁時家里燒喜包袱祈禱婚姻和順的鏡頭,一切真實自然且妙趣橫生。
結尾杜深忠對兒子教誨道:“一些人說對土地有感情,海龍我給你說,實際上我一開始對土地就沒有一點感情,咱就是沒有辦法,無奈……你得好好讀書,千萬千萬的,這個土地不養人,我和你說,咱這里的二畝貧瘠土地不養人,所以說我多么盼望著你,不成功的教訓比成功的經驗還說明問題,這是血的,這是一輩子的心血,一輩子的淚。”這些直接的對話,沒有一句解說詞,既不渲染,也不煽情,只是純客觀記錄,但給觀眾的震撼也十分強烈。正如焦波所說:“我從來沒導演過任何一個場景,沒寫過一個字的策劃,沒編過一句臺詞,這些都是真實生活的自然流露。”這種記錄,直擊人物內心,用鏡頭語言搭起了觀眾和影片之間交流的橋梁。第15屆中國電影華表獎也評價道:“《鄉村里的中國》是這個時代有記錄意義的、不可多得的中國農村生活標本。”
(二)濃厚人文關懷的平民視角
導演焦波和團隊在杓峪村扎根,和村民同吃同住,這種極度的貼近,使得《鄉村里的中國》選擇了平民化的視角和審美趣味。村民自己的俏皮話,就能足夠精準地為事件下注解,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張兆珍和杜深忠爭論村民賣樹這件事情說出了“人家有錢的王八坐上席,你無錢的君子下流坯”;把蘋果入庫的張自恩感慨“蘋果入了庫,還不知道是娘娘還是爺爺呢”;在杜深忠家討論蘋果賣價的村民春田則一語中的說出“你今年盼著明年好,明年褲子改棉襖”。這些農民的自嘲,是用平民化視角對農民自身的生存空間做出的深刻反思。這些場景展示著農民的精神風貌,挖掘出了農民對未來生活的追求和夢想。這種平民視角的聚焦,彰顯了濃厚的人文關懷,帶著對社會的深深焦慮。《鄉村里的中國》高度貼近農民生活,對農民聲音的傾聽,對農民視角的關注,更能引起觀眾的思考和共鳴。
四、敘事技巧:矛盾沖突與細節敘事的雙重“勾連”
《鄉村里的中國》使用強化矛盾沖突的敘事手法,三個線索人物身上本身也具有強烈的矛盾張力,使得片子的情節性和故事性很強。最重要的是:這種敘事手法使得社會現實問題在鄉民矛盾沖突的因果關系里不斷凸顯出來。可以說《鄉村里的中國》關注的絕不僅是杓峪村村民的個人命運,而是在映射著中國農村普遍存在的種種社會問題。
(一)矛盾沖突呈現鄉村問題
1.物質和精神文明的貧瘠
杜深忠的精神追求,改變了人們對農民形象的認知,而正因他的精神追求造成的家庭矛盾,才揭示出當代農民的精神文化追求得不到保障的現實問題。影片里杜深忠一家的生活不過溫飽而已,種蘋果一年到頭收入不過七八千塊錢。杜深忠買琵琶花了690元,都要給妻子撒謊少報200元;女兒出嫁,喜糖多買一袋都要猶豫不決;愛寫寫畫畫的杜深忠,為了省錢,只能在水泥地上練習書法。這種窘迫的經濟狀況,很難支持其文化愛好。外出打工不幸身亡的張自軍,剛入土為安,家里人就為他的賠償款爭得不可開交。在物質貧瘠的時候,親情開始變得冷漠無情。
固然杜深忠在清貧里仍舊保持著對精神文明相當執著的追求,無謂錢財,但包括妻子在內的其他人被物質貧瘠所困,來不及重視精神世界的荒蕪,也實屬無奈。杜深忠說“這個人需要吃飯是吧,他得活著;這個精神也需要吃飯,也需要哺養”,妻子卻只覺得“也不當饅頭吃,也不當衣裳穿”,而大多數村民對精神文明的態度當屬于后者,由此也能窺探出農村精神文明貧瘠的現狀。
2.男女地位的不平等
在杜深忠夫婦的沖突中,鄉村里男女地位不平等現象隱現。杜深忠是開明的,兒女婚事無所謂窮富。但從兩夫妻的對話里,妻子張兆珍總在埋怨丈夫,心疼女兒,話里話外,可以了解到女兒小梅十五六歲就外出打工供弟弟上學。姐弟倆年齡差不多,但清貧之下,只能女兒放棄學業外出打工賺錢補貼家用,男孩則被叮囑好好讀書。杜深忠和妻子的日常拌嘴中,也說的是“莊戶娘兒們的素質太低太低,不和她一般見識”。杜洪法不怎么會給蘋果套包裝泡沫,手法笨拙,被兒子搶過來做,他對兒子說的也是“這是婦女干的活兒,男的沒有干的”,側面佐證了鄉村仍舊存在思想上的性別歧視。
3.農民經濟增收困難
杓峪村的村民依靠種植蘋果養家糊口,哪怕是村主任張自恩,也得守著一畝三分地過日子。但農資及涉農服務價格過高,蘋果帶來的經濟效益微薄,依著老農民杜深忠的話來說那是“花十分代價以后得不到三分收入,我覺得熬這個時間我都熬得很心疼”。而且涉農服務不知真假,經常有騙子冒充科學院的教授兜售化肥。因為沒有什么專業技能,農民外出打工,也只能選擇從事一些簡單的體力勞動。“賣力氣也就罷了,你得賣性命”,杜深忠給人收玉米,累掉了13顆牙,“拿著人肉換了豬肉吃”,而青年張自軍干脆連命都丟了。村主任想開發農業旅游,改變產業結構,但障礙重重。
杓峪村作為中國普通村莊的縮影,它面臨的問題,就是全農村亟待解決的問題。杜洪忠說糟蹋糧食的獾是保護動物,妻子張兆珍卻疑惑并問出了“農民怎么沒有保護”這個振聾發聵的問題。十七屆三中全會總結了“三農”問題的 “三個最需要”:農業基礎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強;農村發展仍然滯后,最需要扶持;農民增收仍然困難,最需要加快。這些需要,仍需要全國上下齊心協力去改善。
4.城鄉二元化之下環境和發展的沖突
農村的建設還沒有完成,但城市對農村資源的掠奪一直存在。農民沒錢,掙錢的路子也少,就打樹的主意,把樹賣進城里去做綠化。杜深忠說這是“剜大腿上的肉貼到臉上”。農村要發展,但是這種發展建立在畸形的供求關系中,是以壓榨農村生態為代價去保證城市環境,這個問題值得反思。
5.基層干部工作的信任危機
張自恩作為村主任,實實在在為村里做了不少事情。雖然作風粗野強硬,但是為了招商引資,四處奔波,還貼上了自己的錢拉關系。卻被幾個村民聯合反對,要查他的賬,影片中,幾次沖突爭執都和這件事有關。他的強勢和尷尬盡數落到鏡頭里,直到管區書記出面,查賬的事情才告一段落。但這種群眾對基層干部工作不信任的問題,是根深蒂固的,是長期存在的。
6.家庭情感表達的缺失
杜濱才一線是本片的淚點擔當,因為父母離異,撫養他的父親又有精神疾病,他的成長經歷是相當坎坷的。童年留下的心理陰影,一直影響著他和父親、母親的關系。因為一點小事,父親把淄博說成了卷舌,他就會大發脾氣。雖然對患病的父親,愛之深,但說出來的話總是針鋒相對。想和19年不見的母親會面,卻一直說“以后吧”。雖然影片最后,母子相擁而泣,父子互相理解,一切重歸于好。但影片中反映出的“留守兒童”“單親家庭孩子”成長中情感溝通缺失的問題,值得深入反思。
(二)細節敘事捕捉農民真實情感
《鄉村里的中國》在敘事技巧上,極為注重細節刻畫,通過細枝末節凸顯各色人物性格形象,再經人物與事件共同發酵,推動情節發展,渲染氣氛,深化人文主題。
生活可以輕而易舉地被記錄,但要讓生活變得生動起來,唯有細節。杜深忠把投進房門的一束陽光當作一張宣紙,毛筆蘸水在陽光投射的地上寫字,這個細節就讓他身上多出了一股文藝氣息,這幅畫面在此刻也顯得分外靜謐美好,一個窮困但仍舊保有精神追求和生活趣致的人物形象躍然于銀幕。
村主任張自恩的形象也在多個細節之下,顯得立體豐滿。他不辭辛勞地多次為村里的項目奔波,是個工作認真負責的村干部。但并不高大全,面對無理取鬧的反對和查賬,張自恩也會不顧形象,破口大罵。既有放狠話的強勢,也有借酒澆愁的辛酸,嘴上不饒人,年底了還是自費買了東西給反對他的村民送了去。這些性格的多面性,片中沒有任何回避。通過細節的堆砌,多處著墨,把張自恩這個基層干部的形象,一點一點塑造了出來。
而在張自軍的葬禮上,孩子天真地跪著問爺爺“那是俺爸爸的家嗎?門口怎么這么小”,爺爺回答“不小了,這里頭很寬敞”,接著微不可見地嘆了一口氣。這段對話,小孩的天真與現實的悲憫著實戳痛了觀眾的心。而爺爺回答之后的嘆息更是將觀眾情緒推向高潮。這段細節對故事情節推動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
還有一些平淡的生活情節,在細節的烘托下顯得溫暖無比。杜洪法賣了蘋果拿到錢,馬上給兒子杜濱才打電話報告。一五一十地交代了蘋果怎么賣,鋪墊著最后一句話“沒錢了跟我說一聲”。一個在別人口中犯病了要打人、罵人的父親,全片從頭到尾沒有對兒子說過一句重話。重重細節鋪墊之下,動人的情感默默流淌在這通電話里。
《鄉村里的中國》的創作運用了多重敘事策略,既充分展示了一個時代波瀾壯闊的變遷,又全面體現了新時代下小人物平淡生活的樸實旨趣。它所呈現的中國農民形象,雖然苦,雖然難,雖然無奈,但不可謂不堅韌。他們一直保有對精神的不懈追求。縱使希望不斷落空,卻總能再度生出熱情、打起精神接著笑對生活。他們用半生心血總結出來的經驗,哪怕只言片語,也耐人尋味,樸實無華,也本真感人。本片把一個宏大的命題用個體的生活細節和際遇感受回答了出來,細膩且真實,在平民化的視角下折射出社會的各種現實問題,引人深思,充滿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人文關懷,包含對題材真摯而充沛的情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鄉村里的中國》那種自然、平實、遵循真實原則的敘事機制對紀錄片創作有現實借鑒意義。而片子忠實記錄農村的發展與變化,反映農村農民的心聲,樹立農民形象的主題亦具有重要現實意義。但不得不說,《鄉村里的中國》只是一個個案,對此個案的敘事策略進行分析,是有一定現實意義的。但如何透過“鄉村”題材紀錄片,去探討其中關于“鄉村”的影像建構、紀錄片中的鄉村“群像”記憶以及“鄉村”題材紀錄片中的國家形象問題,是一些更值得探討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