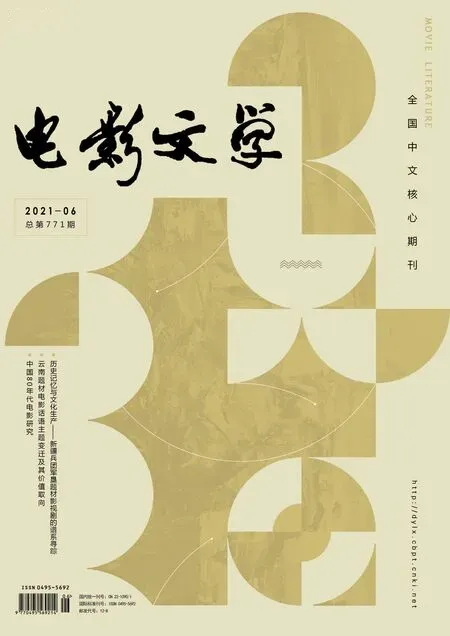80年代初大陸城市電影的敘事邏輯
袁文麗/Yuan Wen Li
隨著現代化的快速發展,人文社科界掀起過對“80年代”命題“集體懷舊”的熱潮,查建英、程光煒等一批學者圍繞“重評80年代”“重返80年”,試圖對20世紀80年代重要的文化現象、文學現象、社會轉型等問題進行歷史境遇性地重新思考。“80年代”不僅是有關時代的個人化經驗,更成為一代人的集體記憶。不言而喻,“80年代”也成為本文思考電影文本的一個重要的場域。本文把視點聚焦在80年代初(以1985年為界),中國社會正處于劇烈的轉型變化和發展中,這一時期不期然地冒出的一批具有經典意義的城市電影,回到特定的歷史場域中閱讀電影文本對城市的想象和表述,對社會歷史變遷和文化價值的表現,具有豐富的文化癥候性意味。
一、20世紀80年代初城市電影的登場與歷史場域中的城市敘述
對城市的敘述、想象的方式隱含著意識形態和社會文化結構性變遷的深層因緣。張英進在概括德國評論家克勞斯·謝爾普時將城市敘述分為四類模式,指出謝爾普的例子完全取材于現代歐洲文學和電影,暗示一種城市敘述從田園牧歌式(如城鄉對立)到現實主義(如階級斗爭)再到現代主義(如審美沉思)的歷史發展,這種發展主要因18世紀以來西方社會的文化、歷史發展而產生。盡管謝爾普的模式產生于西方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和理論語境之下,在中國的文藝土壤中,我們找不到西方那樣的城市敘述線性發展的痕跡,但“他者的視野”所具有的借鑒和啟示意義依然不可忽視。
關于城市的敘述和想象在中國現代的文藝作品中總離不開與“鄉村”的比照框架。從社會歷史變遷的長河中審視城鄉模式的話語內涵、表達方式,我們可清晰捕捉到當代社會結構、文化話語和思潮觀念的變化脈絡。在前工業時代,“城鄉”呈現經典的二元敘述模式,鄉村代表樸素、純凈、自然、美好的人性,是和諧、理想的精神家園的表征。城市則是欲望、墮落、罪惡之都,是人性的深淵、現代工業文明的副產品;在社會主義革命政治語境中,城鄉的表述機制則被置換成了階級斗爭主導下的城市/資本主義和鄉村/社會主義的敘述機制;進入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和現代化進程的20世紀80年代后,城鄉傳統內涵又被新時代的主流意識形態所取代,關于現代化(城市所指代)/傳統、落后(農村所指代)的新話語內涵和敘事修辭在文藝作品中被涌現出來。
1949—1976年關于城市題材的文藝作品比較缺乏,相關作品甚至有意回避對城市形態的表現,在“農村包圍城市”的思維慣性之下,實質上開啟的是一個“去城市化”的過程,換言之,“城市”成了“社會主義文化缺席的在場者”,正如莫里斯·梅斯納曾評述:“對于那些農民干部來說,城市是完全不熟悉的陌生地方……此外,伴隨著的是不信任。以集合農村革命力量去包圍并且壓倒不革命的城市這種做法為基礎的革命戰略,自然滋生并且增強了排斥城市的強烈感情。”對城市的厭惡,有關墮落城市書寫的背后,既隱含著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之爭,又加劇了把城市作為單一的大工業化中心的認知邏輯。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國正處于社會大動蕩之后的重要轉折時期。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向全黨和全國人民提出了把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面來”,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奮斗。中國迎來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成為新時期的主旋律,城市成為現代化建設和發展的重鎮。順應主旋律,80年代初以反映城市現代化建設和發展的新時期電影應運而生。“第四代”導演在經歷動蕩和壓抑的滄桑歲月,像壓緊的彈簧爆發力格外強大一樣,他們攜著新時期一批新電影《都市里的村莊》(滕文驥,1982)、《逆光》(丁蔭楠,1982)、《快樂的單身漢》(宋崇,1983)、《鍋碗瓢盆交響曲》(滕文驥,1983)登臺亮相,記錄和表現那一社會歷史階段的主題和風貌。然而,也許受到電影人自身的知識、經驗及當時社會大環境的影響,這些電影整體上夾雜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風格”的痕跡,其對城市的敘述和表達機制,多少還殘留著“十七年”“文革”中“廠礦文學”“工業文學”的影子,把城市視為大工業的生產空間,城市現代化等同于工業化。不管怎樣,這些文本作為80年代初中國城市現代性的一種特殊的經驗,同時包含著對現代城市的感覺和認識創新的一種探索。
二、都市物質性空間的呈現:現代化工業空間和民族國家想象
在上述所列的20世紀80年代初的四部電影中,除了《鍋碗瓢盆交響曲》以北京春城飯店的改革為線索,其余三部都以上海造船廠及其青年工人為書寫對象。戴錦華精辟論述道:在當代大陸文化中,城市不時成為現代工業的代名詞,城市文化不時被置換為“工業題材”。工人階級作為主流意識形態話語中的歷史的創造力與原動力,則成了當代文化中唯一得到顯影的都市人。新時期(1979— )以來,工業題材再度成為正面表現改革的“重大題材”,工業空間成為轉型中的主流意識形態話語的集散地,成為現代化進程中的當代城市和當代中國的提喻。戴老師指出新時期“城市文化”和“城市”敘述的單一性和政治符號的空洞性,但是回到80年代初的歷史場域中,筆者在給予“理解之同情”時試圖挖掘其敘述的邏輯和意義。
將上海和上海造船廠作為人物活動和人物身份的背景設置有著天然的現實原因。中國現代民族工業源自造船,而上海又是我國現代船舶工業的誕生地和新時期船舶工業發展的重鎮。2010年上海世博會,位于浦西園區占地面積約5000平方米的中國船舶館,就象征著中國民族工業的堅強精神。船舶工業發展,對航運、海洋資源、國防事業的發展有巨大影響。船舶工業成為我國經濟改革的先行者。另一方面,在中國作家和藝術家筆下,上海一直以來是一個津津樂道的話題,是多義、復雜而又曖昧的符號。無論是20世紀30年代新感覺派筆下的摩登上海,或是張愛玲筆下處于淪陷、市井生活意味中的傳奇上海,或是20世紀40年代以矛盾為首的左翼作家筆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上海,或是當代作家王安憶筆下的懷舊上海,甚至到方方、衛慧筆下的“新感性”上海,關于對“上海”的想象、敘述和建構實際上構成了一部中國現當代史。由此,可總結近現代以來有關上海城市想象的三大譜系:其一,在現代性的民族國家意識下認知舊上海擺脫殖民化獲得獨立的國家元敘事;其二,現代化和全球化進程中的摩登上海,表征著物質與文明的擴張及其引領的現代性普遍價值;其三,上海作為凝視大都市現代性、消費性、暫時性、頹廢性的現代主義感性經驗敘述。本文所選擇影片正是立足前兩種敘事邏輯,將“上海”置于民族國家的意義上展開敘述。
把城市作為大工業發展的圖景呈現和表征是20世紀80年代初城市電影的主要景觀,這主要表現在物理空間的鏡像書寫方面。為了強調和突出城市工業化的背景,影片開場鏡頭著力展示上海外灘大樓、高大的廠房、高高的塔吊、集體宿舍和建筑工地等,主要情節的發生也都在高度能指化的工業空間中。《都市里的村莊》開片用搖鏡頭對準高高塔吊和工人們愉快下班的場景。幾個關鍵的情節都發生在工廠,如丁小亞向動力車間求援修高吊時無奈遭遇小伙子掰手腕的挑戰,杜海在事故中舍命救黑子,等等。《快樂的單身漢》片頭也是俯拍高高塔吊,橫搖鏡頭依次呈現黃浦江上氣派的大輪船、高大的廠房、建筑工地的掠影,最后鏡頭聚焦到大批朝氣蓬勃的年輕工人上班的情景。在影片中,除第13分鐘劉鐵和丁玉潔回憶起過往情感的場面,其余部分都發生在車間、工地和集體宿舍中。而《逆光》首先呈現的是伴隨著悠長的汽笛聲的黃浦江上的輪船、江景,電影以全景鏡頭橫移掠影的方式展示,最后定格在正在建筑的高樓和旁邊的塔吊、外灘的一幢歐式建筑的特寫上。
總的來說,幾部電影對上海空間的表現方式常常處理為空間的分割、差異空間的對立以及相關度空間的連接。在電影鏡像中,常常把外灘建筑的掠影與黃浦江兩岸的工業化空間銜接在一起,用破舊狹窄棚戶區和現代的工業空間形成對立,淡化外灘一帶建筑的殖民符號意義,突出新黃埔一帶工業化空間的意義表征,通過這一帶的高大樓房—工廠—黃浦江港口的空間化鏈條,經由造船廠、現代輪船這一具體的意義符碼,體現了一個連接傳統、面向未來、走向世界的新上海的現代城市功能和形態。可以說,這是一種將現代性意念化了的想象性敘述。
《都市里的村莊》和《逆光》中都隱含著兩個地域空間——棚戶區/外灘高大建筑和黃浦江大工業空間——兩個能指的對比。《逆光》開頭就以俯拍橫移的全景空鏡頭,呈現出棚戶區的全貌。而故事展開的另一端又是具有高高塔吊的宏偉工業圖景的船廠。棚戶區是作為舊上海無產階級的空間符號出現的,“仍然是上海灘,仍然可見南京路的建筑群,但就在這些幽靈般的影子的后面,還有一個與解放后的景色極不協調的世界——蘇州河畔的棚戶區。”兩者的并列構成了由舊上海走向新上海的饒有趣味的鏡語敘事。《都市里的村莊》和《逆光》在棚戶區和船廠兩個富有張力的場景交替中展開故事的敘述。這其中隱含著電影敘事的修辭邏輯:棚戶區被命名為村莊/落后/此刻/傳統,南京路和大工業空間被命名為城市/現代/未來/希望,正如電影中獨白昭示:“一個傳統中國和一個現代的中國,而這兩個影子同時疊印在人們心中,希望和未來就在生活中,就在身邊。”這也暗含著另一種“空間政治”邏輯(棚戶區/南京路對應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在歷史話語中的轉換。故事以面向未來的新上海的工業景觀為背景,以社會主義新人——工人階級為主體,表達出一種創造新社會,實現現代化進程的宏大政治愿景。
三、都市歷史空間的表述策略:社會主義“改革敘事”的困境
上述四部電影在類型和敘事邏輯上有著高度的類同性:它們都上映于1982年左右,彼時中央政府正致力于兩個文明的建設“兩手一起抓”。電影《鍋碗瓢盆交響曲》直接以國營飯店的改革為描寫對象,觸及改革的重要命脈、核心問題和關鍵舉措。而以上海造船廠為背景的三部影片,探討經濟建設變革中企業制度和管理的一些問題,而這些問題又主要關涉到無產階級的主人——企業工人,尤其是青年工人的種種狀況:工人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知識教育和技術改進,精神風貌和效率成績等,他們是現代化進程的主要呼喚者、實施者和創造者。概而言之,四部影片隱含“改革敘事”的邏輯和意義:以企業題材(主要是工業題材)為背景,以青年工人為男女主人公,以男女主人公的愛情故事作為推動故事情節發展的戲劇沖突。
程光煒曾認為“改革文學”殘留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諸多因子,它所表現的生活,是高度虛構和抽象的“生活”。這種“抽象生活”常常是以“典型人物”為主體的“英雄生活”,在這里“日常”被看作是要否定和征服的對象,“日常”中的吃喝拉撒以及喜怒哀樂的情緒變化,都應得到嚴格的控制和管理,以服從于更高的目標。程老師對“改革文學”的深度概括雖不能完全代表改革電影的敘述邏輯,但在某些方面也是高度相似的。如電影中對“典型人物”的塑造,丁小亞(《都市里的村莊》)、劉鐵(《快樂的單身漢》)、牛宏(《鍋碗瓢盆交響曲》)、廖星明(《逆光》)都是有著崇高的理想與激情的“英雄”式的人物,影片對其進行大力地歌頌和贊美。雖然影片也試圖表現理想主人公的私人生活——愛情,但才子加佳人式的愛情模式高度抽象化、扁平化,對于愛情生活過于濃縮和模糊。《快樂的單身漢》中對男女主人公從見面、誤會、化解矛盾到結婚的過程只用了三組鏡頭,不到10分鐘。同時通過以“社會公共性”的方式強烈消解“日常生活性”,影片常把對日常生活事件的書寫放置在社會性的“公共性”空間中,放置在工廠、辦公室、工地、住宅客廳的空間中。比如《逆光》中廖星明第一次帶女朋友夏茵茵回家成了整個村的一個“公共事件”;《快樂的單身漢》中人物的日常生活和思想風貌的“蛻變”主要上演在“集體宿舍中”。強烈的社會公共性消解了個體隱私性和日常生活性,在電影的敘述邏輯下,實際上另一種修辭話語正在被置換,青年們以愛情的名義,把美好的愛情化作理想、激情、革命,呼喚改革和現代化,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人。黃平說“重讀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的小說,大量(改革文學的)獲獎作品一個核心的線索是:革命青年在‘現代化’的號召下從‘革命小將’轉變為‘專業能手’”。誠然,電影的改革敘事的一個重要的功能,恐怕也是詢喚“社會主義新人”的出現,讓廣大青年將“愛情和理想”轉化為“革命激情”,將“革命激情”轉化為“工作倫理”,投入各行各業的“現代化”建設中去。
重返20世紀80年代的歷史場域中,回到改革的肇始階段,改革的“動力”在告別“文革”的立場上是清晰的,“80年代”的某些重要共識:啟蒙、改革、現代化、創新……構成了一種80年代式的“態度同一性”。上述幾部電影顯露了其在與主流話語、傳統敘述模式之妥協、合謀和抗爭過程中的歷史局限性。在另一個維度,電影也顯示另一種直面現實的勇氣和敏銳捕捉的時代感,影像立體多維的呈現為我們提供了理解文本的新的向度和可能。如新時期人的思想解放與價值困惑、情感孤獨的并存(丁小亞作為勞模被排擠),特別是物質追逐、商品經濟的交換倫理在世俗社會中的暗流涌動,然而,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并沒有給“欲望”“財產”“商品”等以合適的位置。《都市里的村莊》精心刻畫了一場知識分子哥哥(舒朗)與個體戶弟弟(家林)的沖突的故事。兄弟倆的身份沖突為我們提供了多個理解的面向:精英知識分子和普通百姓在“個體經濟”/“發家致富”的價值觀方面存在沖突和張力,這可謂暗藏副線。滕導不只是客觀冷靜地書寫和呈現,甚至在兄弟倆爭辯的長鏡頭中給予“發家致富”以合理解釋。在這里,影片似乎暗示個體戶家林也是改革的先行者,但對于兄弟倆的態度指涉在文本中是曖昧不明的。誠如張旭東所言:“第四代”所受到的壓制及其復興的社會與文化意義往往被低估了。以“文化大革命”為界限,充滿動蕩經驗的時間跨度決定了他們在新時期電影生產中的潛力與局限性。“第四代”導演同更老以及更年青一代的重疊與不可避免的競爭,使得他們的作品在立場上顯得很不穩定,在表達上顯得曖昧,在內容上表現出自我矛盾,在影片組織上則取一種折中態度。“第四代”導演對于一切都沒有太大的把握。他們依然以懷舊的追尋者的姿態登場亮相——追尋形塑了自身經驗的社會主義時代的真善美。
——評《中國現代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