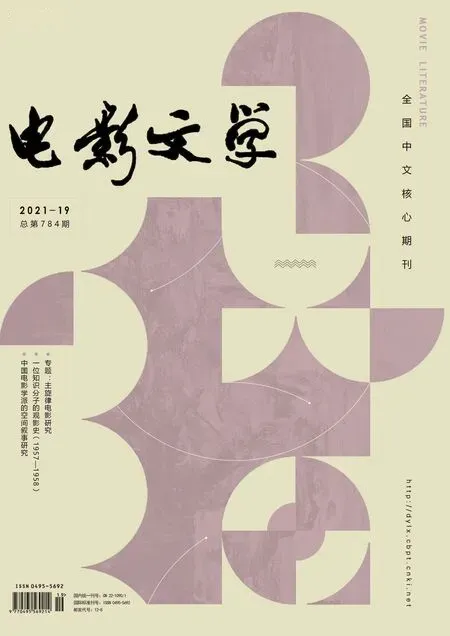租界文化語境下中國早期電影的生態圖景與風貌格調
王 俠
(1.重慶郵電大學傳媒藝術學院,重慶 400065;2.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藝術研究所,北京 100029)
中國早期電影在上海生根發芽、發展壯大,因此研究這時期的中國電影離不開上海這座城市。而彼時的上海又是因租界而興起的城市。因租界的開辟,上海從一個小縣城一躍成為號稱“東方巴黎”“東方紐約”的國際化大都市,提供了電影繁榮興盛發展的土壤。1905年,中國第一部電影《定軍山》在北京誕生,但形成“生產—發行—放映”的完整電影工業體系,創建獨特的中國民族電影業卻是在上海完成的。因此上海電影也是中國早期電影的代表。以往的電影史多從海派文化、都市文化角度詮釋中國早期電影的發展狀況,卻忽略了租界文化之于上海的意義以及對早期電影的生發意義。“租界語境下的上海文化,很難用海派文化或都市文化準確全面地指稱,脫離‘租界’這個根元素,海派文化、都市文化難以解說清楚……以‘租界文化’來指稱現代上海的城市文化特性,或許,它更貼近上海的文化個性。”特殊而穩定的租界環境,商業主義與娛樂消費文化的并重。眾多而稠密的人口、人際關系疏遠的移民城市、中西兼容的文化姿態都為電影在上海的成長提供了雄厚的物質與精神基礎。從某種程度上說,租界文化與早期中國電影具有同源同構同質的特性。租界文化是西方殖民化的產物,電影被引進中國伴隨著殖民入侵這一過程。電影是一種商業化的藝術品,而租界恰恰為中國早期電影的發展繁榮提供了生機蓬勃的市場環境。租界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平臺,同時作為中國電影人發揮才干的舞臺,無疑是中國早期電影成長的息壤。
上海租界從1843年開辟到1945年收回中間有一百年多年的跨度,在上海這座都市建構了與中國傳統城市截然不同的市政制度、文化形態、城市景觀、審美趨向。它以中國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的交融為經,以殖民化、商業化的特質為緯,形成獨屬于特定的文化形態,李永東先生稱其為租界文化,“是指19世紀4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上海、天津、武漢等地外國租界的相繼開辟,在以上海租界為主的租界區域逐漸形成的殖民性、商業性、現代化、都市化、市民化的中西雜糅的文化形態,是與中國傳統文化、海派文化、都市文化既有著一定聯系,又有著明顯區別的一種新型文化”。它主要有三大特征:中西文化的雜糅、商業文化與娛樂消費文化的交錯共融、殖民性與民族性的交織。這些特征在中國早期電影的創作中打上了或深或淺的烙印。
一、租界中西雜糅文化在早期電影中的彰顯
租界作為一個強勢的文化場規約著上海城市的精神氣韻。生活在租界的文化空間中,并學習著歐美電影的表現形式與藝術技巧走向電影創作的中國電影人,不自覺地會將他們所感受到的這種亦中亦西的文化特質呈現在電影中。中國電影人獨立制作的最早的三部長故事片《閻瑞生》(1921)、《紅粉骷髏》(1922)、《海誓》(1922)都呈現了中西雜糅文化的特質。
影片《閻瑞生》的取材就來源于租界上海的一則新聞,講的是洋行買辦出身閻瑞生,為了貪圖錢財謀害了已經從良的妓女王蓮英的故事。洋行買辦這一人物身份是租界社會的產物。其對弱小女子的欺負,也隱約透露出裹挾在西方殖民文化中的極端腐朽墮落的品質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傷害。影片的拍攝方式與表達技巧模仿美國偵探片,迎合了生活在租界中的上海市民的觀影需求,獲得了理想的票房收入。與此同時,管海峰編導的《紅粉骷髏》,將中國自古就有的武打和言情情節披上美國武打片的布景設置,在才子佳人的愛情故事中穿插進洋人律師破案的情節,“是一部‘有偵探、有冒險、有武術、有言情、有滑稽’的影片,湊集了一切不倫不類、不中不西的貨色”,《中國電影發展史》因此稱之為“是十足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上海租界洋場文化的產物”。直陳了影片受租界中西文化雜糅的影響特質。
除此之外,立足上海租界電影市場的但杜宇以“一女二男”的三角戀愛為故事,編導了影片《海誓》。由“號F·F(Foreign Fashion),蠻靴卷發,有西方美人風味”的殷明珠飾演女主角,顛覆了中國溫婉、嫻熟的傳統女性形象。以時髦小姐的身份呈現在銀幕上,引起了上海社會的一時轟動。浸染著租界文化的但杜宇,也通過這部影片顯示了他對租界雜糅文化的認同。影片中的中國人穿西裝、在花園中求愛、在草地上吃西餐、在教堂中舉辦婚禮,完全是租界開辟后,西方文化植入中國文化所帶來的結果。為了營造這種“西化”特質,影片甚至不惜損壞真實性,如讓仆人也西裝筆挺,讓窮困不堪的畫家也“住著一間西式的洋房,家里擺設著銅床、地毯、西式椅子和大大小小的花瓶”。但是影片“西化”特質十足的同時,又保留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元素,如影片中的字幕又都是用古雅的文言文寫成。程季華等人分析“字幕的‘古雅’和畫面場景的歐化,就構成了這部影片形式的不古不今、非中非西、雜亂混合的特點”。而這正是租界中西雜糅文化的直接體現。
繼此三部長片之后,商務印書館的影戲部也拍攝了長故事片,依然顯示出租界中西雜糅文化對其的影響,如1923年拍攝的《孝婦羹》《荒山得金》《蓮花落》,雖取材于中國古典小說,但布景道具、人物服裝造型皆具歐化傾向。1924年先后推出的《大義滅親》《好兄弟》等影片皆因是中國化的故事披上西方化的外衣而遭時人詬病,《大義滅親》中的女主角梅麗蘭:“頗有歐美侍女之風”,其“舉動言笑,吾敢謂同化于西洋式中,已及于爐火純青之境歟”。《好兄弟》中的布景道具設計及人物的生活方式,同樣遭人指責:“臺上陳設俱系西式,各人以巾圍身,如吃西餐,而所進菜肴,又系中國式,不倫不類。”商務印書館作為宣揚先進思想文化的陣地,曾出版了《東方雜志》《婦女雜志》《小說月報》等期刊,在電影如火如荼地在上海放映時,商務印書館成立影戲部拍攝影片,目的是“借以抵制外來有傷風化之品……表彰吾國文化,稍減外人輕視之心”。然而與這種初衷相違背的是,他們在租界土壤中攝制出的電影,依然難以擺脫被“租界化”的命運。
1926年“大中華”“百合”合并成為大中華百合影片公司,刻意走“西化”之路,拍攝了大量以租界都市生活為題材的電影,更是租界文化的中西雜糅在電影中呈現的集大成者。在《小廠主》(1925)、《透明的上海》(1926)、《探親家》(1926)、《王氏四俠》(1927)等諸多影片中,無論從道具安排、環境營造、故事內容上,還是從人物形象、生活方式、思想傾向、價值判斷,都有著“歐化”傾向。這是租界亦中亦西混合文化在影片中的投射。為了能在上海電影市場上取得一席之地,博得租界華人和洋人的好奇,上海的各電影公司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本,競相“掀起了不倫不類的古裝片競攝風潮”。在這股浪潮下拍攝的《紅樓夢》電影,竟然讓人物都穿上時裝,讓“林黛玉穿著一件像舞裙一樣的長衫,足蹬高跟鞋”,“布景則是雕龍柱與西式吊燈并列,太師椅與沙發共陳。”極盡之能事地彰顯了租界文化對這部電影創作的影響。另外,從1928年到1931年間,各大電影公司拍攝的大量取材中國武俠小說的武俠片,其中的主角也因“穿著美國西部與墨西哥式的cowboy服裝,頭穿闊邊尖頂的牧者呢帽,身穿騎馬式的襯衣”而顯得不倫不類、亦中亦西,遭人詬病。
早期中國電影創作中所呈現的租界文化的中西雜糅特征,是租界社會的一個表現。租界特有的文化精神不僅影響了他們的審美趣味,也影響了他們對電影藝術的感知。租界自由、開明、包容、新奇、多樣的文化氛圍讓他們大膽創造電影,希冀既能獲得國人的認可,又能博取洋人的眼球。中西文化的雜糅正是他們在電影反復利用的表現方式,在其中混合著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保守與時髦的豐富訊息,顯得多姿多彩卻又不倫不類。
二、租界文化的商業娛樂性使早期電影的選材充滿投機意味
租界開辟后所形成的以商業為重鎮的上海,使得商業文化成為該城市的主導氣質。外商攜帶著電影到上海放映,是看上了上海這塊肥沃的風水寶地有著巨大的電影消費市場。在攫取豐厚利潤的推動下,他們在人流密集的租界區投資建造了大量電影院和電影公司,聘請中國商人加盟合作拍攝電影,在這種情況下誕生、成長的中國電影本身就有著商業利潤至上的引導。再加上20世紀初內憂外患的中國,工商業十分不景氣,中國商人在多方投資失敗的情況下,有一部分商人轉向了投資方興未艾的電影業。因此,選取什么樣的電影題材,拍什么類型的影片以及何種影片能獲得豐厚收入成為這些商人首當其沖的考慮之處。
在充滿投機思想的引領下,早期中國電影的取材主要是根據觀眾的喜好而來。比如影片《黑籍冤魂》(1916),“就是根據當時新舞臺幾經演出、賣座不衰的文明戲《黑籍冤魂》改編而成”。《閻瑞生》(1921)影片產生的原因也是從“演出半年之久,賣座始終不衰”的文明戲中得來的靈感。從《黑籍冤魂》中嘗到甜頭的管海峰,創作《紅粉骷髏》的動機同樣是出于討好觀眾的投機心理,他后來回憶說“拍什么片子,劇情的選擇十分重要,因為,劇本的好壞直接影響到投資和利潤。根據上海人的心理、口味,當時最受歡迎的,也就是劇院最賣座的一些武俠情節的戲劇。因此,我決定從這方面來選擇劇情”。
從交易所投機失敗的張石川、鄭正秋等人投資明星公司的初衷,同樣認為電影業是有利可圖的大事業。在“處處惟興趣是尚”的創作思想指導下,“明星”僅一年內就拍攝了《滑稽大王游華記》(1922)、《擲果緣》(1922)、《大鬧怪劇場》(1922)、《張欣生》(1922),前三部受觀眾喜愛的美國喜劇片的影響,以多吸引觀眾為宗旨,淋漓盡致地發揮了電影的“娛樂”功能。《張欣生》與《閻瑞生》的創作動機一樣,都是根據在上海轟動一時的文明戲改編。1923年《孤兒救祖記》獲得了巨大的市場效益,“明星”于是接連拍了一系列此類題材的影片,如《苦兒弱女》(1924)、《好哥哥》(1924)、《上海一婦人》(1925)、《最后之良心》(1925)等。1928年,鄭正秋、張石川將《火燒紅蓮寺》搬上銀幕,“不想此片竟萬人空巷,突破了國產影片的最佳賣座記錄,明星公司的初衷本只想拍一集《火燒紅蓮寺》便了事,意想不到的賣座佳績使經濟正陷于困境之中的明星公司欲罷不能,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將《火燒紅蓮寺》一集集地拍下去。”明星公司在三年間竟連續拍攝了18集《火燒紅蓮寺》。在轟動的商業利潤的驅使下,其他公司紛紛效仿,造成了電影創作競相模仿的現象,“形成了一個獨特的影片樣式,即所謂‘火燒片’。中國銀幕上曾幾何時是‘一片火海’:《火燒青龍寺》《火燒百花臺》《火燒劍峰寨》《火燒九龍山》《火燒七星樓》《火燒平陽城》……武俠影片開始席卷中國影壇。”
因商業繁榮而發展的上海租界,最大的特點即是批量生產,以最高的效率、最低的投資獲得最高的利潤。這樣的文化土壤特別適合滋生這種模仿的投機行為。有評論者稱其為“上海的狂潮”:
上海灘上,每逢產生一種新事業,只消時髦些,發達些,就會有人跟著學步。如潮水一般的蜂涌起來。有人說,因為上海人富于“一窩蜂”的天性。也有人說,上海地近大海,天天飲足了含有潮水性的自來水。故一窩蜂的性質,已成為上海人底第二天性了。入民國后,最大的是“交易所潮”。其他如“話劇潮”“卷煙潮”“牙粉潮”“畫報潮”“橫報潮”“模特兒潮”等等,潮來潮去,已犧牲了許多金錢和許多生命。最近的“電影潮”和“武俠小說潮”還在繼續產生,方興未艾。唉,上海的狂潮!
不僅是“火燒片”成潮,各大電影公司看明星公司拍的武俠片賺錢,就大量效仿攝制武俠片,“在1929年至1931年間上海的50多家影片公司,就拍攝了250多部武俠神怪片,占其全部影片出品的60%以上”。另外,大中華百合公司批量攝制的具有“歐化”傾向的影片、各大電影公司競相投機拍攝的大量古裝片、愛情片以及“孤島”時期,再度燃起的古裝片拍攝熱潮,都體現了租界商業主義、娛樂文化對這些電影創作的影響。
三、租界殖民性與民族性交織下早期電影的敘事意圖
租界的開辟帶來了上海都市騰飛猛進的發展,無論從物質層面的市政建設還是從精神文明的文化建設,上海都躋身于世界大都市之列。但是這種發展“并非中國社會內部機制發展到充分成熟的一種自然選擇,而是一種飽蘸著血與火的硬性植入,是一段夾雜著民族恥辱感與現代文明發育的雙重歷史”。因此,身在上海的人,一方面在享受著繁華發達的都市建設所給生活帶來的種種便利;一方面又對西方殖民者在屬于自己的領土上肆意妄為的行為感到恥辱和痛恨。民族主義的情懷與殖民主義的陰影相互交織,使得早期中國電影人不自覺地通過影像表達對上海的復雜情感,在展示上海摩登現代化的同時,揭露出深層的敘事意圖,內隱著對這個“造在地獄上的天堂”的批判。
效仿西方城市建設的租界上海,在給西方人帶來相似感的同時,勢必會給中國人帶來了陌生感,中國內蘊的本土文化與西方殖民文化交錯地呈現在租界上海中,容易給人帶來奇異的體驗,李道新先生稱之為“夢幻之城”。“它的由柏油馬路、汽車、洋房、霓虹燈、高鼻梁外國人和時髦侍女拼接而成的‘奇觀化’外表,及其衍生出來的天方夜譚式的生活方式、或美麗或丑陋的人生傳奇以及大喜大悲的急驟的生命體驗,帶給大多數中國人一種前所未有的‘震驚’。”租界上海因給人帶來的這些“震驚”體驗,成為早期電影著意表現的對象。從最早外商拍攝的充滿著獵奇眼光的短片《上海第一輛電車行駛》(1908)、《上海街景》(1908)、《上海南京路》(1901)、《上海租界各處風景》(1909)到中國電影人拍攝的滑稽短片《二百五白相城隍廟》(1913)、《店伙失票》(1913)、《腳踏車闖禍》(1913)、《打城隍》(1913)以及《滑稽大王游華記》(1922)、《擲果緣》(1922)等,無一不給中西方觀眾以“震驚”體驗。與外商對上海都市風景記錄式展覽不同的是,中國早期的這些短片,在滑稽搞笑之外,內蘊著早期電影人對上海都市文化給外鄉人所造成內在壓迫的同情與調侃。從這點來說,短片中看似在展現外鄉人在上海的種種窘迫“奇遇”,卻揭示了身在上海租界區的編導在表達上海都市影像時的復雜心態,是對都市文明戰勝落后鄉村,西方殖民文化壓倒老中國本土文化的影像寓言。
進入到20世紀30年代,隨著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的爆發,中國人民民族主義情緒更加高漲。因租界上海作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心,更加容易成為播撒民族主義精神和抵制殖民主義侵略的陣地。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下,上海都市風貌與市民生活狀態成為這一時期中國電影展示的中心。尤其是左翼知識分子加入到電影中,使得電影更是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租界上海是“窮人的地獄”的一面。如《城市之夜》(1933)、《都會的早晨》(1933)、《上海二十四小時》(1933)、《新女性》(1934)、《神女》(1934)、《漁光曲》(1934)、《生之哀歌》(1935)、《風云兒女》(1935)、《都市風光》(1935)、《新舊上海》(1936)、《十字街頭》(1937)、《馬路天使》(1937)等,均以租界上海為背景,淋漓盡致地展現了生活在城市底層的市民的掙扎與痛苦,影片多采用蒙太奇的交叉對比鏡頭,將窮人的悲慘與富人的不仁呈現出來;采用移動變位的鏡頭,展示摩登都市繁華的背后所掩藏的灰暗逼仄的生活環境,將一個充滿著摩天大樓、光鮮亮麗與霓虹燈不斷閃爍的夜上海與一個陰暗潮濕、充滿著痛苦哀吟與鮮血死亡的夜上海并置呈現在電影中是這類電影慣用的技巧。
這是早期電影人創作這些電影的深層敘事意圖,上海租界的時尚豪華與摩登現代是殖民主義血腥侵略的結果。它的存在強化著民族主義的情緒,成為左翼電影借此表達革命理想與愛國意識的著眼點,也使得影片的敘事遵循的是實現全民族解放的政治邏輯。有學者將其稱之為“敘述政治”,包括所采取的揭示上海“異質性”的都市生活片段的剪輯、敘述結構上的貧富對立的策略等。上海租界文化的時尚摩登、奢靡頹廢以及撲面而來的殖民氣息給電影提供了向民眾宣傳救亡圖存的材料。影片表面上看似在展示都市場域中中國民眾的苦難生活,實質上是在否定西方的殖民主義文化入侵。從這方面來看,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20世紀30年代中國電影多呈現繁華都市掩蓋下的苦難圖景,而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電影多呈現中西雜糅的“歐化”傾向。太平年代,租界文化的殖民性與現代性相交織,讓中國電影人對西式的觀念、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采取矛盾、漠然甚至迎合的曖昧姿態。但在戰時,民族主義情緒被激發出來,讓中國電影人意識到緊跟著殖民勢力而來的繁華是那么面目猙獰,惹人憤恨。必須努力揭示掩藏在其背后的民眾創傷才是中國人的道義與責任所在。所以在左翼電影的敘事話語里,上海這座迥異于母體的半殖民化的現代化大都市必然遭到隱性的批判,租界文化的民族主義與殖民主義就此縫合進主流意識形態之中,成為20世紀30年代中國電影創作的契機。
結 語
中國早期電影創作、放映均離不開租界文化的影響。租界電影院林立,直接刺激了中國電影的生產與發展,吸引了更多的觀眾前來觀影。《姊妹花》“在上海的新光大戲院(公共租界中區)公映時,創造了連映六十余天的票房紀錄”。中國電影能夠勢如炮竹的發展,離不開租界電影院放映平臺的支持。它盡管是外國影片的天下,“卻并不影響中國民族電影業的蓬勃發展。相反,電影院同時在物質和文化上給城市生活帶來了一種習慣——看電影去;而如果沒有這種文化氣候,本土電影業的迅速發展是難以想象的。”
除此之外,租界的物質與文化景觀,如百老匯大廈、銀行大廈、上海郵政大樓、歐式洋房、沙遜飯店、政權交易所、基督教堂、海關大樓等高大的建筑;寬敞平坦的柏油馬路、富有現代氣息的有軌電車、豪華汽車等交通工具以及閃爍不定的霓虹燈、變化絢麗的廣告牌、瘋狂冒險的跑馬場、富有小資情調的咖啡廳、舞廳等都成為中國早期電影聚焦取材的對象。用都市的摩登繁華建構著電影的“奇觀化”特征,吸引著不同層次的觀眾前來觀影。在租界文化的都市語境熏染下,早期電影觀眾也逐漸形成,電影所帶來的斑駁陸離的視覺奇觀及摩登時尚的生活習慣、審美趨向對觀眾構成一種潛在的吸引力。他們逐漸從傳統的茶園戲館中走出,走進電影院成為他們在都市中的生活風尚。同時,由于租界的存在也刺激了電影雜志的創辦,1921年中國電影的第一本鉛印的專業電影刊物《影戲雜志》在上海創立。其成立的目的之一,即為“在影劇界替我們中國人爭人格”,表明創刊者的初衷是為了抵制西方電影與文化的侵襲。盡管由于商業利潤的原因,該刊物仍然以報道外國影片為主,但也為后來電影刊物的相繼創辦提供了借鑒作用。總之,租界文化影響著早期電影的風貌格調,為我們解讀中國早期電影提供一種新的研究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