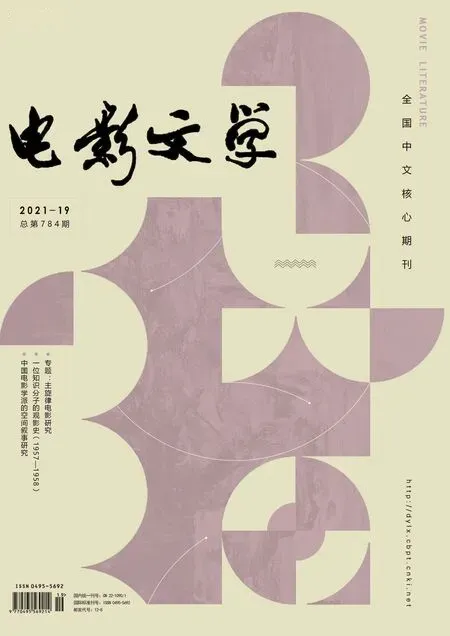話語、符號、認同:主旋律電影創新的邏輯進路
吳星晨(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北京 100024)
法國哲學家特拉西認為,“意識形態”是一種對人的觀念和感知進行系統分析的新學科,被稱為“觀念的科學”。面對各種形式的大眾文化擠壓,主流文化不得不借助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主旋律”這個概念能夠回應當前文化形態。廣義上的主旋律電影,泛指一切以國家意識形態為主導的影片形態。具體到中國,主旋律概念可以追溯到“弘揚主旋律,堅持多元化”口號的提出,也有學者稱其為“紅色電影”。2016年以來,一大批兼具主流意識形態和重工業美學的電影開啟恢宏巨制的模式,推動主旋律概念理解的寬泛化。2021年,在“抗美援朝”“全民抗疫”“建黨百年”三大主題類別下,10余部主旋律電影將先后上映,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多樣化趨勢。總體看來,我國主旋律電影正處于關鍵性的“拐點”,呈現出兩條演進方向:一是形成海峽兩岸導演經驗融合與當紅明星集體參演的形態,基本實現商業化操作;二是從敘事結構、影像藝術、價值訴求都為主流意識形態表達找到相對成熟的運作方式。
一、深度賦能:主旋律電影創新動力及保障
賦能是指個體或者組織對客觀環境與條件擁有更強的控制能力來取代無力感的過程,也就是為誰或某個主體賦予某種能力和力量。“賦能”一詞運用到電影行業,主要是指其如何幫助電影產業實現業務增長,提升管理水平和效率。本文認為,主旋律電影的創新源自技術、文化、政治三個維度的深度賦能。
(一)技術賦能:對電影生產創作模式的改寫
馬化騰在《“互聯網+”:國家戰略行動路線圖》中表示,以互聯網平臺為基礎,利用信息通信技術與行業的跨界融合,推動行業優化、增長、創新、創生。“互聯網+”思維主導下的電影制作,原本具有上下游關系的鏈條式發展方式可能轉化為平臺式的發展,由此帶來的是電影生產各個環節的顛覆與重構。
首先,互聯網技術改寫了電影生產機制。在互聯網語境中,影像、銀幕、觀眾三者的關系徹底改寫,為了掌握話語權,電影工業創作和生產努力尋找新的技術發展路徑。以BAT(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為代表的寡頭企業進軍電影行業,阿里影業、博納影業擁有內容制作、綜合運營的全產業鏈條,在電影票房市場上十分搶眼。在3D、4D、AR、VR、CGI、5G等技術推動下,網絡化、數字化的思維模式已經滲透到電影藝術和技術創新的過程。
其次,互聯網技術豐富了電影營銷模式。除了傳統的海報、預告片宣傳,發行方可以借助微博、微信、抖音等多媒體平臺,制造熱議話題。同時依靠大數據支持,發行方迅速鎖定目標受眾,及時調整宣發策略;基于預售量、用戶關注度、網絡售票等形成對院線的排片建議和對發行方的營銷建議。同時,互聯網雙向互動的特點能夠打破行業壁壘,不同媒介、品牌、產業與電影之間的整合營銷可以產生巨大的協同效應。
再次,互聯網技術改變了電影的觀看模式。縣級影院建設與互聯網購票的興起,“小鎮青年”成為電影票房的重要增量。主旋律電影在迎合青年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方面,有了明顯改進。另外,彈幕影廳、點播影院等新型服務形式的出現,滿足受眾的差異化、個性化需求。
(二)文化賦能:消費文化語境下的主流價值呈現
新世紀以來,中國進入一個物質極度豐富的時代,消費引導生產成為控制社會經濟發展的內在驅動力。當以往電影類型無法滿足市場需求時,電影新類型或重組的形式就會及時補位,這是時代變化與審美消費轉變的產物。在消費文化語境下,主旋律電影重視“視覺特效”“票房價值”,成為極具視覺誘惑力的文化產品。
主旋律電影創新與電影產業轉型相伴相生。2000年開始,國有電影企業集團化改組,民營電影公司、影視制作公司開始介入電影生產,中國電影在投融資方面為電影市場注入新的活力。中影集團和一眾民營企業通過投資多元化、產業鏈延伸的方式推出符合市場規律的主旋律影片。中國電影逐漸觸摸國際脈搏,海外投資遍及能源、農場、戰略性基礎設施等領域,為電影工業奠定了現實基礎。2003年,中國全面走上電影產業化實踐的道路,電影產業形成多門類發展的鏈條經營模式,重視商業元素開發,國產電影票房壓倒海外電影,主旋律電影生產開始具備良好的產業環境。
資本因素是主旋律電影創新的“內在驅動力”。主旋律電影與金融行業互動緊密,“高投入、高收益”的資本特質得到廣泛關注。眾籌、保底發行、票補等系列金融工具與電影產業聯姻,最終指向的是資本對生產、發行和消費的控制。主旋律電影嘗試制片人中心制,在價值表達中加入愛情、懸疑、武打、災難等類型元素,制造電影事件,開展營銷宣傳。但也存在對IP電影、粉絲電影等社會資本的無理性開發問題。
電影工業美學為主旋律電影提供理論護航。新世紀以來,香港影人北上內陸,香港電影的商業精神、娛樂化敘事逐漸加入主旋律電影中。中國電影從業人員直接接觸國際市場競爭所必需的產業鏈條、技術標準、營銷推廣,同時涌現出一批“新力量”導演,他們在電影觀念和實踐上遵循電影工業美學原則:保持電影工業生產特性與藝術審美特性的平衡,追求電影美學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統一。在理論推動下,中國電影的產業和美學不斷形成新的標準,進而推動主旋律電影的可持續發展。
(三)政治賦能:主旋律電影發展的國家調控
作為政治話語介入電影藝術的產物,主旋律電影擁有優越的政治資本,在題材審批、資金投入、拍攝制作、排片發行和宣傳評獎等諸方面都會享受到政府政策的傾斜。
在政策扶持方面,主旋律電影的發展,源自其對市場的絕對控制。中國電影集團作為廣電總局、電影局推動電影發展的重要機構,事實上對進出口影片形成壟斷優勢,并能優先獲得國家和政府的資金支持。中宣部組織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中國電影金雞獎、百花獎和華表獎,在評選中更多地向主旋律電影傾斜。在政府保護、進口配額和對外國電影限制的綜合作用下,主旋律電影生產一度占據行業中心位置。為了彌補主旋律電影競爭力的下降,中國政府將補貼作為最主要的政策手段。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國家設立“國家電影事業發展專項資金”,廣電部、財政部建立攝制重大題材故事片的資助資金,這些補貼至今仍在使用。政府又推出了“9550計劃”,通過財政資助,鼓勵每年生產10部主旋律電影。從2002年開始,中國政府決定改革其補貼政策,從各種票房收入中獲得的官方補貼以獎金的形式提供給電影放映行業。
在題材審批方面,電影行政部門擬定百部主旋律電影選題,努力將中國夢的價值觀念、價值體驗和價值追求與中國道路、中國力量、中國精神相結合。另外,我國先后迎來改革開放40年、新中國成立70年、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等重要紀念活動,獻禮大片可以調動包括演員、制作力量、設備器材在內的各種壟斷性資源,并在制作、宣傳、排片發行環節一路綠燈。政府在傳統媒體上對主旋律影片進行正面、重點和反復的宣傳,號召各級組織組織觀看學習,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還選出“人民院線”簽約影廳,作為主旋律電影的放映陣地。
二、話語建構:歷史與觀眾對話的接口
威廉·A.哈維蘭認為,“所有的人都講故事,在故事中,他們表達自己的價值、關懷和希望,并且在講故事的過程中,他們還揭示關于他們自身,以及關于他們眼中的世界性質的各個方面”。近年來,主旋律電影經過市場檢驗,逐漸形成一種投資收益相對合理、制作流程比較規范的講故事模式。
(一)底層敘事
底層指的是在社會化轉型中被拋出正常社會結構的群體,他們遠離政治中心,文化和收入水平都比較低。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層結構中,作為總體性約束的“道”——意識形態要求文學藝術為“道”而服務。近年來主旋律電影不斷消解傳統的宏大敘事,通過底層敘事對準底層人物的生存現狀和生活實踐,注重對傳統道德體系的書寫。在二元對立的敘事結構中,營造農民工、出租車司機、被拐兒童、孤寡病殘人士、退伍軍人等底層人物的苦難經歷,他們通過一系列努力完成自我救贖,具有典型的示范效應。另外,底層敘事通過人物的命運指向對社會保障制度、救助制度、醫療制度等問題的詰問和反思,既能保證敘事的合理性,又容易引起觀眾的認可。
主旋律電影的底層敘事表達,常見策略是從人物的“小我”到集體的“大我”。“大我”是現有制度的社會秩序和準則,除了傳統的道德體系,還將個人價值觀念納入言說體系。在主旋律電影創新表達中,首先是對“大我”——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強調,有著鮮明的意識形態導向;其次是對“小我”的表達,通過“家國”式的意象符號,最終在“大我”的統攝下,將“小我”與“大我”巧妙聯系,完成對國家、民族命運的觀照。
(二)形式跨界和類型彌合
隨著電影產業化和院線制改革,主旋律電影中的人文關懷不斷凸顯,注重縫合意識形態與消費文化之間的距離。主旋律電影通過糅合動作、戰爭、情感、科幻等類型電影的美學特征實現形式跨界。
獻禮片是主旋律電影中最成熟的類型。2019年國慶獻禮片《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攀登者》落筆于歷史轉折之處的普通人生活。2021年《懸崖之上》的熱映,打造群像式人物形象,將奇觀的冒險、跌宕的劇情、宏大的獻禮都框定在獻禮語境中。當前獻禮片創作已經進入成熟期,在傳遞主流價值觀的同時,表達時代和人文的復雜性及個體的命運走向。
軍事題材電影是近年來主旋律電影的創新選擇。《戰狼》系列、《紅海行動》《湄公河行動》通過現代技術復原戰爭場景,并不是為了再現戰爭的殘酷,而是重點表達英雄主義、革命精神,以及對戰爭的反思、人性的追問。該類型在題材選定、概念選擇、營銷方式上都體現成熟的工業化思維。在表現視角上,宏觀視角強調動作場面的史詩風格,用全知視角呈現事件過程,微觀視角塑造復雜且具有個性的英雄形象。
科幻電影處于弱勢短板的地位。科幻電影的想象偏重宏大題材,如外星文明、生態危機、浩瀚宇宙等,在抽離現實的敘事中提出宏大問題,從而尋求解決問題的可能性。電影《流浪地球》展現出與好萊塢電影媲美的制作水準,在表現科技和未來想象的同時,將傳統倫理與現代人文精神相結合,整個敘事框架相對開放。可以說,《流浪地球》是對主旋律電影價值表達的突破。
三、符號建構:影像表達的編碼與解碼
社會符號學認為,人們能夠體驗外部世界,并將其揭示為符號系統。通過對主流意識形態的順應,主旋律電影逐步形成自己的獨立話語權,通過人物塑造、奇幻化場景、媒介儀式等視聽手段,把歷史記憶、國家認同等較為復雜的問題編碼成簡潔的話語體系。
(一)人物塑造:中國式英雄
主旋律電影塑造的英雄形象實現了從精神內涵到敘述手段的轉型。緝毒警察、特種兵、飛行員、突擊隊、攀登隊員等人物形象,團結協作,剛毅冷靜,臨危不懼,與正在崛起的大國形象契合。但是不完美的人物與世俗融為一體,才能接近觀眾的心理。如《戰狼》中冷鋒因為違反紀律被開除軍籍,《八佰》中老鐵是個貪生怕死的“瓜慫”,《懸崖之上》中張憲臣因為孩子錯失逃離抓捕的機會,頗具生活色彩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國家意志代言者的身份,賦予其“人”的屬性。
從性別角度看,民族國家是男性政治的產物。主旋律電影在人物塑造中,仍然按照男/陽剛、女/陰柔的二元對立模式。國家間的沖突、意識形態斗爭、祖國現代性發展,都屬于男性陽剛的想象與實踐。具體看來,無論是陽剛的特種兵、軍人、警察,還是專業性極強的登山者、運動員、科學家、飛行員,他們自身的形象與國家形象建構同質同構。而女性形象通常表現姣好的容貌、溫柔的氣質,這些都成為消費符號的表征。
(二)奇幻化場景
借助現代化高精尖技術將影片主旨與視覺奇觀融合打造,成為電影獲取畫面的一種手段。主旋律電影雇用頂級的特效團隊,按照好萊塢商業大片形式來打造奇幻化場景。《中國機長》在中國首創“三艙聯動”和“平板控制飛機”技術嘗試;《戰狼》創造“水下打斗”“坦克大戰”“無人機作戰”等軍事戰斗場面;《流浪地球》大量運用數字繪景技術、三維技術、空間場景造型,特效鏡頭達2000多個;《八佰》運用AI技術,還原真實的淞滬會戰戰場。
主旋律電影具有鮮明的時代印記,但對于當今電影受眾而言,很容易呈現一種與時代脫節的懸置。就環境拍攝而言,用大量特殊鏡頭能夠為影片敘事做鋪墊。《紅海行動》中利用慢鏡頭特寫,描繪子彈直穿敵方腦袋的畫面,這種現實中無法被識別的運動軌跡,帶給觀眾更為直接的真實感及現場感;《攀登者》用大量航拍鏡頭、特寫鏡頭表現珠峰的險峻和環境的艱苦;《我和我的祖國》采取了大量的平視鏡頭和仰視鏡頭,拍攝普通人的生活場景,展現人物細膩溫情的畫面。《八佰》用極具隱喻的鏡頭語言,表現對戰爭的恐懼,《懸崖之上》拍攝主人公跳傘的主觀鏡頭,塑造影片開場的視聽氛圍,凸顯人物的悲觀。
奇觀化場景還表現在流量明星的加盟,是主旋律電影工業化的市場嘗試。在軍事題材電影中,起用張涵予、吳京、彭于晏、張譯、杜江等男性演員,用其硬漢形象凸顯軍事動作氣質;《懸崖之上》由張譯、秦海璐、劉浩存、朱亞文組成共產黨特工組核心成員;《八佰》由王千源、黃志忠、歐豪、杜淳等演繹抗戰官兵;《中國機長》打造張涵予、杜江、歐豪的飛行機組和美女乘務員團體;《我和我的祖國》《我和我的家鄉》通過故事單元的形式集結數十位導演和明星。符號化、偶像化的演繹陣容,從根本上適應了“眼球經濟”的市場邏輯傾向。
(三)媒介儀式建構
柯爾迪認為媒介儀式的類型包括媒介報道的儀式性內容,媒介報道該內容的儀式化方式,以及媒介本身成為一種儀式或集體慶典。主旋律電影作為一種儀式傳播媒介,意義在于建構并維系現有秩序,能夠用來支配和容納人類行為的文化世界。《我和我的祖國》中升旗儀式、奧運會開幕式、國慶閱兵式表演、“國旗、國歌、國徽”等“工具性符號”,《戰狼2》中“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的口號及中國護照、茅臺酒,《攀登者》中帶有中國字樣的登山隊服、方五洲倒酒祭奠死在珠峰的攀登者,《八佰》中不應該出現在倉庫的國旗、藏身在地窖的白馬、層層疊疊的血肉之軀,《懸崖之上》慘白的雪景,這些影視形象植根于中華民族的歷史和文化熏陶,具有權威展示、凝聚社會、重申合法化的政治功能。另外,儒家文化,中國武術,中國特色的音樂、色彩、語言等元素的運用,貼近民眾日常生活實踐,是主旋律電影對“中國夢”的全新闡釋。
四、制造認同:集體記憶與自我想象
(一)把國家引入家園——制造共同想象
本尼迪克特·安德烈認為,現代的民族國家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是為了適應世俗社會的現代性發展而人為構建的產物。主旋律電影用民族國家創造一個中國人共同的家園世界,為主人公的愛國行為尋找動機,從而合理完成家園意識構建。另外,個體價值與民族價值在主旋律電影中表現為一體同構的關系。以往主旋律電影中國家利益、集體利益總是高于個人利益,這種敘事方式缺乏合理性基礎,難以獲得觀眾情感認同。近年來,主旋律電影重構國家與個人的關系,將個人與國家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體現了對生命的平等和尊重。登山隊員登頂珠穆朗瑪峰、中國女排在國際賽場的勝利、執行表演的女飛行員順利完成閱兵任務、國旗按時升起、特工取得最終勝利等情節設置,個人價值的實現與國家價值是高度吻合的。通過電影中個體生命的對抗與較量,隱喻了國家、民族之間的對抗與較量,從而喚醒觀眾的民族認同感。
主旋律電影借鑒類型片的敘事方法,嘗試宏觀敘事和微觀敘述的自由轉換。這種敘事策略不僅呈現時代風貌,更是將目光投向了時代人物和思潮。在戲劇沖突的矛盾敘事中,展開對主流價值觀的建構與宣揚。《戰狼2》中以男女主人公情感關系破題,用殺害龍小云的特殊子彈構筑復仇線,避免人物崇高感的動機設置;《流浪地球》再現生態破碎后的末日圖景,在科幻的外衣下表達對生態保護的推崇及人文價值的接續;《我和我的祖國》《我和我的家鄉》采用綴合式團塊敘事,在社會淺層敘事中深挖普通人的情感力量。主旋律電影中通過生動的故事講述,使主流價值觀脫離生硬的政治藩籬,達到從個人到家庭、社會到集體的情感同構與共鳴。
(二)生產集體記憶
法國哲學家哈布瓦赫認為,記憶是社會的,是我們和某些群體和團體所共同擁有的。主旋律電影運用故事敘述和媒體修辭來再現或生產集體記憶,將虛構的故事融入真實的場面刻畫中,使特定民族記憶被喚醒,形成集體的關于國家民族的認同意識。在整個國家民族框架中,主旋律電影以真實事件為藍本,成為現實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湄公河行動》取材于湄公河慘案,《中國機長》取材于川航3U8633航班緊急迫降事件,《戰狼2》以中國在也門等地發生戰亂時的撤僑行動為原型,《懸崖之上》取材于臭名昭著的人體實驗,不僅將電影背后的文化寓意及時呈現,而且成功地宣揚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在大眾文化的參與下,主旋律電影巧妙“去嚴肅化”,進行懸念化、情感化的藝術加工。在故事安排上,通過激烈的打斗、主人公的內心沖突,營造緊張的故事節奏,觀眾在強戲劇沖突下,完成對影片內核的接受。將戲劇化的敘事方式融入宏大的歷史題材中,試圖以人物的個性塑造來推動和展現歷史,還原歷史中的社會現象和社會結構。特別是利用“最后時限”的方式制造懸念,主人公分秒差錯就會導致生死殊途,具有心理驚悚片的色彩,隱約透露出對懸疑因素的大膽運用。
(三)建立“共同體美學”
技術無法解決傳播的單向度問題,唯有立足共同體之上,才能錨定所有觀眾的觀影需求。共同體美學來自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傳統、審美傾向、價值觀念,追求的是創作者與受眾對于電影藝術、美學表達的認同感。該理論汲取了古今中外關于共同體的合理解說,超越其他民族、宗教、文化的構想,為主旋律電影創新轉型貢獻了深刻的倫理智慧。
在以往電影創作觀念中,觀眾被定義為被動接受的客體。事實上,觀眾在觀影行為中始終發揮主體性意識,這就要求創作者的妥協。命運共同體對全人類的共同愿望和共同利益的尊重,使得主旋律電影在講述中國故事的同時,不僅用大眾欣賞的審美形式,而且要展現有利于構建全人類共同精神和價值的文化。如《流浪地球》并非傳統好萊塢式的“逃離地球”設想,而是在災難面前不同物種、種族間的價值觀如何協調統一。創作者通過與觀眾建立對話空間,雙方良性互動,建立一種基于“共情、共鳴、共振”的共同體美學。當共同體美學建立時,可以彌補官方文化與大眾文化的鴻溝,實現意識形態傳播效用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