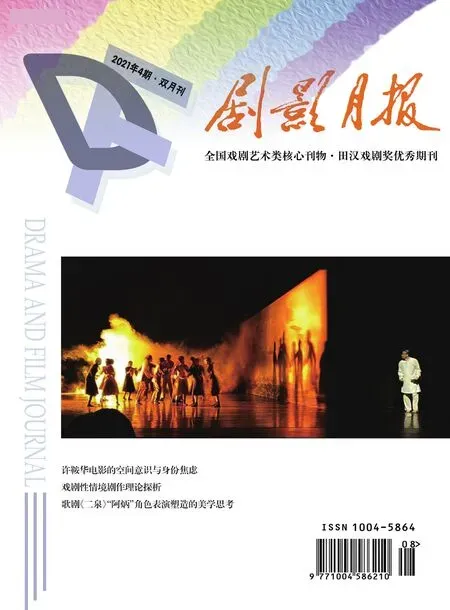心意昭昭云開(kāi)月明
——談京劇《梅蘭芳·蓄須記》
■韓露
江蘇省演藝集團(tuán)京劇院原創(chuàng)新編現(xiàn)代京劇《梅蘭芳·蓄須記》(下文稱《蓄須記》),由泰州市委宣傳部與江蘇省演藝集團(tuán)聯(lián)合出品。泰州是京劇藝術(shù)大師梅蘭芳先生的故鄉(xiāng),《蓄須記》從1956 年梅蘭芳回鄉(xiāng)祭祖演出這一歷史時(shí)刻開(kāi)端,以家鄉(xiāng)人民的盛情歡迎表現(xiàn)梅蘭芳藝術(shù)超越時(shí)空的巨大魅力,又由這飽含深情的返鄉(xiāng)時(shí)刻回溯抗戰(zhàn)期間梅蘭芳告別舞臺(tái)、蓄須明志的抗?fàn)幨论E。可以說(shuō),這部作品的創(chuàng)排,緣起于泰州人民對(duì)梅蘭芳先生的情感,也是當(dāng)代京劇人向梅蘭芳大師的堅(jiān)守進(jìn)行致敬,高揚(yáng)著中國(guó)藝術(shù)家的民族氣節(jié)與文化擔(dān)當(dāng)。
《蓄須記》全劇一共設(shè)置了三重時(shí)空,三個(gè)時(shí)空中的梅蘭芳都面臨一個(gè)問(wèn)題——要不要為日本人演出。第一重時(shí)空以開(kāi)頭《楔子》與結(jié)尾《余韻》串聯(lián)1956 年返鄉(xiāng)經(jīng)過(guò),梅蘭芳回泰州祭祖演出,不僅受到家鄉(xiāng)人民的熱切歡迎,還接到第三次赴日演出的邀請(qǐng)。第二重時(shí)空是舞臺(tái)主體部分,時(shí)間線索從1941 年展開(kāi),通過(guò)《拒票》《拒演》《寫(xiě)畫(huà)》《讀本》四折戲表現(xiàn)梅蘭芳拒絕為日本人演出、堅(jiān)守民族氣節(jié)的事跡。而在第二重時(shí)空之中,日本人對(duì)于梅蘭芳影響力的追逐,又追溯至1919 年的東京,這是梅蘭芳首次赴日演出現(xiàn)場(chǎng),也是戲里的第三重時(shí)空。不同時(shí)空里梅蘭芳做出了不同的選擇,藝術(shù)的影響可以跨越國(guó)界,但藝術(shù)家有自己的祖國(guó),不同的選擇令人看到藝術(shù)與國(guó)家命運(yùn)的關(guān)聯(lián),也讓人感受到一個(gè)偉大藝術(shù)家的坦蕩、赤誠(chéng)襟懷。
抗戰(zhàn)時(shí)期梅蘭芳拒絕為日本人演出,本就是廣為人知的歷史,但京劇藝術(shù)擅長(zhǎng)在眾人皆知的故事中捕捉最動(dòng)人的情感,通過(guò)場(chǎng)上演繹引起臺(tái)下更廣泛的共鳴。從《拒票》到《拒演》,戲中梅蘭芳同家人一起從香港回到了上海,這一次回程最初是梅蘭芳滿心期待的,為躲避戰(zhàn)禍他四處謀求船票而不得;但當(dāng)日本人中島豐也送來(lái)船票,送票的同時(shí)要求梅蘭芳登臺(tái)作“慶賀”演出,這珍貴的船票被梅蘭芳拒絕了。拒絕船票而不被接受,再出場(chǎng)就是上海“梅華詩(shī)屋”中高燒的梅蘭芳,他以《抗金兵》的鼓點(diǎn)來(lái)舒張一種民族立場(chǎng),他為拒絕演出而給自己注射“傷寒防疫針”。從家人的安定到自身的健康,梅蘭芳接連拒絕的代價(jià)在戲曲化演繹中變得清晰可感,日本侵略者從利誘到威逼的的嘴臉也愈發(fā)外露。這樣的兩次拒絕而不被日本人接受,便是全劇題旨高點(diǎn)——蓄須明志的先聲了。
要蓄須,戲里先表現(xiàn)的是剃須,這正合京劇的起伏跌宕韻律。高燒不退令戲中的梅蘭芳形容憔悴,盡管日本人的催逼威脅的壓力還在,但作為一位表演藝術(shù)家,梅蘭芳對(duì)于自身容顏的珍視是自然而然的,《拒演》之中就有了一次對(duì)鏡剃須。舞臺(tái)在這里降下一道鏡框,想象的鏡子因演員的表演而顯形。梅蘭芳對(duì)鏡自照,看見(jiàn)他自己的面容,更看見(jiàn)他所眷戀著的、由他演繹的戲中人——“這是楊娘娘、虞美人、柳迎春、趙艷容、王寶釧、韓玉娘!”粉墨琳瑯癡望定,唏噓無(wú)限妝不成,到這里能看到作為藝術(shù)家的梅蘭芳形象,身懷絕藝卻要遠(yuǎn)離舞臺(tái),這種煎熬的感覺(jué),對(duì)于他而言,比注射“傷寒防疫針”來(lái)得更加劇烈。因此,這一次對(duì)鏡也正是梅蘭芳同內(nèi)心的對(duì)話。此時(shí)的梅蘭芳,越是仔細(xì)剃須,之后將要選擇的蓄須,對(duì)他而言,則越艱難和重大。
不能登臺(tái)的梅蘭芳,是否還是梅蘭芳?這是戲中的梅蘭芳承受的最為痛苦的心理壓力,也是這一次以須生應(yīng)工表現(xiàn)梅蘭芳形象的可能性所在。《蓄須記》中的梅蘭芳,正處于離舞臺(tái)最遠(yuǎn)的一段時(shí)期,主演傅希如在合理借鑒青衣花旦的氣質(zhì)與表演程式后,以京劇須生的堅(jiān)毅同生活化的、不登臺(tái)的梅蘭芳形象實(shí)現(xiàn)了有機(jī)鏈接。這是一個(gè)文質(zhì)彬彬、意志堅(jiān)定、對(duì)舞臺(tái)充滿熱愛(ài)與眷戀的梅蘭芳。而與之對(duì)峙、對(duì)話的中島豐也,則在唱腔與形體上大膽融入和風(fēng),民族立場(chǎng)、文化特質(zhì)由舞臺(tái)上最直接也最本質(zhì)的唱念來(lái)傳達(dá)了。
梅蘭芳的堅(jiān)定拒絕似乎換來(lái)了日方的退讓,從要求梅蘭芳演出變?yōu)橐笏饕淮喂_(kāi)亮相——要他到劇場(chǎng)觀看演出。緊繃的戲劇情勢(shì)到此得到一點(diǎn)松動(dòng),場(chǎng)上進(jìn)入了一個(gè)寧?kù)o的氛圍,這是《寫(xiě)畫(huà)》,不能上場(chǎng)演出的梅蘭芳在作畫(huà)貼補(bǔ)家用。中島豐也再一次來(lái)到梅家,梅蘭芳淡然作畫(huà),回顧昔年赴日演出時(shí)與中島父親之間有過(guò)的藝術(shù)往來(lái)。在這里,中島豐也的形象也出現(xiàn)了變化,此時(shí)場(chǎng)上不單只是梅蘭芳與日本文化侵略的代表者,還有國(guó)家立場(chǎng)之外的文化身份:梅蘭芳是偉大的藝術(shù)家,中島豐也則是被梅蘭芳藝術(shù)感召的后繼者。他在梅蘭芳面前清唱梅派代表作《貴妃醉酒》,不僅表達(dá)自己對(duì)梅蘭芳藝術(shù)的狂熱,更為梅蘭芳在藝術(shù)成熟時(shí)期卻遠(yuǎn)離舞臺(tái)而表示真誠(chéng)的惋惜。這一場(chǎng)戲中,文化后繼者的真誠(chéng)惋惜比文化侵略者的強(qiáng)勢(shì)壓迫,更能撼動(dòng)藝術(shù)家梅蘭芳。但戲中的梅蘭芳向人昭示了一個(gè)更堅(jiān)定也更博大、絢爛的京劇世界——“紙上無(wú)風(fēng)能自舞,悄然水墨奏琵琶,”梅蘭芳從未遠(yuǎn)離過(guò)京劇,從未離開(kāi)他的戲。
掌上何須千變幻,
精妙萬(wàn)般方寸間。
我心自舞虞姬劍,
自催自趕桂英鞭。
楊玉環(huán)醉醉懨懨本空盞,
陳妙常羞羞楚楚按虛弦。
休言嫦娥棄水袖,
散花天女在案上旋?
休言西子枯秋水,
顧盼的洛神使人憐。
休言玉喉生鈍銹,
歌隨筆意瀉珠圓。
休言梅郎不復(fù)見(jiàn)……
這水袖彩鞋、粉黛頭面、西皮二黃、做表唱念,
有哪一月、哪一日、哪一時(shí)、哪一刻離了我,
又哪一刻、哪一時(shí)、哪一日、哪一月不伴著我!
梅蘭芳坐也戲、臥也戲、寫(xiě)也戲、畫(huà)也戲、言也戲、笑也戲,
朝朝暮暮在梨園、在梨園。
——羅周《梅蘭芳·蓄須記》
對(duì)戲里的梅蘭芳而言,這樣的生活沒(méi)有絲竹管弦伴奏,沒(méi)有演出和觀眾;但在舞臺(tái)上,他并不消沉悲傷,這一時(shí)刻涌現(xiàn)出眾多身穿水衣彩鞋的梨園子弟,他們依次上前又緩緩?fù)撕螅袷敲诽m芳的精神世界與京劇追求的一種外化。于是可以理解,筆筆畫(huà)畫(huà)是戲,枝枝葉葉是戲,心心念念的全是戲,梅蘭芳與戲共生共長(zhǎng),屬于他的藝術(shù)生命沒(méi)有終結(jié)。這一份純正博大的藝術(shù)家心懷,同時(shí)映照出侵略者的鄙陋和狹隘,不僅令場(chǎng)上的中島豐也心悅誠(chéng)服,更感染他說(shuō)出了日方的真正意圖——通過(guò)公開(kāi)看戲的契機(jī),大肆宣揚(yáng)梅蘭芳對(duì)日方的“友好”態(tài)度,進(jìn)而動(dòng)搖國(guó)人文化堅(jiān)守的信念,妄圖瓦解中國(guó)人民的抵抗意志。
到這里,梅蘭芳面臨的最大危機(jī)將要到來(lái)了,拒票、拒演之后,無(wú)法拒絕亮相;離開(kāi)舞臺(tái)守著畫(huà)案,也不能回避日方有意安排的接觸。此時(shí)的梅蘭芳更是收到了那個(gè)時(shí)代梨園同行的消息,有拒絕演出而被打罵的,有挺身義演被污蔑投降的,退無(wú)可退,避無(wú)可避,這是《讀本》。戲中梅蘭芳的心是焦灼的,戲的節(jié)奏隨著他的心緒進(jìn)入到最為緊張的時(shí)刻,同樣的,戲也進(jìn)入到最深入角色內(nèi)心的時(shí)候。這一場(chǎng)戲中虛設(shè)了一位老生演員高連魁,在北方義演卻被污蔑為投降偽滿政權(quán),氣憤而死。這個(gè)虛構(gòu)的悲情人物令梅蘭芳無(wú)措的內(nèi)心有了一份具體的寄托,又有了超越個(gè)體悲慨:同儕的命運(yùn)或許是一種預(yù)示,時(shí)代的悲劇與每個(gè)人相關(guān)。因懷念故人而誦讀劇本,高連魁擅演《豫讓橋》,豫讓的故事又啟發(fā)了梅蘭芳。
頃刻間長(zhǎng)夜破空似雷電,
場(chǎng)上人還向場(chǎng)上覓根源。
漆身的豫讓瞞人眼,
伍子胥白頭就過(guò)了昭關(guān)。
貞娥刺虎把公主扮,
還有個(gè)代父從軍的花木蘭、
她著戎裝脫去繡羅衫。
趙艷容佯瘋逃婚、烏云扯亂;
李香君守樓不屈、撞破花顏。
人人皆做姿容變,
個(gè)個(gè)貞亮志節(jié)堅(jiān)。
只為一朝換顏色,
不減風(fēng)流近千年!
梅蘭芳半生繾綣相與伴……
到如今,師故交、法舊友,
心坦坦、意泰然,
要向這戲里戲外正衣冠、正衣冠!
——羅周《梅蘭芳·蓄須記》
被戲成就的梅蘭芳因戲而陷入極困難的境地,解困之道卻也還是從戲中獲得。這是梅蘭芳與戲的交流呼應(yīng),是藝術(shù)與藝術(shù)家的相互拯救,這一次,梅蘭芳不是退避,不是逃離,而是選擇坦然亮相。蓄須改變了藝術(shù)家的面容,卻不會(huì)磨滅他對(duì)藝術(shù)的追求,更袒露著作為中國(guó)藝術(shù)家的坦蕩無(wú)畏心懷。“暢懷儼然添髭須,心意昭昭罷氍毹。守得云開(kāi)月明處,不愧人間偉丈夫。”
新編京劇《蓄須記》在題旨上彰顯了藝術(shù)家的氣節(jié)持守和愛(ài)國(guó)情懷,在舞臺(tái)演繹中以簡(jiǎn)樸大氣的舞美輔助復(fù)雜生動(dòng)角色形象的塑造,在堅(jiān)持京劇優(yōu)良傳統(tǒng)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了跨文化風(fēng)格的融合,是具有開(kāi)拓意義的創(chuàng)造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