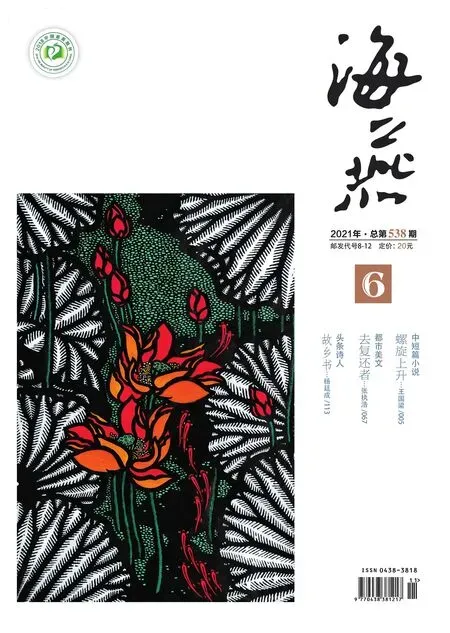河湟谷地,不斷返回的故鄉
——楊廷成詩歌的底色和標志
燎 原
與楊廷成的交往大致上是從上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隨后斷斷續續地一路走到今天,所以一直以來我都覺得對他的詩歌比較熟悉,但當他把近年來的創作全貌展現在我的面前時,還是讓我產生了不小的意外。第一個意外是,這些詩的諸多地理場景,已經溢出了他原先一直所致力的故鄉地理范疇,故鄉的主體場景中,匯入了諸多“遠方月光”的照耀。其次,是他詩歌中的多種色彩信息——包括個人情感信息和藝術審美信息的涌入。這諸多元素的融匯,使得他的詩歌空間明顯地更具張力和彈性,也呈現出一位詩人走向成熟期的開闊與豐富。然而,無論其寫作形態變得如何豐茂,但橫亙在其中的主體,依然是有關故鄉的主題。這是他整個寫作進程中的主脈,也是他詩歌的底色和標志。
對于我們這個農耕文明歷史悠久的民族和傳統農業大國,有關鄉村的書寫,曾是一個經久不衰的詩歌主題。但隨著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開啟,整個詩壇進入了一個以現代主義觀念和技術為王,此起彼伏的潮流性寫作時代,鄉村題材的書寫也日漸式微。當鄉村再次成為被關注的對象,已在不同詩人的筆下,被分解為不同的概念類型和寫作類型。其中最常見的一類,是寄寓鄉愁的書寫。一般而言,這又是一種記憶性的書寫,是把記憶中的鄉村,作為一個純凈精神空間和古老文明的象征,以與喧囂的現代城市壓力相抗衡。另外一個大類,則是時代變遷場景中新聞性的詩歌書寫,這是有關鄉村書寫中一個特殊的中國現象。這一類型的寫作,從上世紀50年代即已開始,此后經過長時間的中斷,到了近年來又重新啟動。介入這一類型的寫作主體,當年主要為定點下鄉、“體驗生活”的專業詩人,近年來則由作協系統組織的下鄉采風團隊來擔當。
兩種不同類型的書寫,給出的是兩個不同的鄉村,在此我們無須探討哪個更為真實,但無論是這一路還是那一路,寫作者在強化這一面的同時過濾掉相反的另一面,就是一個大差不差的事實。此外,這雖然是兩種類型卻又是兩個系統的寫作,但躋身于任何一個系統中的個體,無不表現為寫作的階段性乃至即時性,一俟這一波的心理熱度消退或采風任務完成,便會轉向另外的題材關注。也因此,你在當代詩壇可以列舉出大量的,以長期的寫作積累形成鮮明個人標記的詩人,但以持續的鄉村書寫而著稱者,卻鮮有其人。
從這個角度再來看待楊廷成的寫作,他便成了一個罕見的個案。在他從少年時代開始直至現今的寫作中,鄉村,具體地說,也就是作為其故鄉的青海東部河湟谷地中的鄉村,一直是他詩歌中持續不斷的主題。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看過去,對于當初從鄉村走上這條道路的一位少年詩人,你會產生一定程度的清新感;當他匯入城市人流的多少年后,依舊行走在這條道路上,你既會從其作品中感受到相應的豐富,又會對這種近乎“一根筋”式的行走,產生一種封閉、木然的遲鈍感;然而,當他一直走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其筆下的鄉村物事已匯聚成一個意態繽紛的云空間時,你會突然意識到,他已在不知不覺中,把自己走成了一個“標本”式的存在和現象。
這種“標本”式的存在,既是指他幾十年鄉村寫作形成的龐大體量和系統性,還在于其詩歌內質的純粹。也就是說,他筆下的鄉村,既是一個與他共時性的鮮活存在,又是由不同時段這些鮮活物事所構成的歷時性完整系統。事實上,這也是以上兩種寫作之外的第三種寫作,其與前兩者一個標志性的區別是,鄉村之于他既不是一個消解鄉愁的客體,也不是一種記憶性的存在,而是他出門在外時刻心念相系的家,又不斷回到其中的共時性的現場。
但這樣說又似乎很難使人信服,因為從青年時代開始,他就進入了自己人生的“城市時間”。城市,不但給了他充足的發展空間,也把一個簡單的鄉村子弟,造就成了人生舞臺上不時額頭發光的人物。
對此,我們只能用血液的秘密來解釋。在持續不斷的四十來年間,從當初的鄉村少年直到現今,他的詩歌之所以一直沉迷于相距不到百十公里外的故鄉,這顯然不只關乎“熱愛”,或在“郵票”大的故鄉,下挖一口詩歌深井的策略性考慮,而是關乎本能——由那種鄉村純血所主導的本能。進一步地說,假若我們絕大部分人都帶有這種鄉村的血液,那么這種血液之于他則是控制性的,并賦予了他以根基性的心性特征和文化心理結構。一個特殊的佐證來自我們當年的交往:在通常情況下,他是那種極為真誠友善的人,但卻時而會以智力過剩的鄉間“皮小子”式的“詭詐”,跟你“壞”上一把。這種喜劇性的性格閃電,一直被我視作精彩的鄉村智慧,也是我們長期保持交往而不覺得乏味的重要原因。但也是在這樣的場合,只要幾個人的交談一轉入某個陌生的詩歌話題,他則會立馬支起耳朵,一臉的認真模樣。
一個深刻的記憶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在一次氣氛熱烈的詩歌神聊中,他突然向我提起幾位河北詩人,隨之就背誦起了姚振函的《在平原上吆喝一聲很幸福》:“六月,青紗帳是一種誘惑/這時你走在田間小道上/前邊沒人,后邊也沒人/你不由得就要吆喝一聲/吆喝完了的時候/你才驚異能喊出這么大聲音/有生以來頭一次/有這樣了不起的感覺……”然后感嘆:“姚振函表達的這種感覺真好,每次回到鄉下的老家,我就時常想趁沒人的時候,使勁吆喝上這么一嗓子。”繼而,他又提到了劉小放《我鄉間的妻子》,等等。的確,兩位詩人的這些詩作,當時也出現在我的閱讀中。從某種意義上說,那也是開了當代詩歌中真實還原鄉村生活先河的寫作。但此時我們都沉浸在西部詩歌的潮流中,對此并無更多的驚奇,而當時的楊廷成卻馬上心領神會。此刻想來,他應該也就是從那時開始,看清了他在與我們不同的那條道路上,走下去的依據和目標。是的,對于楊廷成,那一刻的感覺也的確真好——“有生以來頭一次/有這樣了不起的感覺”!
同樣一首詩作,在這個人的心中只能留下泛泛的感覺,在另外一個人那里卻能激起強烈的共鳴,并使之如獲天機,這無疑取決于特殊的個人心理機制。搞清了這一點,你也就不難明白,楊廷成在成就了他的城市與他已經離開了的鄉村之間,看似矛盾的心理取舍。雖然這仍然有些吊詭,但唯有這種吊詭賦予的矛盾與張力,才是詩人的正常心理邏輯。
毫無疑問,城市,作為現代人類居住空間和資源空間的最高文明成果,幾乎對應了現代人類所有的物質欲望和生存想象,并正在對它的人群實施全面同化。在可以想象的未來,對于那些完全生長在城市中的新新人類,鄉村或將只是一個概念。但對于楊廷成,鄉村則是一個大于城市的世界,存在于他血液源頭的一個信息密碼系統。在這個系統內部,首先是他降生的那座村莊,也是村莊內部和周邊世界關系的總和。它文化屬性中的崇尚禁忌、方言習俗、鄉謠民諺、花兒野曲;自然形勝中的山坡谷地、村莊河流、樹林飛禽、寺院廟宇……這一切植入一個人血液中的信息密碼,決定了你一生的心理反應機制類型、價值判斷尺度。決定了你會對什么視而不見,又會對什么做出超乎尋常的敏感反應。
也因此,你就不難理解,當他在城市中一聽到“昨夜西風消息/說河谷里麥田一片金黃”,就何以會涌起莫名的激動,且霎時會回溯到自己的過往——“我曾經也是秋風中/最飽滿的那一株麥穗”“多么想在這個時刻/回到山坳里炊煙四起的村莊”,在夕陽里眼含淚光……
而這片河谷,亦即河湟谷地,則是鄉土中國山坳中一個最小的地理單元。在幾乎已被當代詩歌窮盡了的青海高原,當游牧的高原自西向東一路傾斜而下,而至這片河谷所在的東部農業區,轉換出另外一重天地中的青海時,當代詩歌的追蹤興致卻突然終止——農業區的青海不再屬于詩歌的青海,農耕的山鄉也不再屬于詩和遠方。然而,當楊廷成遙想他的山鄉這樣眼含淚光時,沉默的山鄉隨之影影綽綽:父親那柄不肯生銹的彎鐮整夜里嚓嚓作響,母親在世時向他揮動的手臂炊煙一樣搖晃。再接著,沉默的山鄉隨之五彩繽紛:寺廟“山門下的一叢老杏樹/沉醉于花枝如火的憧憬”;山野中青豌豆的藤蔓手拉著手,“是一群群情深意濃的鄉下姐妹/同享著春日雨絲的喜悅”;“三月,銅嗩吶的聲音震耳欲響/穿一身紅嫁衣的姐姐走出了故鄉”……
這是多少年來,一直縈回在他詩歌中之于故鄉的歡暢基調,但在近年來的詩作中,他此前詩歌中從來不曾出現過的一種元素:夾雜在這歡暢基調中無法稀釋的暮色,卻在字里行間悄然彌漫。彌漫的暮色中,是情不自禁的“回家”意緒:
“傾聽古寺的鐘聲在暮色里響起/遠方的游子踏著夕照夢回故鄉”;
“遠在路上行走的人/夢囈中敘述著遙遠的歸期”;
“老父的酒歌已刻上祖墳的墓碑/親娘的叮囑早就在土地下長眠……//故鄉,我只是趕在夕陽落山之前/流著淚走在回家路上的那個孩子”;
……
這樣的意緒有些感傷,甚至是恓惶,但卻驀然間映現出現代人普遍的精神心理處境,以及糾集在他們心頭的焦慮。被裹挾在一個繁華喧囂、心為物役的現代時空中,他們不時會產生不知身在何處、心在何處的茫然與惶恐。回家,也因之成為一個時代的心靈哲學命題,但對于離開故鄉年深日久的城市子民,故鄉之于他們已是另外一個時空中再也無法融入、無法返回的所在。因此,許多人已不知家在何處,并且無家可歸。
而楊廷成,卻有自己的家、自己的故鄉,也就是可以在內心篤定地宣稱,他是有故鄉的那個人。事實上,他所生活的城市與其故鄉不到百十公里的距離,尤其是他與故鄉之間超乎尋常的血親呼應,已構成了他特殊的心理反應機制和詩歌寫作機制。離開故鄉的時日,使他獲得了一種拉開距離的視角,并在城市生存的反照中,深化自己對于故鄉的心理體認;不斷返回的時日,則使他的心靈處在被不斷激活、持續滋養的良性循環中,也使他得以同步感知歲月遷延中故鄉的變更脈絡,從來不感到陌生。因此,他才一直血脈通暢地既能走出故鄉,又能返回故鄉,并始終與故鄉相互擁有。因此,盡管他關于故鄉的書寫總是伏藏著沉重與疼痛,以及物是人非的滄桑感,但主體基調卻是炫耀式的抒情,在天真式的炫耀中,一個人重返鄉村少年時代的爛漫與歡暢。
而這種天真、炫耀式的抒情格調,從心理原型的角度來看,還有著更深的內涵。楊廷成的那片河湟谷地,又是著名的“河湟花兒”的盛行之地,因此,它所對應的,是一種只有河湟谷地的鄉村時光,才能賦予的歌謠式心理原型。而所有歌謠的本質特征,都是由古老的民間經驗和智慧所滋生的天真,在歷盡了疾苦、看透了萬物后,卻把這一切化解在單純天真的歌唱中,給予沉重的人生以安慰,使沉重的人生在沉重中吐氣,在歡暢中揚眉。
正是基于以上的這一切,楊廷成的詩歌才如同大谷地中的“花兒”一般,在那片靈性的土地上扎下根須、開出花朵、結出果實,并在當代詩歌的鄉村書寫領域,走出了一條獨屬于他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