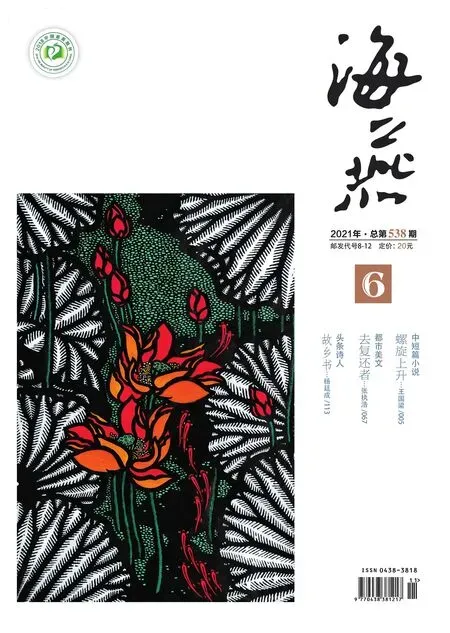西安雪
文 博
一
正月初三早晨,西安的天空,飄下雪花。還未完全醒來的地面上,已有了一層薄薄的積雪。那層積雪披在車轍以外的地方,輕輕柔柔的,如同一襲白紗。每片雪花之間,都留著空隙,松軟地堆疊在一起,有種說不出的柔美和典雅。
我不忍心踩傷腳下的雪,也怕被雪滑倒,在長得像個假小子一樣的年輕女導游的引領下,登上旅行社空蕩蕩的大巴車。女導游等我身后的車門關上后,語調活潑地跟我說:“您第一個登車,就是一號家庭。從現在開始,到今晚旅程結束,為了方便聯系,一號家庭就是我稱呼您的代號。您千萬記住了。”
我一邊點頭,一邊順著過道走到最后一排,坐在靠右邊車窗的座位上。這里既不會被其他游客打擾,又能隨意觀察到每一個人,感覺很不錯。
大巴車啟動了。只行駛了幾分鐘,就接到了二號家庭的三個人。其中一個是身穿淺棕色及膝羽絨服的男人,差不多有五十歲;另一個是三十多歲、皮膚白皙、靦腆羞澀,身穿黑色帶白條紋及膝羽絨服的女人;還有一個十一二歲的男孩,穿了一件跟那個女人一樣的黑色羽絨服,一看就是親子裝。他們都穿著阿迪達斯黑色運動鞋,坐在過道左側司機身后前兩排的座位上。那個男孩靠窗、女人靠過道坐在第一排,男人靠窗坐在第二排。女導游把剛才跟我講過的那番話,又對他們講了一遍。他們一邊聽一邊點頭,男孩還回頭看了我一眼。
在我觀察二號家庭時,大巴車在一個地鐵車站旁,接到了三號家庭。那是一對身高體壯、濃眉大眼的中年夫妻,帶著兩個六七歲左右的雙胞胎小女孩。那個男人戴了一頂稍微嫌小的黑色鴨舌帽,跟兩個小女孩穿著同樣款式的黑色親子冬裝。而那個女人卻穿了一件粉色羽絨服,略顯凌亂的頭發盤在腦后。他們在隔開二號家庭男人身后一排的座位上坐下,兩個大人男人在前、女人在后,都靠著過道,一人橫抱一個小女孩,很快就睡著了。真讓人羨慕。
雪下得似乎比剛才大了些。架在空中的各種電線,讓我想到了火。掛在樹上的大紅燈籠,都被雪花染白了頭,疲憊不堪地在晨風中搖擺,仿佛是已經湮沒在歷史深處的那些古老朝代的縮影。公園里的晨練者,在飛舞的雪花里又蹦又跳,感覺像演戲。行駛在街道的車輛,行走在街道兩旁的行人,都越來越多。
經過一個十字路口后,接到了四號家庭一對疑似夫婦的中年男女。男人高大傲慢,穿一件棕色毛領的黑色大衣,站在車門口把車上的每個人,都拿眼睛挑剔一遍。女人肥白冷漠,穿一件大紅羽絨服,漫不經心地聽女導游重復那番話,連頭都沒點一下。他們徑直走向后面,好像打算坐在我前排的座位上。我連忙裝出感冒癥狀,非常劇烈地咳嗽一氣,感覺大腦都缺氧了。那一男一女厭惡地看著我,躲瘟神一樣毫不掩飾地倒退兩步,選擇了過道右側隔我兩排的座位,女人靠窗、男人靠過道坐下。女人還嘟噥了一聲。應該是說我壞話。但這沒什么。
那個肥白女人的漫不經心,根本沒有影響到女導游。她又在打電話,不厭其煩地強調著一個地點,好像正在安排兩個相距較近的家庭,都到同一個地方候車,那樣會節省時間。在女導游打電話的過程中,司機熟練地拐了幾個彎,又穿過兩條街,接到了兩個家庭。先上車的五號家庭,是兩對神情嚴肅的成年男女和一個戴著白口罩、拿著手機的少女。他們根本沒有向后看。兩對成年男女,都女人靠窗、男人靠過道,占去過道右側座位的頭兩排。而手機少女則靠窗坐在第三排,與四號家庭有一排之隔。跟在五號家庭身后上來的,是六號家庭的三個女孩,看上去像是在校大學生。她們都有一份清純和朝氣,背著雙肩包、穿著牛仔褲和白色羽絨服。她們先往后走了幾步,又猶豫不決地站下,看了四號家庭那對夫婦一眼,回頭坐在二號家庭的男人身旁和身后的座位上。
飄落在車窗外的雪花,像蒲公英一樣上下翻飛。大巴車正經過大雁塔廣場。手持禪杖的唐玄奘,站在大慈恩寺山門前的廣場上,肩頭和腳下都覆蓋著一層圣潔的白雪。我對唐玄奘充滿敬意。他歷盡艱辛求取真經的精神和所求取的真經本身,交相輝映地照亮了東土大唐,在人們的心靈暗處,布了一道柔和的佛光。
在我回望大雁塔的時候,又上來一對中年男女和一雙八九歲的雙胞胎小男孩。車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他們身上。那個身體強健、五十出頭的男人,穿一件深灰佩紅的戶外冬裝,表情莊嚴、目光慈善。女人比他小幾歲,眼睛很大、氣質動人,穿著藕荷色呢質短大衣,像一個熱情的鄰家大姐。兩個英俊的小男孩,都穿著灰色呢料、斜拉索的翻毛領短大衣,戴著時尚活潑、有卡通圖案的頭套護臉帽,毫不拘謹、輕松調皮地走在女人身后、男人身前。他們來到三號家庭后面的兩排座位,兩個大人都挨著過道,女人在前、男人在后坐下來,把一雙不老實的小男孩,分別擋在前后兩個靠窗座位上,配合得非常默契。
大巴車又向前開去。車窗外的古城墻,綿延在飛雪中,被裝飾上各色花燈,如同一支歇息在雪中的秧歌隊。想象著這道古城墻內外,曾出現過的繁華與凋敝,悲歡與離合,戰亂與平安……隨著車身搖晃著,我昏昏沉沉地睡著了。
不知睡了多久,傳來一陣手機鈴聲,驚醒就看見一個年輕女人,坐在我前排的座位上。她優雅的氣質和接聽電話的聲音,都柔美得使我怨氣頓消。這時,年輕女人身旁,靠窗坐著的一個燙了一頭卷發、像洋娃娃一樣的小女孩,回身趴在椅背上,好奇地打量我。我沖她扮了個怪臉。她聲音清脆地開心笑了。而那個年輕女人,面帶歉意地沖我回眸一笑,摟住洋娃娃,讓她重新坐回去。
灰暗的天空,仍然無動于衷地拋撒著雪花。每一個公交站點上,都有許多人等著上車。城市的喧嘩聲,開始像浪潮一樣,一浪一浪地涌動起來。
大巴車在樓房之間轉來轉去,又接到九號家庭的一對母女,坐在四號家庭身后的座位上。那個母親帶著一頂黑白間雜,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八角針織帽。她的女兒總是低頭瀏覽手機,還常常壓低聲音接聽電話,看上去很文靜。
那對母女上車不久,十號家庭的一對五十多歲的夫婦,和我后來得知的他們的女兒、女婿,也上車了。他們不愿意分開坐,別無選擇地走向我身旁的四個座位。我注意到那個年齡大的男人,穿著一身黑色耐克運動裝,腳上那雙黑色運動鞋上的白色耐克商標,特別引人注目。比這更引人注目的,是他的跛腳和一臉羞怯的愧容。我向他遞去友好的目光。他感激地笑了笑,挨著我坐下了,又朝我客氣地點點頭,說了一句:“謝謝大兄弟。”
最后上車的十一號家庭,是三個同樣黑衣黑褲、活躍異常的年輕男子。他們分別坐在四號家庭前面和五號家庭的手機少女旁邊,一落座就開始旁若無人地交談,似乎想引起那三個女大學生的注意。
此時,前排的洋娃娃被年輕女人摟在懷里,睡得很香甜。
二
大巴車駛離城區,經過收費站,行駛上鄉間的原野。公路兩邊都是空曠的黃土地。在黃土地的低洼處,沉積著一片片白雪。女導游向我們做了集體問候,同時要求:昨天只交了定金的游客,在接下來的時間里,需要補交費用,包括用手機完成支付的手續費,也要我們出;還有就是到達漢陽陵以后,需要租用講解器,每個二十元,費用也是我們出;再有就是到達法門寺,為了節省大家的時間,要坐電動觀光車,每位三十元,費用還是我們出。
女導游說完便走到每個家庭跟前,用兩只胖乎乎的手和一個黑著面孔的二維碼,收取現金或手機轉賬。輪到我時,我用手機轉了賬,并表示不需要發票。
女導游回到前面,又舉起一張夾在紅色塑料書寫板上的表格,要求每個家庭按照表格上的序號,填上經她命名的家庭號碼和一個聯系電話,以便在有人走散時,進行聯絡。她把表格遞給五號家庭坐在第一排靠過道的男人。男人填好自己的內容,按照女導游交代的順序,把表格遞給了身后的十一號家庭。表格就這樣從前到后傳到我手中時,我發現在序號4那一欄里,沒有填寫任何文字。而序號4應該由九號家庭那個母親填寫。但她好像填寫了序號5的那一欄,把八號家庭擠到了序號6,使我不得不在序號7和序號4之間來選擇。
對數字的迷信和忌諱,在我看來是件可笑的事。我把我應填寫的內容填進序號4的那一欄,感覺自己又與眾不同了。但我并沒有嘲笑九號家庭那個執筆填表的母親。人生有多少悲苦,就有多少忌諱。趨吉避兇是人之常情。
表格經我身旁的跛腳男人,傳給過道左側的家庭,再傳到女導游手中沒多久,漢陽陵就到了。我最后一個走下車,看見女導游正給大家分發講解器。她教我們如何使用并戴上講解器,去看那些陪葬品。在進入從葬坑之前,女導游把二號家庭的男孩,三號家庭的兩個雙胞胎小女孩,七號家庭的兩個雙胞胎小男孩和八號家庭的洋娃娃,挨個叫到最前面,讓大人們從現在開始,要把方便讓給這些孩子們。三號家庭那個魁梧男人和十號家庭的跛腳男人,也被女導游讓到前面。他們一個是軍人,一個是殘疾人,和孩子們一樣享受優惠優先。
天空不再飄雪。陽光從云朵之間,照射到地面。積雪變得越來越軟,在我們走進帝陵外葬坑展示廳之前,已經開始融化了。由于女導游不建議我們這些活人,跟陪葬品和帝陵合影,沒人耽誤時間,參觀的時間并不太長。一路上也沒什么令人驚異的東西。倒是那六個孩子,剛湊到一起,就嘻嘻哈哈地鬧做一團,甚至把手機少女都帶動過去,跟在他們身前身后,一面玩手機,一面看熱鬧。
準備向下一個景點出發時,幾個孩子的家長們,在車門口和過道上,相互微笑著點頭致意,也有了含蓄得體的互動。大巴車開動以后,我發現五號家庭的手機少女和她身后靠窗坐著的十一號家庭的年輕男子,跟二號家庭的男人身旁和身后,靠過道坐著的六號家庭的兩個女大學生,相互調換了位置。六個分別坐在一起的青年男女,立刻就相見恨晚地交談起來。這輪操作明目張膽,但不費解。
而那個年輕女人在上車以后,把不想和雙胞胎男孩分開的洋娃娃,慢聲細語地商量回座位,給她一粒一粒地剝石榴,哄她慢慢吃。洋娃娃看上去很懂事,不停地抬起小手,把剝好的石榴籽,送到她嘴邊。每當這時,她有著淡淡憂傷和脫俗清純的臉上,便流露出幸福和開心。洋娃娃吃過石榴,躺在她懷里,又睡著了。年輕女人將剩下的半個石榴包好,重新裝進既可背在后面、又可掛在胸前的淺色雙肩包里,把洋娃娃妥帖地托在臂彎,紅潤的面頰貼在洋娃娃臉上,便開始輕輕地搖晃身體。那份專注的柔情,能讓世界安靜、時間靜止下來。
不知不覺間,大巴車開到了唐懿德太子墓博物館。我一直等到十號家庭起身,才跟在他們身后走下大巴車。道路上覆蓋著積雪。人們走過的地方,露出濕淋淋的地面。三號家庭那個軍人、十號家庭的跛腳男人和孩子們,又被女導游集中在隊列前面的入口處。二號、三號、七號、八號家庭的女人們和二號家庭的男人,自動組成一個小團體,緊跟在孩子們身后。五號家庭自成一體,不緊不慢地夾在隊伍中間,竊竊私語地說著什么。十一號和六號家庭的六個青年男女,形影不離地交談得越來越熱乎。四號家庭那對夫婦,經常舉著手機游離在隊伍之外,表情僵硬地相互拍照。我和七號家庭的男人走得比較近,到了隨時可以搭話的地步。九號家庭的母女和十號家庭的其他成員,不由自主地走到一處,不再感覺生分。
博物館里的土闕、石獅、石小人和華表,無不散發著哀傷與凄涼。近七米長的《儀仗出行圖》,無論畫面如何宏大奢華、絢麗精巧,都難以承載一個帝王之父對于兒子的無限哀思,以及一個帝王尚未得勢時的萬般無奈。走在100.8米的斜坡墓道中,我感慨懿德太子即使生在帝王之家,其生命竟也脆弱如斯,其命運竟也不堪作弄,其結局竟也令人如此駭然。
想來人生不僅短暫,還有許多難以把握的轉變,將命運變得吉兇無常。
孩子們的興趣與大人不同,更多集中在墓道的回聲和盜洞上。七號家庭的男人和我一樣,也對盜洞產生了興趣,感嘆退隱在歷史中的摸金校尉們,比鬼魅都難以捉摸。一直到女導游在講解器里發出召喚,我們才相對一笑,被另一伙游客擁擠著,走出墓道,重新回到大巴車上,向乾陵開去。
天上的云層變得更加透明。但陽光還是被云層遮擋在天空,未能直射地面。而路上的積雪,卻早已被過往車輛碾壓得蕩然無存,只剩下灰蒙蒙的瀝青。遠處的積雪,由于變得越來越薄,便不斷有潮濕的土地,破壞了錦緞一樣罩在田野上的白雪,一塊塊地裸露出來,在整個大地上制造出蒼涼的殘破感。
三
女導游怕大家無聊,開始介紹乾縣的蘋果和鍋盔,讓人感到饑餓。大巴車開到乾陵外的一片空地時,我們都饑腸轆轆地下了車。高低不平的水泥地上,到處都是白雪融化后的積水。在一排并不高大的房子前,幾個缺少生氣的小販,無精打采地守在攤位后,沒有一個人主動叫賣,只等游客自己上前。孩子們又高高興興地湊成一團。洋娃娃不知施了什么法術,竟讓兩個可愛的雙胞胎小男孩,一人牽起她一只白嫩的小手,拿她當小公主寵著。七號家庭的大姐和八號家庭的年輕女人,自然而然地走在一起,跟在孩子們身后,并肩走進用餐大廳。三號家庭那對夫妻,正趁機站在路邊抽煙。在我經過時,恰好趕上他們都將煙蒂熄滅在腳下,共同朝我笑了笑,跟在我身后,說笑著走進餐廳。
按照女導游的事先安排,我們被分配在互相挨著的三張餐桌上。我只記得,我和三號、七號、八號家庭,應該同坐中間的那張餐桌。但當我們走到已經有八號、七號家庭和三號家庭的兩個小女孩,圍坐在一起的餐桌前,卻發現有兩個位置,被四號家庭那對夫婦給占去了。他們旁若無人地低著頭,各自翻看著手機里的照片。站在一旁的女導游,發現了問題。她來到四號家庭跟前,請他們回到事先安排好的桌位上。那個肥白女人不耐煩地說:“坐哪不是吃飯呀?”女導游笑著說:“對呀姐!坐哪都是吃飯。您就按事先安排的坐吧。”她指著三號家庭的兩個小女孩說:“小孩吃飯,需要大人照顧。”四號家庭的男人,臉色有些尷尬地起身說:“不好意思。咱們沒想這么多。”他邊說邊拉起肥白女人,按照女導游的指引,走到旁邊已經坐著五號和十號家庭的桌前,重新坐下。
這段插曲沒有演變成爭吵,有些出乎意料。我對四號家庭的男人,開始產生好感。坐下吃飯的時候,我們這桌人,雖然還沒有說話,但卻有了一種同盟般的親近感。七號家庭那個爽快的大姐,啃了幾口鍋盔后,說了一句大家都想說的話:“這個女導游,真能忽悠!這鍋盔又涼又硬,咬一口直掉渣,哪有她說得那么好!”三號家庭那個軍人,聲音洪亮地說:“旅游景點的伙食,都是糊弄人的。好鍋盔我吃過,確實好吃。但這個不行。這不是鍋盔,這是鍋蓋。”年輕女人很含蓄地低頭笑了。兩個雙胞胎小男孩趁機起哄,跟他們的媽媽說:“媽媽,我們還想吃鍋蓋!再給我倆來一塊!”兩個雙胞胎小女孩也叫了起來:“我倆也要吃鍋蓋!再給我倆來一塊!”坐在我旁邊的洋娃娃,唯恐大家注意不到她,用筷子敲著桌子連聲說:“吃鍋蓋!吃鍋蓋!我要吃鍋蓋!”年輕女人連忙按住洋娃娃的筷子,趴在她耳邊告訴她:“這樣不禮貌。”我們左右的另外兩桌,也被孩子們影響了,都開始對鍋盔發表看法。三張桌子之間的氣氛,變得融洽而活躍起來。
午飯后的天空,開始放晴了。天上的云朵,都朝著一個方向飄動。我們走在殘雪化盡的乾陵神道上,覺得兩邊的石人、石獸和石碑,雖然看上去很滄桑,但不再是冷冰冰的了。在二號家庭的男孩帶領下,孩子們都一窩蜂地跑起來,把神道當成了賽道。五號家庭的手機少女也受到感染,將口罩褪到下巴下面,拿著手機追過去,跟八號家庭的年輕女人一道,緊跟著照顧孩子們。追隨在她們身后的,是二號家庭的女人、三號家庭的夫婦和七號家庭的大姐。七號家庭的男人,站在神道邊上打電話,聽上去像是布置工作。而二號家庭的男人,則買了一口袋削好皮的蘋果,挨個遞到我們面前。沒人拒絕這份善意。蘋果很甜、名不虛傳,就是個頭有點小。我有意放慢腳步,跟十號家庭的跛腳男人并肩走到一起。他感激地對我笑了,又無奈自嘲地搖搖頭。十號家庭的其他成員,也都微笑著對我表達友好。六號家庭和十一號家庭的六個青年男女,無所忌諱地男女搭配著站成一排,讓九號家庭的女兒給他們拍照。他們又把九號家庭的女兒拖進來,讓她的母親給他們七個年輕人,拍了一張洋溢著青春朝氣的合影。趕在我們前面的,還是四號家庭那對夫婦。他們的手機始終沒有閑下來,像是把能看見的東西都拍了下來。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個肥白女人,居然對著乾陵主墓,恭恭敬敬地磕了三個頭。走在最后的,是五號家庭的其他成員。他們對眼前的一切并不關注,一直到離開乾陵時,還在什么話題上談論不休。
由乾陵趕往法門寺的時候,車廂里的氣氛更加輕松,除我以外的每個家庭,都在做著互不干擾的輕聲交流。女導游趁機兜售起產自當地的石榴糕和狗頭棗。她告訴我們不必為攜帶不便而擔心,她會把石榴糕和狗頭棗送到酒店,還可以幫我們郵寄回去,意思是大家盡管放心購買。
最先對女導游表示支持的,是二號家庭的男人,他買了四包狗頭棗和六包石榴糕。五號家庭經過商量,只買了兩包狗頭棗。三號家庭很爽快,一樣買了十包,說是要分給鄰居和戰友吃。女導游在六個青年男女面前,遭到了拒絕,他們說還要在外面走幾天,家里也沒人吃零食。七號家庭的大姐,在征求了兩個小男孩的意見后,買了四包狗頭棗和兩包石榴糕。九號家庭的母女先是沒想買,后來改了主意,買了四包石榴糕。到四號家庭的時候,肥白女人的意見占了上風,每樣買了二十包,給女導游留下一個茶樓的地址。八號家庭的年輕女人,微紅著臉說“不想讓孩子吃太多零食”,一樣只買了一包。十號家庭那個跛腳男人,對他的家人小聲說:“這個女導游很辛苦。她剛才在乾陵跟我說,她的孩子已經兩歲了,花錢的地方越來越多。咱們多少買幾包吧。”他們一家人達成了共識,每樣買了兩包。我本來不想買,但怕給別人留下冷漠吝嗇的印象,就用手機向女導游付了四包狗頭棗的錢,并實話實說:“我不喜歡吃零食,特別是甜食。”女導游收完我的錢,才沖我笑一下,走回重新加速行駛的車前,指著前方對我們說:“法門寺到啦!”
我們在山門廣場下車,又分乘兩輛電動觀光車,經過佛光大道,在合十舍利塔前開始步行,穿過一條商街,進入法門寺后,四號家庭那對夫婦和十號家庭的跛腳男人,急匆匆地在真身寶塔前,磕了許多頭。當女導游招呼大家進入地宮時,八號家庭的年輕女人,把洋娃娃交給七號家庭的大姐,自己一個人垂首跪在大雄寶殿內,連地宮都沒進去。我主動走在洋娃娃身后,示意七號家庭的大姐,可以幫她照看洋娃娃。大姐領會了我的熱心,讓我陪著洋娃娃走在她前面。我怕人群擠倒洋娃娃,便征得她同意,把她抱了起來。洋娃娃用手撫弄著我的頭發,顯得很高興。當我們走出地宮時,年輕女人正在地宮出口處等候。我將洋娃娃交給她,順便說:“孩子真可愛!”她感激的微笑和清澈的目光,讓我心生歡喜。
四
踏上歸程時,天空昏暗下來。大巴車單調枯燥地轟鳴著。女導游跟每個家庭核對下車地點時,有種難言的感受,開始在我心里彌漫。其他人準備在哪里下車,我都沒記清,但卻記住了八號家庭的下車地點:永興坊。女導游走到我跟前,問我:“您在什么地方下車?”我問她:“除去大唐不夜城、鐘鼓樓和回民街,晚上還有什么地方值得去?”女導游建議我去永興坊,正好跟八號家庭一道。
奔波了一天的我們,都疲倦地隨車搖晃,半夢半醒地過了好一會兒,在距離機場較近的路邊,感覺大巴車停了下來。十號家庭都站起身,躡手躡腳地通過過道,相互攙扶著走下車門,鉆進一輛等候在路邊的別克商務車。那個跛腳男人在起身的時候,特意跟我握了手。通過過道時,還朝著每個人,都點了一下頭。
過了收費站,城市的燈光,重現眼前。在一個樹上掛滿大紅燈籠的路口,五號家庭下車了。手機少女在下車之前,還兩手扶著過道兩側的椅背,專門走過來,分別摸了摸七號家庭兩個雙胞胎小男孩的臉蛋,對八號家庭熟睡的洋娃娃笑了笑,親了親三號家庭兩個小女孩的額頭,又和二號家庭的男孩,輕輕地揮了揮手。
我的鼻子有些酸,多愁善感的視線,也模糊了。
滿街都是中國結造型的紅燈籠。大巴車在車流中,緩緩地行駛了十幾分鐘,又停在一個寬敞的十字路口。三號家庭在下車之前,那個軍人給大家敬了個軍禮。他讓兩個雙胞胎小女孩朝大家揮揮小手,那個女人留下了一個憨厚的微笑。
車窗外的天空,又飄起了雪花。燈火通明的街市被漸漸密集的雪花,裝點出晶瑩的斑斕。但我已沒有心情欣賞這夜色雪景。已經襲來的離散之情,帶著似曾相識的味道,讓我感到無比惆悵,卻又無法描述它的形狀。
在一條繁華明亮的商業街上,大巴車再次停下來。二號家庭要下車了。那個男孩在他爸爸的示意下,從過道走過來,跟七號家庭的兩個雙胞胎小男孩,幼稚地握了握手,像長大以后的男子漢一樣,鄭重地道別。二號家庭的男人下車之前,沖大家抱了抱拳;女人靦腆羞澀地笑了笑,向我們點了點頭。
又往前行駛沒多遠,六號家庭和十一號家庭的六個青年男女,都站起來跟我們擺擺手,轉身便下了車,很快消失在闌珊的夜色中,給我留下了很多問號。
車窗外的雪,下得越來越大,模糊了街市燈光,加深了我的惆悵。我在這個飄雪的早晨,眼看著一車人,一站站地聚集在一起;又在這個飄雪的晚上,眼看著一車人,一站站地離散在路邊;心里越來越不是滋味,渾身都不舒服。
大巴車開到鐘鼓樓附近時,七號家庭也要下車了。那個男人微笑著跟我們每個人,點頭告別。熱情直爽的鄰家大姐,沒讓八號家庭的年輕女人站起來,怕她驚醒洋娃娃。她讓自己的兩個漂亮小男孩,每人給洋娃娃留下一個手指大的彩色武士俑。我看見年輕女人咬住下嘴唇,眼里有了淚光。鄰家大姐的眼睛也紅了。她倒退著走了幾步,又揮了揮手,才轉身抹了一下眼睛,走下車去。
這一家人的善良和熱情,深深打動了我。
大巴車重新啟動不久,洋娃娃便醒了。她剛接過那兩個彩色武士俑,就瞪著大大的眼睛,發現空蕩蕩的車廂里,少了許多人。她一手攥著一個手指大的武士俑,從過道后面跑到前面,把七號家庭、三號家庭和二號家庭坐過的地方,都看了一遍;又跑到七號家庭坐過的地方,趴在座位下面去尋找;而后撲向那個年輕女人,拉住她的手,突然哭喊起來。年輕女人一邊哄著洋娃娃,一邊抱起她,不知如何是好地走向車門口。大巴車剛好開到了大唐不夜城。九號家庭那對母女,要在這里下車了。女導游也要下車,早已收拾好東西。四號家庭那對夫婦,也都站了起來。洋娃娃拼命地向車門傾斜著身體,不依不饒地哭喊著,非要下車不可,去找雙胞胎哥哥,雙胞胎姐姐,還有那個小哥哥。
眼角掛著淚花的年輕女人和她的洋娃娃,跟隨在其他人后面,走下車門。她在紛飛的雪花中,蹲在地上摟著洋娃娃,顯得很孤單。女導游和九號家庭那對母女,還有四號家庭那對夫婦,分別在洋娃娃跟前彎了彎腰,便各自轉身走遠了。
漫天飛雪在燈火迷離的街市上,將洋娃娃和那個年輕女人,一重重地包裹在中間,離我貼在車窗上的臉,越來越遠。人生如夢、過往成空的無助感,開始讓我懷疑人生。我已無意再去永興坊,便讓司機把車停下,來到飛雪漫天的路邊。
紛紛揚揚的雪花,瞬間便朦朧了我的雙眼,讓我倍感迷茫。它們覆蓋了道路,包括每一條小巷,還有我們的足跡。我在風雪中行走,竟走到大雁塔廣場。站在唐玄奘的塑像下,我看見大唐不夜城燈光迷幻的街市上,如潮水般涌動的茫茫人海,正洶涌澎湃地席卷而來。我茫然地站在風雪中,卻不知何去何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