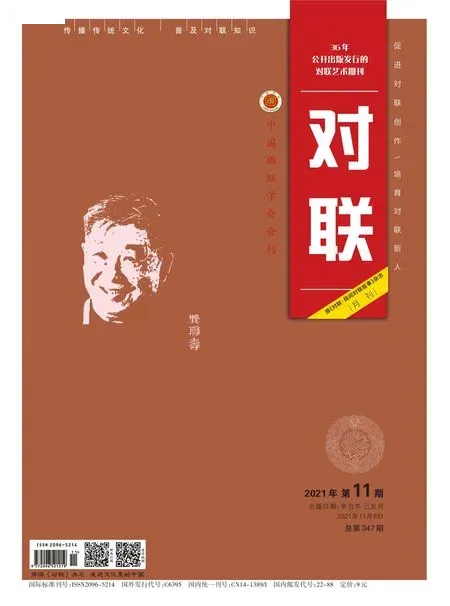論毛澤東對(duì)聯(lián)文化實(shí)踐所體現(xiàn)的辯證思想
文 |魯曉川
綜觀毛澤東一生的對(duì)聯(lián)實(shí)踐可知,有一種思想始終貫穿著,這就是辯證思想。
一方面,對(duì)聯(lián)文化本身是中國古代辯證思想外化形成的成果。另一方面,中國古代辯證思想和馬克思主義辯證思想深刻影響了毛澤東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這不但使毛澤東對(duì)充滿辯證意味的對(duì)聯(lián)文化給予了極大關(guān)注,也使他在對(duì)聯(lián)文化實(shí)踐中將辯證思想進(jìn)行充分的貫徹和發(fā)揮。以下從三個(gè)方面來論述。
(一)文與質(zhì)
文和質(zhì)的關(guān)系,最先是《論語》中提出來的。《論語·雍也》中記載:
子曰:“質(zhì)勝文則野,文勝質(zhì)則史,文質(zhì)彬彬,然后君子。”
《論語·顏淵》中記載:
棘子成曰:“君子質(zhì)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zhì)也,質(zhì)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綜合以上孔子和子貢的論述可知,先秦儒家在討論文質(zhì)關(guān)系時(shí),鮮明地體現(xiàn)了辯證統(tǒng)一的觀點(diǎn)。在中國文化史上,文質(zhì)彬彬逐漸成為一個(gè)要求內(nèi)容和形式辯證統(tǒng)一的標(biāo)準(zhǔn)。對(duì)于這一標(biāo)準(zhǔn),毛澤東進(jìn)行了批判的繼承。在1942年發(fā)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huì)上的講話》中進(jìn)行了富有時(shí)代特色的發(fā)揮:
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和藝術(shù)的統(tǒng)一,內(nèi)容和形式的統(tǒng)一,革命的政治內(nèi)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shù)形式的統(tǒng)一。
在毛澤東的對(duì)聯(lián)實(shí)踐中,也貫徹了這種思想。據(jù)《謝覺哉日記》記載,謝老在1947年9月18日曾“代毛主席挽續(xù)老”。這說的是為著名抗日將領(lǐng)續(xù)范亭作挽聯(lián)的事。謝覺哉的原聯(lián)是:
為民族翻身,為階級(jí)翻身,事業(yè)垂成,公胡遽死;
眼睛亮得很,骨頭硬得很,典型頓失,人盡含悲。
毛澤東將之修改為:
為民族解放,為階級(jí)翻身,事業(yè)垂成,公胡遽死;
有云水襟懷,有松柏氣節(jié),典型頓失,人盡含悲。
對(duì)比可知,毛澤東修改的主要是作品的前面兩個(gè)分句。上聯(lián)中,改“民族翻身”為“民族解放”,主要是從思想內(nèi)涵著眼的,因?yàn)?947年,中華民族正處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關(guān)鍵時(shí)期,這一時(shí)期,中華民族的主要任務(wù),已經(jīng)不只是翻身,更是要實(shí)現(xiàn)解放。而下聯(lián)的修改,則更可見毛澤東對(duì)于對(duì)聯(lián)創(chuàng)作“文”的追求。“有云水襟懷,有松柏氣節(jié)”與“眼睛亮得很,骨頭硬得很”相比,當(dāng)然更具有文學(xué)的美感。而從整體上看,將上下聯(lián)前面兩個(gè)分句由重言變成自對(duì),也更加具有典雅靈動(dòng)之美。由此可見,在對(duì)聯(lián)創(chuàng)作中,毛澤東是文質(zhì)皆重的。
縱觀毛澤東從二十世紀(jì)初到二十世紀(jì)中葉對(duì)聯(lián)創(chuàng)作的歷程,人們會(huì)形成這樣一個(gè)印象:似乎隨著時(shí)間的推進(jìn),毛澤東對(duì)聯(lián)創(chuàng)作日益顯現(xiàn)出重質(zhì)輕文的趨勢。可舉毛澤東一生創(chuàng)作數(shù)量最多、質(zhì)量最高的挽聯(lián)為例。目前能搜集到的毛澤東創(chuàng)作的最早一副挽聯(lián)是1915年挽湖南第一師范同窗易昌陶聯(lián):
胡虜多反復(fù),千里度龍山,腥穢待湔,獨(dú)令我來何濟(jì)世;
生死安足論,百年會(huì)有役,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時(shí)。
到了1928年,其挽戰(zhàn)友王爾琢的聯(lián)為:
一哭同胞,再哭同胞,同胞今已矣,留卻工農(nóng)難承受;
生為階級(jí),死為階級(jí),階級(jí)念如何,得到勝利方始休。
三十年代則有挽黃公略烈士聯(lián):
廣州暴動(dòng)不死,平江暴動(dòng)不死,如今竟?fàn)奚昂薮蟮湉奶旖担?/p>
革命戰(zhàn)爭有功,游擊戰(zhàn)爭有功,畢生何奮勇,好教后世繼君來。
分析比較可知,第一聯(lián)明顯更趨于文言表達(dá),風(fēng)格典雅高古,其中“千里度龍山”“生死安足論”皆是集前人詩句,分別集自南朝鮑照《學(xué)劉公干體》和宋代文天祥《正氣歌》,其風(fēng)格由此可見一斑。筆者對(duì)毛澤東的傳世挽聯(lián)創(chuàng)作進(jìn)行了統(tǒng)計(jì)。二十世紀(jì)第一個(gè)十年中,毛澤東有《挽易昌陶》《挽吳竹圃》《挽七位同學(xué)》《挽某同學(xué)》和《挽慈母二副》等六副。其中《挽吳竹圃》和《挽慈母二副》與上述《挽易昌陶聯(lián)》的風(fēng)格類似,趨于典雅。而《挽七位同學(xué)》和《挽某同學(xué)》則趨于白話表達(dá),風(fēng)格直白爽利。到了二十年代,則有《挽恩師楊昌濟(jì)》《挽學(xué)者易白沙》《挽烈士羅宗翰》《挽戰(zhàn)友王爾琢》等4副。這4副對(duì)聯(lián)風(fēng)格較為一致,上面舉的挽王爾琢聯(lián)即為代表。三十年代,則有《挽黃公略烈士聯(lián)》《挽王銘章將軍》《挽郭朝沛先生》《挽平江慘案烈士二副》《挽楊裕民先生》等6副。四十年代則有《挽蔡元培先生》《挽徐謙先生》《挽張沖先生》《挽葛太夫人》《挽劉志丹同志》《挽鐘太夫人》《挽彭雪楓同志》《挽“四·八”遇難烈士》《挽李公仆、聞一多二先生》《挽劉胡蘭烈士》《挽續(xù)范亭同志》等11副。這兩個(gè)年代中,除了《挽郭朝沛先生》和《挽楊裕民先生》兩副,其余15副都是類似上面舉出的《挽黃公略烈士》的白話為主,風(fēng)格趨于直露的作品。但是否以此就論定毛澤東的對(duì)聯(lián)的越來越不重視“文”呢?這是值得商榷的。關(guān)鍵問題是如何理解“文”。一般人理解的“文”,也許是典雅、蘊(yùn)藉這一類型的語言形式。但毛澤東對(duì)此卻有非同一般的見解。一方面,毛澤東并不排斥典雅、蘊(yùn)藉之文。這可從他對(duì)自己詩歌創(chuàng)作中所舉“較好”的“云橫九派浮黃鶴”可以看出。而另一方面,毛澤東在公開場合所極力提倡的“文”,卻是另一類型,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fēng)和中國氣派。”
也許我們可以這樣概括:毛澤東所肯定的“文”,在個(gè)人化的審美體驗(yàn)中,傾向于詩意化和典雅化;而在公眾化場合中,則傾向于日常化和現(xiàn)代化。
要深刻理解這一點(diǎn),可以從毛澤東對(duì)聯(lián)實(shí)踐中體現(xiàn)的另一對(duì)范疇中得到啟發(fā),這就是接下來要探討的破與立。
(二)破與立
在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huì)上的報(bào)告中,毛澤東曾說:“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gè)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shè)一個(gè)新世界。”這一豪邁的論斷既表現(xiàn)了毛澤東代表的共產(chǎn)黨人作為革命家的氣魄,也表現(xiàn)了其作為建設(shè)者的情懷,正從“破”與“立”的對(duì)立統(tǒng)一中生動(dòng)地展現(xiàn)了毛澤東辯證思想。在對(duì)聯(lián)文化實(shí)踐中,毛澤東也始終貫穿著“破”與“立”的對(duì)立統(tǒng)一。從語體角度而言,主要體現(xiàn)在對(duì)文言和白話兩種語體的辯證處理方面。
語體,又稱言語的體式,它是在語境類型作用下的言語功能變體,在特定語境類型中表現(xiàn)出來的使用語言材料特點(diǎn)的體系。關(guān)于對(duì)聯(lián)創(chuàng)作應(yīng)該用什么語體,毛澤東沒有相關(guān)的論述傳世,但我們可以從他自己的創(chuàng)作中窺見一斑。我們舉毛澤東對(duì)聯(lián)中數(shù)量最多、質(zhì)量最高的的挽聯(lián)來說明。四十年代有挽彭雪楓聯(lián):
二十年艱難事業(yè),即將徹底完成,忍看功績輝煌,英名永垂,一世忠貞,是共產(chǎn)黨人好榜樣;
千萬里破碎河山,正待從頭收拾,孰料血花飛濺,為國犧牲,滿腔悲憤,為中華民族掉英雄。
從語體方面來說,以上三聯(lián)都有較明晰的白話傾向,可見毛澤東要立的,就是白話語體。但立中又有破。在1942年延安干部會(huì)上發(fā)表的《反對(duì)黨八股》的講演中,毛澤東大致梳理了五四以來文化思潮的變化,其中就涉及到了語體的轉(zhuǎn)變:
五四運(yùn)動(dòng)時(shí)期,一班新人物反對(duì)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duì)舊教條,提倡科學(xué)和民主,這些都是很對(duì)的。在那時(shí),這個(gè)運(yùn)動(dòng)是生動(dòng)活潑的,前進(jìn)的,革命的。那時(shí)的統(tǒng)治階級(jí)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學(xué)生,把孔夫子的一套當(dāng)作宗教教條一樣強(qiáng)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但到后來就產(chǎn)生了洋八股、洋教條。……這樣看來,“五四”時(shí)期的生動(dòng)活潑的、前進(jìn)的、革命的、反對(duì)封建主義的老八股、老教條的運(yùn)動(dòng),后來被一些人發(fā)展到了它的反對(duì)方面,產(chǎn)生了新八股、新教條。它們不是生動(dòng)活潑的東西,而是死硬的東西了;不是前進(jìn)的東西,而是后退的東西了;不是革命的東西,而是阻礙革命的東西了。這就是說,洋八股或黨八股,是五四運(yùn)動(dòng)本來性質(zhì)的反動(dòng)。
這里,毛澤東要破掉的,既包括黨八股或洋八股的思維模式,也包括與這種思維模式相關(guān)聯(lián)的死硬的白話語體。
另一方面,對(duì)于傳統(tǒng)的文言語體,毛澤東在對(duì)聯(lián)創(chuàng)作中主要采取破的態(tài)度,但破中也包含著立,即并非一味摒棄文言語體。例如前面提到的挽楊裕民聯(lián),就是白話與文言相結(jié)合而文言成分較多的,至于另一副挽郭沫若之父郭朝沛的對(duì)聯(lián)則更是較典型的文言對(duì)聯(lián):
先生為有道后身,衡門潛隱,克享遐齡,明德通玄趨往古;
哲嗣乃文壇宗匠,戎幕奮飛,共驅(qū)日寇,豐功勒石礪來茲。
之所以產(chǎn)生這樣的現(xiàn)象,主要原因是毛澤東在進(jìn)行對(duì)聯(lián)創(chuàng)作時(shí)特別考慮到了作品的接受對(duì)象和應(yīng)用場所的因素。
破與立的辯證統(tǒng)一,還體現(xiàn)在毛澤東對(duì)聯(lián)實(shí)踐中對(duì)于格律的態(tài)度方面。格律,指一系列中國詩歌和對(duì)聯(lián)獨(dú)有的,在創(chuàng)作時(shí)的格式、音律等方面所應(yīng)遵守的準(zhǔn)則。在對(duì)聯(lián)文體中,格律主要包括平仄和對(duì)仗兩個(gè)方面的要求。根據(jù)吳直雄先生的考察,毛澤東創(chuàng)作的對(duì)聯(lián)中,不拘平仄的作品占總數(shù)的72%。為什么會(huì)出現(xiàn)這種情況呢?這是與毛澤東文化思想中另一對(duì)重要的范疇緊密聯(lián)系的,這一對(duì)范疇就是授與受。下面我們將舉例加以論述。
(三) 授與受
在文化傳播活動(dòng)中包含著兩個(gè)重要的角色,即文化的傳授者和文化的接受者。毛澤東特別重視接受者的地位和作用。謝軍武指出:“從現(xiàn)在見到的材料來看,毛澤東很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個(gè)用‘接受者’這個(gè)詞語的人,比接受美學(xué)的理論家早將近三十年。”⑦ 毛澤東強(qiáng)調(diào)“接受者”的地位和作用,目的是告誡文化傳播者,要明確自己的服務(wù)對(duì)象。必須熟悉、了解服務(wù)對(duì)象,才能提供出為服務(wù)對(duì)象所歡迎的作品。在對(duì)聯(lián)文化實(shí)踐中,毛澤東對(duì)待對(duì)聯(lián)格律的態(tài)度充分貫徹了這一思想。首先,毛澤東對(duì)于對(duì)聯(lián)的格律,包括對(duì)仗和平仄的要求都是熟稔于心的。只要考察一下他早年所作的兩副挽母對(duì)聯(lián)就可明了:
春風(fēng)南岸留暉遠(yuǎn);
秋雨韶山灑淚多。
疾革尚呼兒,無限關(guān)懷,萬端遺恨皆須補(bǔ);
長生新學(xué)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處尋。
兩聯(lián)都可以算是對(duì)仗工整、平仄協(xié)調(diào)的百分之百的符合格律的對(duì)聯(lián)。但在同一時(shí)期為湖南省立第一師范附屬小學(xué)的禮堂題聯(lián)則是:
世界是我們的;
做事要大家來。
此聯(lián)在平仄方面,僅僅符合仄起平收這一條規(guī)則,其余部分平仄基本沒有講究,甚至除了末字以為,上下聯(lián)平仄完全雷同。在對(duì)仗方面,下聯(lián)“做事”與上聯(lián)“世界”完全沒有對(duì)仗,“大家”與“我們”也只能算寬對(duì)。如果以前面兩副挽聯(lián)所遵守的格律來衡量,這副題禮堂聯(lián)是可以被視為“非對(duì)聯(lián)”的。為什么在幾乎同一時(shí)期的對(duì)聯(lián)創(chuàng)作中,對(duì)于格律的守和破有如此兩個(gè)極端的表現(xiàn)呢?筆者認(rèn)為,這并非毛澤東在撰寫禮堂聯(lián)時(shí)無意之失,而恰恰是其有意打破格律束縛的實(shí)踐。為什么要打破格律束縛呢?一個(gè)方面,這是毛澤東在五四新文化思潮影響下有意識(shí)打破傳統(tǒng)的實(shí)踐。毛澤東在與斯諾交談時(shí)曾經(jīng)回憶道:“《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雜志,由陳獨(dú)秀主編,當(dāng)時(shí)我在師范學(xué)校做學(xué)生的時(shí)候,我就開始讀這一本雜志,我特別愛好胡適、陳獨(dú)秀的文章……一時(shí)成了我的模范。”可見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對(duì)于青年毛澤東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而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經(jīng)典文章胡適的《文學(xué)改良芻議》的八大文學(xué)主張中,第七條就明確提出了“不講對(duì)仗”的要求。其原因是為文當(dāng)“先立乎其大者”,不當(dāng)枉廢有用之精力于微細(xì)纖巧之末。但對(duì)聯(lián)文體是以對(duì)仗為前提的,不講對(duì)仗就不能算對(duì)聯(lián),所以,毛澤東在這副禮堂聯(lián)中進(jìn)行了一種嘗試,即大致保存上下聯(lián)的對(duì)稱性,使其在宏觀上有對(duì)仗的形式傾向,但微觀上絕不刻意追求對(duì)仗工整。更重要的一個(gè)方面,則主要是從受眾角度來考慮的。因?yàn)橥炷嘎?lián)是在家鄉(xiāng)韶山?jīng)_農(nóng)村來展示,因?yàn)楫?dāng)時(shí),新文化運(yùn)動(dòng)在農(nóng)村的影響還很小,那里的對(duì)聯(lián)的受眾主要是受過私塾教育的人,毛澤東在創(chuàng)作對(duì)聯(lián)時(shí)除了真切表達(dá)自己的情感外,主要考慮的就是這樣一批舊式讀書人的接受習(xí)慣,所以按照傳統(tǒng)的風(fēng)味來撰聯(lián)就是必然選擇了。而在城市,特別像長沙這樣從近代以來一直領(lǐng)時(shí)代風(fēng)氣之先的省會(huì),新文化的影響是較大的。更何況,是為省立第一師范學(xué)院附屬小學(xué)作聯(lián),毛澤東所設(shè)定的受眾應(yīng)該主要是兩類人:除了他迫切希望以新文化給予熏陶的學(xué)生和教師之外,還包括那些有可能接受文學(xué)改良思想的社會(huì)人士。因此,一師附小禮堂聯(lián)的對(duì)仗不工與平仄不葉,不是毛澤東的疏忽失誤,而是在五四新文學(xué)主張影響下為更充分地發(fā)揮對(duì)聯(lián)文化的傳播教育功能而突破格律束縛的大膽嘗試。此后,毛澤東在公共場所所提的具有宣傳目的的對(duì)聯(lián)就是沿著這個(gè)道路來創(chuàng)作的。如前文引用過的為江西寧都小布召開的蘇區(qū)軍民殲敵誓師大會(huì)會(huì)場題聯(lián)即是如此。
又如1939年,題延安新市場聯(lián):
堅(jiān)持抗戰(zhàn),堅(jiān)持團(tuán)結(jié),堅(jiān)持進(jìn)步,邊區(qū)是民主的抗日根據(jù)地;
反對(duì)投降,反對(duì)分裂,反對(duì)倒退,人民有充分的救國自主權(quán)。
這兩副對(duì)聯(lián)都只是宏觀上體現(xiàn)了對(duì)仗的特點(diǎn),若從字、詞方面考查,則只能算寬對(duì)。至于平仄,則僅僅遵守了末句仄起平收的大原則。
這種對(duì)于格律的態(tài)度,不但是對(duì)于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關(guān)于文學(xué)改良理念的繼承,更是毛澤東經(jīng)過多年思考而形成的“文藝為廣大人民服務(wù)”的文藝思想的體現(xiàn)。
毛澤東同志一生的對(duì)聯(lián)文化實(shí)踐成果及其體現(xiàn)的辯證思想是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chǎn),值得廣大的文化工作者在準(zhǔn)確把握的基礎(chǔ)上繼承下來、弘揚(yáng)開去。以上僅僅是筆者的一孔之見,期待更多有識(shí)之士能展開更廣泛、深入的研究,為當(dāng)代對(duì)聯(lián)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提供更豐富、更有力的理論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