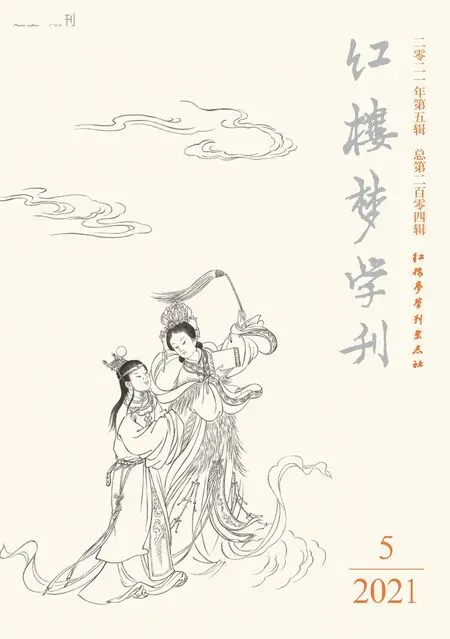以庚辰本為底本整理《紅樓夢》普及讀本的首倡——197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新版《紅樓夢》預案的意義
胡文駿
內容提要:1973年初,人民文學出版社曾組織新版《紅樓夢》整理工作預案,并擬召開相關專家研討會議,后因故中斷。此次預案雖未落實出版,但已擬定了初步且較完整的整理方案,其中提出以庚辰本為底本進行普及讀本的整理,是《紅樓夢》出版史上的首倡;對于其后不久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本《紅樓夢》的整理工作應有一定影響。本文以人民文學出版社保存的相關檔案為主要參考資料,闡述此次預案的過程與意義。
從20世紀50年代至今,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紅樓夢》整理本為國人廣泛閱讀。人文社在不同時期發行的《紅樓夢》整理本主要包括三種:(1)周汝昌、周紹良、李易校點,啟功注釋《紅樓夢》(以程乙本為底本,1957—1981年發行);(2)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本《紅樓夢》(前八十回以庚辰本為底本,后四十回以程甲本為底本,1982年發行至今,分別于1996年和2008年全面修訂再版);(3)俞平伯校、啟功注《紅樓夢》(前八十回以戚序本為底本,后四十回以程甲本為底本,2000年發行至今)。據該社總編室2021年3月統計數據,這三種《紅樓夢》整理本(包括不同版次、不同裝幀形態)累計印數分別為:2541815套、7649405套、1956600套。其中發行近四十年的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本《紅樓夢》(簡稱“紅研所校注本”或“新校本”)影響最為突出,1982年初版至1996年12月修訂版(即第二版)問世前,共發行3412275套;1996年12月至2008年7月修訂版(即第三版)問世前,共發行406900套;2008年7月至2021年3月共發行3830230套。據業內權威的開卷監控系統中國圖書零售市場數據,從2015年至今,紅研所校注本《紅樓夢》在國內銷售量每年均位居同類圖書榜首。
除了發行量巨大,為大眾讀者普遍閱讀,紅研所校注本《紅樓夢》也成為紅學及相關領域研究者據以征引、探析原文的重要版本。據中國知網引文數據庫統計《紅樓夢》原著整理本被征引量排名,2008年修訂版紅研所校注本位居第二,1982年初版紅研所校注本位居第四,此排名與上文所列這兩個版次巨大的發行量呈相應關系。綜合來看,紅研所校注本是當前紅學相關論文征引原著最為通行的版本,對于紅學研究有著顯著的影響。
據馮其庸先生回憶,紅研所校注本最早動議和立項,是1974年時任中宣部文化組副組長的袁水拍倡議的,1975年校注組成立,由袁水拍任組長,馮其庸和李希凡任副組長。此后七年,先后有馮其庸、李希凡、劉夢溪、呂啟祥、孫遜、沈天佑、沈彭年、應必誠、周雷、林冠夫、胡文彬、曾揚華、顧平旦、陶建基、徐貽庭、朱彤、張錦池、蔡義江、祝肇年、丁維忠等二十余位學者參與校注工作,還有吳世昌、吳恩裕、吳組緗、周汝昌、啟功等紅學家擔任顧問。校注組整理校記6000多條,成書時精簡為1000多條;撰寫注釋3500多條,成書時精簡為2300多條。此外,校注組還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和中國紅樓夢學會的成立打下基礎,這項工作的意義遠遠超越了校注本身。1982年3月紅研所校注本《紅樓夢》正式出版,當時亦被稱為新校本《紅樓夢》。
紅研所校注本是出版史上首次以庚辰本為底本進行整理的《紅樓夢》普及讀本,而在紅研所校注本校注組成立前,人民文學出版社曾有過一次重新整理《紅樓夢》的預案,雖未落實到出版成書,但已經進行了整理方案的初步討論和擬定,對于其后紅研所校注本的整理工作應不無影響,同時也是《紅樓夢》出版傳播的重要史料。本文擬以人民文學出版社保存相關檔案為主要參考資料,闡述這次未出書的新版《紅樓夢》整理計劃的過程與意義。
一、古典小說出版的“開放”與恢復
對于紅研所校注本《紅樓夢》出版前的學術背景,已有研究者進行了專門分析。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中國古代文學專業2021屆許鎏源博士在學位論文《〈紅樓夢〉鉛印標點本(1919—1949)研究》“程乙整理本被紅研所校注本代替的歷史背景分析”一節中,回顧了胡適、俞平伯、周汝昌等學者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對于以脂本為底本整理《紅樓夢》的建議和實踐;提出馮其庸先生《論庚辰本》一書為紅研所校注本選擇庚辰本為底本奠定了理論基礎,認為:“用庚辰本和程甲本分別作為紅研所校注本《紅樓夢》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底本,不是一個偶然現象,而是隨著《紅樓夢》研究不斷推進而逐漸變化的結果。并且是在以程乙本為底本的整理本大規模出版的時期就已經埋下了伏筆。”由前文可知,大眾閱讀的《紅樓夢》通行本的更迭,固然與紅學發展相關,而出版機構的所為往往是更主要的因素,尤其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圖書出版集中在少數出版機構,計劃性明顯,有些圖書甚至由國家層面直接進行組織出版。由此也形成了諸多“國民讀本”,在古典文學領域尤其如此。例如《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作為“四大名著”概念的形成,即與人文社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大量發行這四種小說的整理本相關。
“文革”時期,國家的出版管理機構幾經變化,實際工作一度中斷。1970年5月,國務院成立出版口,負責全國出版工作,1973年9月,出版口改名為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根據人文社古典部保存圖書檔案顯示,1971年11月,人文社起草了數份請示國務院出版口的報告,包括《關于開放幾本中國古典文學書籍的報告》《關于重版四種中國古典小說的報告》等。
在《關于開放幾本中國古典文學書籍的報告》后,還附錄了一份“開放〈紅樓夢〉‘致讀者’稿本”。“致讀者”提出:“因重新整理再版需要時日,現暫以舊版存書供應部分讀者的需要,希望在閱讀時能以批判態度對待《代序》及一切封、資、修的錯誤思想。”這里的“《代序》”指人文社1959年出版整理本《紅樓夢》時以時任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何其芳《論〈紅樓夢〉》一文節略本作為序言,1974年印次時,這篇序言更換為李希凡所撰前言。由這份報告及附錄可見,《紅樓夢》在當時考慮圖書恢復發行時顯得更加突出。
《關于重版四種中國古典小說的報告》起草于1971年11月2日,摘錄如下:
出版口負責同志:
根據出版會議紀要的精神、
周總理接見代表的指示,
和廣大讀者的需要,
我們準備在明年上半年內,
將《
紅樓夢》、《
水滸》、《
三國演義》、《
西游記》
四種古典小說,
斟酌情況,
有步驟地重版印行。
這四種小說,
一個共同的關鍵問題是,
需要有一個真正貫徹毛主席批判繼承“
古為今用”
的革命文藝路線的序言。……
總理指示除強調序言的重要性外,
還曾說到“
版本也要注意”。
這四種小說,《
水滸》
和《
三國演義》
的版本,
尚未發現有什么問題;《
西游記》
的版本問題也比較簡單,
即或存在某些校勘疏漏,
也不難檢核糾正。
只是《
紅樓夢》
一書的版本相當復雜,
國內外的研究者(
所謂“
紅學”
家)
爭論不已,
我們現在勉力把《
紅樓夢》
的版本情況作一概略說明,
初步提出幾種可能的辦法,
并表示我們目前比較傾向于何種辦法。(
請參見附件)
這份報告最后還建議出版口負責同志召開一次專題座談會,對這四部古典小說的重版問題進行討論。雖然報告提出存在的問題主要在于序言,但對版本也十分重視,尤其是《紅樓夢》,還附上了專門的版本說明。
由這份報告草案可見,對于《紅樓夢》的版本問題,在人文社內部是有所考慮和討論的。其時,周汝昌、戴鴻森等于古典小說——尤其是《紅樓夢》學養精深的古典部編輯,已經回到社里工作。雖然筆者并未找到上引報告中提及的附錄“關于《紅樓夢》版本問題的簡略說明”,但在檔案中保存了周汝昌看過該報告草案(包括附錄《紅樓夢》版本說明)后提出的修改意見。
二、《紅樓夢》新版計劃的提出
從上文所舉人文社向出版口的報告草案可見,在“文革”中后期恢復圖書發行工作時,對于重新整理《紅樓夢》,尤其是版本的改換,人文社已經有初步設想,而檔案資料中1973年1月9日“召開關于《紅樓夢》新版整理方案的座談會節要”(下文簡稱“節要”),則表明這項工作列入了正式的出版計劃。
“節要”全文如下:
一、
主要內容:
聽取與會者意見,
集思廣益,
明確《
紅樓夢》
新版整理的基本要求和工作方法、
注意事宜。
附帶征求關于中國古典文學今后如何出版的意見。
借此先打個招呼,
為以后另開專門性座談會作準備。
二、
主持者:
由我社負責同志主持會議;
由文研所《
紅樓》
整理小組的負責同志作一口頭情況介紹。——
由我社出面請人,
實際上與文研所共同主持。
三、
邀請對象:
李希凡、
袁鷹(
以上人民日報),
吳組緗、
魏建功、
趙齊平、
費振剛(
以上北京大學),
沈從文(
故宮歷史博物院),
吳恩裕(
政法學院),
陳仲竾、
丁瑜(
北圖),
啟功(
中華書局),
楊憲益(
外文出版社),
邵宇(
人美),
馮其庸(
人大)。
此外,
擬通知以下幾個單位,
由他們的組織指派人參加:
北京師范大學、
北京師范學院、
光明日報、
首都圖書館、
中華書局、
天津南開大學、
文物出版社。
四、
時間:
暫定本月下旬。
具體日期待與文研所商談就緒,
正式發出通知之后一周至十天。——
因需留必要時間供與會者做準備。
五、
地點:
借人民出版社新樓小禮堂。
六、
其他事宜:
知照食堂,
屆時準備三四十人的午餐;
知照司機同志,
屆時可能要用車接送某些道遠交通不便的來客。
此外,
準備茶水,
請管理部門協助解決。
七、
報請出版口負責同志批準,
并請屆時出席指導。
以上,
待領導同意后,
我們即與文研所具體聯系,
抓緊進行。
七三,
一,
九“節要”中提到的“文研所”即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前身為創建于1953年的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1956年劃歸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1977年改屬中國社會科學院。人文社建社初期出版的許多古典文學、外國文學整理作品均是與文研所合作完成的。1955年文研所致人文社副社長王任叔信(現保存于人文社古典部圖書檔案)中提到:“過去談過,我所整理的古典文學作品,均由你社出版。”1953年,俞平伯調入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不久,即開始了“紅樓夢八十回匯校本”的工作,1958年由人文社以《紅樓夢八十回校本》(全四冊,包括前八十回校本兩冊、八十回校字記一冊、后附四十回一冊)的面貌出版。因此,此次《紅樓夢》新版整理的工作,人文社擬與文研所合作似乎是順理成章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主要由俞平伯與其助手王佩璋(署名王惜時)完成,文學研究所的鄧紹基、劉世德也曾參與工作,總體來看還是以俞平伯先生個人為主導;而此次擬定的《紅樓夢》新版整理方案,由“文研所《紅樓》整理小組”擔任具體工作,并且計劃召集人民日報等媒體、北京大學等高校、中華書局等出版機構以及圖書館、博物館等單位的相關專家共同討論具體整理要求和工作方法,更具規模也更受重視。
據周汝昌先生回憶,他早年即與胡適爭論認為其倡導印行的“程乙本”是最壞的本子,并與兄長祜昌計劃進行《紅樓夢》版本的大匯校工作。70年代初他從干校回京后,還曾經寫報告請求完成《紅樓夢》“大匯校寫定真本”的工作。同事戴鴻森曾經“對我說:他原先以為《紅樓夢》不就是《紅樓夢》(按:指坊間流行本,包括上述‘程乙本’等),還要搞什么版本?!這時他偶然看了影印的‘庚辰本’(脂批抄本),拍案大驚,對我說:‘原來俗本子這么壞,與真本這么不同,一直被他騙了!’我見他悟了,遂有了‘共同語言’,乘機與他商量:我們應出一部好本子了。他很同意,且很積極,馬上要與社科院文研所聯系,要他們校注一個新本。當時社方臨時領導人也點頭了,我自不便再提我的大匯校的事情。文研所很高興,很快由鄧紹基等二人持函,到社辦理手續。”
由此可見在人文社古典部推進《紅樓夢》新整理版計劃的主要是戴鴻森和周汝昌。在人文社古典部檔案資料中存有一封周汝昌致時任編輯部主任杜維沫的信件,也印證了這一點,信中提到:
老戴所擬座談會方案十分周詳妥善,
再無其他意見了。
望即照此報領導。
至于會上除由文研的同志負責口頭講解之外,
是否要預先寄發他們所擬的“
整理方案”
打印本,
想來此事應由文研負責辦理,
可俟和他們聯系時說定規了,
我們的這份報告就不必提及了,
但是不要忘記讓文研盡早準備打印件。
三、“垂成之際”的中斷
1973年2月初,新版《紅樓夢》整理方案(征求意見稿)已經擬定并打印,預備座談會討論。方案全文如下:
一、
目的:
根據比較接近曹雪芹原著的幾個早期抄本(
舊稱脂批系統本),
整理出一部普及的《
紅樓夢》
新版本。
二、
任務:
此次整理不是大規模的全面會校。
現存抄本不下十來種,
全面會校工程很大,
曠日持久,
不能適應當前需要。
但也不是只取某一個抄本加以整理標點,
因為現存諸抄本都有不少問題,
或殘缺不全,
或雖全而實由拼湊而成,
各有訛誤凌亂之處。
此次是利用幾個主要的早期抄本來作會校,
并參考現有其他的早期抄本,
吸取諸本之長,
以冀整理出一種較好的本子。
整理工作包括校訂、
標點、
注釋等。
三、
底本和校本:
前八十回為整理重點。
以《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殘存七十八回本(
舊稱庚辰本)
作為底本;
以《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殘存十六回本(
舊稱甲戌本)、《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殘存四十回本(
舊稱己卯本)、
戚蓼生序《
石頭記》
八十回本(
舊稱戚本,
有正書局石印),
作為校本;
以夢覺主人序本《
紅樓夢》(
舊稱甲辰本,
存八十回)、
舒元煒序本《
紅樓夢》(
殘存四十回)、
蒙古王府舊藏本《
石頭記》(
前八十回為脂批系統抄本,
存七十四回,
另六回據程甲本抄配)、
文學研究所藏《
紅樓夢稿》(
前八十回的底本——
即未經改動的正文部分——
為脂批系統抄本,
存七十回,
另十回據程甲本抄配)
等作為參考本。
四、
校訂:
以校本校底本,
凡有異文,
均編寫卡片,
相當于校勘記。
底本有訛誤及文義不可通之處,
得據校本改正。
如校本文字較底本為好,
可斟酌采用。
校本之間有異文,
擇善而從。
如底本及校本均不能解決的問題,
可使用參考本。
如諸本皆訛,
須經過考訂,
慎重處理。
凡屬改動底本之處,
均應作出校記(
明顯的訛字及異體字可不作校記),
列明底本原文及改動根據。
五、
后四十回:
高鶚續著的后四十回,
采用乾隆五十六年辛亥萃文書屋活字本《
紅樓夢》(
舊稱程甲本)
作為底本,
以《
紅樓夢稿》
作為校本,
選擇程甲本系統的本子若干種,
以及乾隆五十七年壬子萃文書屋活字本《
紅樓夢》(
舊稱程乙本),
作為參考本。
六、
注釋:
此次整理,
作較詳細的注釋,
特別注意有關政治、
階級關系及社會歷史方面。
其他凡有助于一般讀者理解原著的地方,
均酌量增加注釋,
如南北土語、
古代名物制度及重要詩詞(
如《
芙蓉誄》)
的用典等,
并從脂批中選取少數有助于了解作者思想和藝術的批語。
七、
標點等:
全書校訂后加以標點,
并附插圖。
為便于廣大讀者,
注釋附在每頁底下。
考慮到校記數量較多,
可另行單印,
供需要者參考。
全書原則上采用簡體字,
橫排。
八、
前言:
由整理小組集體撰寫一前言。
以毛主席思想為指導,
貫串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
幫助讀者了解原書的思想及藝術,
并附必要的整理工作說明。
九、
人員和時間:
此次整理工作由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紅樓夢整理小組》
擔任,
實際工作時間暫定一年左右。
十、
其他:《
紅樓夢》
的早期抄本如:
殘存四十回本(
舊稱己卯本)、
夢覺主人序本(
舊稱甲辰本)、
蒙古王府舊藏本等均歸北京圖書館收藏,
需要取得他們的協助,
解決調用書籍及拍攝顯微影片等問題。
插圖請美術部門協作。
這份征求意見稿的手稿寫于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稿紙上,即如周汝昌所言由文研所擬定。隨后手稿打印數十份,與“《紅樓夢》新版整理座談會”邀請函一起被陸續發送給參會人員。檔案顯示,此次會議最終邀請的名單與上文所引“節要”基本一致,而“節要”中提及的文研所《紅樓》整理小組的負責同志具體為何其芳、吳世昌、俞平伯、鄧紹基、陳毓羆等。
就在會議即將召開時,人文社緊急通知會議暫停。通知非常簡短:“關于《紅樓夢》新版整理座談會,因故暫不召開,特此通知。”大部分已邀請參會學者,是由人文社編輯部人員電話通知或登門面告,少數京外的單位,如南開大學中文系,系發加急電報通知(2月26日)。據周汝昌先生回憶:“此事垂成之際,忽因社外某位同志得知后激烈反對所邀人,不容實行。當時杜維沫新回社擔任古典部的主任,他須向文研所‘打退堂鼓’;那天晚上他到我家訴說風波內情,表示十分為難:‘約請了人家,又要變卦食言,這多么尷尬!’”雖然周先生的回憶有更多細節,但那位“社外某同志”和其反對的“所邀人”具體為誰,并未說明。但可以推想,能夠在一切就緒時強行阻止這次會議的召開,這位“社外某同志”地位應該非同小可,并足以影響出版社的工作進程。
四、影響與意義
1973年初人文社這次《紅樓夢》新版整理座談會因故取消,隨之的整理工作也成為“泡影”。兩年后,由袁水拍倡議并主持的新校本《紅樓夢》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李希凡任副主持者,馮其庸任校勘小組組長,周汝昌、吳世昌、吳恩裕等任顧問,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部仍作為將來的出版機構參會。此后,馮其庸先生組織成立校注組,展開長達七年的新校本《紅樓夢》整理工作。
回顧1973年人文社整理新版《紅樓夢》的預案,對于新校本《紅樓夢》應該是有一定影響的,或者說提前做了一些準備工作。
首先,參與人員有所交集。李希凡、馮其庸由受邀參與討論、提供建議的學者成為校注工作的具體組織者,吳恩裕、吳組緗、啟功等學者均受邀作為指導工作的顧問專家。出版社方面基本是相承接的,均由編輯部主任杜維沫主導,只是具體工作編輯由戴鴻森、周汝昌(1979年調至中國藝術研究院工作)變為王思宇。參與人員的延續很可能使整理工作的理念與方法得到延續的討論,乃至落實。
其次,整理的目的一致。1973年人文社新版《紅樓夢》整理方案“征求意見稿”第一條“目的”提出:“根據比較接近曹雪芹原著的幾個早期抄本(舊稱脂批系統本),整理出一部普及的《紅樓夢》新版本。”“接近曹雪芹原著”這一理念,同樣是新校本《紅樓夢》整理工作的最重要的主旨和目標。1982年初版新校本《紅樓夢》的前言中提到:“在上述這些抄本中,庚辰本是抄得較早而又比較完整的唯一的一種,它雖然存在著少量的殘缺,但卻保存了原稿的面貌,未經后人修飾增補,因此本書在校勘過程中決定采用庚辰本為底本。”據新校本校注組成員呂啟祥先生回憶:“當年校注組得以組建具有凝聚力,從根本上說是因為有一種共識、甚至可以說是一種信念,那就是:努力接近曹雪芹原著的面貌,為廣大讀者提供一個比較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的經過整理的普及本。”可見,“一個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的普及讀本”,是兩次整理工作的終極目標,這一點是完全一致的。
再次,將“征求意見稿”與1982年初版新校本《紅樓夢》的凡例對照來看,一些整理工作的具體原則是一致的。底本與校本方面,前八十回底本均選定庚辰本,參校本均包括甲戌、己卯、戚序、甲辰、舒序、蒙府、夢稿本;后四十回底本均選定程甲本,并以程甲本系統其他版本和程乙本參校。校勘方面,對于底本明顯訛誤文字,均以校本改正,并作出校勘記。注釋方面,“征求意見稿”說得比較簡略,且強調政治、階級關系的內容,但注重注釋的詳細和方言語詞、古代名物制度及重要詩詞用典的解釋,與新校本注釋理念相契合。新校本《紅樓夢》出版四十年來成為國人閱讀的首選經典版本,其注釋的詳細精準、包羅百科是重要原因。
當然,因為“征求意見稿”僅是供會議討論的方案草稿,遠不如新校本成書的凡例完善,甚至有些整理的基本理念也有所不同。如對于底本與各參校本之異文,“征求意見稿”主張“如校本文字較底本為好,可斟酌采用”,而新校本凡例主張“凡底本文字可通者,悉仍其舊”,這一點似乎也使新校本在出版后的被閱讀、研習中受到一些爭議。另外,“征求意見稿”并不打算在成書中保留校記,而新校本則選擇重要的校記一千余條,附于每回正文之后,這一點無疑也是新校本并不止于作為普及讀本廣泛發行,而成為可供學者進行《紅樓夢》版本研究參考文獻的重要原因之一。
綜上所述,1973年初人文社《紅樓夢》新版整理的動議和相關預案,對新校本《紅樓夢》(即紅研所校注本)的整理工作應有一定的影響。而厘清這次未能落實的新版《紅樓夢》計劃的始末過程,也有助于豐富對新校本《紅樓夢》出版背景的了解。20世紀70年代初期,與許多其他行業一樣,出版業也在尋求恢復,具體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小說的重版被列入計劃,而版本復雜的《紅樓夢》是其中的重點,同時也提出了以脂本代替程本作為重新整理工作底本的具體方案,且明確了以庚辰本為底本,有首倡之功。由此可見,新校本《紅樓夢》作為首次以庚辰本為底本整理的普及讀本,除了版本材料的發現和紅學研究發展的學術背景,出版機構的推動作用也值得重視。
注釋
① 1953年12月,
人民文學出版社以副牌“
作家出版社”
名義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第一個《
紅樓夢》
普及讀本,
系以程乙本為底本,
由時任人文社古典文學編輯的汪靜之標點,
參與注釋工作的有俞平伯、
華粹深、
李鼎芳、
啟功等人。
據該社總編室記錄,
1953年到1957年,
這一版《
紅樓夢》
共印行60余萬套。
但因其整理工作并不完善,
存在一些舛誤,
1957年即被周汝昌、
周紹良、
李易校點,
啟功注釋《
紅樓夢》
取代。
1957年至1981年,
周汝昌等點校、
啟功注釋的這個《
紅樓夢》
整理本,
經過了1959年和1964年的修訂再版,
是這一時期國內比較通行的《
紅樓夢》
讀本。
② 該版本簡稱“
俞校啟注”
本,
系人文社古典文學編輯部為適應讀者需要,
征得俞平伯先生后人和啟功先生本人同意后,
于2000年將俞平伯校訂、
王惜時參校《
紅樓夢八十回校本》(
附后四十回,
1958年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的正文部分,
與周汝昌等點校、
啟功注釋《
紅樓夢》
的注釋部分,
組合而成的新版本。
③ 開卷監控數據來自北京開卷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成立于1998年,
是全球最大規模中文圖書市場零售數據連續跟蹤監測系統。
目前一般用戶通過其客戶終端可查詢近七年的中文圖書銷售數據。
④ 該數據顯示,
排名第一者為黃新渠編譯《
紅樓夢》(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1年出版),
該書為英文縮寫本,
實際上并不屬于本文討論的原著整理本范疇。
⑤ 參見馮其庸《〈
紅樓夢〉
校注本再版序》(
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
紅樓夢》,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第3版)、《
懷舊空吟聞笛賦——〈
紅樓夢〉
新校注本25周年紀念座談會上的發言》(《
紅樓夢學刊》
2007年第2輯)。
⑥ 1958年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俞平伯校訂、
王惜時參校的《
紅樓夢八十回校本》,
是以戚序本為底本整理的,
是首次以脂本系統版本作為整理底本。
⑦ 參見許鎏源博士學位論文《〈
紅樓夢〉
鉛印標點本(
1919—
1949)
研究》(
中央民族大學文學院,
2021年,
第158—
160頁)。
⑧ 參見艾江濤《
重看“
四大名著”:
國民讀物如何形成?》(《
三聯生活周刊》
2018年第21期)。
⑨ 參見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編《
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
第14卷《
本卷編輯說明》(
中國書籍出版社2013年版)。
⑩ 據周汝昌《
紅樓無限情——
周汝昌自傳》(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
一書中《
倡導校印新本〈
紅樓夢〉
紀實》
一篇回憶,
1970年9月周汝昌和戴鴻森已經從干校回到北京。
[11] 周汝昌《
倡導校印新本〈
紅樓夢〉
紀實》,《
紅樓無限情——
周汝昌自傳》,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
第229—
230頁。
[12] 檔案顯示,
1973年2月19日,
人文社發出通知變更會議地點,
由原定的人民出版社小禮堂改為國務院第一招待所,
并說明會議需開一天,
請參會人員自備糧票等細節事項。
[13] 周汝昌《
倡導校印新本〈
紅樓夢〉
紀實》,《
紅樓無限情——
周汝昌自傳》,
第230頁。
[14] 據周汝昌先生回憶,
會議召開時已入秋季,
參見《
倡導校印新本〈
紅樓夢〉
紀實》。
但新校本《
紅樓夢》
的首批“
征求意見稿”(
前五回),
完成于1975年6月,
此次會議似應早于周先生所記。
[15]《
紅樓夢》
前言,
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
第6頁。
[16] 呂啟祥《
感恩·
憶舊·
圖新——
寫在〈
紅樓夢〉
新校注本出版25周年之際》,《
紅樓夢學刊》
2007年第2輯。
[17] 這一點在當時是比較常見的,
新校本《
紅樓夢》
最初注釋征求意見稿也有明顯的政治、
階級關系內容。
如第一回“
女媧氏煉石補天”
的注釋,
1975年6月的征求意見稿中有“
作者借這個故事暗示封建社會的‘
天’
已塌壞,
雖然他主觀上想補這個‘
天’,
但是也看出這個‘
天’
是補不起來了”
的詞句,
1975年12月的征求意見稿中有“
作者借這個故事暗示封建社會的‘
天’
已經塌壞了”
的詞句,
在1982年成書出版時,
這些內容有所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