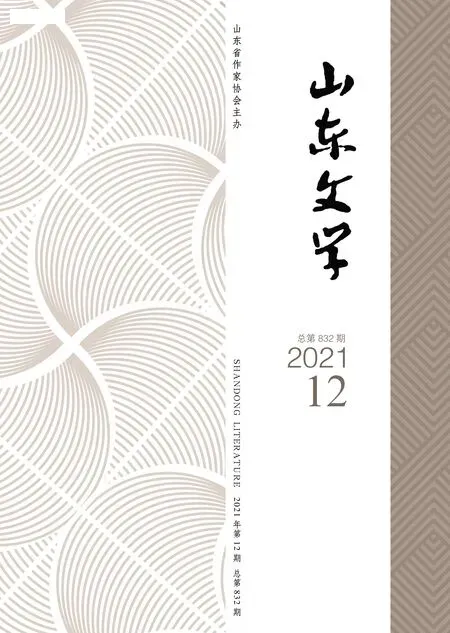壽 釘
2021-11-12 00:08:54黃鑫
山東文學
2021年12期
黃 鑫
一
趙四奶奶火化完已經兩天兩夜,依然無處下葬。兒子阿吉今年入冬就犯了老寒腿,盤在炕上快一個月了,前前后后的事情就由著孫子阿毛來忙活。“村長說還得再等兩天。”阿毛去村大隊屋竄了不下十趟,還去了兩趟村長阿先家里,但趙四奶奶下葬的事情完全沒有著落。“至少還得兩天。”阿毛站在炕前,兩只手垂著,交疊在褪了色的牛仔褲上,跟父親阿吉答話。
阿吉斜了眼兒子,“自家村子的亂墳崗,怎么就下不了葬。”阿吉咳著說完這些,掐滅半截煙卷,用很大的力氣喘著粗氣。“再等,壽釘子都要生銹了,跟用舊耙齒子有什么兩樣。”阿吉還是努力在喚氣的空當嘟囔完自己的不滿,“趙四奶奶活著時就不贊同遷墳,整天嘟囔,先人們又不是些牛羊,可以趕來趕去。”今年的冬天太冷了,行動不便的阿吉偏又染上了一場感冒,感冒過后氣管就受不得半點怨氣。兒子阿毛轉身端來半碗白開水,拿嘴試了涼熱,伸到父親臉前,信手抽走了床頭的半包煙和一次性打火機。父親阿吉漲著臉咳得地動山搖,連連擺手。兒子阿毛只好把碗收回去,在靠近床頭的桌角上放牢。
“那我……先把壽釘子給阿光叔退回去。”兒子阿毛候了一會兒,最后說。
阿光是狗皮洼唯一的鐵匠,打得一手好鐵活兒。只是年齡不饒人,鐵匠阿光畢竟過了六十歲了,早就打不了大型的鐵頭家什,平日里也就逢著村里有了白事,打打一拃長的壽釘子。
狗皮洼村子雖小,幾十戶人家,卻是祖傳的講究。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