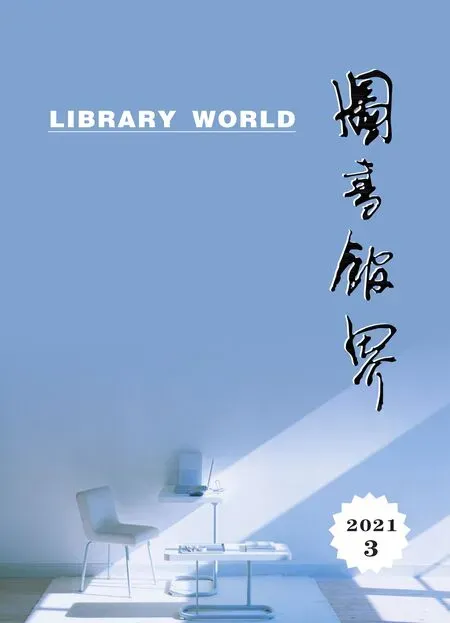《持靜齋書目》及其對丁日昌洋務思想的反映
郝子靖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香港 999077)
丁日昌(1823—1882年),字禹生(一作雨生),號持靜,廣東豐順人。咸豐四年(1854年)入仕,歷任萬安、廬陵知府,后入曾國藩幕府,受曾國藩、李鴻章賞識,被舉薦至上海參與籌辦上海機器局(又稱江南機器制造總局);同治四年(1865年)任蘇松太道,兼任江南機器制造總局總辦,同年10月任兩淮鹽運使;其后又歷任江蘇布政使、江蘇巡撫、福建巡撫;光緒六年(1880年)任會辦南洋海防、節(jié)度水師,兼理各國事務大臣。作為洋務派的重要人物,他在軍事、政治、外交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貢獻。丁日昌還是晚清著名的藏書家,與朱學勤、李盛鐸并稱“咸豐三大藏書家”。
1 丁日昌藏書概況
丁日昌藏書的來源主要有三處:一是在“庚申之劫”收購于蘇州顧沅“藝海樓”;二是收購于上海郁松年“宜稼堂”;三是零星取得于江浙一帶的書肆、藏書家。丁日昌的藏書樓名為“持靜齋”,初名“實事求是齋”,又有“百蘭山館”“讀五千卷書室”“潔園”等名。
丁日昌的藏書前后曾經(jīng)過多次編目,其中較為重要的為以下四次:第一次為藏書于“百蘭山館”時由林達泉所編,編成《百蘭山館藏書目錄》,已佚。第二次則是主要由莫友芝編寫的《持靜齋書目》和《持靜齋藏書記要》,而丁日昌及其門人也對二者進行了增補,增《持靜齋續(xù)增書目》一卷于《持靜齋書目》(合為五卷)。有關《持靜齋書目》與《持靜齋藏書記要》的區(qū)別,馮建福指出,《持靜齋藏書記要》“只著錄丁氏所藏宋元刻本及名抄、名校等‘傳本稀見’者,實為善本目錄”,而《持靜齋書目》則“著錄藏書三千三百多種,較為完整地反映了持靜齋藏書概貌”。這種說法可以同治七年(1868年)八月莫友芝給丁日昌的書信為證:
《靜持齋書目》,自六月中旬考證次敘,其單部及零星之件,都有頭緒,約費四十日整功。唯叢書十余種,尚未件分。其編例大致依《四庫全書總目》,每類各依時代;每部下,其收入《四庫提要》者,但以“《四庫》著錄”“《四庫存目》”分注;中有宋元舊本及舊鈔善本,則于分注下疏記數(shù)語以明之;其《四庫》未收者,但分注刊寫字;其中有未傳秘本,則各系以解題。俟全目脫稿后,更于其中將有解題、有疏說者,別錄出為冊,使一備一精,各自為編,而此目乃完也。
第三次則是在光緒十二年(1886年),由江標“以宋、元、校、鈔、舊刻五類分別部居”,編為《豐順丁氏持靜齋書目》,并于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刊印。第四次是在1945年,由溫廷敬以“宋元刊本”“明本”“鈔校本”三卷編寫的《持靜齋善本書目》(稿本)。而本文的論述對象則是經(jīng)莫友芝撰寫,由丁日昌及其門人加工的《持靜齋書目》和《持靜齋藏書記要》。
2 《持靜齋書目》的特點
《持靜齋書目》(卷一到卷四)大體按照《四庫全書總目》以四部分類法分為經(jīng)、史、子、集四個大類,其中,經(jīng)部十類、史部十五類、子部十四類、集部十類,共四十九小類。具體如下:
經(jīng)部:易、書、詩、禮、春秋、孝經(jīng)、五經(jīng)總義、四書、樂、小學
史部: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史鈔、載記、時令、地理、官職、政書、目錄、史評
子部:儒家、兵家、法家、農(nóng)家、醫(yī)家、天文算法、術(shù)數(shù)、藝術(shù)、譜錄、雜家、類書、小說家、釋家、道家
集部:楚辭、別集類一(漢至五代)、別集類二(北宋建隆至靖康)、別集類三(南宋建炎至德祐)、別集類四(金元)、別集類五(明洪武至崇禎)、別集類六、總集、詩文評、詞曲
與《四庫全書總目》略有不同的是,《持靜齋書目》將集部中的別集又按時代拆分為五個小類,與集部其他類同屬一級。
《持靜齋續(xù)增書目》(卷五)則按四部分類法合為一卷,其中,經(jīng)部七類、史部二十二類、子部十四類、集部七類。具體如下:
經(jīng)部:易、詩、周禮、儀禮、春秋、五經(jīng)總義、小學
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是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無情批判的基礎上形成的科學理論,其目的是為推翻資產(chǎn)階級的政治統(tǒng)治,消除市民社會的異化,最終實現(xiàn)人類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 該理論雖然存在有諸多的不足,但其中蘊含著的基本觀點、立場和方法具有合理性。
史部:正史、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傳記、載記、總志、都會、郡縣、河渠、邊防、山水、外紀、職官、官職、儀制、邦計、目錄、金石、史評
子部:儒家、兵家、法家、農(nóng)家、醫(yī)家、天文算法、術(shù)數(shù)、算學、藝術(shù)、雜技、雜家、類書、小說家、釋家
集部:別集類(漢至宋)、別集類(元)、別集類(明)、別集類(國朝)、總集、詩文評、詞曲
相比主要由莫友芝編寫的《持靜齋書目》(卷一至卷四),主要由丁日昌編寫的《持靜齋續(xù)增書目》(卷五)的分類方法更為細致,他將史部中的地理類拆分為都會、郡縣、河渠、邊防、山水、外紀等小類;政書類拆分為儀制類和邦計類;目錄類拆分為目錄類和金石類;將子部中的藝術(shù)類拆分為藝術(shù)類和雜技類。這些拆分后的小類在《四庫全書總目》中是“類”的下一級分類“屬”,而丁日昌將其提升至“類”的位置,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了他注重實用性的思想。
《持靜齋藏書記要》為善本目錄,分為宋刊本、元刊本、明刊本、鈔本四類。其中,前三者編為上卷,而鈔本則編為下卷。《持靜齋藏書記要》中所記載的書目質(zhì)量很高,珍貴的宋元刻本、鈔本較多,因此,丁日昌也有“百宋千元”之稱,可見丁日昌在文獻保存方面的貢獻是很大的。其中,最為精良的有宋本《毛詩要義》、宋本《儀禮要義》、宋本《漢書》、宋本《西漢會要》,等等。
關于《持靜齋書目》和《持靜齋藏書記要》的貢獻,可概括為以下幾點:1)詳盡記錄了書籍的作者、內(nèi)容、卷數(shù)、版本及流傳,在《持靜齋藏書記要》中還注明了是否收入《四庫全書總目》;2)注明對書目的批注、題跋和校點;3)糾正前人著錄書籍的一些錯誤;4)對書籍版本的優(yōu)劣進行簡要品評。《持靜齋書目》和《持靜齋藏書記要》的學術(shù)價值,正如張燕嬰所言:“由于丁日昌的藏書至今尚存者不少,故此二目的作用不只在了解持靜齋之過去,也有現(xiàn)實的參考價值。特別是《持靜齋藏書記要》收錄的多為稀見刊本、鈔本與稿本,且詳記版本特征,也可以借以作為判斷善本與珍稀傳本的重要依據(jù)。”
除了在文獻學方面的學術(shù)價值,《持靜齋書目》和《持靜齋藏書記要》還從側(cè)面反映了丁日昌的洋務思想。
3 《持靜齋書目》與丁日昌的洋務思想
3.1 西學為用
兩次鴉片戰(zhàn)爭的失敗使丁日昌認識到自強御侮的重要性,認為“船堅炮利,外國之長技在此,其挾制我國亦在此”。而與曾國藩、李鴻章、容閎、王韜等人的接觸也使他加深了對“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認識,主張“師外人之長技為己之長技”。這種向西方學習先進科技的洋務思想,不僅體現(xiàn)在他參與創(chuàng)辦江南制造局、創(chuàng)設新式海軍等實事中,還體現(xiàn)在他的藏書中。
《持靜齋書目》收錄了一些有關西方科學技術(shù)、天文算法之類的著作。《持靜齋書目》前四卷中子部的兵家類收錄了湯若望(德國人)授、焦勖述的《則克錄》一卷,其本名《火攻挈要》,咸豐元年刊本,是火器技術(shù)的著作;子部的天問算法類收錄了《天問略》《月離》《代數(shù)學》《談天》《代微積拾級》《幾何原本》《重學》《圓錐曲線說》等西洋著作;子部的雜家類收錄了李善蘭譯著的《植物學》。《持靜齋續(xù)增書目》子部的兵家類收錄了《則克錄》三卷(丁拱辰刊本);子部的雜技類收錄了鄧若函(德國人)授、王征述的《泰西奇器圖說》(物理學著作);子部的雜家類收錄了英國韋而司撰寫的《化學鑒原》。
《持靜齋書目》還收錄了一些記載海外地理、歷史、法律的著作。《持靜齋書目》的前四卷史部的地理類收錄了《職方外紀》《萬國公法》等譯著以及《佛國記》《西洋朝貢典錄》《海國圖志》等中國人編寫的“外紀”。《持靜齋續(xù)增書目》史部的外紀類收錄了日本人賴襄撰寫的《日本外史》。
除了《持靜齋書目》所記載的,丁日昌還閱讀了王韜和黃達權(quán)翻譯的《火器略說》、容閎翻譯的《地文學》、王韜編寫的《法志》《俄志》《普法戰(zhàn)爭》等書,而他自己也對西學書籍的編寫和翻譯有所貢獻,如編寫了《地球圖說》《槍炮圖說》,招募賢才翻譯西洋軍火書如《炮錄》和各國地理、歷史書如《法人游探記》。
3.2 中學為體
丁日昌認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念,向西方學習的僅限于科學技術(shù),而非西方的思想與政治制度。他在《海防條議》中寫道:“除船械一切自強之具,必須效法于東西洋外,其余人心風俗,察吏安民,仍當循我規(guī)模,加以實意,庶可以我之正氣,靖彼之戾氣,不致如日本之更正朔、易衣冠,為有識者所竊笑也。”丁日昌并沒有倡導從根本上改變政治制度,而是繼續(xù)維護清王朝的統(tǒng)治,固守的依然是封建倫理教化。在對待小說和戲曲上,他的想法和清廷是一致的,認為“淫書小說,最為蠱惑人心”,主張“尊崇正學”“力黜邪言”。
《持靜齋書目》(含《持靜齋續(xù)增數(shù)目》)并沒有收錄通俗小說和戲曲,其子部的小說家類中收錄的作品大多為唐宋的文言小說,而明清時期撰寫的作品僅有15部,像《水滸傳》《紅樓夢》這些作品當然沒有包括在內(nèi)。盡管他青年時期便已熟讀《紅樓夢》,但他在江蘇巡撫任上卻嚴厲查禁這些作品,所禁小說、戲曲者有數(shù)百種之多。他在同治七年(1868年)發(fā)布的通飭令中寫道:
“查淫詞小說,向干例禁;乃近來書賈射利,往往鏤板流傳,揚波扇焰,《水滸傳》《西廂記》等書,幾于家置一編,人懷一篋。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綺膩為風流,鄉(xiāng)曲武豪,借放縱為任俠;而愚民鮮識,遂以犯上作亂之事,視為尋常;地方官漠不經(jīng)心,方以為盜案奸情,分歧疊出。殊不知忠孝廉節(jié)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見為功,奸盜詐偽之書,一二人導之而立萌其禍。風俗與人心,相為表里,近來兵戈浩劫,未嘗非此等逾閑蕩檢之說,默釀其殃;若不嚴行禁毀,流毒伊于胡底。本部院前在藩司任內(nèi),曾通飭所屬宣講《圣諭廣訓》,并頒發(fā)《小學》各書,飭令認真勸解,俾城鄉(xiāng)士民,得以目染耳濡,納身軌物。惟是尊崇正學,尤須力黜邪言,合亟將應禁書目,粘單札飭……此系為風俗人心起見,切勿視為迂闊之言。”
丁日昌親自鎮(zhèn)壓過太平天國運動、捻軍起義等農(nóng)民起義,也曾不敵太平軍,因此,他對農(nóng)民起義恨之入骨。他認為《水滸傳》《西廂記》之類的“淫詞小說”會蠱惑人心,或教人犯上作亂,或敗壞傳統(tǒng)道德,必須嚴令禁止,否則會導致社會內(nèi)亂。這種想法將時局動蕩的原因過于簡單化,也將小說、戲曲的影響過于妖魔化。他并沒有意識到一個封建王朝根基不穩(wěn)的深層原因,而這也正是洋務派“中學為體”思想的局限性,即并沒有從根本上變革社會制度。
4 結(jié) 語
《持靜齋書目》較為詳細地反映了丁日昌的藏書情況,為后人學術(shù)考辨提供了依據(jù),同時,也間接地反映了丁日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思想。隨著晚清新學的興起和書籍空前的繁多,像《持靜齋書目》這樣依循四部分類法已難以滿足分類的要求。相比之下,康有為編寫的《日本書目志》、梁啟超編寫的《西學書目表》、徐維則編寫的《東西學書錄》則摒棄了傳統(tǒng)的四部分類法,與現(xiàn)代的圖書分類法較為接近。從中也可以看出,目錄學的發(fā)展與時代的變化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