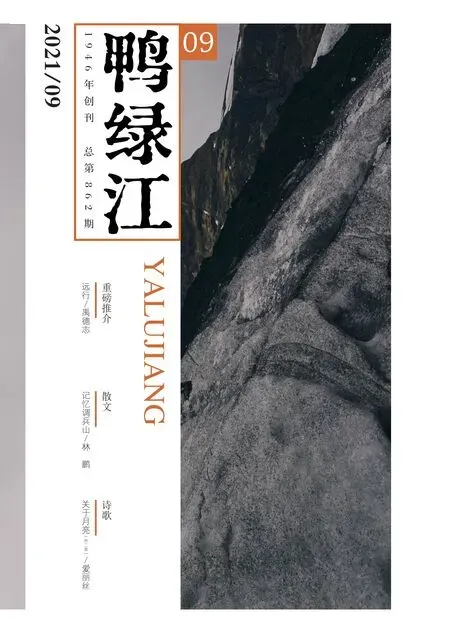重生
英 木
馬路對面市場那個賣羊肉串的女人,我怎么看都覺得在哪兒見過,卻怎么也想不起來。我大病初愈,似乎腦子也壞了,好像什么都記不得了。
“來10串。”一個帥哥手掐肉串走了。陸陸續續地, 又有人買,女人的生意不錯。
有汗順著女人的臉流下來,女人摘下戴在頭頂上的紅圍巾,一雙好看的杏核眼忽閃著,招呼街上走路的行人。
正值下班高峰,街上行人很多。
“來20個肉串。”女人的肉串攤似乎是這一帶最火的。
“好嘞!”女人迅速拿起事先穿好的肉串,放在炭火燒烤爐上,兩面來回翻轉,一會兒工夫,飄著香味的肉串就烤好了。這久違的香味飄向我,讓我小小的胃有一點躁動。那曾是我的最愛,可是,現在我卻不敢再吃它,我的胃被切去三分之二,我得對剩下的三分之一負點兒責。
天色已經暗淡,我選中一家面館,準備在這里吃晚飯,店主殷勤地招呼我,我點了一碗面。
“就這些?不來點兒小菜兒啥的?”
“不來了。”我眼睛望著窗外,再一次看那個烤串女人。
“你認得她?”店主問。
“說不上來,面熟,好像在哪兒見過,想不起來了。”
“我跟你說,這女人怪可憐的,她丈夫在一個工程隊上班,聽說出了事故,給砸死了,丟下她和孩子。街坊鄰居都說女人命苦,四十歲不到就守寡,也有人說女人命硬,克夫。有人勸女人再嫁個好男人。可是,女人為了孩子,咬咬牙就支起了這個小小的烤串攤。女人的肉串攤臨街,每天晚上是最忙碌的時候。”店主嘰里咕嚕跟我講了一陣。
天陰著臉,霧靄茫茫的。昨天天氣預報說今天有雪。這會兒,還沒看見雪的影子。
電話響了,是老公。老公去山區扶貧已經有半年了,這會兒打電話來肯定是問我的病情。
“你在哪兒呢?病剛好就亂跑,在家老老實實待著多好。”老公批評我。
“出來吃點兒飯,一會兒就回去。你怎么樣?工作還順利嗎?”我在電話這端看不見他的臉,心里也蠻擔心的。
“你不用擔心我,照顧好你自己。”他似乎猜到我要說什么。
“知道了,放心吧,一會兒吃完飯就回去。”我知道扶貧工作很辛苦,風里來雨里去的,還要做思想政治工作,工作壓力很大。我能做的,就是別讓他分心,少給他添堵。
電話撂了。窗外烤串女人的臉上一直掛著笑容,那條紅圍巾又系在了頭上。她笑起來真好看,遠遠看去,就像冬天里的一幅畫。
吃完飯我想去洗澡,結賬的時候,店主問:“你是不是想洗澡?”
我嚇了一跳:“你怎么知道?”
店主樂了:“看你的神情我就知道,我很會看人的。”
我聽了拔腿就走,我怕一會兒再聽到我會相面算命之類的話。
“喂!你的圍巾。”店主在后面喊。我回身拿起圍巾系在脖子上,很快消失在越來越濃的夜色里。
回到家的時候,菲兒正在門口等我,見著我就問去哪兒了。菲兒是我發小,也是同事,雖然不在一個部門,但是在一個大院。
我說:“你先別問了,進屋再說。”我用鑰匙打開房門,走進屋。
“菲兒,你說怪不怪,剛才我看見一個女人,我明明認識她,可是卻怎么也想不起來是誰了,你說我這腦子是不是也出問題了?”我邊摘圍巾邊說。
“說什么呢?誰啊,讓你這么在意?”菲兒在門口換拖鞋,一只手拽著褪到腳面上的襪子。
“對面市場邊上那個賣羊肉串的。”我回答。
“她啊,那不是前幾年總到你辦公室求你的那個女人嗎?”菲兒穿上拖鞋往客廳走。
“她?真的是她?”我有點兒吃驚,簡直不敢相信。
“沒錯。你這是怎么了?一驚一乍的。”菲兒坐在沙發上,倒了一杯涼開水。
那年冬天企業轉制那會兒,我正在辦公室寫最后一個批復,辦公室的門吱呀一聲被打開,一股冷風蛇一樣地鉆進來。那個叫秦素文的女人又來了,我皺了皺眉頭。
“我來問問,不買斷工齡行嗎?”
“不行。”
“為什么?”女人身子向后靠,差一點碰翻墻角的洗手盆。
“你坐下說。”我把她按在椅子上。
“轉制是大勢所趨,再說,你那個企業已經開不出工資,再這樣耗下去,恐怕連買斷工齡的錢也沒有人出了。”
“我知道,我知道,那就沒有別的辦法了?”她用祈求的眼光看著我,那眼光里摻雜著許多復雜的東西。她的一雙手捏著圍巾,不斷地來回揉搓著。我正要上前再跟她解釋,辦公室的門又開了。
“溫主任,頭兒說一會兒開會,讓你匯報轉制的事。”小劉站在辦公室門口跟我說。
“知道了。”我點點頭。
女人坐在椅子上,沒有要走的意思,眼淚順著臉頰無聲地流下來。
“你看看你,又這樣,哭有什么用?你還年輕,再找一份工作不就得了。”
“我拖個孩子,哪兒還有人愿意要我。”
我不知道說什么,“要不,你在這兒等我開完會回來再說。”我拿好文件夾,準備出去。
“行了,我也給你添不少麻煩了,我還是自己想辦法吧。”望著她的背影,我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樣不是滋味。
“想什么呢?”菲兒用手指捅我。我重新戴上圍巾,穿上棉衣,對菲兒說:“走,跟我看看去。”我拉著菲兒,再一次朝市場走去。
天色越來越暗,雪稀疏地落下來,像米粒樣的碎屑。秦素文的烤串攤已經不知去向。
那家面館還沒有打烊,我和菲兒掀開門簾,進到屋里。
“關門了,關門了,明天再來。”店主在里間聽見動靜,忙不迭地說。他回頭見是我,“哎呀!這大半夜的,你怎么又來了。我說你吃那點兒東西吃不飽么,可是現在都是涼的了。”
“我不吃飯,我想問,那個賣羊肉串的女人哪兒去了?”
“哪兒去了?回家了唄。我說你這個人還真軸,這大半夜的不在家睡覺,跑這兒來找人,你也不看看現在幾點了?”
雪,已經大氣磅礴地下起來,大片的雪花漫天飛舞。街道、房屋、樹枝已經披上了一層白紗。
第二天晚上,我又去了馬路對面的市場,但是沒看見那個叫秦素文的女人。
半年以后,我因為病情復發,又住進了醫院。再一次手術,再一次化療,我已經骨瘦如柴。
同一病房里有三張床,我占據了靠窗的那張。靠門的那張是一位小姑娘。小姑娘臉色蒼白,很少說話,長時間半睡半醒地閉著眼睛。中間的那張,據說已經有人了,但是一直沒見到人影。
我因為化療,時常嘔吐不止,惹得那個小姑娘情緒波動。她把被子蓋過頭頂,身體在被子下面輕微抖動,似乎在抽泣。
下午三點多鐘,一個女人領著一個臉色蒼白的小男孩,手里拎著住院用的日常用品走進病房。我一眼就認出是秦素文,她也看見了我,并對我微笑著點點頭。
她的臉比以前黑了許多,身上穿著一件紫紅色風衣,那雙好看的杏核眼沒有變,只是比原來明亮了很多;她的嘴唇不再像以前那樣蒼白,多了一點紅潤,是那種從體內散發出的天然色澤。
她沒有認出我,以我現在的身體狀況,她不可能認出我。
她先把東西放在凳子上,蹲下身打開床頭柜下面的拉門,又一點兒一點兒把東西塞進拉門里,然后抽出一條白毛巾放在枕頭上。
“壯壯,你先上床躺著,我去打點兒熱水,一會兒就回來。”她把小男孩抱到床上,拿起暖瓶,一溜煙兒小跑著出去了。
小男孩雖然生著病,但非常活潑好動。他一會兒把白毛巾蒙在臉上,一會兒又掀開枕頭看看,然后,看著我說:“阿姨,你會講故事嗎?”
我躺在床上,用眼睛偷偷瞧著門邊床上的小姑娘,發現她正皺著眉頭,一臉的不快。顯然,她不喜歡病房里弄出任何聲響。
“壯壯,你又纏人了哦,來,躺好,一會兒醫生就來給你會診,你要聽話哦!”
我努力平復自己迫切的心情,對小男孩說:“你是壯壯?”
“嗯,我叫盧大壯。”
“好響亮的名字,她是你媽媽?”
“她是我阿姨。”
阿姨?我疑惑地看著秦素文。
秦素文沒有回答,她對壯壯說:“好好躺著,小心一會兒累著,又難受了。”
“你真的不認得我了?”我問秦素文。
她瞇縫著眼睛思索了一會兒,然后搖搖頭。
我剛要說話,手機響了,是菲兒,“你今天的化療做完了嗎?一會兒我過去哈。”
“你不用來了,我現在已經沒事了,你還是讓我好好休息吧。”
“那好,那我晚上過去。”
撂下電話,我對秦素文笑笑,她端詳了我半天,遲疑地說:“你是溫主任?”她已經認出我來,只是還有點兒將信將疑。
“看你現在的樣子,過得挺好吧?”我用試探的口氣問。
“挺好的!挺好的!”
“那你這……”我指著壯壯。
她笑了,“你怎么病成這樣,我真的沒有看出來,你現在跟原來可是兩個人了,真沒想到能在這兒遇見你。”
我也沒想到。我想告訴她,去年剛冷的時候我看見過她,后來也找過她,可是……我想了想還是不說為好。
我打開水杯,喝了一口水,然后起身下地想去廁所,秦素文過來扶我,我擺擺手說:“讓我自己來。”
我坐起來,晃晃悠悠地下地,搖搖擺擺地往病房外面走。
“怎么沒人陪你呢?”她問。
“有,我今天的項目都做完了,針也打完了,我讓他們回去休息了。”我不能說我沒人陪,我沒有孩子,丈夫在山區扶貧。我舊病復發,沒有告訴他,我不想成為他的累贅。
“等會兒,一會兒回來,你給我講講你這些年的經歷。”我說。
窗外又起風了。我從外面回來的時候,那個小姑娘和壯壯都睡著了。
“我那會兒,覺得天都塌下來了,你知道的。可是,我得活啊!我還有孩子,如果我倒了,誰來管孩子。
孩子放暑假的時候,我拿買斷工齡的錢帶著孩子去了我丈夫的老家四川德陽中江縣。我想讓孩子知道他爸爸小時候在哪里長大的,那也算是他的故鄉。可是,我們剛到德陽就遇上了暴雨,出不了站,我們只好留在里面等雨停。滯留的旅客很多,我正在猶豫怎么度過這個暴雨的夜晚,就有幾個女人上來拉扯我,想讓我住她們的店。我甩開她們,去了候車室,可是候車室的人也很多,已經沒有座位了。正在進退兩難的時候,一個男人從座位上站起來,把我讓到座位上。我千恩萬謝,和孩子在椅子上度過了那個夜晚。
好不容易等到雨停,又傳來去老家的公路有一段因山體滑坡被掩埋的消息,搶修最快也得一天時間。我一夜沒合眼,疲憊不堪地倚在座椅上,不知如何是好。這個時候,我才看清給我讓座的男人的模樣,憨憨的,看著很踏實。
他問我去哪里,我告訴他去中江縣。他看了看外面的天空說,今天去中江縣恐怕不成了,要不你找個旅店先住下吧。我得走了,昨天晚上的暴雨把我撂在這兒,耽誤了進貨,我得趕清晨的頭班車回去干活兒。
他說話的時候并沒有看我,而是望著天空,我對他的話很感興趣。我想,反正也是等,還不如看看他干的是什么活兒。
能不能帶上我,我在這兒閑著,心里慌得很。我不會拖累你,我也想找點兒事做。我的話剛飄出口,就覺得有點兒唐突了,可是,話已出口,收是收不回來了。
他猶豫片刻,用手撓撓頭說,我那活兒又臟又累,不太適合你。
什么活兒?我睜大眼睛。
賣羊肉串。他說。
賣羊肉串?
對,我來這里有幾年了,一直干這個。我也干不了別的,這個活兒雖然辛苦,但是成本不高,我承擔得起。其實,干這個挺好,可以遇見各類人,也能見識以前沒有見識過的事,我覺得很快樂。
一直以來我都沒有一個明確的方向,我不知道我自己到底能干什么,現在,他的話似乎讓我找到了方向。
如果不太麻煩的話,你能不能帶上我,讓我試兩天。我不要錢,有飯吃就行。
他看著我,我那兒沒有你住的地方。
我自己找住處,不會連累你的。我生怕他拒絕,馬上申明。
他很為難,想了一會兒。看著我眼巴巴的樣子說,好吧。
他住的房子既狹小又黑暗,還沒有窗戶,我想象不出在這樣的環境里他是怎樣生活的。
我在鄰近的地方找到一處小旅店安頓下來。
我從最基礎的選肉開始學起。其實,干這個活兒,前期的準備工作還是挺煩瑣的。我每天都幫他打下手。他要去買肉,買回來后要洗,要去筋膜,然后切成小塊進行腌制,腌制時要準備各種作料,再把肉塊穿成串,還要準備炭火。總之,白天一刻都閑不著,第二天中午拿到市場上賣,晚上到酒吧或者人流聚集的夜市上賣,有的時候要賣到半夜或者凌晨。我在那兒待了一個星期,心里實在過意不去,就在一天早上收拾好行李,帶著孩子離開那個地方。”
“那你沒去你丈夫的老家?”我興致不減。
“去了,也是匆匆忙忙就回來了。”她給壯壯掖了一下被角,接著說,“回到家,我就開始著手干這個行當,也沒什么難的,就是辛苦點兒,習慣就好了。”
“那,這是怎么回事?你再婚了?”我指壯壯。
她看看腕上的手表說:“不早了,該休息了,身體要緊。”
關于壯壯,我雖然有疑問,但還是遵從她的提議,睡覺了。
壯壯依然活潑可愛,從外表看不出有什么大病。他還總是把秦素文帶給他的好吃的、好玩的東西拿出來堆在小姑娘的床邊。如果小姑娘閉著眼睛裝睡,他就把東西放到她的床頭,然后沖著我們伸舌頭、做鬼臉。
壯壯的天真爛漫,讓那個小姑娘的心情好了一些。說實話,我的心情也好了很多。
一天,我去醫院外面的報刊亭買雜志,看見一個中年男人來到醫院,直接進了我的病房。我沒進去,坐在病房外面的走廊里想著心事。
一會兒,中年男人出來,叮囑秦素文幾句什么就走了。
“你怎么不進病房,在這里站著干什么?”菲兒來了,手里拎著我要的日用品。
“出來透透氣。你今天不用去基層調研啊?”我示意菲兒坐下。
“今天不去了,我跟頭兒說了,你沒人照顧。”菲兒挨著我坐下了。
“少拿我當借口。”我不領情。
“真是好心沒好報。”菲兒挽住我的胳膊,臉上掛著得意的笑。
回到病房,秦素文正給壯壯洗衣服。午后的陽光透過玻璃窗灑在她黑里透紅的臉上,我急不可待地問:“剛來的那人是誰?”
“我表哥,給壯壯送點東西。”她臉上的汗珠正往下滴。
她看我一臉疑惑,解釋說:“這話得從頭說起。那次去四川,那個賣羊肉串的男人做了一件讓我意想不到的事情:他自愿出錢,幫助那些因為窮差點兒沒了未來的孩子。當時我就想,等我賺到錢,也去資助貧困山區的孩子。我母親的娘家也是山溝的,我把錢捐到婦聯的時候,就告訴他們要捐給那里,后來,我想知道我捐的錢到底給了什么樣的人家。
第一次去壯壯家嚇了我一跳。一間半簡陋的低矮房屋,有的地方墻皮已經脫落。里間是臥室,外間是廚房,一鋪土炕,上面沒有席子,用舊畫報粘的炕面,炕上有兩床破鋪蓋。炕的對面有一個木制大柜,已經舊得看不見油漆。屋里一個呆呆的女人散著頭發,看見人進來就往墻根兒躲。那是壯壯的母親,是個智障者。這個女人生完壯壯后,病情愈加嚴重,已經完全不能自理。有人勸壯壯父親把孩子母親送進精神病院,但是孩子父親堅決不肯。就這樣,孩子父親拖著一條殘疾的腿,一邊照顧幼小的孩子,一邊又要照顧瘋癲的女人。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扯大了,孩子又病了。”
“壯壯得的什么病?”我問。
“就是鼻子和牙齒總出血,等會診呢。”她說,他們住在大山深處,出來一次要過三道嶺,這些年山區雖然修了公路,可是出來一次也不容易,何況壯壯父親的腿有殘疾,行動不便。
菲兒把我扶到床邊,我上床躺下,看著窗外的流云,接著傾聽秦素文的講述。
“我也是從農村出來的,對他們的難處感同身受。這些年,國家實施了一系列扶貧開發政策,現在,又把關愛貧困人口提到議事日程。我舅舅家表哥,在改革開放初期就去了深圳,這些年做生意賺了不少錢,半年前,他知道我捐助的事后,決定回家鄉創業,幫助山區貧困戶脫貧。現在,在鄉政府和鎮政府的支持下,他在山村建起了養雞場、香菇種植場,最近還要在下面河套建養殖基地。
壯壯家也有扶貧干部一對一地幫扶,已經建起了香菇大棚,壯壯父親的生產熱情很高,壯壯的母親也被送醫院治病去了。我只幫他們照顧壯壯,相信未來的生活會越來越好。”
這可太好了。我沉浸在秦素文的講述中,像個孩子一樣,聽得津津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