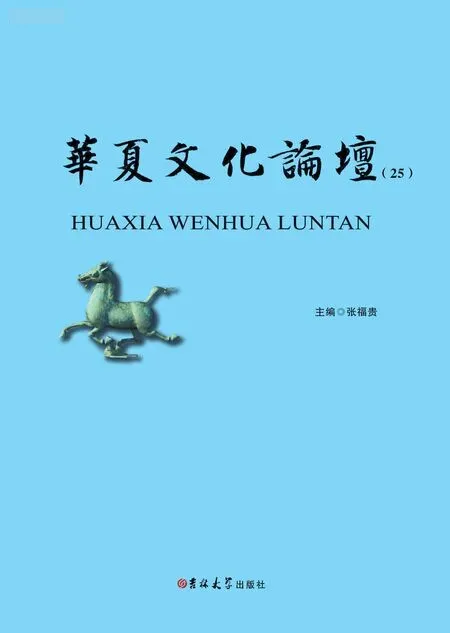探秘消費時代的生命延續
——80后作家生殖敘事的基本類型
馬芳芳
生殖是人類生存活動之始,是物種延續鏈條上的基本環節,人類的經濟、政治、軍事與文化的所有活動,歸根結底也都是從這個鏈條派生出去的次生形態,生殖的問題就是人類一個最基本的核心問題。作為有性繁殖的哺乳類動物,區別于植物界,也區別于其他與自然界共生的動物,生殖從來就是一個文化問題,與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婚姻制度、法律制度等種種制度緊密糾結,成為不同種族的文化標志。當一個種族的文化制度發生變異的時候,特別是基本的權利關系扭轉的節點,生殖制度就會隨之發生變異,相關的敘事就會發生急劇的演化。
1980年代出生的作家,生命的起點適逢社會文化的兩個裂隙,一是計劃經濟的驟然終止,突兀遭遇兇猛的市場經濟;二是“一胎化”的計生國策——一九八〇年九月與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布文件,從提倡到硬性規定“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前者使他們的成長顛簸于家道的起伏與親屬關系的結構性裂變,身陷物欲橫流的消費時代。后者使他們的精神心理被民族集體的生殖焦慮有形無形地擠壓。這就使他們的生殖敘事具有前所未有的復雜性,地區與社群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社會撕裂中的層級固化,全球化進程中外來文化的沖擊,信息時代獲取方式的更新,與高科技數碼化頻繁刷新的“日常生活中的革命”,都以光怪陸離的形色投射在他們的生殖敘事中,最集中地體現出一代人成長的沉浮、身臨其境的心靈掙扎、文化批判的鋒芒與最終走出誤區的生命感悟,以及自我救贖的不同路徑。他們講述的生殖故事是一代人成長的心靈備忘錄中折射出的民族精神震顫的光譜,為我們提供了最鮮活的社會學、文化學與人類學的資料,也呈現出新的美學形態。
如果說中國文化場域分為以制度為核心和以市場為核心的兩大區塊,那么80后文學群體就是兩種場域交叉共生的最好代表。從20世紀90年代末對80后作家的造星運動開始,韓寒、郭敬明、張悅然、春樹等進入大眾視野;此后從主流文學刊物誕生出來的蔣峰、笛安、鄭執、宋小詞、文珍等人,則通過主流文學獎項而進入文學體制;也有部分隨著互聯網興盛而百花齊放的市場滋養出來的寫手,如辛夷塢、孫睿等人后來也一并被文化體制所吸納。可以說他們起點不同,但是殊途同歸,主流文學界以代際的“霸權”集體命名了這一代人的文學。因為這一代人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出生的權利就被憲法規劃的一代,因此他們的生殖敘事也必然有著前無古人的獨特形態。作為一個群體,他們的生殖敘事有著極大的相似性,大致都是以處于邊緣的民間立場為基本的視角,其中包括鄉村視角、都市外來者視角和性別視角,敘述成長中見聞的種種生殖故事以及心靈遭遇的震蕩,兒童、少年、青春,直至為人父母的成年,不同的周期是這個基本的視角中的旋鈕,旋轉出不同層面故事形態的變化,以及語義場的疆域。因此,大致可以歸納出如下的敘事類型,并且掃描出各類型之間動態的發展曲線,以及聚合為文化批判之維的同一敘事立場與最終走出心靈迷津、建立生命倫理詩學的自我救贖之路。
一、童年視角:窺視“非法超生”的悲情故事
為了應對“天下第一難”的阻力,1986年5月中央[1986]13號文件,用法規制定了人們的生育的懲罰條例,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正式完善。這一不斷完善的嚴密的基本國策,瓦解了幾千年農耕文明深入的多子多福、養兒防老等生育理念,遭到首先來自鄉土社會的頑強抵抗,以各種方式與政策博弈。迫使1980年代以后出生的一代人,出生之始就面臨著不同的機運,生殖的主題超前進入他們的頭腦,成為童年記憶中最普遍的“精神強迫癥”。
因此,他們的生殖敘事幾乎是和成長敘事伴生的現在進行時,獨生子女群體遭遇的所有問題,都有民族集體生殖的宿命背景,大規模的宣傳攻勢與嚴厲的懲戒方式,使他們過早進入成人的思想維度,生殖的秘密公開化,超越了他們自然年齡的心理承受力,這形成了子一代窺視非法超生的基本敘事模式。
從孩童時代開始,他們身邊因為違反政策和逃避政策的種種故事的碎片已經是深嵌在他們心靈的創傷記憶中最恐怖的夢魘,這以鄉土社會出身的作家最強烈。比如,1986年出生于湖南隆回縣鄉村里的鄭小驢(原名鄭明),童年的記憶就是以對民間的觀察為最基本的敘事視角。他的長篇小說《西洲曲》以第一人稱的敘述人和親屬稱謂的人物關系講述父母一輩人(也包括了同輩年長者)的生殖故事,運用反諷的手法,借助南朝樂府《西洲曲》浪漫的文化鏡像反襯出計劃外生殖的悲情,戲仿勾連法片段式的結構方式連綴出親友們逃避計生的各種厄運故事。曖昧、朦朧的意義表達正是過早涉世的兒童認識理解世事最基本的視角與懵懂的感受,上溯可到蕭紅《呼蘭河傳》的生殖敘事,王大姑娘與馮歪嘴子未婚生育幾乎是這個時代超生故事的前塵往事,只是文化制度由婚姻的觀念約束,變成了純粹生物學的數碼管理法規,這幾乎是歷史的勾連法,雙重的文化鏡像映射著同樣的生殖悲劇,只是單本的故事,變成了連臺的戲劇,情節有變異,而主題都是一個——不法的生殖。在蕭紅的時代非法生殖尚有一線生機,身處話語的絞殺生命悄然在親情中延續,而在高度數碼化的計生時代,只能以各式各樣的悲劇完結,并且瓦解了最基本的生命倫理。作者圍繞著第一人稱的敘事人“我”展開了非法懷孕、躲避稽查、悲劇發生、后續的其他人倫慘劇的情節序列:有我母親懷胎七月被迫引產;姐姐未婚被騙懷孕堅持不打胎,在慘遭強暴之后孩子流產;計生組的突擊檢查使得北妹躲進菜窖里,孩子因缺氧早產而死,死嬰的男性體征也使得北妹痛苦自殺,她的丈夫譚青在家破人亡后成了反社會的殺人犯,負責稽查北妹的羅副鎮長獨生子慘遭譚青仇殺,他開始信奉基督教,每天對人講述神可造人的神秘囈語。鄭小驢以親屬稱謂連綴起多起生殖敘事,而且基本情節不斷重復,流露出他感同身受的情感指向與無法治愈的童年心理創傷。“兒童視角的描述”則將敘事變成一種噩夢式的體驗,正如童慶炳所言:“隨著一個作家的經驗的不斷豐富和變化,他就可能不斷地‘修改’他的童年經驗,從而變異出新的內容,發現它的新的意義。”以當事人來承擔民間現場的記錄更加具有震撼性,這些童年記憶也為成年后的作家對價值重估積蓄了情感和文化的源泉,編輯出可靠的生殖悲劇的篇目,成為新一代人的生命倫理意識形成的最初培養基,是他們來到和平人世的初始場景中最隱晦恐怖的拼圖。
在兒童窺視的父母一輩及年長者“超生”悲情的故事類型中,蘊含著古老的母性悲劇,而且是兩代人重復的共同情節,基本的結構有變異,但母性的悲哀是一樣的。窺視的敘事視角,展現的本雅明所謂“意象的蒙太奇”聚合的生殖語義場中,是子一代的目光質疑現代文明的倫理基礎,對數碼化管理的排斥與生命詩學的生機萌動。
作為獨生子女的80后作家,女作家則更敏感于由此產生的身份尷尬。其中以張悅然中篇新作《大喬小喬》最典型,她著力講述的就是溢出計劃的生命文化身份的曖昧與自我心理博弈的艱難掙扎。小說中的敘事視角是全聚(上帝視角)加內聚焦模式(主體的心理走勢)以第三人稱和第一人稱不斷切換的方式敘述,但仍然是以兒童的窺視為敘事的起點。敘事主體許妍以第三人稱和心理內置視角相切換的方式,追溯了從兒童時代開始就因為自己的非法身份而四處躲避的慌亂體驗、審視原生家庭超生的不幸遭遇、窺視合法出生姐姐的生活歷程,直到自己成人離開家鄉,才切換為上帝視角從故事的全部發展進行敘述。但是作者還是采用一種較為客觀的敘述方式,以一種相對隱蔽的態度敘述故事,使得主人公許妍能以另一種身份進行重新的審視和躲避。但從始至終,對于非法與合法的身份糾結,都是構成敘述人許妍和喬家血緣關系夢魘核心的命題。
都市長大的張悅然和鄭小驢窺視非法超生的情節模式大有不同,她沒有悲情的高調質疑,而是將視角對準非法超生者的心理演變,低調客觀地延展,讓結論以人物心靈的邏輯呈現給受眾。她的命運因此始于原罪(超生),心靈的重負也如影隨形,計劃內出生的姐姐喬琳成為她存在的陰影,而她又成為喬家整體的陰影。許妍成年后進入都市,她的人生價值因此在全球化的時代被重新自我建構,開始恐懼別人知道自己本姓喬,努力迎合富二代男友及男友家族需要的兒媳品位,并建立起在都市北京安身立命的生存邏輯:不回老家、偽造出身、拒絕和原生家庭交往。作者用內聚焦模式,在敘事視點移動的過程中,真正的敘事者寄居于人物的意識和感官中,在用全知視角描述的同時,偷偷粘附于許妍的內心深處,成為她靈魂的窺探者。許妍的不孕癥隱喻著無果的婚姻以及為此徒勞的種種身份偽裝,對應姐姐喬琳的未婚生育,使得兩人的身份最后融為一體。張悅然以習以為常的見怪不驚,冷靜客觀地敘述這一對姐妹遭遇計生時代的厄運,借助題目的原型文化鏡像,以辛辣而又心酸的反諷,轉喻出計生/消費時代女性的文化處境。古代的喬氏姐妹成功嫁入豪門,得以被鎖在銅雀樓中,現代的喬氏姐妹則走在不歸路上,要么死亡,要么退回原生家庭,此外別無出路。這個家庭的日常生活陷入了混亂,喬父因超生而丟掉工作忙于上訪,喬林的心理創傷成為追逐金錢的內驅力,張悅然波瀾不驚的敘述,以近于羅蘭·巴特所謂零度敘事的低調,客觀冷靜地呈示了喬家兩姐妹在命運節點各自的文化認同。看似是一個家族因計生政策走向沒落的悲劇故事,但敘述的重點是喬林自我治愈的荒唐之舉,內置著中國隨著市場興起,時代急劇變遷的轉型時代,民族精神的迷茫和價值觀念的紊亂。多年后,媒體把喬家的悲傷作為“獵奇城市故事”納入時代變革后的故事類型,這又使許妍獲得的合法身份成為她渴望進入都市富人階層的前定詛咒,這種荒誕的身份變形記,再次成為她逃離血緣家族身份的動機,也是對童年噩夢又一次的簡要重復。
80后這一代人不是遭遇計劃生育的被迫害者,就是親歷者,周圍關于計劃生育的“精神強迫”從幼年開始,一直貫穿他們成長至青少年時代。窺視者的身份作為隱形作者,也作為作者的第二自我,他們的反應并不像父母一輩那樣激烈,更像一個在場的幽靈,窺視中的心靈震顫伴隨著精神的成長。
二、多角度變幻:殘酷的青春物語
80后一代,經過30年的獨生子女政策規劃后,又于2011年11月,適逢國家生育政策的調整,中國各地全面實施雙獨二孩政策,到2015年國家又實施全面二孩政策。80后一代人都趕上了生育的最佳年齡。此項政策的調整,對80后生育的觀念和行為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和震動,他們的生殖敘事也隨之轉變。他們的生殖敘事伴隨著生命周期的變化,貫穿著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文化史,生殖也成了他們正在發生的生存體驗,童年的視角的窺視自然切換為此在的生命體驗,大量蒙昧生殖的殘酷青春物語成為80后作家普遍的敘事類型。生殖敘事和青春敘事重合,圍繞成長的困擾分解出縱橫交錯的不同青春文本,都記錄了她們成長過程中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80后作家郭敬明早期的《悲傷逆流成河》是郭敬明第一次描寫普通少年男女的成長故事,小說中底層的女孩易遙從十三到十八歲的成長的青春故事構成敘事的主干。易遙16歲開始混亂的戀愛直到發現自己懷孕。她迷茫地處理著自己的身體,隨著打胎這一違反了同齡價值判斷的事件升級,她周圍的環境成為群體的惡,進一步推進了她向歧路上滑落,成長變得異常艱難,“無主名、無意識殺人團”的道德迫害。小說從男性齊銘的視角對流產場景進行了殘酷的描述。對隱秘之事的血腥描寫,用中產階級標準的優秀少年立場和價值觀,展示了這驚心動魄的一幕現場,抒發心靈遭遇的震顫式體驗;渙散而蒙昧無知的易遙,在即將付出生命代價的時刻,反倒是一副漫不經心的態度,兩相對照更顯出這一則青春物語情境的殘酷。郭敬明用這個血腥的青春物語為休止符,結束了自己悲傷的成長敘事。
80后的其他男性作家則更善于將社會文化現象內化為精神心理的幻覺,以虛構的方式升華為人類末世寓言的精神高度。李德南《遍地傷花》中的大學生周克因沒有避孕導致女方宮外孕摘掉了子宮,使得莜麥從此和男友周克產生性交恐懼。轉喻出男性在未婚打胎中產生的恐懼和負罪感的同時,也表達了身陷現代文明倫理悖論中的主體,在性別的博弈中心理返祖的荒誕感受,順便解構了進化主義的文明觀,是米歇爾·福柯式的批判,胚胎不屬于人類的拼圖臉和筱麥子宮被摘除的身體相呼應,是現代人超越倫理悖論之上、喪失了創造生命功能的焦慮,性交的恐懼則是生理心理退化的表征,人類在墮落。
青春敘事中愛情本該是重要的主題,殘酷青春敘事的類型基本情節相似,都是成長陣痛、未婚先孕、極端形式打胎。甚至其發生的情境順序都有類似固定(從原生家庭不幸或父母、學校管束壓抑)——結識會帶來殘酷情節的人物(流氓、騙子、無能的少年)或遭遇意外(校園霸凌、引誘)——災難降臨(懷孕打胎、身心受傷、死亡)。形成一個殘酷青春成長敘事的基本模式。而敘事視角也多角度并行,可以容納各方面聲音,整體形成復調的敘事方式,使少年的殘酷青春更加趨近客觀,也使得殘酷在多視角的拉伸中意義多元化,更加觸目驚心。使整個敘事作品因為充滿這種心理張力而更富有魅力。
三、全知視角:荒誕生殖的社會悲劇
80后作家隨著年紀的成熟,很多人已近不惑。除了對自身的記錄,他們的視線也在不斷向社會、乃至更廣的方向延伸。作家的責任也漸漸融合到他們的作品中,而作為人類最為古老的生殖命題,在一些80后作家筆下,也滲透了哲學的思考和對人類、文化意義上的反思與批判。很多作家潛意識中對這一巨大母題充滿著敬畏,用隱晦的象征描述著自己對生殖的理解和感悟,也會從一些描述中內置隱喻。消費時代來臨,人的異化現象,一直是他們想要批判的主題,他們通過對畸形生殖的描寫尋找對時代問題的答案,通過某種隱疾的形式,揭示行為背后的隱秘原因。這樣的故事基本一般采用一個全知視角或者第三人稱的心理視角。作者躲在作品背后,把自己的真情實感投射到各個角色中,達到全知全能的敘述效果。
對于生命倫理的質疑以對合法化的人工流產最為集中,前幾代作家通常是以非虛構的報告形式直述,多以對女性的悲憫為主題,流露著文明主體的良知與潛在的自信。而80后的作家則更多地集中在對女性生殖功能的審視,以及與社會文化變遷中的價值轉換,極端的例子是在消費主義盛行的時代,女性的生殖功能也作為商品被消費。宋小詞的《血盆經》中,智障少女從十五歲就開始被婚配,到二十歲已經嫁了四家,生完兒子之后,她就可以重新成為自由的人,在連續的轉嫁中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生殖工具人。民間以她是一個“俏八字”和誰都很合為借口,掩蓋了集體心理中對待翠兒的買賣行為的罪惡感,群體的愚昧行為合謀剝奪了她的人性權利,由古老的傳宗接代的生殖理念置換出強大的行動力,在一個消費主義的時代上演著荒唐的生殖悲劇,女性的身體被分解得只剩下了子宮的價值。宋小詞是一個特別關注鄉村遭遇城鎮化擴張侵襲的80后女作家,她的視角聚焦逐漸縮小到鄉村中的那些眷戀鄉土或者逃離不了鄉土的老人、孩子、失智者,描述他們和鄉土捆綁在一起的無望命運。而女性生殖功能被消費的極端生殖敘事,也延續著五四新文學中的情感史,是柔石《為奴隸的母親》、羅淑的《生人妻》、許杰《賭徒吉順》等作品代孕母題的惡性延續,而鄉土社會的愚昧保守則轉變為鄉村迅速潰敗的歷史文化語境中,其中都涉及女性僅剩的代孕屬性。對弱勢群體的施暴依然在民間被默許,而且母親的文化功能也只剩下生殖一項,連哺育也被刪除,因為是智障之人,只有子宮的功能凸顯出來,具有特殊商品的價值。
現代主義文學的衰敗母題再一次在80后作家群體中高峰涌現,家族的衰敗是一個重要的分支。顏歌《我們家》中“我的爸爸”,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好男人”,是鎮上最大豆瓣廠的廠長,算是鎮上事業有成的代表。“爸爸”就是平樂鎮一個中國小縣城的化身,農耕時代結束,后工業社會席卷而來,小鎮的民間鄉土宗族系統被打破,曾經不變的超穩定的家族傳統被外來的消費文明大規模沖擊,“爸爸”作為一個小鎮的喻體,以寫實和象征的手法完成故事的敘事。他從對自身生命本身的周期變化的感觸出發,并用男性原始的方式抗拒著這些變化,在外面找年輕的女人性交,拼命挽留自己的生命力。如亨利·列斐伏爾所言:“每一個獨立活動源于一個微觀決策,而且因為這些獨立活動系列是在一個與生產緊密聯系起來的社會空間和時間里展開的。換句話說,像語言一樣,日常生活包括了表現形式和深層結構,深層結構蘊含在日常生活的活動中”。寂寞和欲望、物質社會的不成文交易,代替了紅高粱地里面野合的浪漫灑脫。情人懷孕,他有些得意地想要留住這個孩子,這種豪情象征著固執挽留住身邊的那些消失的日常生活,哪怕放棄以往遵守的道德規范、打破舊的文化秩序,為這個不倫的生命抗爭。作者把這種傳統文化面對生命本能壓抑的對撞放置在生殖的敘事中,以情婦懷孕來展開文化問題的倫理探討。在最后成了荒唐的一幕鬧劇——爸爸和情人的孩子是“司機”與情人合謀騙爸爸錢財的陰謀,這個當代中國版的“陰謀與愛情”,象征著消費時代道德淪喪的罪惡,而爸爸對現有生活的顛覆和抗爭被唯利是圖的陰謀徹底打回原形。
顏哥作為80后的代表作家,用象征主義的手法把中國最平凡的家庭和人性中的小感觸寫成了一個衰敗文化的大寓言。小說敘述視角是一個叫薛興逸的傻孩子來完成的,這個從福克納到阿來都運用過的敘事技巧,形成更深刻的隱喻,只是性別發生了轉換。她沒有行動和思考能力,卻是洞悉所有秘密的全知者,看似無知,卻客觀記錄了一個家族的興衰。薛興逸本是這個家族中唯一的孫子輩人物,由于血緣的合法而具有進入家族隱秘的便捷,又因為弱智,可以不用正常的道德和情感來客觀敘事。類似《紅樓夢》中冷子興演說榮寧二府的旁觀者敘事功能,因為是家族中人,又增強了在場者的可信度。而敘事者的身份也寓意了這個傳統中國家族在變遷的大時代中的衰落。
在荒誕生殖的悲劇中,作家大量運用全知視角,輔之以身體的象征隱喻表意策略,普遍具有整體潰敗的大寓言的文體特征。體現著80后一代人,對生殖的獨特倫理認知和對文化、文明、社會的批判精神,以及以身體為中心整合天/地、男/女、城/鄉、貧/富、正/邪、貞/淫等種種差異范疇的修辭特征。
四、多元視角:健康生殖的新生祝福
80后這一代,很幸運地迎來了第三次科技革命,如果說大航海帶來人種與物種的交換,那么互聯網興起帶來了世界空間的縮小。隨著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80后這一代具備基本的外語知識,與世界的溝通也因此更加便利,這是由于生產力發展帶來不可逆的關系變革,國家之間的交流和全世界的人員流動,使得思想與思想的交融日益多元發展。
這不僅僅是一代人生存方式的走向,也是個體隨著眼界的擴展,而自覺的選擇。此時的80后已從青春走向生命的盛年,他們的人生主題也從單純的反叛轉向對世界、自然、生命等等的深刻思考和自我審美的確立,為人父母之后的一代人,開始與父輩及其抗拒的某些恒定的價值觀和解,曲終奏雅使他們的生殖敘事從窺視開始的悲情、殘酷物語到荒誕戲劇的一路痛苦體驗與驚悚的歷險終成正果,對于健康新生的祝福成為一個新的敘事類型,承載著他們最終的精神歸宿,具有神學意味的生命倫理也由此建構完型。
80后的文化習得和全球時代的背景相重合,他們的文化血液中也就自然而然地雜糅著中國傳統文化與外來文明。這使他們相近的回歸式祝福新生的生殖敘事類型,也呈現出交叉錯落的泛文本背景與形態各異的美學特征。
韓寒的小說《1988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就是較為明顯的公路小說的代表作品,文體和美國作家杰克·凱魯亞克創作于1957年的長篇小說(On the Road
中文譯《在路上》相似),這篇小說也成為80后表達自我最前衛的時尚潮流標志,1988的歷史節點與邂逅生殖的基本情節重合共生,遭遇歷史與遭遇生殖互文見義,為一代人的精神狀態做了生動的注腳。而且,“漂泊者的邂逅敘事”中不期然而遇的生殖事件,新生作為起點,比20世紀杰克·凱魯亞克《在路上》的主題加入了更多未來希望的成分,80后已經不是“迷茫的一代”,他們通過一個迎接生命的方式續寫了人生的價值。韓寒以第一人稱的敘事者,從始至終講述一個沒有目的地的流浪者“我”陪伴一個患有艾滋病、臨盆在即的妓女一起漂泊的故事。故事從男人和女人的原始欲望開始——當嫖客遇上妓女,當得知妓女身懷有孕的時候,“我”心中涌起對一個陌生新生命的感動;患有絕癥的妓女由于孕育了父親不明的孩子而轉身為博大的現代地母,雖然是一個瀕臨死亡的絕望母親,但現代科學的阻隔手法成功幫助她誕出健康的嬰兒,她幸福地死去。病態的死亡與健康新生的接續,喚醒了漂泊的嫖娼者的良善本性,激活了他父愛的本能,義無反顧地承擔起代父的職責,這與20世紀初魯迅“救救孩子”的吶喊何其相似?而且更加樂觀,被毒害的母親生出了純潔健康的嬰兒。游記的古老文體與公路小說的現代形式,交織在這邂逅的悲催現代地母的生殖故事中,置換出勾連著五四精神、通達最永恒也是最神圣的價值——生生不息的生命倫理。這個公路之行也是一場具有象征意義的生命之旅,運用了詩的修辭手法,雖然母親娜娜生活不堪,哪怕生殖過程也帶著“紅字”般標志的恥辱符號——艾滋病患者,女兒則非婚生且不知道父親是誰,母女關系完全沒有現代倫理道德支撐和婚姻制度的保障。但是這個孩子卻被母親深愛、被陌生人祝福來到世間。孩子的父母和撫養人是誰都已經不重要,生殖被升華了,這是一個突破了道德審判,通過對健康新生的禮贊,寄寓作者對低賤職業和弱勢群體的關注、為他們發聲的道義擔當,因此這次旅行是一段具有社會意義的“行程”。而“我”最后帶著這個嬰兒繼續上路,倫勃朗式“浪子回頭”的主題借助邂逅的生殖故事得到全新的闡釋,意味著生殖之路對人性與社會追問的同時,也不言自明地使無聊的漂泊者的人生獲得了意義的承載。而邂逅生殖也是自成序列的敘事類型,鏈接著高爾基的《一個生命的誕生》和知青作家阿城的《迷路的接生漢》,并且演繹出新的語義:從喪父的女工之子,到父母雙全的邊地嬰兒,再到不知父親的病毒妓女之女,環境從大海之濱、深山密林到現代公路,漂泊者們一路走來,身份不斷轉換,接力式的主題則帶有意義鏈接的奇異功能,只是更復雜,更錯綜,更曖昧,也更純潔。整個故事是荒誕的,人物也是荒唐的,但是人性迸發,母愛的天性,卻回歸了質樸的自然。這次生殖事件伴著嫖宿、不倫,絕癥而艱難完成,臟亂不堪,也可以看作歷史急劇錯動中民族生存的整體象征。他以最為艱難的生殖狀態,凸顯了絕望中對生命本身的敬畏,一個帶有“骯臟”符號的女性轉為母體而變得圣潔偉大,回歸到生命本身的象征意義的同時,也象征著病痛中未來的希望,這是小說標題隱含的冒號之后的主要語義: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式的祈福祝愿。
80后一代人正在走出消費時代精神的虛無,他們已經漸漸成熟,人生經歷使他們有耐心開始反省曾經的迷茫和叛逆,對生命延續的思考是重建父子關系的重要環節,生育讓他們寬容理解了上一代人,很多作品中既寫實也象征,以各自不同的生殖故事,敘述自己內心的皈依路徑。這是一代人成人禮過程的心靈記錄,完整而千秋各異。適逢市場經濟的獨生群體的生殖敘事是一個民族遭遇現代性、融入全球化時代,集體心理的共時性生命圖譜,提供了最寶貴的急劇悸動的民族精神的心理資料,是一個種群隱秘的心靈密碼,一代人最終的回歸也是整個民族走出消費時代的迷津,生命節律中最健康的情感矢量。而他們生殖敘事的四個基本類型,從童年—少年—成年三個人生周期的時間序列呈現的不同視角的敘事方式,也以這一代人演繹生命延續心靈奧秘的精神光譜中,貫穿了整個民族在歷史轉型的激變時代中痛苦的掙扎與最終升華的精神心理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