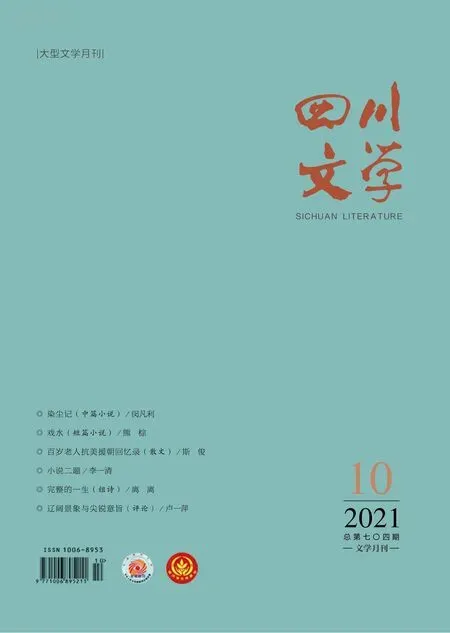向壁而生讀麥家
——關于麥家的不完全社會閱讀報告
□ 文/朱鐵軍 林培源 洪嘉陽 等
參與者:
朱鐵軍 林培源 洪嘉陽 向紅燕 劉小雨 何藝珊 劉大強 彭梟俊 何苗 王義樺 江關統籌整理:
洪嘉陽朱鐵軍(《特區文學》總編輯,現居深圳):
閱讀麥家是從《解密》開始的。時隔多年,追溯起當初的感受,坦誠地說,是有些模糊的。我想《解密》沒能為我提供一位叫作“麥家”的作家,小說所提供的文本和其文學能力,也并未能完整地說服我,我只感覺到作家寫得很用力,有些拖沓,甚至還有些邏輯傷痕和敘述失策。但可喜的是,在我們所熟悉的漢語文學生態里,它是陌生的,也是少見的。它的陌生性,則很容易被包括我在內的一部分讀者首先地認為文學性虛弱。隨后便是通過影視劇而折返閱讀的《暗算》,以及《人民文學》發表的《風聲》。這兩部作品讓我看到了一位明顯的自我進化的寫作者,作家更加從容地實現了個性化的風格建立。毫無疑問,麥家通過異質化的世界、人物、故事和理想主義與英雄主義的情懷力量,建就了一個“如現實般離奇”的敘述王國,他所展現的出色的結構能力和綿密的情節組織能力,以及“諜戰”這一類型題材的獨特視野,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眾所周知,麥家的成功也帶動了“諜戰劇”這一文學衍生品,這不禁讓我想到在其隨后幾年出現的盜墓題材網絡小說。作為一名讀者,單就閱讀本身而言,我在讀天下霸唱和南派三叔的時候,閱讀快感是高于麥家的,這是個有趣的現象。我想原因也很簡單,這是“前意識期待”造成的。閱讀之前,我所預期的,是故事化的網絡小說與文學化的麥家。李敬澤老師曾說,麥家的作品有獨特性,它沒有參照物。他也認為麥家的出現,于中國的文學環境而言是一個很好的開端。我非常認同。對于麥家的“接受史”,于我個人而言是一次思考和映襯,我所供職的期刊正在進行“文學的多樣性可能”的探索,我相信作為一個具有樣本意義的作家和其作品,對新時代文學的創作未來,是能夠提供更加多元的方向性價值的。林培源(作家,現居廣東):
初識麥家,是以電影的方式。2009年,根據麥家長篇小說《風聲》改編的同名電影(由高群書、陳國富聯合執導)于新中國成立60周年前夕上映,與當年的國慶“獻禮片”《建國大業》一道匯入了“國家主義敘事”大流。時隔多年,《風聲》仍是觀眾津津樂道的諜戰片“神作”。那時我還在讀本科,麥家和他的《解密》已經“火”了好幾年,《風聲》的銀幕光彩,大約也是通過網上下載,在宿舍里熬夜看完的。故事的情節早就模糊了,但觀影過程的緊張,詭譎幽暗的氛圍依舊歷歷在目。直到十年之后的2019年,我才第一次讀麥家。原因何在?首先,讀博期間,我的研究重心落中國現當代文學,20世紀60年代出生的一批作家,是我研究之余時時關注的對象,每逢這批作家出新作,便欣然研讀;其次,我向來對科幻、諜戰、武俠等“類型小說”不感興趣,但麥家這部“轉型”之作《人生海海》,其中涉及的“革命”與個體的問題恰好也是我感興趣的。在培浩兄長的大力推薦下,我很快就把小說讀完了。
后來和培浩兄交流,我又動起了寫作評論的念頭。主意既定,便從頭開始,讀了麥家的成名作《解密》和其他作品,搜集相關資料,一個月內就將評論寫完了。不曾想,評論輾轉到了麥家手中,受到作者本人的贊賞(那是最初一批針對《人生海海》的評論)。同一年,這篇文章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上發表,在學界泛起微瀾,我也陰差陽錯成為“半個”麥家研究者。
2019年5月,北大召開麥家《人生海海》的新書首發儀式,陳曉明教授主持,嘉賓請的是李敬澤和蘇童。活動當晚,我從清華騎自行車到北大聽講,第一次見到麥家。活動結束后,我與麥家一行人到五道口吃夜宵、喝啤酒、閑聊,度過了非常美好的孟夏夜晚。
2020年,麥家另一部重要作品《風聲》再版,出版方“讀客文化”聯系上我,邀我寫書評。11月間,我到杭州師大參加當代文學研究年會,開會間隙,與培浩兄前往西溪濕地的“麥家理想谷”,再次見到了麥家。
2021年,廣州一家做知識付費的公司邀我做小說解讀的錄播,合作的第二篇稿件,講解的便是《人生海海》。時隔兩年重讀這部小說,我又有了新的體驗。
我閱讀麥家的過程,是不折不扣的“逆行”行為,讀新作,再往前回溯,將作家的創作歷程分條縷析。這樣的閱讀,對同樣寫小說的我而言頗有助益。類型小說的敘事模式并沒有在《人生海海》中全然消隱。麥家借《人生海海》回望故鄉,實際上匯入了同時代作家的寫作主流,只不過是以其獨特的方式,這在當代中國文學中幾乎無人可以替代。
《人生海海》近期舉辦了200萬冊的紀念活動。我相信,麥家“傳奇”還將繼續。
洪嘉陽(學科教學語文在讀碩士,現居福建):
對于一個天真爛漫、向往美好的人來說,一般不會去主動接近懸疑、暴力、血腥的世界。從沒有涉足過這個世界的我機緣巧合之下,有幸了解到作家麥家,進而去了解他的書。麥家,是繼魯迅、張愛玲、錢鐘書后首位入選英國“企鵝經典文庫”的當代作家,茅盾文學獎得主,南方文學盛典年度杰出作家,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小說家。最近我拜讀了他的《風聲》《暗算》等諜戰小說,被《風聲》里面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
《風聲》分為東風、西風、靜風,其實就是從不同的視角對同一事件的敘述。東風是以李寧玉哥哥的視角去敘述,西風則是由顧曉夢的視角去講述。靜風則是作者對故事的補充,敘說著似乎不相關卻也有關的事。在此前,我從未接觸過這種敘述視角的小說。看到的小說更多的是,作者對同一件事的來龍去脈梳理得清清楚楚,把一個完整的故事情節娓娓道來。這樣的敘事視角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視角,這樣的敘事更為一帆風順,但也缺乏波折、懸疑。袁枚的《隨園詩話》中說道“文似看山不喜平”。麥家先生采用的這種敘述視角有效地使小說情節超出讀者的閱讀預設,又合情合理。使小說能符合讀者的閱讀期待,對于日益“挑食”的讀者來說,非常不易。在對麥家的訪問中,著名評論家何平也曾提到這個問題:《風聲》的寫作過程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述一個故事。你好像很享受這種近乎游戲的快樂。作家麥家回道:“我喜歡一個故事顛三倒四地寫。我不知道有多少故事值得我們去寫,但知道一個好的故事值得我們反復寫。好小說都是改出來的,我迷信這個。《風聲》也是這樣改出來的,它從最早的《地下的天空》出發,挨了一刀又一刀,除了心臟,其他都換完了。這個過程一點都不游戲,而是充滿挑戰。”確實能看到麥家的小說到處充滿著自我否定和篡改,也就是這種三重敘述對峙結構,因為對峙使小說的情節具有多種可能,懸念,形成更強大的藝術張力。就像麥家自己說的,不是真相或真理越辯越渾,而是多了視角、多了切面。我們接受的教育過于正面、單一,這不符合認清歷史真相的邏輯。在只有一個聲音的環境中,我們需要其他聲音,需要一個懷疑的聲音,一種懷疑的精神:懷疑從來不會傷害真相,只會讓真相變得更加清白、更加穩固。
小說的故事情節確實類似于網友所說的諜戰主題的劇本殺。把所有出場的人物從故事一開始就集中到一個場景中來,故事發生的時間跨度也短。故事主線是在猜測、試探、暴力中,找出“老鬼”,而“老鬼”需要想辦法傳出消息。在肥原一步步的試探下,我為“老鬼”提心吊膽。我無法想象一個正常人如何應對屢屢出其不意的試探,從相互檢舉到鴻門宴,再到驗筆跡,還有通過吳志國的死亡來指控李寧玉,再到“假營救”。隨著肥原的一步步緊逼、一招招試探,我既苦惱于分析誰最有可能是“老鬼”,又擔憂“老鬼”被發現會遭受非人的磨難。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當李寧玉的“老鬼”身份被顧曉夢識破時,我深深地折服于她的應變能力。通過自己的聰慧,因模仿顧曉夢筆跡而向顧曉夢道歉,置之死地而后生,套出顧曉夢國民黨臥底的身份,并以此威脅顧曉夢,甚至策反她幫她傳遞信息。有一段對麥家《風聲》的授獎詞道出了我心目中麥家作品《風聲》優秀之處:麥家的小說是敘事的迷宮,也是人類意志的悲歌;他的寫作既是在求證一種人性的可能性,也是在重溫一種英雄哲學。他憑借豐富的想象、堅固的邏輯,以及人物性格演進的嚴密線索,塑造、表現了一個人如何在信念的重壓下,在內心的曠野里為自己的命運和職業有所行動、承擔甚至犧牲。在李寧玉跪求顧曉夢那個情節,在李寧玉以死相逼顧曉夢,幫她傳遞消息,我深深為李寧玉所深深地打動了。一個人內心該如何的強大才能做到這種地步。
向紅燕(自由職業,現居重慶):
拜讀完《人生海海》這本書,感慨于麥家老師筆下的上校這一英雄形象,他天資聰慧,學木工一學就會,治病救人也能無師自通;當兵打仗不成問題,特務周旋亦不在話下。養貓是他重歸故里后“消磨”時間的日常;沒命根子是他成為村里人“笑柄”的源頭,他哪有什么“罪過”,不過是在保護自己的隱私不被他人知曉。可那個時代卻給了這個英雄一記又一記耳光。日本女軍官看他帥氣,將他軟禁起來當男寵,在他肚子上刻字,這成了他心中永遠無法抹去的傷疤。村里人喊他太監,窺探他隱私,還趁機批斗他,雖然他幫鄰里做過好多事,最后卻被自己的故鄉人活活逼得瘋掉。這是那個時代被欲望和好奇支配所衍生的悲劇。充滿好奇的人心促使他們總是想要了解真相。知道真相又如何,不知真相又如何?愚蠢的村里人無法明白,世界本身就是混沌且無序的,以平常心面對周遭的一切,接受優秀的上校和他不愿讓人知曉的秘密,給他個人空間,也給自己多個朋友,豈不樂哉!
在劍指人性本惡的同時,麥老師亦在有意刻畫難以言表的父子情,準確來講,是父親對兒子的一種本能似的父愛。在《人生海海》第3章第14節中上校給“我”講了一個挖煤塌方的小故事,父親為了哀求大家不要停下搜救工作,一直在講“你們把我兒子救出來后我就做你們的孫子,你們要我做什么都是我的命。”“講過千遍萬遍,喉嚨啞了還在講,從發生塌方后,十來天他就沒出過坑道,人家換班他不換,累了就睡在坑道里,餓了就啃個饅頭,誰歇個手他就跟人下跪。”這些細致入微地描述了父親的偉大。平日里父親嚴肅而寡語,但在危急關頭,他總會第一個站出來保護我們。這讓我忍不住想到自己的父親,他會為了想馬上見到我,而提前兩個小時在車站等我回家。通過這本書也讓我更加珍惜父親對我的好,更加明白父愛的真諦,更加深刻地認識到父母才是這世上最牽掛自己的人。
劉小雨(稅務局公務員,現居廣東):
第一次接觸《風聲》是看到影視劇版的剪輯,全場狼人高能推理深深地吸引了我。因此,我慕名去閱讀了小說《風聲》。不得不說,麥家實在太會講故事了,讓沉浸其中的讀者根本不知道這究竟是虛構的故事,還是真實傳記。小說正文共有兩部,東風和西風。東風其實是一個相對完整卻又疑點重重的故事,麥家從一開始的描述就在有意引導讀者相信故事的真實性。作者第一人稱的使用以及介紹《風聲》原型故事的來源,詳細的時代背景,細膩的心理描寫,貼合人物性格的對話,仿佛將塵封許久的歷史畫卷向讀者展示。它的精妙之處就在于此,看似符合故事走向卻又不合邏輯,讓人找不到頭腦。因為讀完東風并不意味著故事結束,西風的接續使整個故事更加真實以及符合常理。重復講的都是同一個故事,每一次的故事講解帶給讀者的都是全新的體驗。
閱讀此書時,我多次驚嘆于麥家情節推進的深厚功底,作為一個讀者,我迫切想要知道接下來主角的行動,想要知道老鬼如何在重重封鎖中傳遞情報。說實話,東風順理成章卻又撲朔迷離,西風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作者以及讀者對于故事的疑問。我從前從未見過如此的敘事方式,真假與否,全憑自己。
相較于《風聲》,《暗算》由多個小故事構成,講述了天才“聽風者”阿炳,“看風者”黃依依,“捕風者”韋夫在701發揮自己頂尖的才能幫助國家行動局完成任務。他們讓我想起了一本書《天才在左瘋子在右》,他們是天才與瘋子的結合體,極高的天賦也使得他們具有執拗甚至偏激的性格,但他們都是戰爭年代的無名英雄。
《風聲》和《暗算》都是諜戰類的小說,讀完這兩本書,給我帶來的不是解密后的暢快,而是對于無數為中華民族自強而奮斗甚至不惜犧牲生命的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無數的“李寧玉”潛伏敵營,不懼死亡,只為那一線曙光。我十分佩服他們大無畏的精神和濃烈的愛國情懷,我想這可能也是麥家在小說中想要傳達的思想。
何藝珊(公益與社會組織管理在讀碩士,現居澳門):
認識麥家,始于《非虛構的我》;感悟真我,也源于《非虛構的我》。廚川白村在《苦悶的象征》中表示:“讀者和作家的心境帖然無間的地方,有著生命的共鳴共感的時候,于是藝術的鑒賞即成立。”當作家把腦海中的想法、通過神經元把指令傳到手上,再用筆和文字呈現在紙上的時候,即完成了本人思想輸出的全過程。而后,讀者則通過閱讀的方式,與作家進行“跨時空的交流”、彼此之間的“私密對話”。文字其實蘊含著作家的喜怒哀樂、記錄著作家的百態人生、傳遞著作家的思想意志,所以,一口氣將《非虛構的我》讀完的感覺,很是過癮。這種感覺,就好像我也在經歷著他的經歷、感受著他的感受、感動著他的感動。
但是麥家為什么偏偏要把這本書叫《非虛構的我》,難道不能是《真實的我》或《紀實的我》嗎?此時,我無意中憶起《莊子·齊物論》中這么一句話:“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由此聯想到麥家他筆下的文字,全皆源于他的觀察、他的學習、他的經歷、他的聽聞,或直接或間接地發生在他的身上,但又不一定是附著于他而生,所以故事中的我實則是“非虛構”的“我”,而非等于“真實”的“我本人”。當然,也由此引發出我新一輪的思緒:
當成長到一定年齡的時候,每個人都有或多或少的經歷。在虛實之間見真我,于虛實之間悟人生,但終歸還是會有迷茫時:自己到底是“莊周”,還是那只夢中的蝴蝶?在這般情況下,我又該往何處、請教誰,找出答案呢?麥家先生給出了答案“很多感悟并不需要我們主動去感去悟,而只要照搬套用即可”,頓時讓我茅塞頓開、醍醐灌頂,因為同樣的道理,父親在麥家初中最后一學期、當時在麥家看來也是人生求知途中的最后一站之時說了一番話,以其異常華麗的色彩和哲理深度,永遠烙在了麥家的心里——“家有良田,可能要被水淹掉,家有宮殿,可能要被火燒掉,肚子里文化,水淹不掉,火燒不掉,誰都拿不走”。
讀書吧!多讀書吧!多讀好書吧!把好書一讀再讀吧!再迷茫的人,讀書悟理,總歸能從虛實之間見真我,找到下一步前進方向的答案。
劉大強(建筑設計師,現居河南):
麥家的作品常常被改編為影視作品,卻并不媚俗,反而極其強調文學性,被批評家稱為“日用奢侈品”,他的作品常常書寫“天才”,被譽為“新智力小說”,但其本人卻并不相信所謂天才,認為:好作品是由爛作品堆出來的。他是只寫“小東西”的大師博爾赫斯的崇拜者,但其最重要的小說便是一本“大東西”。麥家在當今文壇上屬于一個絕對的異類。盡管針對麥家批評聲和贊揚聲平分秋色,但麥家幾乎是不可替代的。《暗算》獲得第七屆茅盾文學獎,并引起了很大爭議。麥家無法解密生命之謎,或許就打算暗算它。《暗算》寫了情報部門的奇人們是怎么暗算別人,又逃不過被命運“暗算”的結局。他們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往往因為“是一念之間,是冥冥中的一種混沌”。全書自始至終繚繞著一種濃重的神秘感和悲觀主義。麥家認為破譯家要成為“山巔的豹子”,真的需要一種運氣。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當然把這虛無縹緲的運氣作為答案只能是權宜之計,最終在《風聲》中,麥家找到了答案。
據麥家說,《風聲》是一部用“腦子”寫成的小說。它分為三部分,“東風”“西風”和“靜風”,以多種視角來描述同一件“捉老鬼”事件,每一部分都建立在另一部分的“漏洞”之上,使整個事件產生了“羅生門”效果。真相在證據越來越多的情況下反而越來越撲朔迷離。“歷史就像遠處吊詭的風聲”。然而麥家自己解釋道:“把小說當作一門手藝活來做。我想用密室和囚禁之困來考量一個人的智力到底有多深,丈量一個人的信念有多大。我希望在一種驚心動魄的心智較量中,為人性那無法度量的邊界下一個‘我’的注腳”(《八談風聲》)。麥家小說往往把人置于一種極端的環境,《風聲》之后,麥家終于留下了“我”的注腳——他知道了神秘也是可以把握的。
總的來說,麥家的寫作是最接近于內心的寫作,卻沒有缺少小說技巧,這是優點。麥家小說因為幾乎沒有與他類似的寫作而顯得難以評價,他的意義在于把類型小說寫成純文學,不僅僅要求雅俗共賞,而且要超越雅俗,順便帶來了一個新的小說類型。但他寫得太窄了,分量太輕了,從人物到技巧說實話都太吃老本了。
彭梟俊(軍隊文職,現居湖南):
第一次知道《風聲》還是從電影了解的,周迅扮演的顧曉夢靈動活潑,又心思縝密,故事的反轉又令人唏噓及稱贊。再看書的時候,又更深切地感受到了麥家自己說的:“看似寫了一群無情之人,而又恰恰是最深情的作品。”無情是為了信仰可以放棄一切,其中包括自己的生命,而無情的背后卻是對同志、組織、祖國蘊含的深切情誼。無情的背后是深情,深情的背后是無畏,支撐著無畏的是一種稱之為信仰的力量。戰火紛飛的年代,多少人懷抱著這種信仰奔走赴死,就像書中美麗的裘莊是先輩黨人的煉獄,獨行其中,唯有信仰為照明的燈火,戴著鐐銬、吞著血淚,卻不辱使命。
畢業之后,我進入部隊相關行業工作,這部作品引起了我的一些共鳴。單位的工作并不是時時按部就班進行的,有時候會下達一些緊急任務。每次任務下達下來,整個單位所有的小齒輪都嚴絲合縫地契合起來,高效率、嚴紀律地運轉。為了保障一次演習,同事們夜以繼日地加班、演練,做好保障工作,工作不高標準完成就不合眼不睡覺,這并不是需要提醒的事情,而是所有人的默契。和平年代的我們,所面臨的危險少于先輩們,但只是服務的場所轉變了,不變的還是那種無畏與無私的精神。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為任務圓滿完成提供好保障工作,就是我輩對信仰的具體落實吧。
何苗(實習律師,現居四川):
電視劇《風聲》的爆火,讓我對麥家的作品產生了極大的好奇心,那是我第一次接觸麥家的作品,緊接著,我閱讀了《解密》《暗算》等作品,讀完以后我的內心久久不能平靜,每一本書的劇情都引人入勝,跌宕起伏的劇情拽著我的心,驅使我一口氣讀到底。麥家的幾部作品里,每個主角既是天才,也是瘋子,《解密》里的數學天才容金珍;《暗算》中的瞎子阿炳;《風聲》中的“老鬼”。《解密》的出現像個重磅炸彈,讓麥家一炮而紅。《解密》的主角是容金珍,一個有著極高天賦的數學天才,雖然有著不幸的童年,卻最終成長為一位優秀的破譯密碼的專家,最后卻戲劇性地隕落了。
麥家的《解密》很吸引人,是一種新型而獨特的類型。書中出乎意料的故事情節,把人們引向一個未知的解密世界。麥家探究的是一個黑暗的領域,一個充滿刺激性的領域,里面遍布無窮無盡的密碼追蹤。雖然容金珍是一個解密天才,但也是一個孤獨的人,他在黑暗中孤獨地前行。那個筆記本的丟失,讓他在黑暗中失去了方向,最后令人惋惜地隕落了,這個結局十分戲劇。
《暗算》則是麥家另一部關于密碼破譯的小說。麥家在書中寫道:“7”是個奇怪的數字,它的氣質也許是黑的。黑色肯定不是個美麗的顏色,但肯定也不是世俗之色,它是一種沉重、一種隱秘、一種沖擊、一種氣憤、一種獨立、一種神秘、一種玄想。
《暗算》講述了具有特殊天賦的一群人的命運,書寫了聽風者、看風者和捕風者的曲折經歷,他們的命運各有不同,卻有相似性。他們破譯密碼,也是在破譯自己的命運。書里面的故事十分真實,人物個性鮮明,描寫手法獨具匠心。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阿炳的故事,阿炳將自己的能力全部奉獻給組織,他的忠心毋庸置疑,但是他的自殺結局令人唏噓,阿炳也被命運算計了,這也許是天才的悲劇。讀完這本書,我對書中的人物產生了由衷的敬意,在物欲橫流的今天,沒有多少人能保持如此單純的奉獻信念,他們不為名利,無私奉獻。《暗算》中那些為國家默默奉獻的人物是無名英雄,他們信念堅定、擁有高貴的人格信念。
麥家的作品普遍語言樸實無華,讀起來通俗易懂,作品中大量使用俗語,通俗又透徹地反映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活動。除此之外,麥家的語言十分細膩,作品中出現的數字十分準確具體,值得我們推敲。
麥家的小說中不僅充滿懸念和神秘感,也充滿著奇異的想象力,故事情節曲折,構思獨特多變。麥家是一位勇敢的拓荒者,他的作品開辟了一個新的寫作領域。
王義樺(鎮政府公務員,現居湖北):
人們對小說家麥家的成就早已耳熟能詳,或許是童年不平凡經歷的原因,他的筆觸時常充滿濃郁的生活氣息,語言表達簡單、純樸而又不失對另一種生活的無限遐想。他的故事中有普通人對不公平的命運的無可奈何,也有傳奇曲折、充滿懸念的諜戰大戲……他奇幻的想象力與別具一格的作風為人所敬仰。我對麥家的了解源于他的“故鄉三部曲”之一——《人生海海》,這部作品顧名思義講述的是普通百姓在起伏不定、暗藏洶涌的人生海洋中輝煌、挫折和悲哀的種種歷程。小說中最令我唏噓的是“上校”這一人物,他一生中扮演過許許多多的角色,曾是輝煌的營長、救死扶傷的軍醫,也是赫赫有名的大領導,但也會因為刺字傷疤而活在陰影中,飽受世人非議。“上校”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是因為他和小說中許多鄉里百姓對比起來如同蒙上了神秘的面紗一般,他既是被人“尊敬、討好”的,也是被人“貶低、非議”的,圍繞著他的生活環境與整體的社會環境有著巨大的心理落差。“上校”被捕后,肚皮上的刺字被當眾掀開,最終被逼瘋,不可謂不是一場悲劇。
麥家對“人生海海”這個標題解釋為:“既然每個人都跑不掉逃不開,那不如去愛上生活。”人的一生中或許沒有“上校”一樣傳奇的巔峰和低谷,但一定不乏“小瞎子”“父親”“爺爺”的煩惱和苦悶。一個人的成敗與背景、環境、性格有脫不開的關系,這些既定因素一點一點累積成了“命運”,每個人對此都跑不掉逃不開,但我們可以選擇被陰影籠罩的方式活著,也可以選擇愛上生活,包括它的悲劇色彩。
在看完《人生海海》后的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在思考:如果人們能夠換個方式去思考生活,會不會擁有更多選擇?如果人們能夠換一種心態對待人生大海的起伏,會不會更容易愛上生活?
故事終究是一紙定稿,而人生卻有無限可能。人生海海,潮落之后是潮起。
江關(工程師,現居山東):
麥家獲得茅盾文學獎,其實在最初時廣受詬病,原因在于許多文學批評家說起其作品,總是會將“諜戰”“類型”捆綁在一起,但其實如果這樣粗暴簡單地歸類,就大大削弱了麥家作品中更深層次的意義。其中,筆者認為麥家作品中關于“人性”與“英雄性”的處理,就體現了他敘事層次的深刻性。麥家善于塑造英雄形象,但在求取英雄審美意蘊的動人魂魄之外,他刻畫的人物往往又是具有反英雄意味的。如“701”系列的阿炳就是一個有血有肉的“異類”英雄,阿炳無疑是個天才,他憑借天才的聽力和記憶力為國家安全組織立下了赫赫戰功,但同時,阿炳又不同于世俗英雄形象的“偉光正”,他是個因病致瞎的殘疾人,他的智力還有缺陷,最戲謔的是,他以他天才的聽力聽出了妻子腹中的孩子不是他親生;“701”系列的另一人物黃依依也是個性格復雜矛盾的“問題”英雄,作為密碼專家的她形貌昳麗,她是麻省理工的高材生,也是中科院最年輕的研究員,她接二連三破譯敵國的高難度密碼,為世人所景仰。但作為一個女人,她又由于頻頻插足他人家庭鬧出緋聞而備受批評,最終還由于這種過于奔放的浪漫個性被置于死地;又如對于數字極其敏感但出身卑微、對于人情世故極度愚鈍的容金珍;再如能夠輕而易舉完成任務但精神卻又異常脆弱的“黑室英雄”陳家鵠。在麥家的筆下,這些英雄都是立體的,他們異稟的天賦讓他們不可能埋沒于眾生,但是麥家將他們放在真實可感的世俗環境中,使他們在個性與世俗的尖銳矛盾下,在痛苦掙扎中甚至自我毀滅中,消解他們偉大光輝的形象。正如麥家自己所言:瑣碎的日常生活對人的摧殘,哪怕是天才也難逃出這個巨大的、隱蔽的陷阱。說到底,我筆下的那些天才、英雄最終都毀滅于“日常”。日常就像時間一樣遮天蔽日,天衣無縫,無堅不摧,無所不包,包括人世間最深淵的罪惡和最永恒的殺傷力,正如水滴石穿,其實也是一種殘忍。麥家的這種描寫,是游走于“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雙重索解過程,而這種過程,也正是在挖掘人性矛盾的普世價值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