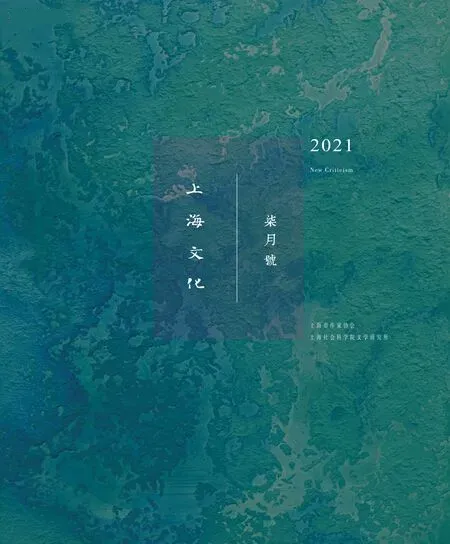歷史陰影·雙重“自我”·代際悖論
重讀王蒙《活動變人形》
顧奕俊
一
1988年冬至1989年初,作家王蒙與批評家王干“先后進行了十次對話”,“涉及的內容較為斑雜,兩人的想法也不盡一致”。在其中一次對談中,王蒙特意強調了寫作《活動變人形》初稿的具體時間:“我開始寫的時候是1984年,第一章是在武漢寫的,1985年完成的,當時還沒有尋根、文化熱。”這顯然是為了表明《活動變人形》在創作層面與1980年代中后期喧鬧的文化思潮保持著某種可見的距離。不過,就單部(篇)文學作品發表出版與相應時期階段文學思潮脈絡之間的關系切入,《活動變人形》卻又是一部“恰逢其時”的長篇小說。由于作品本身對父輩知識分子生存狀況、精神結構有著意味深長的追蹤,以及《活動變人形》問世前后愈演愈烈、讓人多少有些暈眩的“文化熱”、“尋根熱”,實際上很容易促使當時眾多批評者依循“慣用”的文學史觀念與文學評價機制對《活動變人形》作出自認為妥帖的論述。但假如重新看待王蒙在與王干對談時特意提及的小說《活動變人形》之于“尋根熱”、“文化熱”的距離感,就應該意識到1980年代中后期以來諸多有關《活動變人形》的文章或觀點一定程度上只是憑著“自以為如此”的主觀意愿將小說與相應時期顯著的思潮態勢進行“匹配”“鉚合”,而沒有觸及到王蒙寫作《活動變人形》時的某些更為隱晦、同時也更為復雜的意圖。相關評論者的闡發只不過是在試圖確認《活動變人形》與某個具體時期階段的關聯性,或是以“舊中國與新中國”這組切分對象作為“小說敘述的動力”,卻沒有充分理解《活動變人形》所涉及的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具有重復性、延續性的身份危機與精神危機。
在初步梳理了作者、批評者有關《活動變人形》的立場態度后,單就小說人物倪藻(包括敘述主體)的抽離性問題而言,作者與部分批評者其實存在著分歧。如許子東在進入新世紀后重讀《活動變人形》時就有過這樣的判斷:“通觀整部長篇小說,誰都有錯,誰都可憐,誰都不幸,誰都是悲劇人物——除了倪藻(及敘述主體)之外。”但與之相對,王蒙本人則將倪藻(也包括小說的敘述主體)納入到批判對象范疇當中:“然而我畢竟審判了國人,父輩,我家和我自己。我告訴了人們,普普通通的人可以互相隔膜到什么程度,誤解到什么程度,忌恨到什么程度,相互傷害和碾壓到什么程度。我起訴了每一個人,你們是多么丑惡,多么罪孽,多么愚蠢,多么不幸,多么令人悲傷!我最后宣布赦免了他們,并且為他們大哭一場。”許子東與王蒙所拋出的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也映照出王蒙在寫作《活動變人形》過程中異常糾葛的心理動態。
《活動變人形》起篇于語言學副教授倪藻在1980年代出國訪問期間,前往H市拜訪父親倪吾誠的舊友史福岡教授。但作為尋訪者的倪藻本人其實對于這趟拜訪之旅的目的也不甚明了,甚至還自我埋怨“史福岡究竟和他有什么相干?”。但倪藻與故人趙微土,包括史福岡太太的相遇,則推動了倪藻童年記憶的展開,繼而《活動變人形》以童年倪藻的視角與口吻返照其父倪吾誠在1940年代的惶惑彷徨。值得注意的是,中年倪藻的“聲音”在這一過程間幾乎是“缺席”的,相反,他似乎扮演著一名“沉默的觀眾”。即使當他在小說的“續集”再次登場,中年倪藻依舊保持著讓人難以揣明其意的冷淡與緘默。如果借用若干敘事學理論將中年倪藻視作王蒙在文本內的“化身”,那么這一“化身”的存在方式又是讓讀者感到困惑的——因為中年倪藻似乎一直游離在對應父親的記憶之外。以至于不免讓讀者懷疑:其究竟是不愿面對年輕的父親,還是不愿面對那個與父親血脈相連的自己?
而如果要討論《活動變人形》中的倪吾誠及其知識分子身份,或許首先有必要對這個人物的知識結構、教育背景進行剖析。一定程度而言,探究倪吾誠的知識結構、教育背景,也是從個案角度梳理20世紀以來國內一類知識分子對象的精神溯源、言行特質、實踐局限。依照小說《活動變人形》提供的時間線索,倪吾誠出生于“辛亥革命爆發前三個月”的“宣統三年”,其或應作為許紀霖所言的20世紀六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后五四”一代進行考察。對于這一代知識分子,許紀霖認為:“他們在求學期間直接經歷過‘五四’運動的洗禮,是‘五四’中的學生輩(‘五四’知識分子屬于師長輩),這代人大都有留學歐美的經歷,有很好的專業訓練。”這也同倪吾誠的成長環境與個人經歷大致吻合。不過,倪吾誠這一代知識分子經歷的留學培養與專業訓練,并不意味著相應的“現代性方案”實踐能夠徹底消抹掉始于前現代社會內部綱常倫理、道德規范的制約。討論倪吾誠的留學背景與知識結構,其實是作為一種特殊的參照系,從而說明宗法家族結構關系與儒家意識形態對晚清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所形成的異常堅固的“環結”。作為遺腹子的倪吾誠年少時因舅舅的挑唆與母親、表弟的引誘而染上惡習,“等他長大成人之后,他覺得有充分的理由判定這位表哥的教授與母親的教授(吸鴉片)具有同樣的性質,出自同一個設計與謀劃,是精心安排好了的籠罩在他身上的網的兩個環結”。青年時代的倪吾誠看似在竭力擺脫“身上的網的兩個環結”,卻又為達成住縣城上學的意愿而被迫接受母親替其說親的舉動。從這一視角來講,“環結”指向于一種承襲家族規范秩序的不容置喙的日常儀式與程序。倪吾誠在青少年時代的遭遇較為普遍地體現了自晚清以來諸多知識分子進退維谷的生存悖論:特殊的社會氛圍、時代任務原本使得他們有理由也有機會擊碎“環結”的桎梏,但他們最終得以“開眼看世界”的先決條件卻是妥協于一種與“環結”相依存的矛盾命運。

值得注意的是,與《活動變人形》出版年份相近的1988年,楊絳出版了以新中國成立后在北京“文學研究所”工作的知識分子為描述對象的長篇小說《洗澡》。與倪吾誠相似的是,《洗澡》中的知識分子人物也大多具有海外留學或居住的背景經歷(這也涉及到《洗澡》與錢鐘書1947年出版的《圍城》之間的承接關系)。不過看似光鮮的教育學歷、社會身份并沒有掩蓋“河馬夫人”施妮娜、余楠這些知識分子在學識方面的淺薄與人格方面的卑瑣。將施妮娜、余楠,與倪吾誠等人放置在同一代(類)知識分子譜系下進行考察,能夠意識到無論是王蒙,抑或楊絳,他們對于相關知識分子人物的言行描摹,絕非僅僅是針對個別人物形象的戲謔反諷,而是試圖表明晚清以來通過留學途徑塑造知識分子的設計途徑、設計意圖的局限性。

從《活動變人形》至《洗澡》,可以看到一道“歷史的陰影”投射進倪吾誠這一批20世紀初期知識分子的日常世界。“歷史的陰影”,大致可理解為一種對應特定身份對象、且在歷史進程演變中具有延續性、循環性、普遍性等的困境結構。除了理想目標的無從談起,“歷史的陰影”也將“倪吾誠們”限定在某種求而不得的生存狀態中,以至于這些受到現實“環結”制約,渾渾噩噩、隨波逐流的知識分子最終都難以說明為何而求——當然,也就更談不上“安身立命”云云。相反,他們只能以不斷重復的失望、嗟嘆、抱怨代替向內轉的自我反省、自我審視,而他們一度高蹈的理想主義、鮮明的主體意識趨于消弭在瑣碎的世俗世界。
二




三
《活動變人形》是否僅僅是一部審視父輩知識分子的長篇小說?對于這一疑問的思考,還是需要回到最初王蒙與許子東有關倪藻(包括敘述主體)抽離性問題的分歧上。而探究兩人產生分歧的起因與過程,也是從一個側面探究《活動變人形》的批判向度、批判效用。如果依照許子東的論見,將倪藻(包括敘述主體)拋擲于相應的批判對象之外,《活動變人形》則從時空層面而言呈現為“靜態”的文本。這也意味著作者對于倪吾誠等20世紀初期國內知識分子人物的書寫,將被定位在某段固定的歷史維度中加以分析判斷。相應的推斷也只能徘徊于某個具體時間階段從而形成狹隘的“歷史與邏輯的統一”,難以達成具有連續性、延展性的歷史反思與文化反思(這也是1980年代中后期“尋根熱”屢遭詬病的癥結所在)。因此也就可以理解王蒙為何在《關于〈活動變人形〉》這篇文章里要強調“我畢竟審判了國人,父輩,我家和我自己”。而更具意味的是王蒙隨即談到的“起訴”與“赦免”。假如“起訴”眾人是作者反思20世紀歷史進程中國內知識分子精神意緒、知行表現的邏輯前提,那么“赦免”則聯系著王蒙更為耐人尋味的情感態度。
《活動變人形》的“續集”部分,有一處并未得到充分重視的細節。1985年夏天,即將步入老年的倪藻與“筆者”在海濱療養地重逢,兩人相約一起去游泳:




? 王蒙、王干:《〈活動變人形〉與長篇小說》,《王蒙王干對話錄》,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1頁。
? 王蒙、王干:《〈活動變人形〉與長篇小說》,《王蒙王干對話錄》,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229頁。
? 朱偉:《重讀八十年代》,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21頁。
? 許子東:《重讀〈活動變人形〉》,《當代作家評論》2004年第3期。
? 王蒙:《關于〈活動變人形〉》,《南方文壇》2006年第1期。
? 王蒙:《活動變人形》,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2頁。
? 王蒙:《活動變人形》,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48頁。
? 許紀霖:《20世紀中國六代知識分子》,《中國知識分子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83頁。
? 王蒙:《活動變人形》,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第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