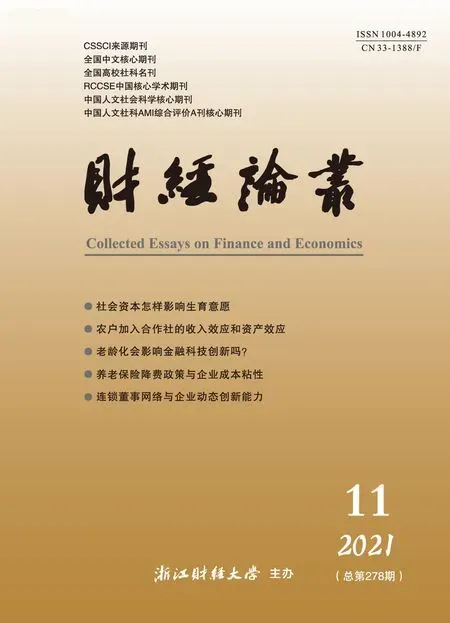社會資本怎樣影響生育意愿
——基于CGSS數據的實證研究
徐萌娜,王明琳
(1.杭州師范大學經濟學院,浙江 杭州 311121;2.杭州蕭山民營企業傳承與創新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1202)
一、引 言
我國人口紅利消失的拐點已出現。2012年,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首次出現絕對下降,比上一年減少345萬人[1]。自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出臺,2016年全國出生人口比2015年僅增加95萬人,比2014年也只是增加63萬人[2]。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相關數據,2016—2019年的人口出生率分別為12.95‰、12.43‰、10.94‰和10.48‰,呈逐年下降的趨勢(如圖1所示),要了解其背后的原因離不開對生育意愿的探究。

圖1 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的統計結果
生育行為首先取決于生育意愿,“不同國家生育率不同的主要原因是人們想要的孩子數量不同”[3]。生育意愿受育兒成本的影響,隨著教育回報率的上升,密集型教養方式(時常插手并強烈干預孩子的生活)在許多工業化國家變得越來越流行[3],使育兒成本大大增加。夏志強和楊再蘋(2019)的研究指出目前我國生育成本分擔普遍呈現非均衡狀態,家庭承擔了大量的生育成本,導致生育意愿下降等社會問題[4]。從生理特點和社會分工的角度看,大量育兒成本由女性承擔。相關調查顯示,女性作為生育主體擁有高于男性的生育決策權[5],女性的生育意愿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6]。2019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這是家庭育兒成本向社會化育兒成本轉移的重要舉措。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對生育意愿的影響是國內外學者在對正式制度影響的研究中除生育政策外最關注的話題[7],而目前對社會非正式保障影響的關注和研究則相對匱乏,其中典型的非正式保障就是社會資本,因此本文擬就社會資本對女性生育意愿的影響展開實證分析。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Bourdieu(1986)開拓了微觀層次的社會資本分析,強調社會資本是個人通過社交網絡可獲取的資源[8]。從資源獲取的角度看,社會資本可被視為非正式保障。在微觀層面上,相比于個人實際獲取的社會資本,對生育意愿產生影響的其實是個人認為可獲取的社會資本,社會資本通過個體認知和決策作用于生育意愿。個人的社會資本通過社會信任和社交網絡兩個方面來衡量[9][10]。首先,個人社會資本往往被認為與其社交網絡密切相關[11][12],社會資本的資本屬性被視為個體通過網絡成員獲得稀缺資源的一種特征[13]。擁有廣泛的社交網絡往往意味著個人豐富的社會資源,以避免風險和解決問題,促使個人對社會資本形成較高的預期。其次,普適性的社會信任往往使人對從他人(即使是陌生人)那里能獲得的資源和幫助等具有更高的期待,而沒有將信任局限在親緣關系等較小的范圍內[14][15]。信任本質上是個體的一種主觀預期[16],即使擁有相同的社交網絡,社會信任也使不同個體對可獲取的社會資本的認知產生差異。近年來,普適性的社會信任開始被用于我國相關研究中社會資本的代理變量[17][18],但很少出現在生育意愿的相關實證研究中。
從社會資本對生育意愿影響的相關實證研究看,Balbo和Mills(2011)在法國、德國和保加利亞等國家的研究發現,社會資本對生育意愿具有積極的影響,與特定資源(情感、資金、照料支持)提供者的數量成比例[19]。姚丹(2017)基于四川省成都市80后、90后已婚人群的調查發現,該群體的生育意愿受到社交網絡中以血緣、親緣為基礎的強關系和以業緣、友緣為基礎的弱關系的影響[20]。但總體上,目前將社會資本與育齡人群的生育意愿聯系起來進行實證分析的文獻還是比較薄弱。
就社會資本對生育意愿影響的方向而言,一方面,社會資本可能使“養兒防老”的重要性降低,即隨著可獲取的社會資本增加,育齡女性認為養老已有一定程度的保障而沒有多生育的意愿,Holmqvist(2011)發現在養老系統覆蓋率高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育齡女性的生育率明顯降低[21];另一方面,社會資本通過育兒成本社會化提升女性的生育意愿,Aassve等(2016)的研究認為普適性的社會信任有利于通過撫養子女活動的外包來提高生育率[22]。因此,社會資本的非正式保障作用可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養老的保障;二是對育兒的保障。二者對生育意愿的影響是相反的,目前哪一個占據優勢地位尚未可知。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1a:社會資本與女性的生育意愿呈顯著負相關;研究假設1b:社會資本與女性的生育意愿呈顯著正相關。
進一步地,根據社會資本的相關文獻,我們將親朋關系加入到社會資本的測量中[9][17][18]。在對研究假設1進行驗證的同時,社交網絡中的不同關系對女性生育意愿的影響可能不是完全相同的。相關研究已發現,不同類型的關系可產生不同的影響,大多通過區分關系強度加以探討。Granovetter(1973)首次提出關系強度的概念,認為代表異質性的弱關系具有“關系橋”的作用而更有力度[23]。而Bian(1997)則認為在中國情境下個人工作更多的是通過強關系而非弱關系獲得[24]。前者常常被稱為“弱關系(力量)假設”,后者則被稱為“強關系(力量)假設”,這兩個假設的運用并沒有局限于職業流動領域的研究,對社會互動影響個體行為和決策的其他議題亦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25][26]。
就關系強度的具體區分而言,王毅杰和童星(2004)在探討流動農民的社會支持網時將親屬關系作為強關系、朋友關系作為“中間性關系”[27]。熊艾倫等(2016)將與普通朋友的交流和聚會的頻率作為弱關系連接,而將與不住在一起的親戚的互動頻率作為強關系連接,認為強關系和弱關系對城市和農村居民的健康水平具有不同的影響[28]。楊明婉和張樂柱(2019)劃分親緣類社會資本和友緣類社會資本,認為前者屬于強關系社會資本,后者屬于弱關系社會資本[29]。參照已有文獻,相比較而言,我們可將親戚關系作為較強的關系、朋友關系作為較弱的關系。這兩者對生育意愿的影響也許是相似的,但也可能是不同的,更加符合“弱關系(力量)假設”還是“強關系(力量)假設”亦未可知。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設2a:親戚關系和朋友關系對女性生育意愿的影響是相似的;研究假設2b:親戚關系和朋友關系對女性生育意愿的影響是不同的。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和樣本選擇
本文采用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5年,CGSS項目覆蓋全國28個省/市/自治區,共完成有效問卷10968份。由于一般認為15—49歲的女性具有生育能力,我們根據受訪者的年齡篩選樣本,剔除“無法回答”等無效樣本后,最終樣本的年齡段為18—49歲。
(二)變量定義及其描述性統計
1.被解釋變量。基于原始問卷中對“如果沒有政策限制的話,您希望有幾個孩子?”的回答,本文設立被解釋變量m-child,并將回答為0個、1個、2個及以上的分別賦值為0、1和2。
2.解釋變量。根據原始問卷并參照已有文獻[9][17][18],本文從社會信任和社交網絡兩個方面衡量個人社會資本。
(1)社會信任trust。具體問題是“總的來說,您同不同意在這個社會上,絕大多數人都是可以信任的”,由于答案選項“說不上同意不同意”并沒有體現普適性的信任傾向,我們將其與回答為“非常不同意”和“比較不同意”的一起賦值為0、“比較同意”和“非常同意”的賦值為1。
(2)社交網絡network。具體問題是“在過去的一年中,您是否經常在空閑時間進行社交/串門活動”,該問題的回答可測量個體總體社交狀況[30],原始問卷中使用的是五級量表,我們將回答為“從不”和“很少”的賦值為0、“有時”的賦值為1、“經常”和“非常頻繁”的賦值為2。同時,本文使用“與不住在一起的親戚聚會的頻次”來反映與親戚之間的關系,使用“與朋友聚會的頻次”來反映與朋友之間的關系,分別設立變量為relative和friend,將回答為“從不”和“一年數次或更少”的賦值為0、“一月數次”的賦值為1、“一周數次”和“每天”的賦值為2。
3.控制變量。本文控制社會正式保障變量和家庭保障變量。基于原始問卷中社會保障項目的參與情況,本文圍繞“城市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公費醫療”和“城市/農村基本養老保險”分別設立變量medi-insurance和aged-insurance,將回答為“沒有參加”的賦值為0、“參加了”的賦值為1。一方面,社會保障制度可能降低了人們“養兒防老”的意愿;另一方面,家庭收入既要分配給育兒成本,又要分配給醫療等相關費用,社會保障支出中長期而言有助于減少對育兒成本的“擠出”,使未來的預算相對寬松,也可能間接提升育齡女性的生育意愿。
家庭保障變量包括:(1)年家庭總收入(income),具體問題是“您家2014年全年家庭總收入是多少?”,為避免數據異常值的影響,我們對回答的數值取自然對數并在5%的水平下縮尾處理,考慮到收入對生育意愿的影響可能是非線性的,年家庭總收入的平方項income_squared亦加入回歸;(2)家庭人口規模(family),具體問題是“您家目前住在一起的通常有幾個人?(包括本人)”,從增加養老成本的角度看,家里老人較多時可能產生對育兒成本的“擠出”,而家庭人口較多意味著可能有帶孩子的幫手,這又提升了育齡女性的生育意愿。
此外,本文還控制個體特征變量和省份效應。在個體特征變量中,年齡變量(age)根據受訪者的出生年月和調查時間計算得到,教育程度變量(education)將未接受過教育、小學私塾、初中畢業、職業高中(普通高中、中專技校)、大學專科/本科、研究生及以上學歷分別賦值為0、1、2、3、4和5,城鄉變量(rural)是按樣本類型設立的虛擬變量并將農村賦值為1,健康狀況變量(health)將自我評價從“很不健康”到“很健康”分別賦值為1—5。對于婚姻狀況變量(couple),就影響生育意愿而言,由于與另一半的實質性陪伴和互動顯得更為重要,而不局限于法定的夫妻關系[31],因此將“同居、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賦值為1,“未婚、分居未離婚、離婚和喪偶”四種情況一并賦值為0。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1所示。

表1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N=2419)
四、實證研究結果及分析
(一)社會資本對女性生育意愿的影響
本文首先采用有序Probit模型進行基準回歸,為消除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問題,回歸結果都經過Huber/White/sandwich穩健標準誤差調整(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OPROBIT模型的回歸結果(N=2419)
從表2來看,衡量社會信任的變量trust無論單獨進入回歸還是同時處于回歸中,其系數均為正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在模型(2)、(3)的回歸結果中,衡量社交網絡中個體總體社交狀況的變量network無論單獨進入回歸還是同時處于回歸中,其系數亦均為正且在5%的水平下顯著,從而研究假設1b得到支持。無論高收入家庭還是低收入家庭,社會資本均對生育意愿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表明其主要作用是降低育兒成本而不是形成一定的養老保障,否則其回歸系數應為負。也就是說,隨著可獲取的社會資本增加,育齡女性認為“養兒防老”的重要性在下降。模型(4)—(6)的回歸結果顯示的是親戚關系和朋友關系對女性生育意愿的影響,relative的系數為正且在10%的水平下顯著,而friend的影響并不顯著。以上結果表明,隨著個人社會資本的提升,育齡女性的生育意愿確實會增強,但個人對社交網絡中不同關系的認知是有差異的,親戚關系作為強關系有利于增強女性的生育意愿,而朋友關系作為弱關系對女性生育意愿則沒有顯著的影響。這一結果支持了研究假設2b,較符合我國本土的“強關系(力量)假設”(1)如前所述,與Granovetter的“弱關系(力量)假設”相對應,Bian(1997)通過對中國社會的研究后認為要找回強關系并形成“強關系(力量)假設”[24][25]。。
在控制變量方面,首先,年家庭總收入income在表2的各項回歸中的系數均顯著為負,其平方項income_squared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家庭收入與女性生育意愿呈非線性的U型關系,家庭收入處于高低兩端的育齡女性多生育的意愿較強。這意味著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類似于“養兒防老”的投資品,父母的意圖是將未來的養老支出分攤到多個子女身上,關注點在于從生育多個孩子中能獲得的總收益。隨著家庭收入的增加,育兒質量對孩子未來發展和幸福生活的影響變得難以忽視,孩子開始更多地類似于耐用消費品,父母注重從孩子身上得到心理滿足或精神慰藉。其次,family的回歸系數為正且始終在1%的水平下顯著,家庭人口規模對女性生育意愿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與國內相關文獻的研究結論相符(2)呂碧君(2018)的實證分析指出來自于祖父母家務上的支持對婦女的“二孩”生育意愿產生積極效應[32]。方大春和裴夢迪(2018)發現家庭共居人口越多時生育“二孩”的意愿越強烈[33]。。再次,是否參加“城市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公費醫療”及“城市/農村基本養老保險”的影響并不顯著。目前來看,家庭層面的保障對女性生育意愿的影響相對顯著。最后,education對女性生育意愿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受教育水平越高的育齡女性越沒有多生育的意愿,可能是生育子女的機會成本提高所致;rural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農村的受訪者相對而言具有較強的生育意愿。
由于OPROBIT模型的回歸結果僅能從顯著性和符號方面給出有限信息,接下來需考察表2的模型(3)和(6)(包含了主要的回歸結果)中變量的邊際效應。邊際效應的含義為當其他變量處于其均值且保持不變時,解釋變量變化1個單位導致的被解釋變量m-child取值為0、1和2的概率變化(結果如表3所示)。m-child變量的值小于或等于1時與m-child變量的值大于1時相比,主要解釋變量的邊際效應方向是相反的。在兩個回歸模型中,trust每增加1個單位,m-child取值為0的概率減少0.0074和0.0073,取值為1的概率減少0.0439和0.0435,取值為2的概率增加0.0513和0.0508。因此,trust越大,育齡女性愿意生育的數量為0或1個的可能性越小,2個及以上的可能性越大,其他變量同理可知。network和relative的邊際效應顯示其影響幅度小于trust。

表3 OPROBIT模型的回歸邊際效應(N=2419)
(二)內生性偏差和穩健性檢驗
為使回歸結果更加穩健,鑒于可能有變量對社會信任和生育意愿二者都產生影響并導致測量誤差,我們對社會信任(trust)采用工具變量法來解決潛在的內生性問題。由于文中的因變量是離散變量,社會信任變量是二值變量,基于連續變量的兩階段最小二乘法可能會失效。因此,本文以條件混合過程方法(ConditionalMixedProcess,CMP)對模型進行重新估計[34],第一階段采用Probit模型,第二階段采用Oprobit模型。目前,CMP已得到學術界的認可和較為廣泛的應用[35][36]。
考慮到文化傳統傾向和成長環境從不同角度影響社會信任,前者使人超越封閉的人際關系形成情感信任從而更具普適性信任[37],后者則通過艱苦的成長經歷使個人不易具有普適性信任,我們在原始問卷中兩個問題的基礎上構建工具變量:針對“下列宗教或文化傳統中,您對哪個最有好感?”這一問題,本文設立變量cultural并賦值為0,將明確回答為宗教或文化傳統的賦值為1;針對“在我們的社會里,有些人處在社會的上層,有些人處在社會的下層,您認為在您14歲時,您的家庭處在哪個等級上?”這一問題,問卷中最高的“10分”代表最頂層、最低的“1分”代表最底層,本文設立變量bottom并賦值為0,將回答為“1分”的賦值為1,該變量經檢驗后與income的相關性系數小于0.2。
由表4可知,第一階段的回歸結果顯示,cultural的系數為正且在5%的水平下顯著,bottom的系數為負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說明工具變量存在相關性,具有明確宗教或文化傳統好感的受訪者傾向于認為大多數人可信任,成長過程中家庭處于底層的受訪者則相反。第二階段的回歸結果顯示,對女性生育意愿而言,trust的系數依然為正且在1%的水平下顯著,network的系數亦為正且在5%的水平下顯著,relative的系數顯著為正,而friend的影響并不顯著,這與表2的回歸結果一致,從而研究假設1b和2b仍然得到支持。內生性檢驗參數atanhrho在1%的水平下顯著異于0,意味著trust是內生變量,CMP方法得到的估計結果更為準確,進一步印證社會資本對女性生育意愿的正向作用及親戚關系和朋友關系的不同影響。在控制變量方面,年家庭總收入income的系數為負,其平方項的系數為正,二者均在5%的水平下顯著,說明家庭收入與生育意愿的U型關系依然成立;family、education和rural的系數的正負方向與表2的回歸結果一致,同樣都是顯著的,從而佐證了研究結果的穩健性。

表4 CMP模型的二階段回歸結果(N=2419)
表5列示了CMP模型的第二階段回歸中主要解釋變量的邊際效應,發現邊際效應的方向與表3的結果是一致的。這里,我們將內生解釋變量和外生解釋變量的邊際效應分開加以討論[38]。首先,從內生解釋變量看,當其他變量處于其均值且保持不變時,在兩個回歸模型中,trust=1的概率每增加Δ,m-child取值為0的概率減少0.0810Δ和0.0882Δ,取值為1的概率減少0.2085Δ和0.2121Δ,取值為2的概率增加0.2895Δ和0.3003Δ。其次,從外生解釋變量看,當其他變量處于其均值且保持不變時,network每增加1個單位,m-child取值為0的概率減少0.0058,取值為1的概率減少0.0150,取值為2的概率增加0.0209;relative每增加1個單位,m-child取值為0的概率減少0.0072,取值為1的概率減少0.0174,取值為2的概率增加0.0246。結果表明,本文的研究結果仍然是穩健的。

表5 CMP模型的回歸邊際效應(N=2419)
進一步地,我們探討社會資本與其他保障之間可能產生的交互效應,并作為穩健性檢驗的一部分(如表6所示)。加入交互項network*medi-insurance之后,第一階段的回歸中cultural的系數顯著為正,bottom的系數顯著為負,第二階段的回歸中trust和network的系數均顯著為正,回歸系數的正負方向和顯著性水平均與表4的結果一致。同時,交互項network*medi-insurance的系數為負且在10%的水平下顯著。這表明參加“城市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公費醫療”使社交網絡層面的個人社會資本對女性生育意愿的積極作用在減小,社會資本與“城市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公費醫療”之間存在一定的替代性,進一步佐證了將社會資本視為非正式保障的可行性及本文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表6 交互效應的回歸結果(N=2419)
五、結論與啟示
本文基于2015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的數據,實證分析作為非正式保障的社會資本對女性生育意愿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社會資本對女性的生育意愿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對個人社會資本預期更高的育齡女性具有更強的多生育意愿,當前社會資本的主要作用在于減少育兒成本而非形成一定的養老保障;社交網絡中的不同關系帶來的個人社會資本預期是不一樣的,親戚關系作為強關系有利于增強女性的生育意愿,朋友關系作為弱關系對其生育意愿則沒有顯著的影響,就生育意愿的影響因素而言,目前社交網絡中強關系的作用相對顯著,在作用方向上同樣是有助于減少育兒成本而非形成一定的養老保障。
從本文的研究結論看,除家庭育兒成本向社會化育兒成本轉移的各項措施外,為提升生育意愿,還可在正式保障措施的基礎上結合非正式保障,充分發揮社會資本的非正式保障功能。普適性信任跨越血緣、親緣的范圍界限,有利于減輕生育的阻力。因此,政府一方面可加強文化引領,營造普適性信任的良好社會氛圍;另一方面可通過降低家庭育兒成本等方面的更完善的制度建設,推動以制度為基礎的信任對提升生育意愿的積極作用,使國家鼓勵生育的各項政策得到更好的貫徹和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