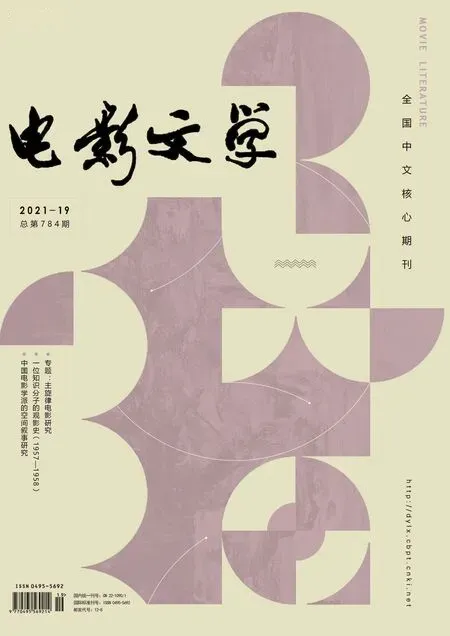新時期以來中國電影在韓國的傳播與拓展
陳 慧(黃淮學院文化傳媒學院,河南 駐馬店 463000)
作為特殊的市場商品與文化產品,電影不僅具有創造經濟效益與滿足精神需求的核心功能,而且具有凝聚時代共識、形塑國家形象、傳播民族文化、提升文化軟實力與促進文化融合等多重政治、文化與意識形態功能。有鑒于此,世界各國都異常重視民族電影的對外傳播與異國電影的對內傳入,并積極出臺電影振興、文化例外等相關政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異常重視國產電影的海外傳播。而新時期以來中國電影得以不斷在韓國市場進行上映并取得一定成績。本文便以韓國市場為中心,探究中國電影在韓國的傳播現狀并借此深入研究中國電影的競爭力與傳播力。針對存在的問題,進行認真反思并努力解決。
一、中國電影在韓國市場的傳播現狀
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電影在韓國的傳播已近40年,上映了超過500部中國電影,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其成績主要表現如下:首先,中國文藝片得以不斷傳播到韓國并對韓國電影產生積極影響。第三代導演謝晉的《芙蓉鎮》《最后的貴族》、第四代導演謝飛的《香魂女》、第五代導演田壯壯的《藍風箏》、第六代導演賈樟柯的《任逍遙》《三峽好人》以及新生代導演畢贛的《地球最后的夜晚》等,由于具有深刻的思想內涵、先進的電影語言等,都獲得韓國市場的引進。其次,中國類型片,特別是香港動作片、中國式大片源源不斷傳到韓國。在中國電影在韓國市場觀影人次排名前50名中,涵蓋武俠片、青春片、動作片、動畫片等多種類型,而中國式大片《英雄》《十面埋伏》《夜宴》等都取得較高的票房成績,其中《赤壁》(上下)、《英雄》等創造了超過百萬的觀影人次的票房成績,引發觀影熱潮。再次,武俠片、動作片、青春片以及動畫片等類型在韓國獲得歡迎,而犯罪片、喜劇片等由于存在文化折扣問題而顯得水土不服。其中,香港的《神話》《警察故事》《葉問》等諸多動作片,《少年的你》《最好的我們》等青春電影獲得韓國市場的肯定,實力不容忽視;而馮小剛的《甲方乙方》《私人訂制》等系列喜劇電影,由于喜劇因素的民族性而存在文化折扣問題并最終造成水土不服,市場接受度較低,與在國內的票房表現形成強烈的反差。最后,張藝謀、陳凱歌、李安、王家衛、徐克、陳木勝等導演,成龍、周潤發、章子怡、劉德華、李連杰、鞏俐、金城武等演員,在韓國具有一定知名度與票房號召力,對推動華風具有名人效應。其中,張藝謀憑借中國式大片而獲得韓國受眾的肯定,韓國市場中國大陸電影前三名都是張藝謀電影,而陳凱歌憑借高超的電影藝術造詣也得到韓國受眾的尊重,《霸王別姬》成為韓國受眾的集體觀影記憶并得到數次重新放映。具體見表1。

表1 中國電影韓國市場觀影人次前50名

(續表)
不過,總的看來,韓國市場主要由韓國電影與美國好萊塢電影所占領,占比高達90%,而日本、英國與中國等外語片份額占比不足10%,而中國電影的整體票房或觀影人數占比更低,絕大多數年份徘徊在1.0%以下,甚至多年只有0.1%,不及日本、法國與英國等國家。其中,在中國獲得較高票房的國產電影在韓國的票房卻相當不理想。在中國最終斬獲近60億的《戰狼2》,在韓國僅有1244觀影人次;近47億的《流浪地球》僅僅獲得不足18萬的韓國觀影人次;24億票房的《捉妖記》,韓國觀影人數不足3萬,全國排名209位,票房僅僅106萬元;而《建國大業》等主旋律電影更是沒有引進。從表格中,我們也可以輕易看出,前50名中國電影中,有多數在1萬觀影人次以下,可以說中國電影在韓國市場的傳播現狀,整體而言不容樂觀。
二、中國電影的文化實力:文化記憶與現代意識
基于分析,我們基本可以明確韓國市場主要由韓國本土電影與美國好萊塢電影占領,其余國家共享不到10%的票房份額。中國電影在放映數量、電影類型等方面雖然占有優勢,但電影票房、影響力等方面則顯示為缺乏市場競爭力,無法真正實現中國電影的走出去戰略。那么,這是否意味著中國電影也缺乏文化競爭力?從一定意義上說,市場競爭力與文化競爭力成正比,市場表現的確可以印鑒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導演的文化競爭力,但也必須明確,市場與國家政策、民族情緒、傳播渠道等息息相關,這就決定了市場競爭力并非對等于文化競爭力。從韓國市場中國電影的傳播現狀上看,相較于韓國電影以及其他國家電影,中國電影在文化記憶、現代意識與影像韻味等方面具有一定文化競爭力。
首先,大陸電影具有富有文化記憶的文化傳播力。文化記憶理論是德國學者揚·阿斯曼所提出的一個重要理論,涉及回憶、認同與文化的延續之間的關聯,且作為文化的凝聚性結構,在社會層面與時間層面,“它起到的是一種連接與聯系的作用”。可以說,文化記憶通過儀式與媒介等展演方式與符號系統來實現對過去的指涉、政治想象與集體記憶而產生民族/身份/文化認同,最終實現文化的記憶與傳承。而電影同時還具有儀式與媒介的雙重性質,或者說是一種儀式化媒介,可以起到重要的文化記憶功能。眾所周知,中國蘊含豐富的傳統文化資源(傳統歷史資源、傳統文學資源、傳統藝術資源、傳統民俗資源、傳統景觀資源與傳統思想資源等)與現代文化資源(嚴肅文學、新聞事件、網絡小說、漫畫、游戲等),而中國電影通過對其利用、呈現與建構的“影像回憶”,可以重塑文化形象、傳播中國文化與詢喚民族認同。依據先秦、三國、唐朝、明清、近現代等歷史文化資源而創作出的《英雄》《戰國》《王的盛宴》《趙氏孤兒》《孔子》《銅雀臺》《影》《大唐玄奘》《狄仁杰系列》《妖貓傳》《大明劫》《投名狀》《鬼子來了》《東京審判》等,依據《三國演義》《西游記》《木蘭辭》等中國古典文學而創作出的《赤壁》《西游記之大圣歸來》《西游之女兒國篇》《花木蘭》等,依據當代嚴肅文學而改編出的《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霸王別姬》,特別是《滾蛋吧!腫瘤君》《最好的我們》《28歲未成年》《心理罪之城市之光》《盜墓筆記》《少年的你》等IP改編電影,無不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的歷史與現實、物質與精神、思想與價值,從而賦予中國一個文化大國形象,而這是韓國電影所難以比擬的,因此,韓國觀眾對眾多中國歷史題材電影表現出強烈興趣,對古典文學改編電影以及近年的IP改編電影也投入了極大熱情。此外,中國擁有豐富的繪畫資源、音樂資源、戲曲資源乃至電影資源等藝術資源,而這些藝術資源所蘊含的故事情節、藝術形式、美學意味等,都可以賦予中國電影以獨特的文化魅力,獨具極高的美學價值。《英雄》中的意境、《十面埋伏》中的詩詞歌舞、《影》中的黑白灰水墨畫、《霸王別姬》《梅蘭芳》中的戲曲、《活著》中的皮影戲、徐浩峰電影(《倭寇的蹤跡》《箭士柳白猿》《師父》)中的武術、武林與武德以及改編自同名樣板戲的《智取威虎山》中的互文性等,都因傳統藝術資源而具有了特殊的文化競爭力。其中,中國武俠電影之所以能夠風靡世界,便與傳統的武俠電影資源密不可分,因為武俠電影作為一種模式化、標準化的類型影片,經過百年的發展,已然成為世界最為接受的中國電影,對此后的創作與傳播帶來先天的優勢。新世紀以來,韓國電影也曾嘗試創作《武士》《俠女:劍的記憶》等韓式武俠片,但最終口碑與票房都不甚理想。這也從側面反襯出中國武俠電影的文化軟實力。不過,我們也必須承認,這些中國電影還沒有形成深層次的文化記憶競爭力,僅僅停留在表層,而且《戰國》《關云長》等對歷史的曲解、《英雄》《夜宴》等呈現出的價值觀錯亂等更是消解了文化競爭力,難以塑造中國正面的文化形象與傳播優秀的中華文化。
其次,中國電影具有含蘊現代意識的文化傳播力。現代意識是人類對世界予以現代性認知的思維方式,核心為現代性。起源于歐洲啟蒙時期的現代性,秉持啟蒙與理性,主張理性主義,承認人的主體性,具有線性時間觀念并對近現代中國產生深遠影響,使當時的中國人接受了“進化與進步的觀念,實證主義對歷史前進運動的信心和科技可能造福人類的信仰,以及廣義的人文主義架構自由與民主的思想”。新時期以來,被遮蔽的現代性重新出場,成為當時電影中重要的時代主題。盡管現代性具有多副面孔,但第五代導演所秉持的“民族反思”與第六代所追求的“個體意識”成為新時期乃至當代中國電影現代性最為明顯的兩方面。站在中國/落后與外國/發達的改革開放初期,陳凱歌、張藝謀等第五代導演癡迷于對歷史的宏大敘事,試圖反身過去與凝視歷史而揭示傳統的沉重、文化的腐朽、人性的壓抑與民族的呆滯,從而找尋到阻礙民族進步、人性解放與國家發展的病因。因此,《黃土地》《黑炮事件》《紅高粱》等電影儼然成為富有現代性主題的民族寓言電影,也正是憑借電影語言的大膽創新與現代性主題的深刻表達,第五代導演才橫空出世并在西方電影節閃亮登場,也于20世紀末陸續走向韓國并持續至今。韓國一共上映了超過10部的張藝謀電影,韓國市場大陸電影票房排名前三名都是張藝謀電影,具體為《英雄》《十面埋伏》《滿城盡帶黃金甲》,其中2003年斬獲191萬觀影人次的《英雄》,至今在大陸電影排名第一,中國電影排名第二,在《赤壁》(下)之后;而且《菊豆》《英雄》等多部電影被反復放映。韓國市場的陳凱歌電影也多達7部,《霸王別姬》被來回放映三次。從這些數據上可以看出,張藝謀電影與陳凱歌電影,其前期代表作品具有一定競爭力,其競爭力核心便是充溢的現代意識。進入新世紀,作為“看碟的一代”,王小帥、婁燁、張元、張揚、管虎、賈樟柯等第六代導演開始另辟蹊徑。他們的電影同樣呈現現代意識,但與第五代卻明顯不同。他們從過去回到現實,從歷史大人物回到現實小人物,從精英意識回到平民意識,從宏大敘事回到日常敘事,從民族反思回到現實關照。他們尊重人這個主體,關注大時代里小個體的生存境遇與精神面貌,反思人的異化與人性迷失,追求人的主體性價值。由此,現有的第六代作品多少帶有某些現代主義間或可以稱之為“新啟蒙”的文化特征,即現代性的另一個面向:對社會現代性的批判與對審美現代性的追求。而這正是全面追求好萊塢化的韓國電影所普遍缺乏的。新世紀伊始,王小帥、婁燁、賈樟柯等第六代導演的電影便得以在韓國上映,贏得韓國電影人的普遍尊重。單從數據上看,在所有第六代導演中,王小帥與賈樟柯在韓國無疑具有一定的競爭力與傳播力。其中,賈樟柯創作的《小武》《山河故人》《無用》《二十四城記》等被韓國引進,獲得理想的口碑與票房。比如,《三峽好人》由于獲得戛納電影節重要獎項的加持而獲得1.2萬的觀影人次。可以說,賈樟柯電影在韓國獲得一定粉絲并影響到韓國的電影創作,實現了良好的文化傳播力。
最后,中國電影具有散發影像韻味的文化傳播力。韻味是我國傳統美學的重要范疇。南朝梁劉勰首次提出“余味說”,“味”開始成為一大美學范疇;南朝鐘嶸繼而提出“滋味說”,強調詩歌“指事造形”“窮情寫物”,重形象,含味道,有藝術感染力,“滋味”亦成美學范疇;晚唐司空圖進而提出“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后可以言韻外之致耳”與“以全美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后人對其詩歌貴在“韻外之致”“味外之旨”的觀點稱之為“韻味”說。“韻味”即是強調作品有意境而生神韻,意味含蓄而余味無窮,“給人更深切更持久以至永無窮盡的美感享受”。中國電影亦受“韻味”說的影響,形成費穆、謝鐵驪、吳貽弓、陳凱歌、楊超等一風格脈絡,“此條線上的電影作品,追求的是電影的‘韻味’,風格上不以戲劇性見長”。謝鐵驪的《早春二月》、陳凱歌的《黃土地》《孩子王》、楊超的《長江圖》、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與畢贛的《路邊野餐》《地球最后的夜晚》等電影,去戲劇性而求抒情性,予自然以詩意、情意、思意,用象征、隱喻以賦“象外之象”“味外之旨”,是富有綿延不絕審美意味的詩性鏡語。例如,《地球最后的夜晚》的韻味并非來自像《長江圖》中的山水物象,而是現實與夢境、過去與現在的并行與交雜而帶來的含糊與神秘。其敘事破碎而龐雜,隱喻眾多而多義,過去與現在時空的隨意轉換,記憶、現實與幻覺的堆疊,都使得該電影盡顯奇異、魔幻。其實,除此之外,張藝謀、賈樟柯等導演的作品中也含有韻味。《英雄》是一部韻味之作,絢爛之畫面、詩意之“雨滴”等慢動作以及劍字相通的藝道,都給人以美的感受與對道的思考。以上電影所具有的意境、詩意、神秘都使電影生發韻味效果,顯示出它的獨特性與珍貴性,而這都使得韻味成為中國電影所具有文化競爭力的明顯特質。反觀韓國電影,盡管也有《醉畫仙》《燃燒》等含具意境與韻味的電影,但從數量與世界影響力上,都不及中國。不過,影像韻味在賦予中國電影文化競爭力的同時,也影響到了傳播,進而影響到了市場競爭力與傳播力。盡管《英雄》在韓國有多次放映,觀眾對其給予較高評價,但其理想的市場表現主要來源于高概念大電影而非點綴其中的韻味;而《影》《地球最后的夜晚》《大象席地而坐》等富含韻味的中國電影,由于觀影門檻較高,阻礙了受眾的觀影熱情,也真實影響到了市場表現,僅僅獲得3000以下的觀影人次,而這種藝術形式也會影響到這些電影的二次傳播等,最終僅僅獲得較小文藝圈子的討論與認可。
結 語
中國電影在韓國的市場表現,獲得一定成績并具有文化記憶、現代意識等文化競爭力,但市場占比卻始終較低,不具市場競爭力,傳播力較弱。造成此現狀的原因有多種,但中韓電影的美學差異卻不容忽視。可以說,中國具有與韓國電影明顯的美學差異且美學價值卻越發不足。文化/美學具有民族性,而這一性質就決定了電影美學也存在差異性。深受憂患意識與樂感文化/儒道美學的中國電影美學,在主題闡釋、情感表達與形式追求上,多追求陽剛/崇高/悲壯美學且陰陽悲樂間趨向中和美學,在滿足視聽快感與情感快感基礎上,更要影以載道,趨向倫理快感,讓人胸懷積極樂觀與心向真善美。《雙旗鎮刀客》《天地英雄》《讓子彈飛》《紅海行動》《戰狼》系列等是典型的陽剛美學,充溢著積極而充沛的力量感與力比多但又融入少許抒情元素,在極易調動觀影者高亢情緒的同時,也給予一定情緒緩和;《英雄》《霸王別姬》《霍元甲》《妖貓傳》《影》《江湖兒女》等則屬悲壯美學,有悲劇意味但又滲入積極價值,讓人于悲喜交集中而不至于完全墜入悲觀、絕望等負面情緒。但韓國電影卻有所不同,具有極端的美學傾向。深受韓民族恨文化的韓國電影,審美趨向極端,蘊含恨意識。而《戰國》《關云長》《夜宴》《小時代》等呈現出的價值混亂等更是影響了中國電影的海外傳播,繼而消磨中國電影的文化競爭力與傳播力,無法傳播優秀的中國文化與形成強有力的文化傳播力。
因此,中國電影應該清晰地認識到自己的優勢而不能盲目地自我否定,但也應該承認,價值混亂、民族主義等內外原因,中國電影的海外傳播不容樂觀,文化傳播力依然十分薄弱。中國電影一方面要提高內容質量,融入中國文化,特別是吸引韓國受眾的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加大形式創新,吸收中國傳統山水畫等藝術元素,創造新的電影語言;另一方面也要拓寬傳播渠道,加大與韓國營銷公司合作,積極宣發中國電影。唯有多方面改進,中國電影才能在韓國占有一席之地,才能提升中國電影的文化競爭力與傳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