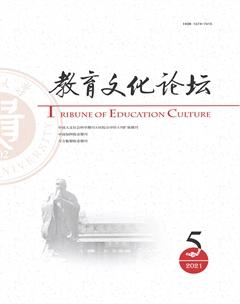政治哲學視角下的古希臘自由教育思想
侯素芳
摘 要:古希臘自由教育指與奴隸相對的自由人的教育。自由教育思想首創自蘇格拉底,經由柏拉圖推進,至亞里士多德發展成熟。本文以政治哲學為視角,通過深入閱讀經典文本,從自然自由、德性自由與政治自由三個維度對自由教育思想進行解析。自然自由認為自然性是人性的重要組成部分,要給予適度的滿足;德性自由是明確個體對德性的自我要求,做一個高貴的人;政治自由是明確個體所應承擔的社會職責,以建構正義的理想城邦為己任。
關鍵詞:古希臘;自由教育;政治哲學
中圖分類號:G5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7615(2021)05-0015-07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1.05.003
古希臘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思想以人的理性發展為前提,以個人追求高貴的精神生活為路徑,以實現城邦的正義為目的。自由教育思想首創自蘇格拉底,經由柏拉圖推進,至亞里士多德發展成熟,是古希臘最重要的教育思想,也是對后世影響最為深遠的教育思想。特別是列奧·斯特勞斯在民主時代對古希臘自然目的論的推崇,對自然權利的研究,對古希臘自由教育思想的回歸,使得對這一教育傳統進行反思顯得尤為必要。本文以政治哲學為視角,深入閱讀經典文本,從自然自由、德性自由與政治自由三個維度對古希臘三位哲學家的教育思想進行解析,力求客觀再現其教育思想的“自由”特色。
一、自由教育之自然自由
自然自由是指人出生就擁有的作為人的各種權利。這里借用這一概念,專門用來說明三位哲學家對于人的自然性的認識,對于人的自然性與理性關系的處理。自然性是人性的重要組
成部分,“不可去”亦“不可盡”,要給予適度的滿足,重點在于發揮人的理性的指導作用。自然是人類生存的物理時空,也是人自身的重要屬性,古希臘自由教育思想具有鮮明的人本特色,對于理性人的認識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1.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在申辯的法庭上不止一次提出自己生活的貧困,他以省察自身與他人為使命,以證明人應該追求高貴的生活,并在申辯即將結束時提請陪審團監督他的兒子們,如果他們關心錢財或別的東西勝過關心德性,就要譴責他們、懲罰他們。這些細節仿佛表明,蘇格拉底并不關心人的物質需要,他的注意全部集中在人的精神層面,那么他對于人的本性到底有怎樣的認識?人的自然屬性在他的人性論中有什么樣的地位?通過經典著作中蘇格拉底形象的描繪,大致可以回答上述問題。
通過柏拉圖的描述大體可知,蘇格拉底本人是個身體強健之人。《申辯》中蘇格拉底自陳參加過三次著名戰爭[1]109,《會飲》借阿爾基弼亞德之口,道出了蘇格拉底身體的強健:戰爭時期,在霜凍厲害的嚴寒天氣,其他人穿著鞋裹著氈子和毛皮時,他卻可以光著腳;缺乏糧食時他擅于忍饑挨餓,食物充足時又最懂得如何享用。在戰爭敗退時,他不僅救了阿爾基弼亞德的命和武器,而且自己扛著重兵器徒步堅持作戰,直到隊伍被完全打散[2]。透過這些細節描述可以看出,蘇格拉底追求身體強健,也有相對充足的物質資源保障其基本的自然需求。“無論如何,直到他46歲的時候,他不可能是屬于雅典公民中最窮的階級,因為在公元前424年他還作為一個‘重武裝步兵或者全副武裝的步兵在服役,而且必定有官方認定的使他有義務參與這種服役的收入。”[3]可見蘇格拉底的生活基于自然又不完全受制于自然,他以強大的自我節制力,以自身的理性駕馭自然,從而展現了他的自然自由。
《云》中的蘇格拉底以否定人的必然性的方式來追求自由。在他的學校——思想所里,他測量跳蚤跳躍的距離,觀察蚊子的身體結構;但他卻忘記了自身的身體性存在,為了保證不受外界物質的影響而思考高深的東西,他將自己懸掛在半空中的吊籃里,仿佛人可以脫離物質而生活,甚至用幾何學代替食物。阿里斯托芬就這樣呈現著蘇格拉底的矛盾性,他以擺脫物質的方式研究物質,他以替代食物的方式無視食物,在令人捧腹的笑聲中消解了蘇格拉底超越身體需要,超越人的必然性以追求無限自由的企圖。
蘇格拉底在思想里尋找高深的東西,即非人化的自然的普遍性,在此過程中呈現出的卻是人本身的物質性。人的自然需要是人生命的重要組成部分,對超越自然性的自由不加節制地追求只能是以疏離生命為代價,阿里斯托芬筆下的蘇格拉底正是以損害人性的生活方式在教導人們對于人的自然性的認同。
2.柏拉圖
柏拉圖對待身體的態度與其老師有異曲同工之妙。表面上看起來柏拉圖的《理想國》是在言辭中建立理想的城邦,事實上恰恰是言辭中理想城邦建構的不可能性反證了剝奪人的身體的自然需要之路是行不通的。
護衛者的生活方式。柏拉圖借用“高貴的謊言”建立城邦,“他們雖然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鑄造他們的時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黃金,這些人因而是最可寶貴的,是統治者。在輔助者(軍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銀。在農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鐵和銅。”[4]415-A金、銀和銅鐵者的靈魂中占主導地位的分別是理智、激情和欲望,心靈的正義在于理智能主宰激情與欲望,城邦的正義在于三種人的正當分工,“當生意人、輔助者和護國者這三種人在國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擾時,便有了正義,從而也就使國家成為正義的國家了。”[4]434-C在此基礎上,柏拉圖對正義城邦中的護衛者的生活提出了明確要求:“第一,除了絕對的必需品以外,他們任何人不得有任何私產。第二,任何人不應該有不是大家所公有的房屋或倉庫。”[4]416-E
護衛者的生活最幸福。理想城邦的出發點是城邦整體,是所有人的幸福,因此,護衛者生活最幸福。“我們的護衛者過著剛才所描述的這種生活而被說成是最幸福的,這并沒有什么可奇怪的。因為,我們建立這個國家的目標并不是為了某一個階級的單獨突出的幸福,而是為了全體公民的最大幸福;因為,我們認為在一個這樣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正義,而在一個建立得最糟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不正義。”[4]420-C
為了城邦的正義,護衛者個人的物質生活是微不足道的,他沒有私有財產,甚至沒有家庭,這種對人性的自然性的極端無視怎么可能成就理想的城邦?所以,柏拉圖說,這樣的城邦只可能存在于天上。柏拉圖借助理想城邦的不可能性說明,人的自然性是人性的基本組成部分,“不可去”亦“不可盡”,只能給予適當的滿足。柏拉圖為此塑造了一個心靈的塑像,一個人形的外殼下面包裹著三合一的心靈,其中,最大的一個是多頭怪物的獸像,第二大的是獅形的像,第三個是人形的像。柏拉圖借此表明,人的欲望、激情與理性的沖突,表明自然自由的限度。
3.亞里士多德
“自然物的生長、運動和變化過程就是一個實現其目的的過程。在某些情況下,自然物的目的就是它的形式,其生長、運動和變化就是一個從‘潛能不斷向‘現實轉化與實現,最終獲取形式的過程。”[5]此所謂亞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論。他將其質料與形式二分思想運用于人自身的研究,認為人由身體與靈魂構成,而靈魂又可區分為理性與非理性兩部分——理性靈魂主宰人的思想,非理性靈魂掌管人的情欲。身體受制于靈魂,靈魂的非理性部分受制于理性部分。人的發展受自然目的論支配,人的自然本性在于靈魂統治身體,人的目的就在于實現人的靈魂由“潛能”向“現實”的轉向。人的創生程序是身體先于靈魂,靈魂的非理性又先于理性,因此,教育應首先關注兒童的身體,之后是情欲,最后是理性。對前兩者的教育都應以有益于理性發展為目的。正所謂人的發展受制于“[出生所稟的]天賦,[日后養成的]習慣,及[其內在的]理性。……人類對此三端必須求其相互間的和諧,方才可以樂生遂性”[6]1332a40-1332b5。
從自然目的論出發,亞里士多德將人區分為奴隸與自由人,區分二者的標志當然是靈魂的差異,但人的身體也是決定一個人自由與否的重要條件。就身體而言,“自然所賦予自由人和奴隸的體格也是有些差異的,奴隸的體格總是強壯有力,適于勞役,自由人的體格則較為俊美,對勞役便非其所長,而宜于政治生活。”[6]1254b30為生育身體健康的自由人,亞里士多德要求立法家預先關注婚姻制度,在合適的年齡成婚,并給予適當的生育知識教育,要鍛煉身體,孕婦也要養成經常運動的習慣。要重視兒童營養以促進身體發育,乳類食物是首選。要讓兒童及早鍛煉,養成良好習慣。五歲前以游戲或娛樂方式促進身體活動,之后可以學習輕便的體操。但身體的訓練不能過度,要與兒童的年齡相適應,兒童身體應自然生長。不應給予過度的與職業相關的訓練,身體是高貴的,任何粗鄙的訓練都與兒童的自然自由相違背。
綜上,三位哲學家對自然教育之自然自由的探討,在一定意義上為教育設計了理想的人格形象,“美善的理想人格作為個體的理想型相是哲學作為愛的教育對人進行教化的目標”[7]。“亞里士多德認為,從人性向神性攀越的這種普遍意義上的人的尊嚴純粹植根于人的理性即邏各斯。”[8]身心和諧發展的至高境界是對美善的不懈追求,人性深植于理性之中,有尊嚴的人生才是幸福的。
二、自由教育之德性自由
德性是三位哲學大師探討的一個重要主題,其最高境界是善。善有兩個層面的含義:一個是本體論意義上的,是事物的本質,表現在人自身,就是一個人如何面對自我,追求個人正義;一個是倫理學意義上的,用以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追求倫理美德。所謂德性自由,就是明確個體之人應對上述兩個面向進行自我要求,做一個高貴的人。
1.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志在追求高貴的生活,而生活的高貴在于人對道德的認知與踐行。蘇格拉底的德性體現在他的愛知求真的哲學生活中,他視哲學生活為最大的政治,為雅典城邦的自由可以付出生命的代價。
講真話。在《申辯》中,蘇格拉底為自己辯護的起點是表明自己的態度,那就是在法庭上自己要講的都是真話,而不是修辭術,不會把弱的變強,他所追求的是真理,這是作為一個演說者應具備的德性,更是一個哲學家必備的德性。
是我所是,秉持無知之知而非智者之知。什么是智者之知?就是他在辯護開始時提到的修辭術,智者教人以政治智慧或政治德性,其最大特點是把弱的變強,以從中謀利,這與他追求的求真向善的哲學智慧相背。德爾斐的神諭說蘇格拉底最智慧,而他自認為自己并不智慧,于是他開啟了自我求證之旅。他拜訪據說很智慧的政治家,發現他們并不智慧,于是告知對方他并不如自己認為的那樣智慧,聲名顯赫的政治家都被他證明是不智慧的。他拜訪詩人,發現詩人的創作并不因為智慧,而是靠靈感的激發,他們甚至都不理解自己的詩歌,竟然還自認為自己在其他事情上也是最智慧的。他拜訪匠人,這些人的確知道他所不知道的,但也同詩人一般,因為自己的技藝而膨脹地認為自己在其他事情上也最智慧。通過這番考察,蘇格拉底如此回答神諭:自己既不像他所考察的那些人那樣智慧也不那樣愚蠢,他就是他,“是我所是”才是他的選擇。
堅守使命,何懼死亡。蘇格拉底的考察為的是證明只有神是最智慧的,是神意讓他通過省察自己和那些強不知以為知的人,對雅典人進行德性教育,不是金錢、名聲與榮譽,而是智慧與真理成就高貴人生。“最好的人,你是雅典人,這個最偉大、最以智慧和力量著稱的城邦的人,你只想著聚斂盡可能多的錢財,追求名聲和榮譽,卻不關心,也不求知智慧和真理,以及怎樣使靈魂變成最好的,你不為這些事而羞愧嗎?”[1]108為了自我辯護,他以特洛伊戰爭中的英雄阿基琉斯為喻:英雄在出征前,母親告訴他替朋友報仇的代價是自己生命的終點,而英雄寧愿選擇死亡也不要在恥辱中茍活。蘇格拉底贊美英雄的壯舉,以此告誡雅典人,只有堅持真理,人活著才有意義。
真正解決問題的辦法是把自己教育成最好。蘇格拉底的申辯并沒有打動雅典人,投票的結果支持他有罪的石子比反對的多了30個,法庭判決他有罪。在臨終告白中,他仍然堅守自己的使命,教育雅典人:“你們靠殺人來阻止人們責備你們活得不正確,這念頭可不美。因為這種解脫既全不可能,也不美。而那最美和最容易的解脫,不是阻止別人,而是把自己培養成最好的。”[1]136
2.柏拉圖
自由人的教育是實現心靈的轉向。通過“高貴的謊言”在言辭中建構的城邦一定是善的,要使城邦保持統一、和諧與秩序,就必須強化其道德基礎,確保它“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節制的和正義的”。城邦正義的根本在于城邦公民個體四主德的實現,即個人的智慧、勇敢、節制與正義。為此,柏拉圖設計了一條哲學家的教育之路。
20歲前的初等教育:節制、勇敢與智慧美德的訓練。《法律篇》中柏拉圖探討了六歲前的兒童教育。分兩個時段,三歲前的養育與三歲后的游戲,倡導對兒童的身體進行鍛煉,以求其發展的平衡。這種鍛煉要在胎兒期開始,在柏拉圖看來,無論是自主活動還是被動的活動都將有助于兒童對營養的吸收,以促進早期的身體生長。更為重要的是運動可以克服由驚嚇與恐懼而養成的膽怯的習慣,培養心靈的勇敢美德。溫和的脾氣有助于良好道德品質的養成,暴躁則易導向邪惡,因此,孕期的婦女要保持好心情,不能無節制地痛苦或快樂,要持中庸之道,養成“仁慈、明智、安詳的精神”[9]548。三歲前的教育目的在于兒童養成“一絲不茍地服從指令”的習慣。“正確的撫養制度必定最能使身體、靈魂完善和卓越”[9]543。這種教育的風俗與習慣雖不是正式的法律,但卻是城邦制度的支柱。三到六歲的兒童教育仍然遵循中庸的法則,這個時期兒童要游戲,兒童出于自然本能會發明各種游戲,要把兒童集中在所在地的圣地進行統一教育,要有專人負責管理。六歲后男女兒童分開接受教育,以跳舞和摔跤訓練身體,以音樂卓越心靈。進行軍事訓練,培養守城能力、勇敢美德對于男女兒童都是必要的。智慧的訓練途徑是閱讀、書寫與琴弦,音樂與體育的配合是為了愛智與激情達到和諧。
20歲后的高等教育。高級層次教育內容包括算術、幾何、天文、音樂及辯證法,面向心靈中的理智層面,教人以智慧的美德,并能以智慧指導欲望與激情,做一個正義之人,達到心靈的至高境界,實現心靈的正義。
《理想國》卷七開篇,柏拉圖借用著名的洞穴比喻,說明教育就是實現心靈轉向。在洞穴式的地下室里,一群被束縛了頭與腿腳的囚徒,他們無法活動,只能看前面洞壁上的陰影,看不到任何真實的事物,于是將陰影當成真實。如果一個人被解除桎梏,轉身后被人拉著沿著陡峭崎嶇的坡道走出洞穴,就可以看見真實的世界。柏拉圖把這個過程看成是靈魂上升的過程,是人的認識由可見世界上升到可知世界的過程,結果是看到善的理念。在柏拉圖看來:“知識是每個人靈魂里都有的一種能力,而每個人用以學習的器官就像眼睛。——整個身體不改變方向,眼睛是無法離開黑暗轉向光明的。同樣,作為整體的靈魂必須轉離變化世界,直至它的‘眼睛得以正面觀看實在,觀看所有實在中最明亮者,即我們所說的善者。”[4]518-D
問題是桎梏是如何解除的?關鍵在于哲學,“哲學有解放作用和凈化作用,是不能抗拒的,因此心向哲學,一切聽從哲學,拳拳服膺。”[10]39哲學可以讓人擺脫感官欲望的誘惑,實現靈魂的自由,學習哲學就是心靈擺脫身體的干擾,用柏拉圖的話就是“練習死亡”[10]36。人的靈魂是不死的,“一個人應當為自己的靈魂打氣,在生活中拒絕肉體的快樂和奢華,以為這是身外物,對自己有害無利,而一心追求知識的快樂,不用外在的飾物打扮自己的靈魂,只用它自己固有的東西來裝點它,如明智、公正、勇敢、自由、真實之類。”[10]80
3.亞里士多德
亞里士多德將德性劃分為“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11]1103a15。
道德德性的培養依賴于習慣的養成,道德德性取決于一個人的實踐活動。“在我們身上的養成既不是出于自然,也不是反乎于自然的。首先,自然賦予我們接受德性的能力,而這種能力通過習慣而完善。其次,自然饋贈我們的所有能力都是先以潛能形式為我們所獲得,然后才表現在我們的活動中。但是德性卻不同:我們先運用它們而后才獲得它們。……第三,德性因何原因和手段而養成,也因何原因和手段而毀喪。……一個人的實現活動怎樣,他的品質也就怎樣。所以,我們應當重視實現活動的性質,因為我們是怎樣的就取決于我們的實現活動的性質”[11]1103a25-1103b20。這明確表達了亞里士多德關于道德德性培養的基本主張。道德德性通過習慣來養成,人沒有天賦的道德,卻具有接受道德的能力;道德的形成依靠現實的活動,一個人只有從事道德的行為,才能成為一個道德的人;現實活動對人的影響如此之大,從事什么樣的活動決定成為什么樣的人,“我們是怎樣的就取決于我們的實現活動的性質”[11]1103b30。比如,正是由于在危境中的行為不同和所形成的習慣不同,有人成為勇敢的人,有人成為懦夫。
道德德性的培養應遵循適度的原則,道德德性就是中道、中間,既不是過度,也不是不及。首先,避開最與適度相反的那個極端。以慷慨這一中庸德性為例,揮霍與吝嗇是過度與不及,相對于把財物看得過重的吝嗇,亞里士多德認為不能自制、揮霍鋪張是更惡劣的品質。所以,要培養一個人慷慨的德性就要避開與之距離更遠的揮霍一端,做到兩惡相權取其輕;其次,矯枉過正。遠離錯誤一端,努力將自己拉向相反的方向,要如同矯正一根曲木要矯枉過正一樣去接近適度;再次,警惕令人愉悅的事物或快樂。亞里士多德認為,保持適度的德性是一件困難的事,雖然一個人的行為偏離適度走向兩端必須受到譴責,但偏離程度多大應當受到譴責是沒有特定邏輯支持的,需要取決于具體情狀,依據我們的感覺而定。
理智德性。亞里士多德將人的靈魂區分為邏各斯(理性)與非邏各斯。他研究科學、明智、智慧與努斯,認為智慧是“努斯與科學的結合”[11]1141a20,所謂理智德性就是“哲學智慧”,就是努斯與科學的結合。努斯“基本上是指一種目的性思考——推理”[12],是對事物始因的認識,或者說第一原理的認識。“努斯就是某物之外觀于其中得以被看見的光”[13]。在亞里士多德看來,這種智慧之光依賴于人的感覺,與生俱來且隨著年齡而增長,因此,對于沒有經過證明的經驗見解,應當像得到證明似的給予尊重,努斯因而是最高貴的、神圣的。亞里士多德進而提出沉思的生活最幸福。因為沉思最高等、最連續持久、最愉悅、最自足、最被人們喜愛、最具閑暇,使人的生活充滿屬人的神圣性。“應當努力追求不朽的東西,過一種與我們身上最好的部分相適合的生活。……合于努斯的生活對于人是最好、最愉悅的,因為努斯最屬于人。所以說,這種生活也是最幸福的。”[11]1177b30-1178a5
如上所述,德性自由是哲學家們對個體心靈的哲學觀照,是對節制、勇敢、智慧、正義的畢生追求,對心靈自由的最熱切呼喚,正是這種充滿神圣性的德性自由彰顯著人的生命尊嚴,使生命走向高貴。
三、自由教育之政治自由
政治與教育的關系是三位大師探討的另一個核心問題,自由教育之政治自由就是要實施哲學教育,培養人的理性,明確個體所應承擔的社會職責,以建構正義的理想城邦為己任。
1.蘇格拉底
不參與政事。所謂不參與政事是指不在公共場合為城邦出主意,而是私下里為人們奔走忙碌。《申辯》表明無論是雅典的民主政治還是三十僭主政治,都曾經逼迫蘇格拉底去行不義之事,這對于從不屈服于任何違背正義之人的蘇格拉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自認參與政事的結果就是早早走向死亡,無法為城邦正義做更多有益的事。“凡是坦誠地反對你們或別的大眾,阻止在城邦里發生很多不義或犯法的事的人,都活不了,而其實,誰若一定要為正義而戰,并且想多活一段,他必須私下干,而不是參與政事。”[1]113-114當然,他也曾經指出,反對他參與政事也是神意。
哲學作為政治。蘇格拉底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證明,他不會屈從于任何違背正義之人,而是依據法律和正義而行動,正因如此,他說自己不適合公開從政,但是,他的愛知使命促使他私下里省察他人,教育青年追求正義,以此哲學的方式參與政治。“我私下到你們每個人那里,做有最大益處的益事,我嘗試著勸你們中的每個人,不要先關心‘自己的,而要先關心自己,讓自己盡可能變得最好和最智慧,不要關心‘城邦的,而要關心城邦自身,對其他事情也要按同樣的方式關心。”[1]127他勸勉雅典人要關心城邦與城邦的正義,“人啊,你只想著聚斂盡可能多的錢財,追求名聲和榮譽,卻不關心,也不求智慧和真理,以及怎樣使靈魂變成最好的,你不為這些事而羞愧嗎?”[1]152他以愛知為榮,勸勉人們未經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一個人要關注自己的靈魂,關注城邦的正義。對正義城邦的哲學追問就是蘇格拉底參與的最大政治。
2.柏拉圖
哲學家王。教育首先是一條自我提升之路,經由哲學的教誨,掌握萬物所從出的善的理念,實現人的解放,成為哲學家。哲人要向大眾回歸,重回洞穴。一個志在城邦的正義者向洞穴的回歸已然超越了個人自由的生活境界,他的“下降”意在城邦政治的整體提升。在政治這個實踐領域僅僅具有知識是不夠的,還需要15年的實踐鍛煉,“派他再下到地洞里去,強迫他們負責指揮戰爭或其他適合青年人干的公務,讓他們可以在實際經驗方面不低于別人,還必須讓他們在這些公務中接受考驗,看他們是否能在各種誘惑面前堅定不移,或者,看他們是否會畏縮、出軌。”[4]540-A
哲學家王的善治。經由洞穴中艱難的上升與勇敢的下降,經過知識學習與實際工作所有面向的考驗,在50歲上終于迎來哲學教育的最后關頭,他們將把靈魂的目光轉向上方,轉向善,他們將繼續進行哲學研究,同時在需要時成為城邦的統治者,直接參與城邦的政治事務,用善的理念去治理城邦的公共生活與個人的私人生活。“我們將要求他們把靈魂的目光轉向上方,注視著照亮一切事物的光源。在這樣地看見了善本身的時候,他們得用它作為原型,管理好國家、公民個人和他們自己。在剩下的歲月里他們得用大部分時間來研究哲學;但是在輪到值班時,他們每個人都要不辭辛苦管理繁冗的政治事務,為了城邦而走上統治者的崗位——不是為了光榮而是考慮到必要。”[4]540-B
3.亞里士多德
政體及分類依據。亞里士多德認為政體即城邦公職的分配制度,他以能否照顧全邦人民的利益為標準,將政體分為正當政體與變態政體。“依絕對公正的原則來評斷,凡照顧到公共利益的各種政體就都是正當或正宗的政體;而那些只照顧統治者們的利益的政體就都是錯誤的政體或正宗政體的變態(偏離)。這類變態政體都是專制的(他們以評價管理其奴仆那種方式施行統治),而城邦卻正是自由人所組成的團體。”[6]1279a-20考察城邦政體就是考察城邦“最高治權的執行者”,最高治權的執行者可以是一個,是少數人,也可以是多數人。在照顧全邦共同利益的前提下,正宗政體可以是以一人為統治者的“王制(君主政體)”,不止一人而又不是多數人為統治者的“貴族(賢能)政體”,以群眾為統治者的“共和政體”;而相應的僭主政體為王制的變態(追求個人利益),寡頭政體為貴族政體的變態(追求富人利益),平民政體為共和政體的變態(追求窮人利益)。
理想政體與教育。基于城邦最高治權執行者的研究,亞里士多德提出理想政體是中產階級執政的共和政體,因為只有中產階級擁有節制與中庸的德性,能服從理性而又少有野心。城邦的目的在于公共利益、公共善,在于城邦的正義,城邦的德性取決于城邦公民的德性,取決于人是否智慧、勇敢、節制與正義,取決于個人之善,因而取決于城邦提供給個人怎樣的教育。亞里士多德從天賦、習慣與理性三個維度考察個人的發展。其中,天賦是教育的基礎,習慣的力量不可小視,會成為第二天性,要通過教育養成好的習慣,而理性要發揮指導作用,使三者和諧發展,完善個人才能與德性。這種教育是自由教育,是自由人應當享有的身心和諧發展的教育,是城邦正義的教育。“我們這個城邦的公民們當然要有任勞和作戰的能力,但他們必須更擅于閑暇與和平的生活。他們也的確能夠完成必需而實用的事業,但他們必須更擅于完成種種善業。這些就是在教育制度上所應樹立的宗旨。”[6]1333b
綜上,哲學家對于城邦的認識差異明顯,他們都強調哲學的價值:柏拉圖明確提出哲學家王,以哲學家治理城邦;亞里士多德強調中產階級執政,一個是政治的“一元化模式”,一個是“多元化模式”[14],一個是對確定與不變的極致追求,一個是對中庸適度,依具體情境作出抉擇的態度分野,使其教育思想也表現出對不變與變不同追求的精神氣質。
四、結語
古希臘自由教育思想具有鮮明的哲學特色、倫理特色及政治特色。奠基于雅典精神哲學的古希臘自由教育思想,具有十足的人文氣息,高揚人的理性精神,為后世建立了理性教育的典范;追問何謂美好生活,人如何能夠過上美好生活,從蘇格拉底的“認識你自己”“未經過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到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對智慧、勇敢、節制、正義四主德的研究,無不彰顯著教育思想的倫理特色;其政治特色表現為哲學是最大的政治,哲學家王,“人依據自然是政治的動物”,對個人正義人生的追問最終指向正義的城邦,教育是實現城邦正義不可或缺的重要路徑,培養正義城邦的正義公民是自由教育的終極目的。古希臘自由教育思想的上述特色決定其教育思想指向人性、心靈、教育與政治、教育與人生等宏大問題,在闡述這些問題時又能夠緊密結合現實社會的風土人情、習俗風尚,理論建構與實踐關切緊密相連。這種充滿豐富想象力的學說為世人敞開無限的意義空間,因而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時空轉換,問題不變,行行重行行,回顧與反思亦然。
參考文獻:
[1] 柏拉圖.蘇格拉底的申辯[M].吳飛,譯/疏.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
[2]柏拉圖.會飲篇[M].王太慶,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79-80.
[3]A.E泰勒,T H龔珀茨.蘇格拉底傳[M].趙繼銓,李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24.
[4]柏拉圖.理想國[M].郭斌和,張竹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5]王濤.人、城邦與善——亞里士多德政治理論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44.
[6]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
[7]羅興剛.美善:柏拉圖理想人格的構型[J].道德與文明,2020(3):72.
[8]謝芳.人性之維:亞里士多德論邏各斯[J].倫理學研究,2016(4):61.
[9]柏拉圖.柏拉圖全集:第三卷[M].王曉朝,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0]柏拉圖.裴洞篇[M].王太慶,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11]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M].廖申白,譯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12]廖申白.亞里士多德的“努斯”作為目的性推理:一種解釋[J].世界哲學,2013(5):24.
[13]溥林.海德格爾論亞里士多德的“努斯”概念[J].哲學動態,2017(3):61.
[14]王巖.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政治哲學比較研究[J].政治學研究,2001(4):45.
(責任編輯:楊 波 鐘昭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