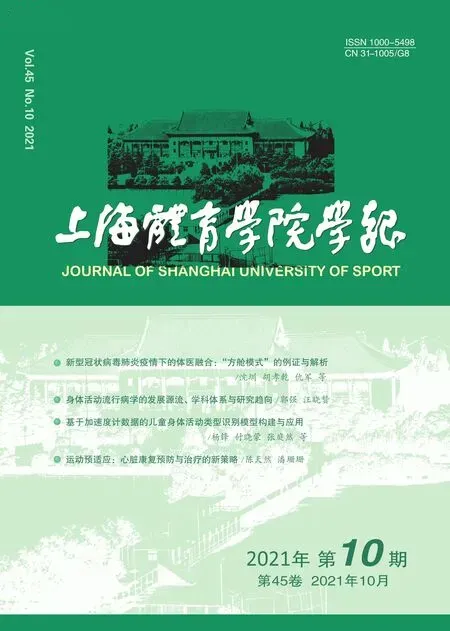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的發展源流、學科體系與研究趨向
郭強,汪曉贊
(1.寧波大學體育學院,浙江寧波 315211;2.華東師范大學體育與健康學院,上海 200241)
身體活動(physical activity)又稱體力活動,其作為人類一種最自然、最基本的生存狀態,使人們在長期的進化過程中達到了能量攝入與消耗持續且高效的平衡。然而,在以信息化、數字化為基本特征的現代社會生產、生活中,人們的身體活動似乎越來越少,科技的“便利性”造就了人們日益慵懶的生活方式,身體活動的平衡被打破,預示著人們最簡單的健康基礎發生了動搖。一項基于全球190萬人的研究[1]發現,2001—2016年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人們身體活動不足的問題日趨明顯。針對兒童青少年乃至成年人身體活動和身心健康水平下降的問題,我國學者從測評方法到影響因素、從橫斷面調查到縱向追蹤開展了多種視角和方法的相關研究,但其認識維度與提升策略似乎仍未跳出單一的“生物學”視角,而轉向從社會生態系統理解身體活動在生產、生活中角色作用的根本變化。
本文試圖剖析身體活動流行病學(physical activity epidemiology)的發展源流、學科體系和研究趨向,探討如何在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的研究框架下考察身體活動與社會生態以及整體健康的關系,厘清“身體活動水平—健康風險因素—積極生活方式”之間的有機聯系,為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的學科定位和研究實踐提供參考。
1 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的研究緣起
1.1 身體活動誘導的生物進化的底層邏輯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2]統計數據顯示,全球每年6%的死亡與身體活動缺乏有關,身體活動缺乏已成為人類的四大死亡風險因素之一。盡管積極參與身體活動的健康效益顯而易見,但是世界范圍內兒童青少年乃至成年人身體活動不足的問題仍不容忽視。人們的身體活動具有最天然的行為屬性,也是日常生活最基本的需求。Cordain等[3]研究發現,人類在1萬年前已基本形成了現在的解剖結構和生理特征,甚至舊石器時代人類的基因組就已“決定”了現在人們久坐少動的生活方式[4]。因為人們對能量攝入的儲存效率在基因表達方面存在差異,在食物匱乏的舊石器時代,這種高效轉化和儲存能量的“優良”基因得以生存和延續[5]。但在物質極為豐富的現代社會,這種“高效”反而助推了肥胖癥和“三高”(高脂血癥、高血壓、高血糖)等慢性病的發生,這可能也是人們難以長期堅持體質量管理的原因之一[6]。Cherow等[7]認為,人類身體活動的進化符合“達爾文主義”自然選擇的生物特性,在舊石器時代,狩獵、采摘等高強度身體活動是人類生存和發展必備的技能,人類進化的自然選擇結果是保留和延續能夠支持劇烈的、持續的身體活動的人類基因[8]。如果說舊石器時代的身體活動是人類為了基因延續的自然選擇結果,那么現代社會則是人們主動放棄了以身體實踐為特征的生產、生活方式,當然也為此付出了文明的代價。從基因、結構到行為,人類基因表達和身體結構的“底層設計”似乎并未隨著工業化和信息化完成適應性的改變,致使身體活動似乎陷入了“生物體”的底層邏輯和“社會人”的行為特征“悖論”之中。
在遠古時期,人的身體活動始終被狩獵或農耕的戶外環境所“支配”,而在現代文明社會似乎依然如此,人們“享受”的社會文明帶來的久坐生活方式是現代科技對自身的“支配”。那么到底是人類面對自然進行了主動適應和積極變化,還是生物遺傳以疾病的形式實施了對人類的悄然改造?并未可知。人類的進化就是對環境變化的生理反應過程,身體活動的進化即為一個典型的例子[9]。所以,理解在當前自然和社會環境下人們的活動狀態可能對人類選擇最優化的生存方式有基礎性的指導作用。從慢性病與久坐行為的強相關性及其低齡化的發展趨勢來看,顯然久坐少動不是人類最恰當的生活方式。根據進化醫學的觀點[10],疾病往往是與人們當時所處的生活方式、環境與生物進化的不匹配有關,同理,身體活動誘導的基因表達與現代生活方式變革的不兼容催生了現代社會慢性病的高發。Booth等[9]研究認為,身體活動不足對基因表達的重要作用普遍缺少科學的、醫學的、公正的審視,導致低估或忽視了身體活動不足誘導的基因表達的現實意義。因此,回顧人類遠古狩獵、采摘生存狀態的進化過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現代人的生存和健康問題。
1.2 剝離了身體實踐的現代生活方式
科技的浪潮推動著人類文明的跨越式發展,機械化、電氣化、自動化、信息化儼然成為社會進步的代名詞,而在以工業機械和信息網絡驅動的工作、學習和娛樂生活中,人們的身體角色發生了扭轉,身體實踐參與程度的減少甚至成為判斷科學技術先進性的關鍵因素。然而,人類長期進化而來的解剖學特征仍然是為滿足穩定的站立、行走和奔跑而設計的[11],從狩獵捕食、采摘野果到屯墾土地、圈養動物,從家務勞動到交通出行,從體力勞作到休閑娛樂,這一系列基本的身體活動似乎都已從日常生活中逐漸剝離甚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自動化、信息化的便捷生活方式。即便人類文明經過現代科技的洗禮,“為動而生”的身體結構仍未發生根本性的改變[11]。與之相對應的是,工業革命徹底改變了人們身體活動與食物供給的關系,從而動搖了人類身體行為模式的底層邏輯,生產效率的提升和物質資源的豐富使人們不再為食物疲于奔命。物質文明的快速發展與人類健康之間的失衡是亟待解決的關鍵問題,但從當前社會普遍的亞健康狀態和低齡化的慢性病發生率看,人類似乎還未找到其間自洽的邏輯。
基于WHO的“每天60 min中至高強度身體活動(moderate to vigorous physical activity)”的建議標準,在歐洲、美國兒童青少年中能夠滿足該標準的比例分別僅為15%和18.4%[12-13],我國同齡人群中每天進行持續60 min以上體育鍛煉的比例也僅為21.2%[14]。更為嚴重的是,不積極的身體活動行為習慣可能會從兒童延續至青少年甚至成年時期[13]。與過去相比,同齡兒童[15]和成年人[16]每天的能量消耗都減少了600 cal(1 cal=4.184 J),人們身體活動水平的變化可見一斑。西班牙學者Merino等[15]較為全面地總結了人們“少動多坐”生活方式的主要原因:①以電視機、計算機、手機和互聯網為代表的休閑娛樂相關的久坐行為日趨增多,導致戶外活動時間減少;②學校體育課數量和質量欠缺,無法滿足學生的日常活動需求;③休閑娛樂的活動形式發生變化,視頻類活動取代了傳統戶外活動;④私家車、公共汽車替代了走路和騎車,成為主要交通出行方式;⑤鋼筋水泥的城市化建設沒有提供良好的人居環境,社會的安全隱患導致人們減少了步行、騎車等活動;⑥信息化和機械化現代社會的生產和生活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⑦家長過度的“安全焦慮”導致其“限制”子女及自身的戶外活動;⑧沒有建立起學校、家庭和社會一體化的、綜合性聯動機制和身體活動支持性環境。由此可見,社會環境的整體變化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和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身體活動減少與久坐行為增加則是最具代表性的變化特征。
1.3 慢性病低齡化趨向的潛在健康危害
根據WHO的數據模型預測,到2030年非傳染性疾病死亡人數將高達5 200萬,占死亡總人數的68%以上,而身體活動不足與吸煙、酗酒、不健康飲食并稱為非傳染性疾病的四大健康風險因子[16]。無論是結構化的健身鍛煉還是非結構化的體力勞作,身體活動往往與日常工作和生活交織在一起。Salbe等[17]研究發現,在針對成年人的身體活動干預中,那些兒時在學校和日常活動中比較活躍的人,其實驗干預效果更佳,兒童進行身體活動的經驗會影響其成年后參與身體活動的動機。1985年電視機普及之初,Dietz等[18]對13 600名兒童青少年開展了一項大規模調查研究,結果顯示看電視時間每增加1 h,肥胖檢出率即增高2%。同時,看電視、使用計算機這類久坐少動的生活方式不僅導致了能量消耗水平的降低,往往還增加了零食等休閑食品、“垃圾”食物的攝入,也會受到更多高熱量產品廣告的誘惑[19]。現代社會生活與身體活動水平相輔相成,心血管代謝相關的“生活方式病”“富貴病”的高發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現代文明的代價,電子化的生產、生活方式將人們牢牢地“拴”在了椅子上,身體活動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悄然發生改變,而人們也樂此不疲。從這個意義上看,人們既是科技文明進步的貢獻者,也是身體活動方式變革的受害者。基于對身體活動水平改變及其健康效益的認識,發現整個社會生態系統似乎缺乏積極的身體活動支持環境,而社會環境的各個組成要素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身體活動流行病學應運而生,對于身體活動不足的流行性普查、影響因素的“病因”推斷、“易感”人群的特征規律識別、健康風險的模型預測等,都需要進行基于多學科交叉的持續探討。
2 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的發展源流
WHO將身體活動不足解釋為“一種流行在世界各個國家的全球性、非傳染性慢性疾病”[20],其嚴重程度可見一斑,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以流行病學的視角將身體活動不足導致的健康問題提升到了新的高度。1996年,Jeremy Morris和Ralph Paffenbarger被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醫學委員會授予奧林匹克勛章,表彰他們在身體活動與健康研究領域作出的突出貢獻[21]。至此,身體活動流行病學被醫學、運動科學等主流學科認可,并形成了流行病學的一個新的分支。
20世紀50年代初,流行病學專家Morris等[22]開展的英國倫敦公交車司機與售票員健康調查揭示了身體活動與冠心病發病率之間的關系。該調查結果顯示,公交車司機和售票員的冠心病發病率存在顯著性差異,即公交車司機心血管疾病的發病率比售票員高出了30%,死亡率也更高。售票員經常走動的工作狀態決定了其具有更高的身體活動水平,而這被認為是導致其冠心病發病率與公交車司機存在差異的最主要因素。1958年,Morris等[23]開展的英國倫敦郵政系統員工健康研究也顯示,郵局客服人員和郵遞員的身體活動水平不同是導致兩者心血管疾病患病率存在差異的主要原因。身體活動與心血管健康之間的關系被研究證實,這被視為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發端的里程碑[24-25]。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的核心在于研究身體活動與健康之間的辯證關系,為發現和解決健康問題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26]。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體育運動遠離于人們的日常生活,僅被用于軍隊訓練和運動競賽[24],早期的公共健康研究主要以“衛生運動”為主導[27],并未與公共健康建立聯系。Morris等[22-23,26]關于身體活動與心血管疾病的研究向人們彰顯了身體活動是一種抵抗疾病和改善健康的方法和手段,也自此樹立了身體活動流行病學在預防疾病和健康風險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20世紀60年代,Paffenbarger設計實施了哈佛大學校友健康追蹤研究,同樣證明了身體活動是一種影響人壽命和慢性病發病率的重要因素[28]。身體活動健康效益的證實使更多公共衛生和運動生理領域的學者涉足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研究。在當時,運動科學研究的焦點在于技術動作、活動行為的生理與心理調節及人體機能的功能表現,但促進健康的身體活動并未得到足夠的重視[24]。1981年出版的Exercise:The Facts一書首次綜合性地評價了運動鍛煉的健康效益,認為運動鍛煉具有預防疾病、促進健康的積極作用[29]。Morris[30]將“通過體育運動預防心血管慢性病”稱為“最劃算”(best buy)的健康行為。1984年,美國疾病與預防控制中心召開的流行病學研討會首次圍繞“身體活動”的主題探索旨在提高居民身體活動水平的行動計劃[31]。這次會議摒棄了臨床研究方法,而是以公共健康的視角探索如何提升身體活動水平進而改善健康水平[32]。自此,身體活動流行病學開始為人們所認識和熟知。Haskell[33]認為,以往單純關注運動訓練如何提升人的機能表現的時代已過去,現代流行病學更加強調身體活動對整體健康的積極影響。1989年,美國疾病與預防控制中心專家Caspersen[34]率先闡釋了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的核心概念、研究方法與應用,探討了身體活動的特征規律及其與各種病因風險之間的復雜關系。1994年,英國邀請了來自全世界的流行病學、運動科學、教育學等領域的學者,召開了以“身體活動”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35],并對身體活動水平的推薦標準(每周至少5 d、每天至少30 min的中等強度身體活動)達成一致意見,這也使各國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研究的國際比較成為可能。《2008年美國身體活動指南》(2008 Physical Activity Guidelines for Americans)[36]的發布極大推動了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的新發展,肯定了身體活動的健康效益,并提出了身體活動的國家標準,隨后加拿大[37]、澳大利亞[38]、英國[39]、新加坡[40]等國家也提出了身體活動建議標準。
人們趨向于久坐少動的工作、生活和娛樂方式是現代社會的新常態。Ekelund等[41]開展的一項覆蓋全球100萬人口的研究揭示了久坐時間、中至高強度身體活動與全因死亡風險的動態變化關系(圖1)。該研究結果證明,身體活動水平越低且久坐時間越久的人,其死亡風險越高。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不控制久坐時間,即使具有較高的中至高強度身體活動水平,仍然存在較高的死亡風險。因此,身體活動流行病學需密切關注久坐行為的類型、強度、時長及其與健康風險之間的關系。

圖1 身體活動、久坐行為與健康風險的動態關系[42]22 Figure 1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activity,sedentary behavior and health risk
3 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的學科體系
3.1 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的研究對象
身體活動最早被Caspersen等[43]于1985年定義為由于骨骼肌活動所產生的任何消耗能量的身體移動形式,該定義被WHO和世界各地的研究者沿用至今。健身鍛煉(exercise)和運動競賽(sport)作為身體活動最常見的組織化活動形式,長期以來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焦點。此外,身體活動還包括日常生活中大量的非結構化活動形式,這些活動同樣產生了能量消耗和健康效益。促進健康身體活動(health-enhancing physical activity)[44]是身體活動的一個解釋維度,其強調不僅應通過專門性的運動鍛煉獲得健康水平的提升,更應關注以走路、騎車、手工勞動、休閑娛樂等為代表的日常身體活動的健康效益。這種非鍛煉性的身體活動恰是人體能量消耗的最大組成部分,并且生命中的大部分時間都處于非鍛煉性活動狀態。與促進健康身體活動相對應的是被認為存在潛在健康危害的久坐行為,其主要指靜坐或躺臥的較低能量消耗的行為組合[45],或在非睡眠狀態下,能量消耗≤1.5 METs的坐或倚靠行為[46],換言之,久坐行為是一種能量消耗較少的特殊身體活動行為。國外有學者提出,每分鐘步行<100步[47]或每天步行<5 000步[18]即可認為處于久坐生活方式。需要注意的是,久坐行為的含義強調低能量消耗的靜坐行為,而那些不滿足身體活動建議標準的無效活動可被認為是身體活動不足[2],但其與久坐行為并不存在線性關系[46]。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研究往往指向總體的身體活動水平,包括促進健康身體活動的健康效益、身體活動不足與久坐行為的健康風險。
“流行病學”的英文翻譯為“epidemiology”,其詞根來源于拉丁文epi(……之中)和demo(人群),主要研究疾病或健康風險的分布特征、發展趨勢、傳播途徑和決定因素等,并有針對性地進行疾病或衛生事件的預防和控制[48],在歷經大量的理論與實踐檢驗后,已逐漸形成社會流行病學和行為流行病學等多個分支。流行病學旨在幫助人們認識和理解慢性病的成因,探索預防和控制疾病發生的方法和手段,其對人們健康的積極作用已被認可,它與生物統計學(biostatistics)并稱為“公共健康”的2個基礎研究工具[49]。WHO已在全球調研報告中提出身體活動不足是一種高危因素,是導致肥胖和慢性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50]。身體活動流行病學作為行為流行病學的一個新興分支,主要關注什么人群、什么時間、什么地方、什么形式的身體活動行為特征,以及怎樣認識不同水平的身體活動與健康的潛在關系[51]。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研究不同人群身體活動的分布特征、影響因素及其與健康水平的關系,重點關注的是身體活動與疾病和其他潛在健康風險的關系,并探究、識別影響人們身體活動發生、發展及健康風險的生物學、心理學、遺傳學和社會學因素。身體活動流行病學被應用于疾病預防和健康促進的干預實踐及人口流行性普查。值得注意的是,人們即便達到了日常身體活動建議標準,仍可能伴隨著嚴重的久坐行為,從而帶來心血管疾病方面的健康風險。因此,需要進一步明確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的理論體系和研究范式,以加深對身體活動與健康水平之間內在關系的認識。
3.2 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的理論體系
3.2.1 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的學科定位
隨著醫療水平和社會生活的發展變化,流行病學對疾病譜系的關注焦點從天花、鼠疫等傳染性疾病轉向了心腦血管疾病、糖尿病、肥胖癥等慢性非傳染性疾病。針對非傳染性疾病的研究,現代流行病學經過了3個主要發展階段[52]:①起步階段(20世紀4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早期),明確了流行病學的基本概念和計算方法;②發展階段(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早期),產生了匹配、交互等新的數據觀察思想,形成了基于計算機的大規模數據分析方法;③成熟階段(20世紀90年代至今),建立了多元化的統計方法和多樣化的暴露因素觀察系統。如前所述,從1953年Morris等[22]探討公交車系統員工身體活動與心血管疾病關系的經典案例開始,到1981年Exercise:The Facts一書明確了身體活動對疾病預防和健康促進的積極作用;從1989年Caspersen首次提出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的學科發展雛形,到1996年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醫學委員會的勛章頒授確立了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的學科地位,這些標志性的時間和事件,與現代流行病學理論體系的發展完善過程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身體活動流行病學始終以流行病學、行為科學、運動科學等跨學科交叉為基礎理論的底層邏輯。例如,美國健康與人類服務部[53]于1996年發布的關于身體活動與健康的科學詢證報告是系統考察和論證身體活動與健康關系的標志性案例報告,該報告協同美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美國慢性病預防與健康促進中心、美國總統體質與競技體育委員會等多個部門、多個領域的學者,共同探討了身體活動的核心概念、影響因素、疾病關系、提升策略,確立了非傳染性疾病的流行病學觀察視角和研究思路。身體活動流行病學向上依次追溯到母學科“行為流行病學—流行病學—預防醫學”的價值定位,可歸納為通過有效地篩查和識別疾病或風險因素、預防和控制疾病或風險因素進而維護與促進人的健康水平。身體活動流行病學作為預防醫學的學科分支,主要從群體視角認識身體活動不足及其健康危害的現象、本質和規律。
3.2.2 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的理論框架
身體活動不足作為一種慢性非傳染性疾病,認識其發生、發展的變化過程有助于開展疾病的診斷、預防和控制,而行為流行病學是認識身體活動不足的人群分布特征和健康危害,提供行為促進策略的重要實踐性方法。Sallis等[54]對367項流行病學研究進行綜述,提出了行為流行病學研究階段分類的系統框架,用以指導有效改善吸煙、營養、心理等方面的不健康行為。本文結合該理論的主體框架和身體活動的研究實踐,提煉了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研究的理論框架(圖2),以便系統、客觀地觀察身體活動與健康水平的關系。

圖2 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研究的理論框架Figure 2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physical activity epidemiology research
(1)建立身體活動與健康的分布關系。身體活動與健康關系的研究既是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的邏輯起點,也是推動身體活動流行病學后續各階段研究的基礎和前提。The Lancet分別于2012年、2016年和2021年出版了3期“身體活動專刊”(physical activity series),有力論證了身體活動不足與全因死亡率、心血管疾病、代謝綜合征、2型糖尿病、肥胖癥等慢性病的關系。身體活動的健康效益或身體活動不足的健康危害具體體現為一定規則下的劑量效應關系,進而驅動了身體活動指南的研制,為不同特征人群的行動實踐提供參考和建議。對于不同年齡、性別、地域、職業等人群,明確其身體活動的分布特征是流行病學研究的基本任務,而不同特征人群(如銀行職員、程序員等長期處于靜坐工作狀態的白領及搬家公司、建筑工地的重體力勞動者)的身體活動強度、時長與健康的關系是否存在特異性差別,以及如何明確不同特征群體身體活動與健康的劑量效應關系以實現健康效益的最優化,都有待持續研究。
(2)發展多樣化的身體活動測評方法。身體活動的有效監測是流行病學研究的關鍵因素。身體活動具有促進健康身體活動和非鍛煉性活動行為等多維屬性,并且滲透在學習、工作、生活的各個場景中,這要求其測評方法具有多元化的特征。總體而言,身體活動測評方法主要涉及以調查問卷、測試量表等為代表的主觀性測評方法和以計步器、加速度計、心率監控儀等為代表的客觀性測評方法。不論采用何種測評工具和方法,都需要體現身體活動的強度、時長、頻率、類型等基本要素,以觀察身體活動與健康水平之間的劑量效應關系。早期有關身體活動水平的大規模人群流行性調查及其分布特征的研究主要采用國際身體活動量表、全球身體活動量表、身體活動階段量表等主觀性調查方法,而運動傳感器技術的革新使不同條件下身體活動的累積時長、能量消耗水平、類型識別的精確測量成為可能。這種不間斷的、自然狀態下身體活動的有效測量極大地提高了人們對身體活動與健康之間關系的認識深度。但是,主觀與客觀測評方法的信度、效度一致性,以及規模性人群的使用成本和可操作性等問題還未得到根本解決。
(3)識別身體活動的多維影響因素。在行為流行病學的語境下,影響身體活動的因素主要是導致身體活動不足發生率增加的因素。基于群體性的觀察視角,身體活動流行病學更關注身體活動行為與整體社會生態學系統的互動關系。根據社會生態模型,身體活動的影響因素包括個體因素(性別、年齡、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自我效能、運動基礎等)、人際關系因素(同伴、家人、教師等)、制度或組織因素(單位規章制度、安全服務保障等)、公共政策因素(財稅支持、教育政策、法律法規等),考察不同維度影響因素下身體活動水平的差異可評估身體活動不足的高危人群和易感環境。社會生態模型中各維度的影響因素可能是身體活動不足的預測因子,由于個體、環境、制度、政策因素的不穩定性,這些預測因子與身體活動的關系往往處于動態變化的狀態。科學技術的革新使預測因子測評的精細化和多元化特征更加明顯,并且多元化的影響因素與身體活動之間可能存在更加復雜多變的交互作用關系,而人們對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的認識也必將更加清晰、具體、明確,這為提升身體活動水平的干預實踐提供了方向性參考。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研究應識別風險因素和保護因素,以正向地加強人們身體活動的保護因素,這對人的健康乃至公共衛生更具現實意義。
(4)評估身體活動的干預實踐效果。身體活動的干預實踐建立在測評方法有效運用和影響因素有效識別的基礎上,其中以“金標準”隨機對照試驗的檢驗效果最為嚴謹,因為這種觀察方式更容易接近身體活動與健康之間最真實、客觀的關系,可提供更有說服力的證據支撐。但實驗研究所需的人力、財力、物力和時間成本也較高。身體活動的影響因素涉及社會生態系統的多個方面,在身體活動的干預實踐過程中難以控制所有變量而進行準實驗研究,這也是行為流行病學研究的難點之一。所以,研究設計應充分結合影響因素的觀察結果,遵循“成本效率最佳”原則,即干預實踐中考慮預期改變的行為目標的數量和優先級,如身體活動社會支持環境、自我效能、體能水平等。實踐干預研究的論證思維是在身體活動分布基礎上進行的分析與歸納,通過研究設計不斷“追問”身體活動與健康效益或危害存在什么關系,不同的身體活動水平對健康結果產生促進還是抑制作用,以及不同身體活動的類型和強度對健康結果影響效果的強弱。
(5)轉化身體活動研究成果的應用實踐。身體活動流行病學涉及的分布特征、測評方法、影響因素和干預實踐等研究成果,終將從數理統計和實驗研究走向普通大眾的生活實踐,即落實于不同政府、機構、團隊等各職能主體的政策引導和不同人群的生活場景之中,以彰顯其更高的公共健康價值。隨著久坐行為與健康風險劑量效應關系研究的深入,在大量的實證研究基礎上建立了專門化的身體活動建議標準和行動指南,如WHO[2]提出的兒童青少年每天進行60 min中至高強度身體活動,成年人則應達到每天150 min中等強度或75 min高強度身體活動,并需要兼顧強健骨骼肌與有氧能力的活動類型,美國[42]5、加拿大[37]、澳大利亞[38]、英國[39]、新加坡[40]等國家也出臺了面向本國人群的身體活動行動指南。我國的陽光體育運動開展、社區健身路徑和公園健身步道建設等也需在相關職能部門主導下進行,在身體活動政策制度保障和城市規劃指引下,制訂真正惠及普通大眾的行動指南和健康促進計劃。
3.3 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的研究范式
研究范式由美國科學家Kuhn首次在其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55]中提出,主要指某一學科共同體所認可的一套概念體系和分析研究模式,遵循一致性的理論基礎、知識體系和研究方法[55-56]。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的研究范式指向了2種問題類型,即身體活動與健康結果之間的相關性與因果性,具體到研究類型則對應描述性研究和分析性研究(包括觀察性研究和實驗性研究)。早期研究往往使用決定因素解釋身體活動與個人、社會、環境、政策等的關系。這些因素被觀察到與身體活動之間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緊密聯系,被認為是身體活動的一種決定性因素[57]。然而,對于身體活動決定性因素的研究實際上多是運用橫斷面調查的描述性分析方法,其強調在統計方法上推算和預測各要素與身體活動之間的關系,但不能提供充分的證據或不能用于證明這些因素與身體活動之間必然的因果關系。一般認為,通過長時跟蹤研究和實驗干預研究可以識別身體活動與影響因素或健康結果之間的決定性關系。因此,身體活動流行病學中橫斷面研究、隊列研究、回顧研究、實驗研究等的作用都是從不同角度論證人們的身體活動與身心健康之間的內在聯系。這種基于群體觀念和疾病分布的研究邏輯是身體活動流行病學區別于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的獨特研究視角。身體活動不足及其健康危害在不同人群、地區和時間的“三間分布”是典型的流行病學特征。無論是描述性研究還是分析性研究,身體活動不足的分布特征都是健康風險和疾病的外在表現,核心問題還是不同身體活動水平與健康結果的互動關系,而身體活動水平的流行性調查、身體活動不足的“病因”推斷、身體活動的健康效益、身體活動不足的預防與干預措施則共同構成了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研究的實施路徑[58-59]。
Dishman等[58]認為,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研究具有兩大基本特征:①使用傳統流行病學方法研究身體活動水平及其與健康之間的關系;②研究不同身體活動水平的人群分布及其影響因素,建立身體活動不足與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并通過進一步的實驗來驗證和判斷這些關系的可靠性和穩定性,進而改善身體活動不足產生的健康風險。基于國內外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相關研究,筆者提出了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研究的整體框架(圖3),各個主題環節在整個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研究中具有相互影響的基礎性作用。國外運動科學與公共健康領域的學者廣泛地開展了體育與公共衛生的學科交叉研究,推動了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的發展。然而,我國公共衛生或流行病學領域的學者鮮有涉足身體活動領域的研究,尤其身體活動不足與健康風險關系的研究及運動促進健康水平提升的實踐干預研究少之又少。這不僅是研究主體或研究范式的學科差異,而且反映了對于身體活動健康效益的認知程度和學科發展程度的偏差,身體活動流行病學必然要走向體育、衛生、教育等跨學科的合作發展。

圖3 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研究的整體框架Figure 3 Research domain of physical activity epidemiology
眾所周知,流行病學研究主要分為描述性研究、分析性研究和理論性研究3種類型,較為常見的觀察性研究和實驗性研究歸屬于分析性研究(圖4)[60]。我國學者較多運用橫斷面研究進行身體活動水平的流行性調查及其年齡、性別的差異分析,但鮮有考察身體活動與健康風險潛在關系的實驗性或觀察性研究。當前,學者們已認識到身體活動水平與健康風險之間緊密的相關性,但將身體活動作為疾病診療的參考指標或健康提升的處方方案,還需要更多的臨床研究來明確身體活動的形式、強度、類型及其與健康風險的因果關系及劑量效應關系。2016年,美國心臟協會在Circulation發表了科學聲明,“將心肺功能作為重要的臨床生命體征,認可心肺功能能夠有效預測慢性心血管疾病風險,而身體活動能夠有效提升心肺功能”[61]。至此,反映心肺功能的有氧能力成為除呼吸、體溫、脈搏、血壓之外的第五大基本生命體征。對于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研究,將不同活動強度、類型和時長作為預測疾病風險、慢性病診斷和運動處方的參考指標,還需大量的實證研究論證支撐。

圖4 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研究類型[60]Figure 4 Research methods of physical activity epidemiology
4 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的研究趨向
4.1 明確不同特征人群的行動指南
縱觀歷史,人類依靠狩獵或耕種的勞動形式維持自身的生存與發展,強健的身體始終是基礎保障,“為動而生”的身體結構和活動形式也是順應自然規律的進化結果[11]。在此過程中,身體活動承擔著維持機體健康平衡的關鍵作用。當前,電子化的學習和工作方式融入了人們的社會生活,信息技術的日新月異加速了社會文明的發展,身體活動從社會生產、生活中逐漸剝離,取而代之的是信息化生活的社會新常態[62]。但人類身體進化的程度似乎沒有跟上科技革新的步伐,“為動而生”的底層邏輯還沒有徹底改變。機械化、自動化、信息化是當前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僅靠人們的自覺來抵擋“去身體活動化”的現代生活方式是十分困難的,所以面對“少動多坐”的現實情況,相關研究機構、行業團隊及政府部門有義務通過建立科學的分類標準與合理、可操作的行動指南進行引導,從而關照不同特征人群的身體活動與健康需求,這也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表現。目前,針對身體殘障人群、超重和肥胖人群、嬰幼兒人群、老年人群、慢性病人群及職場白領、司機、學生等族群,身體活動的類型、強度、時長的判別標準及其參考依據是什么,身體活動與健康的關系是否存在人群特異性,不同特征人群身體活動指導方案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和特殊性等,都需要進一步明確,解決這些問題也有助于識別身體活動不足的流行性特征及其潛在的健康風險。因此,面向我國居民的身體活動指南需建立在人群特征和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從借鑒到改造,從研制到推廣,明確滿足不同特征人群需要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身體活動行為指南是未來需持續探索的方向。
4.2 促進群體與個體研究視角的融合
身體活動流行病學涉及的描述性、觀察性和實驗性研究方法的應用都具有鮮明的數理統計特征,有助于考察身體活動與健康的關系。由于流行病學的研究設計基于群體分析的視角,要求身體活動的分布特征、影響因素及反映其與健康的關系的檢測指標能夠體現清晰、明確、可觀測性的變量語言,如橫斷面研究、跟蹤研究或實驗性研究中,身體活動時長、強度、頻率的地域和年齡分布特征及與健康之間的直接或間接關系都具有鮮明的定量研究特征。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的宏觀趨勢研究為政策導向和行動指南提供了積極的反饋,但可能也意味著研究過程中主動“放棄”了一些不易定量的變量信息。人們在社會生態系統中的日常活動行為不可避免地與個體環境、物理環境和社會環境相互融合[63],而個體心理特征、城市建成環境、社會人際關系等非結構化信息具有不易定量和動態變化的特點,但其可能實實在在地影響著人們身體活動的行為選擇。例如,兒童青少年在體育課堂、親子活動、運動競賽等場景中獲得的積極或消極運動體驗,可能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其持續的身體活動參與行為和意愿,所以宏觀大數據的定量統計或許可以分類甄別出喜歡運動和不喜歡運動的人群,但是可能難以簡單地回答為何有的人喜歡運動,有的人則不然。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研究強調定量方法,以大數據獲得群體特征的宏觀預測,但也導致了對微觀信息捕捉的缺乏,尤其在身體活動不足的預防和行動干預方面,身體活動的“小數據”在分析方法和操作實踐上都需要被更多地關注。
4.3 厘清健康風險的生理生化機制
缺乏身體活動和持續的久坐行為不應以“生活習慣”簡而論之,因為長期身體活動不足可能會產生身體機能的器質性變化,直至形成具有潛在健康風險的頑固慢性病。身體活動不足的危害性和嚴重性則需要相關研究深入其對人體生理生化的影響機制層面,這也是建立不同活動行為與健康效益或危害的劑量效應關系和指導方案的邏輯基礎。身體活動水平與個體心理特征、家庭環境、社會認知水平等顯著關聯[64],因而應將身體活動不足的問題在社會生態語境下進行整體性探討,而干預措施的重點也在于營造和構建身體活動支持性的環境氛圍。當前,我國身體活動相關的研究實踐主要呈現以下2個特點:①多年來持續關注體質健康研究,學校體育研究長期以來幾乎將運動鍛煉作為改善健康水平的唯一手段[65],但日常生活中同樣累積健康效益的非結構化、非規律性身體活動似乎還未引起足夠的重視。②北京、上海、沈陽、廣州、成都、武漢[66-68]等地區相繼出現了基于問卷調查或加速度計測量身體活動水平的調查研究,但很少涉及身體活動與健康水平劑量效應關系的干預研究及相關影響機制的生理生化研究。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的研究實踐多為描述性的橫斷面調查和生態學的相關性研究,鮮有觀察性的隊列研究、病例對照研究和實驗性的隨機對照研究,并且過多地強調了描述性研究而難以觀察到不同身體活動水平與慢性病風險之間的因果關系。
5 結束語
“健康的選擇成為一種簡單的選擇”是世界健康促進大會自1986年發布《渥太華憲章》(The Ottawa Charter on Health Promotion)[69]以 來 始 終 堅 持 的 宗旨。而人們的身體活動本身就交織在日常生產生活中,當前的政策驅動和行動導向都致力于幫助人們恢復這種天然能力,使身體活動成為一種自然、輕松且富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選擇。從Morris等[22]的公交系統員工經典研究案例開始,至今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經過了60多年的發展歷程,其主要職責在于識別、判斷和預測身體活動水平與健康的潛在關系,但歸根到底是通過對積極生活方式的正向引導和干預實踐促進人們健康水平的整體提升。身體活動水平與久坐行為的主觀問答或客觀測量仍無法捕捉人們活動行為的全貌,這影響著人們對身體活動行為模式與健康結果復雜關系的全面認識。例如,肥胖人群的身體活動水平往往較低,也反映了其存在較高的慢性心血管疾病風險。但身體活動不足的行為表現是運動技能缺失導致的運動方式受限的身體問題,還是對從事運動的自信心缺失的心理問題?是生活作息與飲食不規律的習慣問題,還是羞于與人在運動中互動交往的人際關系問題?這些都會影響身體活動流行病學研究對現實問題的理解深度和解決路徑。
作者貢獻聲明:
郭強:提出論文選題,設計論文框架,收集資料,撰寫論文;
汪曉贊:提出論文選題,設計論文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