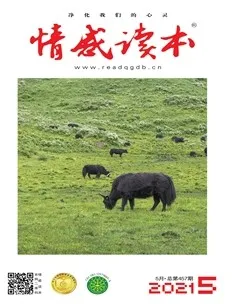在媽媽最后12年
陸曉婭


像所有的認知癥患者家屬一樣,等我們感覺到事情不對頭時,老媽早已在病魔的偷襲下失去了往日的優雅。
每到日落時分,老媽就要叫罵
有一年“五一”假期,照顧媽媽的保姆請假回家了,我得全天候地照顧老媽8天。
果然,我發現了老媽也有《聰明的照護者》一書中所說的“日落綜合癥”。每到日落時分,老媽就陷入糟糕的情緒當中,非發一陣脾氣不可。如果你不理她,她就叫罵不止,或者使勁地拍桌子拍床。
記得一天傍晚,當老媽在發作中罵出“什么玩意”時,我難過地哭了。
好在我有點心理學知識,知道這種情緒的變動可能與光線漸暗引起認知癥患者內心不安有關,甚至是一種大腦的生化反應,不是她故意要這樣。
當老媽第二天又開始發作時,我不再“認領”老媽的辱罵。我情緒穩定了,似乎對她也有某種示范作用,她的叫罵聲小了很多,發作時間也短了很多。
我總結了一下去和群里的朋友分享。
第一步,我叫它“心理區隔”,就是在患者發作罵人時,一定不要“認領”,千萬別犯傻把他們的氣話當真。
第二步,我稱之為“物理區隔”,就是在有安全保障的情況下離開他/她,讓他們單獨待一會兒。認知癥患者感到自己對生活失去了控制,會有很多挫敗感、焦慮感和恐懼感,憤怒其實是由這些感覺轉化而來。心理學上有句話,叫“憤怒不是第一感受”,因為憤怒之前他們已經感受到了別的。
第三步,就是“積極傾聽”。當他/她平靜下來,給他們機會去說。
“老太太的襪子這么白,有福氣啊!”
我有時也感到委屈,尤其是她拍門、拍床,表達她的不滿時。雖然知道這是她病態的表現,但我心里的火苗還是“噌”地點著了。委屈,真的很委屈。不知道哪天,我能修煉到放下自己的委屈,全心全意地給她當好“媽媽”?但我不得不努力扮演好“媽媽”這個角色,像對孩子一樣對她,比如哄睡。
在這張她平時睡的單人床上,我選擇和她對頭躺著,不光是因為床的尺寸小,我還“別有用心”:這樣我可以觸摸到她的腿,可以輕輕地撫摸和拍打她,好讓她感到安心,不會“鬧”。
我就這么輕輕地摸著她消瘦的腳踝,每當她發出一些聲音表示煩躁時,我就會改為有節奏地拍打,就像女兒小時候哄她入睡時一樣,只不過那時候是把女兒抱在懷里。媽媽真的就安靜下來,不再出聲。我悄悄抬頭去看,發現她已經睡著了。
我不曾記得媽媽對我有過這樣親密的愛撫。我1歲零9個月的時候,爸媽調進北京外交學院學習。我被送到了外婆家。快5歲的時候,父母將我接回北京,送進幼兒園。還沒等我和他們“混熟”,他們就出國工作了。
我長大了,自然不再像小孩一樣渴望媽媽溫情的擁抱和觸摸,但內心深處,這份渴望就像長明火一樣不曾熄滅。
幫媽媽洗澡,我開始觸摸到她的身體。我不知道,命運這樣安排,是否是借著病魔來打破母女間僵硬的界限?
一次帶媽媽去修腳,完事后師傅和我一起給媽媽穿襪子。師傅拿起媽媽的襪子,感慨了一聲:“老太太襪子這么白,有福氣啊!”
我好奇地問:“您從襪子中能看到什么嗎?”修腳師傅說:“一個老人被照顧得好不好,從襪子就能看出來。有些老人的襪子,就跟泥鰍一樣。”
父母在不敢老,這是高齡社會的要求
這兩年,為了有更多的時間照顧媽媽,我放下了許多我想做的事情。
我現在是多么的分裂:在精神上,我仍然保持著一種活躍,但我的軀體背道而馳。我能清晰地感覺到腳步一天比一天沉重,精力一天比一天衰退。這種分裂令我非常痛苦。我不太在乎衰老,但我真的在乎怎樣“活著”,害怕余下的人生成了所謂的“垃圾時間”。所以,當我不得不在生命的天平上,減去能發揮潛能的砝碼,將它們放在照顧媽媽一邊時,心理難免也會失衡。院子里的老人只看到我照顧媽媽時的“孝順”,在他們眼里,我仍然是個孩子。他們不知道這個孩子也過了60歲,不僅要照顧媽媽,也要面對自己的掙扎和病痛,還要照顧其他親人。
臺灣導演楊力州拍了《被遺忘的時光》,這是一部關于認知癥老人的紀錄片。他說,當初并沒有打算拍攝這個題材,但那天,他看到了這樣一個場景:一位六七十歲的老人,來送自己八九十歲的父親入院,辦好手續準備離開時,患認知癥的父親突然明白了什么,對著兒子大吼:“我到底做錯了什么,你要這樣對待我!”頭發斑白的兒子,只好哭著將老父親帶回家。
過去,一個人活到了退休年齡,父母多半不在世了。現在,從職場退休后直接到父母家上班的比比皆是!六七十歲的老人,照顧八九十歲的老人,這將是老齡社會最典型的場景。這樣的場景是很溫馨,還是也會讓人傷感和無奈?
或許有人會說:你媽媽(爸爸)還在,多幸福啊!不過別忘了,除了少數非常健康的高齡老人,大多數高齡老人已經“返老還童”,需要得到很多的照顧,更別說像我媽媽這樣的認知癥老人了。
因為是照顧自己父母,這里的真實感覺是不能為外人道的。留給外人看的,是孝順、是幸福,留給自己的,是勞累,是辛苦。
父母在,不敢老,這是高齡社會對我們的要求。
告別,再也不用擔心半夜鈴聲
在西班牙,當地時間深夜兩點多鐘,我被電話鈴聲驚醒。我聽到了話筒里急促的聲音,我知道最擔心的事情可能發生了。
媽媽離世后,我想想就覺得很神奇:從她第一次心梗發作到最后離世,一共10天。她好像就是為了等我回國,從第一次心梗中恢復過來。她給了我最后一次見面的機會。
我把手放在媽媽的額頭上輕輕撫摸,她睜開了眼睛,一眨一眨地看著我,接著嘴里發出咕咕嚕嚕的聲音。我撩開被窩,找到她那只沒有扎針的手,把我的手放到她的手心。
她攥住了我的手。我彎下腰,對著她的耳朵,輕輕地和她說:“媽媽,我是曉婭,我是你的大女兒,我從國外回來了,你能認得我嗎?你女兒在你身邊,別害怕……”
老媽的大腦里是個什么狀況?她的內心還有情感流動嗎?她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情嗎?她害怕死亡嗎?她希望我們為她做些什么嗎……一切的一切,我們都想知道,卻又無法知道!
我輕輕把手抽出來,但分明能感到媽媽不想松手。她雖然沒有很大的力氣,可我還是能感覺到她在拉住我。幾天后,媽媽走完了她89年的人生。
送走媽媽,回到家,我決定關上手機睡覺,再不用擔心半夜鈴聲了。
關燈后,爸爸離去的那個夏夜浮現出來。那是1987年7月24日的夜晚,我在媽媽房里陪她睡覺,黑暗中,傳來媽媽陣陣哭泣。
還有,1969年1月16日的夜晚,15歲的我即將離開北京去陜北插隊。媽媽讓我上床睡覺,自己在臺燈下為我補一件襯衣。我聽到很少表達感情的她,在輕輕地抽泣。
已經半個世紀了。我淚流滿面。
楊春一摘自《給媽媽當媽媽》(廣西師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