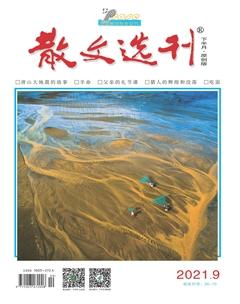我與阿憶
芮平

1998年,我參加了湖北省成人高考,考上了夢寐以求的武漢航海學院駕駛專業。
在武漢的時候,我們嫌棄學校食堂的伙食太差,就經常光顧學校大門斜對面的小巧餐館。年輕的老板娘一口地道的武漢話:“同學,你們吃什么?有熱干面、炒粉、蛋炒飯、武昌魚、鴨脖,還有各類小炒等。”那個年代,一塊五角錢可以吃上一碗熱干面。我雖不是湖北人,但也偏愛這些武漢特色小吃。每當我們想聚餐的時候,會叫上班里關系要好的同學,四五個人,每人出上十元錢。AA制就可以到小巧餐館點上武昌魚、鴨脖、虎皮青椒等,同學們就美美地吃上一頓。
AA制聚餐維持不到兩個月,大家還是解散了。于是,阿憶和我商量著合伙自制熱干面。我們步行半小時到達徐東平價商場合資買一個微型電爐、鋼鍋,芝麻醬、香醋、白糖、面等,開始自制武漢熱干面。
一個周六的晚上,因我倆做熱干面而帶來了一件不幸事情。阿憶小心地拿出電爐和鋼鍋,開始加水做面,我在宿舍門口放哨。我們做到一半的時候,意外發生了,因電爐插座被燒煳了,剎那間跳閘了,整個宿舍樓一片漆黑。阿憶和我臉色也變黑了。隔壁宿舍的同學順著燒煳的氣味找到了我們宿舍,有人告訴了我們駕駛系吳老師。不一會兒,吳老師打著手電筒跑到了我們宿舍。她一進門就聞到一股難聞的熏鼻子的煳味,很不高興地責問:“你們在宿舍燒什么了導致停電了?真不懂事,跟我去辦公室把檢討寫了。”我們倆就像犯罪分子一樣,低著頭任憑系主任對我們懲罰。自從偷做熱干面把宿舍樓的電弄跳閘事件后,阿憶和我再也沒有違反過校紀校規,從此慢慢地變得成熟。
過了一個月后,阿憶就經常開始吃起中國式三明治——饃夾白糖。我有時候稱呼他“大饃哥”。當時不知道他為何如此節省,后來了解到阿憶他爸是黃岡龍感湖造紙廠一名普通工人,母親得了阿爾茲海默癥,不能上班,還需要家人照顧,家里一直比較拮據。相比之下,我的狀況要比阿憶寬裕得多,我來上大學是帶薪的,每個月有基本工資200元,公司每個學期發給我獎學金1000元。之后,我對他的處境深表同情,還經常請他吃飯和加餐。我們加餐基本上是虎皮青椒和武昌魚兩個菜,米飯是免費的。他也會請我吃開水沖土雞蛋花、孝感的麻糖。漸漸地,我成為了他最信任的好友。
因為阿憶的家境不是太好,所以他抓住每一次勤工儉學的機會。我們大二的下學期開始,學院鼓勵在校大學生主動獻血,聽系主任吳老師講,獻血對身體有好處,且家人需要的時候又可以免費用血,還發獻血證;另外,學院發放200元錢的補助。阿憶身體瘦弱,胳膊很細,他又經常吃饅頭夾白糖,我真有些替他擔心。我對阿憶說:“阿憶,你這么瘦就不要去獻血了,你撐不住的。”他笑笑說:“沒事,你多慮了。我在老家帶來了80個土雞蛋沖蛋花喝,可以補氣血的。明天分你20個,你還擔心什么?”
一個周日的清晨,武昌區的一輛獻血車停在校門口。車上拉著橫幅“捐血救人,與我同行”。橫幅在瑟瑟秋風中飄蕩著。醫護人員在獻血車附近搭起了紅色帳篷,帳篷里的辦公桌上放著血壓計等體檢設備。醫護人員期待獻血的同學們和喻家湖小區人們的到來。早上八點左右,我陪同阿憶來到了獻血車前,他測了血壓、體重,同時進行了血型、血色素等化驗檢查,體檢一切正常。他爽快地擼起左手的袖子,醫生把抽血的針管深深地扎在他的靜脈上。鮮紅的血液順著管子在流淌著,十來分鐘就完成獻血400毫升。我幫他領取了獻血證、兩包紅糖,及學校給他200元獻血補助。我扶著弱不禁風的阿憶回到學校宿舍休息。回去后他睡了一覺,就立即從床鋪上爬了起來。他惦記著第一時間給家里轉那200元錢給他母親看病。他飛奔到銀行給家里轉了賬,隨后回到了宿舍撥通了他爸的電話,阿憶說:“爸,我給家里轉了200塊錢,給媽看病用的,這錢是我在學校學習成績突出得的獎學金。”他爸說:“你要在學校好好學習,為家里爭光,家里莫要太牽掛。”我在一旁,無意聽到了他們父子的談話,我的眼睛有些濕潤了。自那以后,阿憶依舊吃饅頭夾白糖,每周末還去喻家湖的角落發放超市展銷的宣傳單,掙來的錢都攢著轉回家給母親看病,還一直堅持說錢是學校發的獎學金。
如今,想念阿憶的時候,我就翻看相冊里與阿憶在黃鶴樓前門的合影。想必千里之外的阿憶一切安好,我盼望著某天能再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