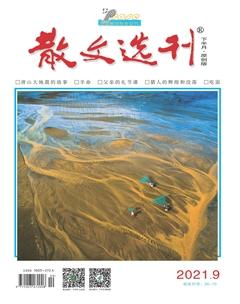獵人的輝煌和沒落
楊啟彥

上世紀80年代,我到鄉下教書,結識了非老師。他是一位老獵人,十里八鄉,名聲如雷貫耳。
狩獵,我們老家叫跑山、攆山。滿山遍野瞎跑,灰頭土臉,野人似的,但對非老師獵獲歸來的酒局,不離不舍。那些年月,我們的糧油供應本都由單位保管著,長時間聞不到肉腥,能吃到點野味是多么不容易啊。非老師扛槍出了門,我們幾個小青年就深夜不睡地候著。凌晨兩三點,或者三四點,他終于回來了。大伙像綠頭蒼蠅嗅到屎臭味般圍了上去,七手八腳搶著幫忙,生火的生火,找鍋的找鍋。獵物細細剁了,油炸了上桌,一干人圍著喝酒。天快亮了,酒也干了,才散場子。然后,是下一次漫長而焦灼的等待和期盼。
非老師給鄉下枯燥乏味的生活平添了許多樂趣。他常乘著酒興,給我們講狩獵的事。他說,沒月的時候,傍晚到了山上,貓著腰,賊兮兮地在密林中伏著,豎著耳朵聽野雞飛動的聲音。天黑定了,鳥就不再飛了,記住它最后停留的那片區域,打開手電光去找,跪著爬著找——夜間,鳥是不動的。找到后,手電光照定獵物,“嗵”的一聲,一條火龍疾飛而出……有月的時候,戴了頭燈,伏在荒草地里,豎起耳朵聽。月亮升高了,人只嫌耳朵不夠用。有時伏兩三個小時,也沒有等到兔子,蟲子把身體叮了個遍。有時不大一會兒,草地里就傳來“嚓嚓嚓”的聲音,那是兔子吃草了。估計了兔子的位置,舉槍,突然打開頭燈,射向兔子,扣動扳機,火龍映紅了夜空,兔子應聲而倒。這樣的夜晚,我們就忙亂得雞飛狗跳,比水還淡的日子,有了甜蜜,有了歡笑。有時,老非也會把一只生擒活捉的野雞或野兔賣掉,用來購買彈藥,更換槍證,也有時用來給老母親看病買藥。我們雖然有一絲遺憾,也能理解他。賣掉獵物,救急生存,而我們一次不吃,不會死人。老非有時也會很沮喪,忙碌一整夜,只弄到幾只老黃雀或是兩三只小松鼠。我們就會安慰他:十跑九空嘛,哪有常勝的將軍。
然而,老非竟封槍了。他講述時的聲音都充滿了追悔和沒落。那是一次大型的圍獵活動,派出所的老張也帶著功勛卓著的大黃狗來了。非老師負責老鷹山西面的埡口。大黃狗的叫聲戰栗了整座山頭,人們的傳令聲一陣緊似一陣。不多會兒,一只小黃牛一樣的麂子被大黃狗攆著,飛奔而來,像一道閃電。“嗵”一聲,老非的槍響了,可不幸的是,地上躺著的,不是麂子而是大黃狗。獵人們圍攏來,充滿了惋惜,老非啊,吃了一輩子素,倒把手伸進豬油罐子里了。老非黯然神傷,一屁股坐在地上,半天一言不發。
按規矩,獵人誤傷了人或是家畜,就應洗手封槍,否則要遭報應,災難臨頭。“非老師封槍了”。這給他輝煌的人生,抹上了無法消除的污點。他反復只說著一句話,語調是無盡的感傷,明明瞄準了麂子的,卻偏偏打了大黃狗。
上世紀90年代中期,政府收繳了槍支,不準打獵了。非老師很高興,他說日子好了,市場上的肉都吃不完,用不著跑山了,讓野雞、野兔、小麻雀們也過安生日子吧。不幾年,非老師退休了,他到城里買了房子,帶孫子,還養了很多鳥和兔子。木條裝釘成的柵欄里,整整三大欄兔子,擺滿了陽臺,最上層是鳥籠。那個夏天,我見他打著傘,背著草,一身泥巴地在街上走著,像個農村的老頭子。我勸他說:“市場上的草多便宜,不用親自到野外去。”他說:“市場上只要買點飼料就可以了。野外多好啊,泥巴、小河、青草的味道多好聞啊。一到野外,人就清爽了,健康了。”我開玩笑地說:“當年你可是有名的獵手啊,現在倒成兔崽子們的‘奴隸了。”他也笑了,說:“奴隸好,奴隸好,又休閑又養生。最鬧心的,是孫子不讓殺兔子,這龜孫子要把兔子放回山里去。”于是背地里,非老師常常在孩子們去學校的時候,殺了兔子,給我打電話。我便屁顛屁顛跑了去,兩人偷偷地背著孩子吃兔肉。
這樣的生活,非老師一過就是十多年。
再次見到他,是在幾年前,他正在醫院的走道上,一瘸一拐地挪動。奔走如飛的老獵人,變成這樣,我有些心酸。扶著他慢慢坐下來,他的兩個膝蓋,疼得厲害。他有些悲觀地說:“到底還是遭天譴了,殺生太多,這雙腳的使用期限怕是到了。”我說:“不就是骨質增生嗎,醫生總有法子的。”我給他介紹了桐子葉泡酒擦,他雞啄米似的點頭。后來我給他買了硫酸軟骨素片,說這個能營養骨頭呢。他高高興興地收下了。
非老師就這樣蹣跚著了,日復日,年復年,跑山成了陳年舊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