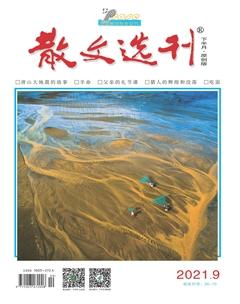一條狗
宋揚

狗命賤如斯。跟了我家的狗,命更賤。
岳母安完心臟起搏器一周后,醫生宣布她短時間內不宜再獨自一人生活。岳母雖極不愿意,也只得敬畏著聽從醫生的話,隨我們進了城。進城前,我們載她回老宅收拾屋子,往返皆匆匆。雞鴨鵝一次性全處理了,有生命的只剩“樁樁”。鄉下,有人惦記狗肉,我們不敢敞放“樁樁”,大門一鎖,鑰匙交給幺爸,讓幫著給它碗剩飯。
最后一次看“樁樁”,是回老家吃一個百日宴。宴后,我們把吃剩的給“樁樁”打包了滿滿兩袋,凍在冰箱里,等幺爸取。原以為夠它吃好幾頓的了,沒想到它風卷殘云,幾分鐘就吞下了一整袋——它太餓了。幺爸家經營著一家酒坊,忙生產,忙銷售,三頓作兩頓的,哪顧得上一只狗!
十年前,岳父趕集,回來的路上撿了“樁樁”。剛進家門時,“樁樁”還只是一小團麻黑麻黑的肉團,在寒風中瑟縮著。岳父偕岳母在外打工多年,說是替建筑大老板當管理,沒少下苦力,但到年關,挪到手的錢尚不及一個小工。他供妻讀中師,供妻弟讀大學,又好圍朋結友抽煙喝酒,哪有余錢?
那段日子,房地產生意不好做。一次,老板上工地視察,工地板房辦公室里,岳父心愛的收錄機咿咿呀呀惹老板心煩,老板一遷怒,收錄機粉了身碎了骨。岳父性子也剛,鋪蓋卷兒一捆,回了老家。
然后造新屋。妻和妻弟各湊了三萬塊錢,才勉強給他們修起幾問磚房。曾經風光無兩,一時老境頹唐,岳父精氣神不再,身體亦每況愈下。
以前破破爛爛的草房只有一些鍋碗桶碟,似乎也用不著狗去看護。新房造好后,“樁樁”回來了。再后來,岳父腦溢血不在了,“樁樁”還在。
那天,岳母一大早去了山上做農活,挨近中午回家,才看見岳父倒在床下已不知幾個鐘頭——他大概是起床太急,加之有高血壓,血往上沖……
并沒有發生和某些電影里一樣的狗向旁人報警,救活主人的事,無人知曉“樁樁”當時有沒有狂吠不止,它也沒有奔到山上找回岳母。也許,在“樁樁”看來,岳父倒在那里,只是換了一個睡覺的地點,擺了一個與往日不同的姿勢而已。岳父是“樁樁”的菩薩,“樁樁”卻不是岳父的救命稻草。“樁樁”不是一只有靈性的狗。
岳父去世后,我們把岳母接到城里住過一段時間。她閑不住,讓我們給找個活兒做。她聽力不好,對助聽器很不習慣,說耳朵里有蜂子飛,一直嗡嗡飛,又像有火車在跑。聽力不好,與人說話就吃力,岳母連廣場舞大媽的圈子都融人不了,更別說找工作。好不容易在一個家具賣場掃上地,可賣場生意不好,很快關了張。岳母自行主張,堅持回了老家。她去20里地之外的妻舅家接回“樁樁”時,“樁樁”已寄人籬下整三個月。
被我斷定靈性不夠的“樁樁”在經歷了喪失男主人,被女主人丟下又接回幾件大事后,仿佛越來越懂得了一個家、一個窩的彌足珍貴。岳父在世時,家里喝茶打牌的、祝壽拜年的還算鬧熱;主心骨不在了,門庭陡然冷落。“樁樁”逢人便吠的霸氣也慢慢鈍了——年頭到年尾,沒人上門,它能吠誰呢?
岳母的聽力日漸委頓,“樁樁”的耳朵卻一天天靈光起來。每次回老家,我的車還在離家幾十米外的徐三茶鋪時,它興奮的吠叫便傳來。它居然能隔了幾十米從每天來來往往的眾多機動車中聽辨出我的汽車的聲音,聞嗅出我們身上揮之不去的,與它身上一樣的,與這個家的一磚一瓦、一筷一碟同樣的獨有氣息!是孤獨,錘煉出它特殊的聽覺和嗅覺。終日被拴在圍墻內的“樁樁”的世界,注定沒有白天,只有黑夜和孤獨。
父親說,三十多年前他當村主任,每次去鄉上開會,我家的那條老狗都要去渡口等他回家。那年,全鄉轟轟烈烈的打狗運動突然開始了,說是狂犬病肆虐。政策一刀切,拴養的也不可豁免。怎么辦?與其讓狗被工作隊打死拖走,不如自行解決。如此,老婆娃兒還能得一頓狗肉打牙祭——我家的碗里,已半年不見葷腥,頓頓酸菜、豆瓣下飯,我和幾個堂兄弟口水唆嘴角,終日掛著,父親也覺得好像有一只只饑餓的嘴在搶奪他胃里的最后一星油水。就這樣,父親和大伯用一根鐵絲勒住老狗的脖子,結束了它的生命。父親作這個決定時,有沒有片刻的猶豫?我無法想象老狗哀號著掙扎著望向父親的眼神,那會是怎樣的震驚、悲屈、絕望與痛恨!這條狗后來被父親多次提起,父親的話語里有無奈,有愧疚。但我想,假如重回彼時彼境,讓父親再做選擇,他依然只能那般決絕。
狗命如斯。
一條狗的壽命有多長?三爸家的那條老狗與濤弟是同一年生的。濤弟已三十歲,有了兩個娃兒,今年,狗死了。多數犬種的壽命不過一二十年,也就是說,狗與人無論多么長久的陪伴,總有一個要先走,或如我的岳父,或如三爸家的老狗。
“樁樁”整十歲了,已算一條徹徹底底的老狗。吃完打包的飯菜,它搖頭擺尾地跑到我的面前。我摸它,它溫馴而滿足地享受我沿同一方向的撫摸,享受來自我掌心的溫度。我給它拍照,它一副淚眼汪汪的樣子。它已經明白,我們此番回來是待不久的——它從我們收拾家什、裝袋蔬菜和大米的手忙腳亂中早已知曉又一次別離的到來。它不叫不跳,只默默看著我們。我們從堂屋走向灶房,從院壩東南角走到西北角,它的目光也從堂屋走向灶房,從院壩東南角走到西北角,眼沁沁地。這次,我們不敢把它送到20里外的妻舅家。臨近年關,回鄉的人多了,有的連不值錢的玉米、谷子也偷。那是岳母的口糧,一粒一粒都是汗,總得看著。
鎖上圍墻大門的那一刻,我和“樁樁”再次四目相望,我說:“‘樁樁,你要守好家,我們過幾天就回來了。”
一別又是月余,我們終是沒能回去。晚飯時,岳母怯怯地說,她夢見“樁樁”死了,縮在圍墻內的草窩中,執意要回去住了。我的心,被什么狠狠刺了一下,眼淚幾乎就要流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