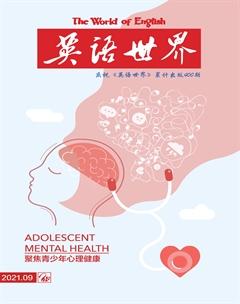我與陳羽綸
林巍


【編者按】今年9月第9期是本刊累計(jì)出版400期,10月本刊創(chuàng)刊40周年。40年來(lái),幸賴英語(yǔ)教學(xué)界和翻譯界眾多專家、學(xué)者鼎力襄助,一代代英語(yǔ)學(xué)習(xí)者深情厚愛(ài),恰如涓涓細(xì)流匯聚成海,方有40年出版400期的成果。
為追念一路走來(lái)的不易,感謝作譯者、讀者、相關(guān)合作單位對(duì)雜志的幫助,我們?cè)?、10兩期上辟出專版刊登讀者征文和各方賀詞,與大家共憶珍貴往昔,憧憬更美未來(lái)。
一晃,《英語(yǔ)世界》已經(jīng)誕生40年了。此時(shí),不禁想起了陳羽綸先生,該刊的創(chuàng)辦人。與他的日日夜夜,歷歷在目,就像在昨天。
上世紀(jì)八十年代,陳先生是商務(wù)印書館的資深編輯、翻譯家,這我是知道的,但直到某天他突發(fā)異想,決定辦一本全國(guó)獨(dú)創(chuàng)的英漢對(duì)照雜志,我才和他有了更多的個(gè)人接觸,有了更深的了解,最后成了忘年交。
據(jù)我所知,館里答應(yīng)他辦雜志的條件,就是沒(méi)有條件——一無(wú)資金,二無(wú)人力,三無(wú)編制,四無(wú)房屋。所以,從策劃、選題、編輯、審稿、出版、經(jīng)營(yíng)、發(fā)行等全靠他自己。他當(dāng)時(shí)已年逾花甲,但人很精神、睿智、干練,全然不像一個(gè)飽經(jīng)磨難的老人。他有很多想法,要干很多事情,正是當(dāng)時(shí)國(guó)家剛從十年動(dòng)亂走出后一代知識(shí)精英的典型風(fēng)貌。
于是,北京站正對(duì)面的頂銀胡同36號(hào),一座德國(guó)式老舊三層小樓,他的家,成了編輯部,一群大都退休了的英語(yǔ)教師、編輯,聚集在了他的麾下。我當(dāng)時(shí)在文化部下屬的一個(gè)雜志社,后調(diào)往外文局,亦從事英語(yǔ)編輯,因工作關(guān)系與陳老相識(shí),他也歡迎我來(lái)此兼職。我每次騎車來(lái)這里,都看到長(zhǎng)輩們趴在小屋、樓道、走廊、陽(yáng)臺(tái)的簡(jiǎn)陋書桌甚至是紙箱子上改稿、校稿、定稿,還有從印刷廠拉來(lái)的一捆一捆剛出版的雜志……儼然是一家民間出版機(jī)構(gòu)。
該雜志在廣大英語(yǔ)愛(ài)好者特別是大學(xué)生中不斷走紅,單期發(fā)行量一度達(dá)到了35萬(wàn)冊(cè),可算是中國(guó)出版史上同類刊物中的一個(gè)奇跡。
陳先生的忙碌程度也可想而知。而且,容易讓人忽略的是,他是個(gè)殘疾人。“文革”當(dāng)中,他受到種種虐待,重病染身,因未能得到及時(shí)治療,一條大腿被截肢。但他所承受的工作量,在我看來(lái),恐怕一個(gè)年輕力壯的健全人都難以勝任。
光是各種信件就堆積如山。我試圖從各方面減輕他的壓力。除了選題、翻譯方面的事務(wù),他讓我主要負(fù)責(zé)信件的回復(fù)。具體做法是,他定期從眾多來(lái)函中挑選出需要回復(fù)的,然后逐件向我介紹相關(guān)的背景,口述需要回復(fù)的內(nèi)容,由我記錄下來(lái),整理成文,他過(guò)目一下,然后簽上自己的名字。在那個(gè)沒(méi)有電腦、網(wǎng)絡(luò)、手機(jī)的年代,對(duì)他來(lái)講,這不失為一種特定有效的對(duì)外溝通方式。而此項(xiàng)勞務(wù)是有報(bào)酬的,到了月底,他都會(huì)把一個(gè)信封塞到我手里,說(shuō):“拿著吧,辛苦了!”陳先生在這方面很大方,記得有時(shí)竟超過(guò)了我的月工資。
信件回復(fù)的內(nèi)容,從開(kāi)始的工作往來(lái)、讀者答復(fù),到后來(lái)他的私人信件。這樣,我對(duì)他的經(jīng)歷、為人、家庭及社會(huì)關(guān)系等也有了更廣泛、深入的了解。他原就讀于西南聯(lián)大,與著名翻譯家許淵沖是同學(xué)。后在各種戰(zhàn)爭(zhēng)、運(yùn)動(dòng)中從事英語(yǔ)教學(xué)、翻譯、編輯、出版工作。他是華僑,海外關(guān)系“復(fù)雜”,為此吃盡了苦頭,甚至落下殘疾。除英語(yǔ)外,其實(shí)他還通曉多種語(yǔ)言和方言。以前,聽(tīng)他的口音,我一直以為他是個(gè)“老北京”,后來(lái)聽(tīng)他對(duì)著電話說(shuō)出各種讓我一頭霧水的方言,才知道他原來(lái)是個(gè)“外地人”。
我們還經(jīng)常就社會(huì)、時(shí)事、家庭、個(gè)人的問(wèn)題聊天,有時(shí)會(huì)到夜里很晚。我們的年齡相差四十歲,但卻聊得很投緣,許多觀點(diǎn)高度一致。記得他是個(gè)相當(dāng)隨和的人,善于聽(tīng)我說(shuō),從不倚老賣老,而多用商量口吻。
我的出國(guó)留學(xué)手續(xù)辦好后,特意去向陳先生告別。他表情寧?kù)o,有點(diǎn)復(fù)雜。“你還年輕,當(dāng)然應(yīng)該去留學(xué)”,但話語(yǔ)中也流露幾分不舍。他執(zhí)意拖著拐杖下樓,把我送到了大門口,使勁握了幾下我的手,又拍了下我的肩膀說(shuō):“走吧!”
出國(guó)行李箱的分量是很吃緊的,但我還是塞進(jìn)了好幾本《英語(yǔ)世界》,一是為了學(xué)習(xí),再是看見(jiàn)它就像見(jiàn)到了陳先生。到了澳洲及其他國(guó)家后,幾經(jīng)奔波都舍不得丟掉。
出國(guó)后我們還保持著書信來(lái)往。想來(lái),我在他身邊時(shí),是為他代筆與別人聯(lián)系,現(xiàn)在他卻要親筆給我寫回信。有時(shí)我們也通電話;那時(shí)打個(gè)越洋電話是要咬牙的,因?yàn)橄喈?dāng)昂貴。一些片段印象深刻:我讀“自然療法”后,他說(shuō)“好!學(xué)英語(yǔ)最好圍繞一個(gè)專業(yè)展開(kāi),而醫(yī)學(xué)英語(yǔ)和翻譯很有的做”。讀碩士、博士后,也向先生匯報(bào)。記得他的一句話:“小林,到目前為止,你走的每一步都是正確的!”先生的肯定讓我非常愜意。
十余年后,第一次回國(guó),雖然知道先生已經(jīng)搬家,但我還是迫不及待地去尋“頂銀胡同36號(hào)”,要的是找回當(dāng)年的感覺(jué)。打車在那里轉(zhuǎn)來(lái)轉(zhuǎn)去,怎么也找不到;北京站對(duì)面已是高樓一片。的哥說(shuō):“聽(tīng)你口音是北京人,怎么哪兒都不認(rèn)識(shí)啊?”我說(shuō):“變化太大了!”。余下的,便只有不盡的惆悵。
后來(lái)在方莊先生的新家見(jiàn)面了。敘舊話新,難免感嘆一番。令人驚奇的是,先生的面容并無(wú)大變化,只是記憶力大不如前,且顯出老年癡呆癥跡象。他說(shuō),已基本不再參與編輯部的日常事務(wù),年輕一代很頂勁。而且,雜志社在朝陽(yáng)區(qū)買了新的辦公樓。我去后,大吃一驚:當(dāng)年一個(gè)身有殘疾的老學(xué)者,靠辦英語(yǔ)學(xué)習(xí)雜志,竟然可以在北京市區(qū)買下一層辦公樓,今天看來(lái)簡(jiǎn)直天方夜譚!
之后,我們又相約在北大與許淵沖等他當(dāng)年的西南聯(lián)大老同學(xué)相聚。先生在他們當(dāng)中竟然是老大哥,他說(shuō):“我實(shí)在太老了!”
先生的老年癡呆癥不斷加重,但每次我打電話,小保姆告訴他是我的時(shí)候,他還是要接聽(tīng)的,不過(guò)越來(lái)越語(yǔ)焉不詳,前后重復(fù)。我知道,這時(shí)對(duì)他最大的安慰就是耐心聽(tīng)他說(shuō),正如他當(dāng)年耐心聽(tīng)我說(shuō)。直聽(tīng)得我心里陣陣難過(guò),甚至淚濕眼眶。真是歲月不饒人!
2010年8月的一天,我在澳門,得知了先生去世的消息。我走到窗前,遙望北方,佇立良久。眼前浮現(xiàn)的是北京頂銀胡同36號(hào)的那座小樓,小樓書桌前坐在我對(duì)面的先生,那個(gè)定格了的畫面,無(wú)論過(guò)多少年,無(wú)論我走到哪里,永遠(yuǎn)也不會(huì)改變。
先生的遺產(chǎn)固然很多,但對(duì)于我,最大的就是這本雜志。每次翻開(kāi)它的時(shí)候,先生的音容笑貌,都會(huì)以或快或慢的速度,在我眼前閃過(gu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