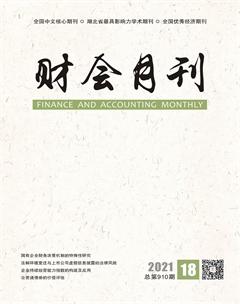證券交易所非行政處罰性監管的效應分析
閆明杰
【摘要】近年來, 非行政處罰性監管這一行政手段的使用率越來越高, 其監管效應也逐漸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基于會計監管視角, 剖析非行政處罰性監管的實質, 并分別從信號傳遞理論、有效契約理論視角解讀非行政處罰性監管效應的產生機理。 在此基礎上分析發現, 非行政處罰性監管的預期效應主要表現在提升信息披露質量、發現契約設計缺陷、識別機會主義行為和防范財務舞弊四個方面, 其非預期效應主要體現為對實施環境、關聯制度、非直接參與主體和監管路徑的效應。
【關鍵詞】非行政處罰性監管;信號傳遞理論;有效契約理論;預期效應;非預期效應
【中圖分類號】 F234? ? ?【文獻標識碼】A? ? ? 【文章編號】1004-0994(2021)18-0131-5
一、引言
自2002年證監會提出“非行政處罰性監管”(以下簡稱“非處罰性監管”)以來, 這一行政手段因解決問題迅速且適度而被證券交易所(以下簡稱“證交所”)頻頻使用。 非處罰性監管措施種類繁多, 監管范圍涉及會計信息披露、公司治理結構、證券發行、紅利分配等多個方面, 其作為一種對上市公司尚未明晰或尚未揭露的潛在性問題予以事先督促或警示的預防性行為, 相比行政處罰性監管, 起初并未受到太多關注。 但隨著證交所非處罰性監管行為頻次和數量的不斷增加, 非處罰性監管效應逐漸進入學者們的研究視野。 學者們對我國證交所非處罰性監管的預期效應(直接效應)進行了研究, 發現其具有信息含量[1] 、增強了會計信息可比性[2] 、改善了公司業績預告質量[3,4] 、產生了顯著的市場反應[5] 、加劇了融資約束和股價波動性[6] 、有助于預測和發現公司違規行為[7] 、能夠有效識別和防范內部控制風險和并購風險[8,9] 、提升了審計質量[10-12] 、有助于提高未來關鍵審計事項信息量[13] 等。 此外, 還有少量研究涉及非處罰性監管的非預期效應(溢出效應), 發現非處罰性監管具有聯動效應, 受到非處罰性監管次數越多的會計師事務所, 其IPO客戶會收到更多輪數的審核問詢函和更多問題[14] ; 受到非處罰性監管公司的子公司、同行業以及與其具有審計聯結和董事聯結關系的未收函公司, 其財務報告質量[2,15] 、年報可讀性[16] 亦會提高。
雖然學者們對我國非處罰性監管效應進行了一定的研究, 但由于非處罰性監管制度的關聯效應和嵌入效應, 非處罰性監管行為所產生的效應具有復雜性、多樣性和廣泛性, 需予以進一步明晰。 此外, 為了研究的系統性和深入性, 還需要劃分非處罰性監管效應的類別。 鑒于此, 本文立足會計監管視角, 對證交所非處罰性監管的實質、非處罰性監管效應的產生機理以及所產生的效應進行分析, 以期為非處罰性監管目標的實現提供借鑒, 為學者們進一步研究非處罰性監管效應提供參考。
二、非處罰監管的實質: 督促高質量會計信息的充分披露
會計信息作為一種公共產品, 由于外部性、搭便車等原因導致的市場失靈, 使得會計信息披露僅依靠市場力量是無法完成的, 對會計信息披露進行管制則成為必需。 證交所作為一個行為主體, 基于其功能與職責所在, 其具有促使上市公司充分披露高質量信息的動機, 在該動機的驅動下, 證交所會采取一系列行為, 非處罰性監管則是其中之一。 從表面上看, 該行為的目的是防控風險、預警、制止和矯正違法違規行為, 但這一目的的實現主要是要求對上市公司尚未明晰或尚未揭露的潛在問題提供解釋性信息或者補充性信息, 這些信息是對上市公司原來已披露信息的修正或補充, 可以提升會計信息的可靠性和可比性。 因此, 從會計監管視角來看, 非處罰性監管的終極目的是提升會計信息披露質量。
以問詢函為例, 證交所主要針對重組、股票發行、債券發行、股價異常波動、股份轉讓、資產處置、關聯方交易等重要或異常項目予以問詢, 要求上市公司針對問詢項目補充資料、詳細披露、予以解釋、提請注冊會計師審核等, 當上市公司的回函未能達到要求時, 證交所會通過再次問詢的方式, 要求上市公司進一步予以解釋、補充資料等。 比如, 2018年雅戈爾對中信股份的會計方法變更使得其凈利潤增加930210.84萬元, 對此, 上海證交所向雅戈爾及時送達了問詢函, 要求其對這一會計核算方法變更進行審慎核實, 并請公司年審會計師發表意見。 上海證交所的這一非處罰性監管, 使得雅戈爾對上述會計核算方法變更進行了審慎思考, 決定不再進行會計核算方法變更, 并對信息披露中可能存在的問題進行了修正。
綜上所述, 從會計監管視角來看, 證交所通過非處罰性監管這一手段, 對會計信息披露進行管制, 督促公司對高質量信息進行更充分的披露, 進而達到非處罰性監管目的。
三、非處罰性監管效應的產生機理
1. 基于信號傳遞理論的分析。 非處罰性監管的行為過程以及效應產生過程, 是一個信號傳遞、信號識別交替進行的過程。 對于上市公司傳遞的信息, 信息使用者需要甄別, 而這一信息甄別行為必然是由信息劣勢方先行動。 與上市公司相比, 證交所和投資者一樣, 亦屬于信息劣勢方, 但由于證交所可以采取一系列監管措施, 相對于投資者而言, 其具有較強的管制性和威懾性; 而且, 證交所作為監管機構, 在信息占有量方面優于投資者, 便于其適時對異常信息和行為進行識別、預警和糾偏。 因此, 在信息或行為識別中, 證交所比投資者更具有獨特優勢。
當證交所識別出上市公司所提供的信息或者上市公司行為可能存在異常時, 便通過非處罰性監管予以督促或警示。 與此同時, 證交所的這一督促或警示信息將迅速傳遞到資本市場, 引起投資者、債權人等信息使用者的廣泛關注, 可能導致投資者、債權人等信息使用者對上市公司的預期下降, 從而使得上市公司的股價下跌、融資成本增高等。 在可能的處罰性監管以及可能的股價下跌、融資成本增高等不利影響的威懾下, 將會倒逼上市公司傳遞高質量的信息, 或者其違法舞弊行為被揭示。 此外, 受到非處罰性監管公司的同行業公司、關聯公司等受信者亦會相應調整自己的行為, 且會為其他的非同行業公司、非關聯公司等提供前車之鑒, 避免類似行為的發生, 非處罰性監管的溢出效應得以產生。
2. 基于有效契約理論的分析。 公司作為信息生產者, 是具有優勢的一方, 投資者、債權人等信息使用者, 以及證監會、財政部門等監管機構是信息劣勢方, 信息不對稱使得信息生產者與使用者、監管者之間的契約有效性被削弱。 而管制則是緩解信息不對稱、提升契約有效性的有效選擇。 監管機構可以通過要求報送專門報告、披露資料等, 增強企業信息披露的充分性; 通過指定中介機構進行核查、記入誠信檔案等, 提升企業信息披露的可靠性; 通過出具問詢函、警示函等, 壓縮企業盈余管理的空間; 通過限制業務活動、限制分配紅利以及限制向高管支付報酬和福利等方式, 保護信息劣勢方。 可以看出, 非處罰性監管提升了企業信息披露質量, 緩解了投資者、債權人與企業管理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降低了代理成本, 促進了有效企業契約的締結。
需要注意的是, 非處罰性監管的實施主要是通過識別異常信息或行為、督促信息的充分披露以及糾正異常行為而實現的。 對于監管主體而言, 這一實施方式的執行成本較低; 對于被監管主體而言, 其守法成本低于違法成本。 被監管主體遵循監管比不遵循監管更有利, 若其本身由于信息披露不充分而導致被監管, 通過充分披露信息則可能會解除監管; 若其本身信息披露存在違規行為, 通過及時修正則可能免除進一步的行政處罰。 非處罰性監管以較低的監管成本緩解了信息不對稱, 增強了監管方、投資者、公司管理層等之間的契約有效性。
綜上可知, 非處罰性監管效應的產生過程為“信號傳遞(上市公司)——信息甄別(證交所、投資者等)——信息傳遞(上市公司)——信號甄別(受信者)”, 是信息傳遞方和信息甄別方博弈的過程, 也是緩解信息不對稱以增強契約有效性的過程。
四、非處罰性監管的預期效應
由于非處罰性監管的實質是督促公司高質量信息的充分披露, 其主要是對公司行為進行管制, 因此非處罰性監管的預期效應主要體現在被管制公司層面。 被管制公司在制度環境、市場環境以及輿論環境的綜合作用下, 產生非處罰性監管的預期效應, 具體如下:
1. 提升公司的信息披露質量。 提升信息披露質量是非處罰性監管最直接的效應。 非處罰性監管行為的發生本身就是對公司經營情況的一種信息披露(如上市公司發布的問詢函收函公告), 而公司亦針對非處罰性監管提供了增量信息(如上市公司發布的問詢函回函公告), 這些信息可以緩解監管方、信息使用者與公司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以及提升公司的信息披露質量, 進而有助于信息使用者做出正確的經濟決策。 以問詢函為例, 研究表明, 無論是問詢函收函還是回函, 市場均會做出反應, 且問詢函特征(如是否涉稅、是否需獨立董事發表核查意見)不同, 市場的反應也有所不同[1] , 所以問詢函是具有信息含量的。 非處罰性監管行為除了本身能夠帶來增量信息, 還具有連帶提升信息質量的功能, 這是因為非處罰性監管降低了投資者等外部信息使用者與公司對信息需求的不一致性。 由于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存在, 公司外部信息使用者和公司管理者對信息的要求不同, 雖然兩者均對信息的可靠性具有要求, 但外部信息使用者還要求對公司信息提供某種形式的保險。 而證交所作為具有權威性的監管機構, 其所進行的監管行為相當于對公司披露的信息給予了保險, 從而有助于提升公司信息披露質量。
2. 發現公司契約設計的缺陷。 公司治理需要通過有效契約協調公司活動, 使其與投資者、債權人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保持一致, 而有效契約的形成則需要通過公司信息來緩解契約各方的信息不對稱。 當公司受到非處罰性監管時, 意味著其公司治理存在不足、信息披露未能滿足要求, 不能有效協調公司管理者與投資者、債權人等之間的沖突, 公司契約設計存在缺陷。 受到非處罰性監管的公司, 其公司契約設計缺陷主要體現為兩種形式: ①公司契約設計形式有效, 但履行程序無效。 比如, 按照董事會職能分化理論, 獨立董事應承擔監督職責, 以達到內部權力制衡的目的。 由于當前獨立董事提名制度、選舉制度所存在的局限性, 獨立董事的獨立性難以保證, 獨立董事與其監督主體之間出于共同利益的考慮, 產生了違規性合謀的基礎。 受到非處罰性監管的公司的某些行為雖然形式上經過了獨立董事的監督與認可, 但實質上獨立董事的獨立性未得以保證, 契約有效性受到沖擊。 ②公司契約設計形式和履行程序均無效。 比如, 由于缺乏科學的對外擔保授權審批制度或對外擔保授權審批制度流于形式, 違規對外擔保是公司受到非處罰性監管的常見原因之一, 這表明公司契約制度設計和執行存在缺陷, 各利益相關主體之間的權力、責任和利益存在失衡。
3. 識別公司機會主義行為。 當公司可能存在機會主義行為時, 證交所通過非處罰性監管要求公司提供增量信息, 為進一步識別公司的機會主義行為奠定了基礎。 研究表明, 非處罰性監管不僅有助于識別機會主義盈余管理行為, 而且具有降低盈余管理程度[3] 、規避機會主義盈余管理的作用。 以康美藥業為例, 其因控制權變更、經營托管、股權激勵回購注銷、股票交易異常波動、年度報告事后審核、媒體報道的有關事項、重大會計差錯等原因, 多次收到證交所的問詢函, 監管部門的適時監管使得更詳盡、更真實的信息得以充分披露, 為利益相關者有效識別公司的機會主義行為提供了信息基礎。 但應該注意的是, 證交所對公司機會主義行為更多給予的是事后關注與監管, 而且由于管制成本、企業利益自我保護等方面的限制, 證交所并不能對公司予以面面俱到的監管, 監管所發揮作用的大小是多方面因素平衡、協調的結果, 這將導致非處罰性監管在事先識別機會主義行為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 更多的是當公司機會主義行為具有跡象時能夠更快速地進行識別和揭露。
4. 防范公司財務舞弊行為。 非處罰性監管不僅有助于識別公司的機會主義行為, 而且壓縮了公司財務舞弊的空間, 防范了公司財務舞弊行為的發生。 證交所通過對高管權力、薪酬以及高管變更等的監管, 從制約高管權力、防范職務侵占等方面壓縮財務舞弊的空間; 通過對擔保業務、關聯交易、債務重組、商譽減值等高舞弊風險點的監管, 從監控公司內部控制、風險管理等方面降低財務舞弊行為發生的可能性; 通過對會計核算方法變更、金額巨大交易等的問詢, 從會計信息披露方面規避財務舞弊行為的發生; 通過業務資格申請與審核、對證券交易等活動的限制, 從公司的業務范圍、業務活動限制等方面防止財務舞弊行為的進一步惡化; 通過記入誠信檔案、違反承諾情況的公示, 從公司聲譽方面防范財務舞弊行為的發生; 通過指定中介機構核查、提請司法機構介入, 從第三方輔助監管方面對公司財務舞弊行為的發生起到威懾作用。 但應該注意的是, 同樣由于監管成本、信息不對稱、企業利益自我保護等原因, 非處罰性監管對防范財務舞弊行為的作用亦是有限的。
五、非處罰性監管的非預期效應
以上非處罰性監管的效應均是直接作用于被監管主體且可以被直接觀察到的預期效應, 除此之外, 還存在非預期效應。 這是因為: 首先, 除了證監會、證交所等非處罰性監管的執行主體, 監察機構、司法機關、輿論媒體等行動主體與被監管主體之間的互動關系也會影響非處罰性監管效應, 這些主體之間的互動博弈合力決定了非處罰性監管的最終效應。 其次, 關聯制度間存在關聯性(現有制度之間的耦合性)和層次性(現有制度約束力、可操作性、制度表現形式之間的差異性), 這也將影響非處罰性監管效應的最終結果。 最后, 由于公司信息的受眾面較廣, 公司因非處罰性監管而提供的增量信息, 將使得非處罰性監管的非直接參與主體亦受到影響, 非處罰性監管的連帶效應將促使非預期效應的產生。 可見, 非處罰性監管所產生的效應具有不確定性, 其可能產生非預期效應, 而這些非預期效應不易被觀察和控制。 因此, 非處罰性監管的非預期效應亦應成為關注的重點。 結合非處罰性監管的實質以及其效應的產生機理, 其非預期效應預計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 非處罰性監管對實施環境的效應。 非處罰性監管有其自身的實施環境, 需要相應的制度環境、技術條件和資源條件等支撐, 非處罰性監管的實施會倒逼實施環境的優化以使其符合實施條件, 從而對非處罰性監管的實施環境產生影響。 制度環境決定了這一制度安排的實施范圍, 以及這一制度執行主體所能達到的效用增進的限定空間。 鑒于此, 為突破非處罰性監管自身的局限性, 培育良好的制度環境則成為必需。 比如, 《證券法》的修訂為非處罰性監管的實施創造了較好的法律環境; 證監會發布的《監管規則適用指引——會計類第1號》促進了會計準則在資本市場的有效、一致執行, 有助于減少非處罰性監管的頻次, 節約監管成本。 技術條件是影響非處罰性監管目標實現的重要因素, 亦是影響非處罰性監管實施效果的重要變量。 鑒于此, 為促進非處罰性監管目標的實現和實施效果的提升, 創造與提供先進的技術條件則成為必需。 比如, 大數據技術在監管領域的應用, 有助于推進證交所監管能力現代化, 讓監管者及時識別和預警潛在風險。 資源條件為非處罰性監管的實施提供了保障, 其應與非處罰性監管目標相匹配, 資源條件需能支撐非處罰性監管的實施, 若要對非處罰性監管的期望進行升級、目標予以放大, 則需要更多的資源條件支撐。
2. 非處罰性監管對關聯制度的效應。 非處罰性監管這一外部監管制度安排, 作為制度結構的一個組成部分, 在創新和變遷過程中會影響其他制度的變遷, 非處罰性監管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審計制度、內部控制制度、風險管理制度、有效契約制度等相互影響、相互依賴。 其一, 這些制度之間具有關聯效應。 當公司受到非處罰性監管時, 會倒逼其披露更詳細的信息、提請注冊會計師進行審核、修正內部控制設計不合理處、制定更完善的風險管理制度、調整和完善契約條款等; 而公司為了規避非處罰性監管, 也會主動提高信息披露質量、尋求注冊會計師提供的審計保險、完善內部控制制度、強化風險管理、提升契約有效性。 其二, 這些制度之間具有嵌入效應, 存在跨域的嵌入與交叉。 非處罰性監管行為促使的信息披露, 本身就是信息披露的一個組成部分, 非處罰性監管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具有一定的內嵌性, 而信息披露制度又是有效契約制度執行所必需的。 制度之間的關聯效應和嵌入效應使得任一制度的執行均可對其關聯制度產生影響。
3. 非處罰性監管對非直接參與主體的效應。 除了證交所、公司這些直接參與主體, 投資者、債權人、分析師、審計師等非直接參與主體亦會受到非處罰性監管的影響。 以投資者為例, 非處罰性監管有助于增強投資者對公司行為的識別能力。 信息不對稱的存在使得投資者需要充分的信息以滿足其決策需要、對企業行為進行識別, 而證交所的非處罰性監管使得公司重要的、復雜的或者異常事項的信息被更充分地披露, 這為投資者有效識別公司行為奠定了基礎。
其一, 非處罰性監管減少了投資者與公司之間的信息溝通障礙。 當公司涉及多個行業、業務, 具有復雜性時, 投資者和公司之間的信息交流成本會非常高, 投資者進行經濟決策和識別企業行為時所需要的信息數量、信息質量亦會更高, 那么, 通過非處罰性監管督促公司補充披露或者修正調整后的信息將有助于減少投資者和公司之間的信息溝通障礙。 其二, 非處罰性監管增強了投資者對綜合性信息的可理解性。 公司披露的信息中, 有些是關于會計人員職業判斷過程和結果的總括披露(如收入信息, 其只是對收入會計政策、收入總額以及針對主要客戶的收入總額進行總括披露), 有些是關于會計人員職業判斷過程和結果的具體披露(如會計變更信息, 其對每一項會計變更的過程和結果進行具體披露)。 對于前者, 由于信息披露概括性比較強, 投資者進行識別具有一定的難度, 對投資者的識別能力要求較高; 對于后者, 由于信息披露比較詳細, 投資者進行識別相對比較容易, 對投資者的識別能力要求較低。 通過非處罰性監管, 可對總括披露信息予以更詳細的補充, 從而有助于投資者識別公司行為。
4. 非處罰性監管對監管路徑的依賴效應。 非處罰性監管作為一種行為方式, 會影響到各相關主體(包括直接參與主體和非直接參與主體)的偏好和選擇, 各相關主體在長期受影響的過程中, 意識形態效應會逐漸形成并固化, 非處罰性監管的制度范圍便成為各相關主體的關注重點。 以問詢函這一非處罰性監管方式為例, 滬深證交所于2016年共發出1200余份問詢函, 2017年共發出1300余份, 2018年共發出1800余份, 呈逐漸上升趨勢。 可見, 非處罰性監管逐漸成為強有力的監管工具, 也成為一種監管新常態。 實踐中公司業績預告質量的改善、審計質量的提升等, 均表明了非處罰性監管效應的存在。 此外, 非處罰性監管制度在執行過程中, 其正向效應的存在將會激勵人們在實踐中不斷強化該制度的執行, 逐漸形成對該制度的依賴, 非處罰性監管亦將步入“好”的路徑。 由于路徑依賴的慣性作用, 這一監管路徑將逐漸強化, 產生路徑依賴效應, 非處罰性監管這一監管手段將在較長一段時間內存在并發揮作用。
六、結語
非處罰性監管既具有預期效應, 又具有非預期效應。 非處罰性監管效應的產生是各相關主體施加監管行為或者接受被監管行為的過程中, 在意識形態效應和學習效應的作用下, 受一系列具有關聯效應和嵌入效應的制度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制度本身變遷動力的推動而產生的。 由于非處罰性監管行為的作用面較廣, 且作用機理和作用路徑具有復雜性, 本文只是對非處罰性監管效應進行了定性分析, 對于這些效應的存在性、性質等還需要大量的實證研究予以驗證, 本文為進一步研究證交所非處罰性監管效應提供了方向和思路。
【 主 要 參 考 文 獻 】
[1] 陳運森,鄧祎璐,李哲.非處罰性監管具有信息含量嗎?——基于問詢函的證據[ J].金融研究,2018(4):155 ~ 171.
[2] 翟淑萍,王敏,韓賢.交易所財務問詢函監管與會計信息可比性——直接影響與溢出效應[ J].當代財經,2020(10):124 ~ 137.
[3] 翟淑萍,王敏.非處罰性監管提高了公司業績預告質量嗎?——來自于財務報告問詢函的證據[ 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9(4):92 ~ 107.
[4] 夏一丹,陳婕妤,夏云峰.交易所問詢函對業績預告質量的影響[ J].財經科學,2020(11):41 ~ 53.
[5] 吳浩哲.交易所監管函的市場反應及其影響因素研究[ J].中國注冊會計師,2020(7):63 ~ 68.
[6] 翟淑萍,王敏,毛文霞.財務報告問詢函與上市公司融資約束[ J].金融論壇,2020(10):46 ~ 57.
[7] 王春峰,黃盼,房振明.非處罰性監管能預測公司違規嗎[ J].經濟與管理評論,2020(5):112 ~ 125.
[8] 趙立彬,傅祥斐,李瑩等.交易所問詢函能識別公司內控風險嗎?——基于年報問詢函的經驗證據[ J].南方金融,2020(10): 40 ~ 51.
[9] 傅祥斐,崔永梅,趙立彬.監管問詢函有風險預警作用嗎?——基于證券交易所重組問詢函的證據[ J].證券市場導報,2020(8):12 ~ 21.
[10] 王艷艷,謝婧怡,王迪.非處罰性監管影響了審計質量嗎?——基于年報問詢函的經驗證據[ J].財務研究,2019(4):62 ~ 73.
[11] 陶雄華,曹松威.證券交易所非處罰性監管與審計質量——基于年報問詢函信息效應和監督效應的分析[ J].審計與經濟研究,2019(2):8 ~ 18.
[12] 陳運森,鄧祎璐,李哲.非行政處罰性監管能改進審計質量嗎?——基于財務報告問詢函的經驗證據[ J].審計研究,2018(5): 82 ~ 88.
[13] 耀友福,林愷.年報問詢函影響關鍵審計事項判斷嗎?[ J].審計研究,2020(4):90 ~ 101.
[14] 魯桂華,韓慧云,陳運森.會計師事務所非處罰性監管與IPO審核問詢——基于科創板注冊制的證據[ J].審計研究,2020(6):43 ~ 50.
[15] 丁龍飛,謝獲寶.年報問詢函的監管溢出效應研究——來自企業集團A股上市子公司的證據[ J].南方經濟,2020(8):98 ~ 113.
[16] 翟淑萍,王敏,張曉琳.財務問詢函對審計聯結公司的監管溢出效應——來自年報可讀性的經驗證據[ J].審計與經濟研究, 2020(5):18 ~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