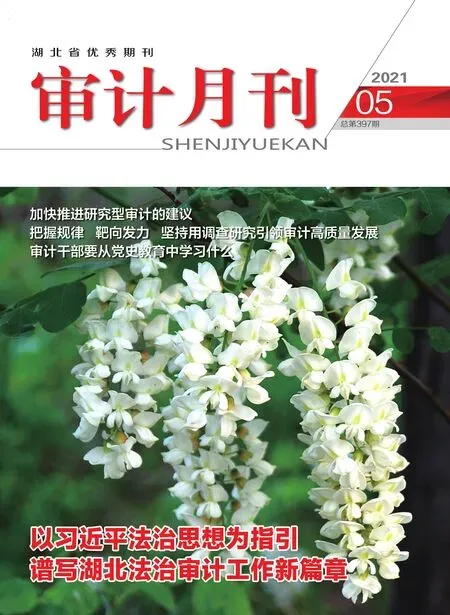勞動者的古歌
◆苗連貴/武漢

原始勞動歌謠,口耳相傳下來的不多,有文字記載的更其寥寥,但僅就散見于先秦典籍中零星的篇什看,大多鏗鏘有力、意氣昂揚,催人奮發。其中最為后世稱道的,當屬《彈歌》(載《吳越春秋》):斷竹,續竹,飛土,逐宍(古“肉”字,代指禽、獸)。
“斷竹”,砍伐并截取竹子;“續竹”,是用韌性的藤葛或竹索做弦,制成彈弓,強勁有力;“飛土”,把泥做成彈丸,裝在竹箭上,干了后堅硬異常,這樣才能擊傷獵物;“逐宍”,這樣的弓箭不一定能“一‘箭’封喉”,獵物負傷而逃,這就要追逐了。八字短歌,流露出原始人對自己學會制造得用的獵具的自豪感、以及追逐并獲得獵物的喜悅心情。
《蠟辭》(載《禮記》)也寫得簡短而有力:“土,反其宅;
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
土,從哪里來的返回到哪里去;水,回到山谷中;害蟲不要猖獗;草木,回到沼澤地帶生長。大水泛濫,土地淹沒,蟲害猖獗,草木荒疏。這看似“咒語”,但態度堅決,聲勢凌厲,命令似的語氣,表現了先民改造自然的理想和堅定的信念。
《易經》中還有這樣的一首:“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
男的看似宰羊,但不見血;女的將羊毛裝筐,但沒有重量。這首歌,大約是男女邊勞動,邊相互戲謔時對唱的,有情有景,表現出勞動中的嬉鬧之態。
到了春秋,《詩經》記載的勞動詩歌就多了。
原先以為,上古洪荒,生產力低下,那時生民勞作不知怎樣受苦受難呢!近又讀《詩經》,讀到有關勞動的篇章,發現全然不是“想當然”那么回事,詩里描繪的勞動情狀不惟不苦,反而輕松愉悅,極具生活情味。
我特別喜歡《詩經》中的《周南·芣苢》,這是一首女子采摘車前子草的樂歌。余冠英先生將之譯成白話,十分精妙,盡顯民歌風味:車前子兒采呀采,采呀快快采起來。車前子兒采呀采,采呀采到手中來。車前子兒采呀采,一顆一顆揀起來。車前子兒采呀采,一把一把捋下來。車前子兒采呀采,手提衣襟兜起來。車前子兒采呀采,掖起了衣襟兜回來。
這首小詩章節回環復沓,通過反復詠唱,我們仿佛看到三五成群的女子在山坡曠野勞動的身影,聽到她們的歌聲,感受到她們采摘時的歡樂心情。
如果說,《芣苢》是一首浸染著田野風的抒情小調,《大雅·緜》則是一首氣勢磅礴的創業者之歌。《緜》記載周人為了生存和發展,進行的一次全國性的大遷徙,開疆辟土,建設家園,是一首帶有史詩性質的古歌。共四章,其中第四章直接寫他們到了新地,整田筑室的勞動場景。上學時,老師褚斌杰先生把它譯成白話:裝土運泥響陾陾,投土入板響轟轟。搗土打墻登登登,削墻拍打砰砰砰。百堵高墻平地起,勞動歌聲勝鼓聲。
如此艱辛的勞動卻看不到先民們的苦楚,有的只是高揚的勞動熱情和創業的自豪感。這使我想起在“戰天斗地”年代,那種出大力,流大汗,以苦為樂的情懷。勞動并不苦,勞動換來成果,勞動讓人憧憬美好幸福的明天。
在《詩經》中,有關勞動的詩幾乎都寫得很“樂呵”,即如《伐檀》《七月》,也是“以勞動為起興”,表現對不勞而獲的貴族老爺的不滿、諷刺、甚至反抗,勞動者對勞動本身并無怨尤的。
勞動是人的自身需要,所以勞動起來多不覺苦。即使勞動的過程艱辛萬分,人們也會從中找樂,使之變得輕松愉快起來。我記得上世紀的勞動工地,譬如修路或筑壩,常見人們唱“夯歌“,邊打夯邊唱,一人起頭,眾人齊和,歌詞即興發揮,出口成章,合轍押韻,風趣調侃。夯歌使人們在高強度的勞動條件下心情放松,精神飽滿,感到有使不完的勁。
這種隨口創作的“夯歌”,也許就是所謂的詩了。原始社會和《詩經》里勞動的歌聲,我想也就是這樣產生的吧?勞動是詩歌創作的源泉,這自然是另一個詩歌的話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