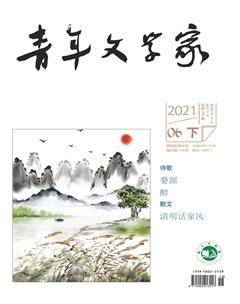以“離去—?dú)w來(lái)—再離去”模式分析《故鄉(xiāng)》《曼斯菲爾德莊園》敘事的相似性
倪金鑫
魯迅是20世紀(jì)中國(guó)偉大的思想家與文學(xué)家,他創(chuàng)造了“內(nèi)外兩面,都和世界的時(shí)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國(guó)的民族性”。即他不但關(guān)注了本民族文學(xué)的發(fā)展,而且關(guān)注了思考人類(lèi)共同面臨的問(wèn)題,所以他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不僅僅具有民族性,而且具有世界性。“中國(guó)現(xiàn)代小說(shuō)在魯迅手中開(kāi)始,又在魯迅手中成熟”,魯迅創(chuàng)造小說(shuō)的能力很強(qiáng),而且他可以借助西方文學(xué)思想的啟蒙方式來(lái)進(jìn)行引用,他開(kāi)創(chuàng)了中國(guó)現(xiàn)代小說(shuō)的開(kāi)端,同時(shí)又專(zhuān)心致志于小說(shuō)的研究和發(fā)展,終于成就了中國(guó)現(xiàn)代小說(shuō)的高峰。“離去-歸來(lái)-再離去”的小說(shuō)模式,也稱(chēng)歸鄉(xiāng)模式,常被魯迅運(yùn)用到小說(shuō)的創(chuàng)作中,作品如《故鄉(xiāng)》《祝福》《在酒樓上》等。
簡(jiǎn)·奧斯汀是19世紀(jì)初英國(guó)著名的女作家,她繼承和發(fā)展了英國(guó)18世紀(jì)浪漫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傳統(tǒng)。簡(jiǎn)·奧斯汀居住在英國(guó)的鄉(xiāng)村小鎮(zhèn),過(guò)著祥和、安寧的生活,接觸到的也都是中小地主、牧師等人物,因此作品中沒(méi)有重大的社會(huì)矛盾,代表作品有《傲慢與偏見(jiàn)》《理智與情感》《曼斯菲爾德莊園》等。筆者在閱讀過(guò)程中發(fā)現(xiàn):產(chǎn)生于不同時(shí)代、不同國(guó)家、不同背景下的《故鄉(xiāng)》與《曼斯菲爾德莊園》,在小說(shuō)情節(jié)的展開(kāi)中都運(yùn)用了“離去-歸來(lái)-再離去”的模式。下面將從三個(gè)方面展開(kāi)詳細(xì)論述。
一、“離去”的被逼無(wú)奈
魯迅的《故鄉(xiāng)》以“我冒了嚴(yán)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別了二十余年的故鄉(xiāng)去”為開(kāi)頭,采取橫截面的寫(xiě)法省去了“歸鄉(xiāng)”模式第一階段“離去”的情節(jié),而通過(guò)《故鄉(xiāng)》中的某些提示、魯迅當(dāng)時(shí)所生活的社會(huì)環(huán)境以及人生經(jīng)歷,我們可以得知,黑暗混亂的社會(huì)中,中國(guó)最底層的廣大農(nóng)民,無(wú)疑成為最終的受害者,他們生活困窘,過(guò)著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生活,毫無(wú)權(quán)利可言。而魯迅早年喪父,家道中落,嘗盡了世間的人情冷暖,他面對(duì)這日益被都市文化消解殆盡的封建宗法制度下的農(nóng)村文化,面對(duì)黑暗的現(xiàn)實(shí)與生活的壓力,魯迅選擇“尋異路、走異地”,他不得不到外面的世界去尋求新的出路,魯迅的離鄉(xiāng)是被迫的。
簡(jiǎn)·奧斯汀以寫(xiě)英國(guó)的鄉(xiāng)村風(fēng)情著稱(chēng),她曾說(shuō)自己的作品無(wú)非是鄉(xiāng)間村莊里三四戶人家的故事,其中代表作品之一便是《曼斯菲爾德莊園》,這個(gè)作品是有關(guān)一個(gè)人對(duì)一個(gè)地方的愛(ài)的小說(shuō)。作品中的女主角芬妮·普萊斯的“離去”也同樣是被迫的。芬妮的母親弗蘭西斯小姐有兩個(gè)姐姐,分別是大姐沃德小姐和二姐瑪利亞小姐。大姐嫁給了牧師諾里斯先生,諾里斯先生在托馬斯爵士的幫助下,取得了一份教區(qū)牧師的俸祿,每年有將近一千英鎊的收入,而二姐瑪利亞小姐,她嫁給了托馬斯·伯特倫爵士,一躍成為曼斯菲爾德莊園的主人以及男爵夫人,這門(mén)顯貴的親事得到了普遍的贊揚(yáng)與家庭成員的一致認(rèn)同。而芬妮的母親弗蘭西斯小姐卻使她的家庭丟盡了臉面,她嫁給了一個(gè)海軍中尉普萊斯,一無(wú)文化,二無(wú)財(cái)產(chǎn),再加上她生育眾多的孩子,丈夫又無(wú)所作為、整日喝酒取樂(lè),她的家庭生活入不敷出,極其拮據(jù)。為了獲取姐姐們的幫扶,普萊斯太太給多年未曾聯(lián)系的親戚寫(xiě)了一封求助信,伯特倫太太為了減輕妹妹生活的壓力,在諾里斯太太的提議下,經(jīng)過(guò)丈夫托馬斯爵士的同意后,決定撫養(yǎng)普萊斯太太的長(zhǎng)女芬妮。這對(duì)于普萊斯太太來(lái)說(shuō)無(wú)疑是天大的好消息,這意味著家庭開(kāi)支的減少與生活負(fù)擔(dān)的減輕,而對(duì)于諾里斯太太來(lái)說(shuō)則滿足了她想要的仁慈的美好名聲。此刻,沒(méi)有人會(huì)詢問(wèn)九歲的芬妮是否同意前往曼斯菲爾德莊園生活,她沒(méi)有選擇,只能被迫與熟悉的環(huán)境分開(kāi),與自己最好的玩伴威廉分別,來(lái)到這個(gè)令她害怕與不自在的曼斯菲爾德莊園,她在這里經(jīng)受著諾里斯姨媽喋喋不休的“教導(dǎo)”,遭受著兩位表姐的指指點(diǎn)點(diǎn)與嘲笑,時(shí)刻面對(duì)著托馬斯爵士威嚴(yán)的面孔,過(guò)著寄人籬下、順從聽(tīng)話的生活。
二、“歸來(lái)”的事與愿違
魯迅《故鄉(xiāng)》中的“我”回鄉(xiāng)名義上是為了處理賣(mài)老屋和搬家的事情,實(shí)則是為了找尋自己內(nèi)心的精神故鄉(xiāng)。魯迅在外漂泊數(shù)載,為了生活東奔西走,嘗盡人間冷暖。作為一個(gè)現(xiàn)代知識(shí)分子,魯迅感到迷茫和困惑,回鄉(xiāng)也是為了“尋夢(mèng)”。在魯迅的記憶里,故鄉(xiāng)是美好的,色調(diào)是明快的,那里的人也都是淳樸有趣的。但當(dāng)他看到“蒼黃的天底下,遠(yuǎn)近橫著幾個(gè)蕭索的荒村,沒(méi)有一些活氣”這樣的故鄉(xiāng)的時(shí)候,他內(nèi)心感到了一絲悲涼,不禁問(wèn)道﹕“啊!這不是我二十年來(lái)時(shí)時(shí)記得的故鄉(xiāng)?”下面又有說(shuō)到他的故鄉(xiāng)比這個(gè)好多了,但是卻又沒(méi)有影像。這是因?yàn)樗麅?nèi)心的故鄉(xiāng)是以小孩子的視角理想化了的精神故鄉(xiāng),實(shí)際上是不存在的,因此他沒(méi)有言語(yǔ),也沒(méi)有影像。回鄉(xiāng)后,那個(gè)曾經(jīng)被稱(chēng)為“豆腐西施”的楊二嫂,在生活的摧殘下,也變得尖酸、丑陋、刻薄、愛(ài)占小便宜,不由得讓人聯(lián)想到當(dāng)時(shí)廣大底層農(nóng)民生活的艱難與困苦。最令“我”震驚和失望的無(wú)疑是閏土的一聲“老爺”,這讓“我”感到悲哀,原來(lái)“我”與閏土之間已經(jīng)隔了這么厚、這么高的壁壘,是絕不可能打破的。那個(gè)在金黃的月光下、海邊的沙地上、在一望無(wú)垠碧綠的瓜田里刺猹的少年;那個(gè)在雪地里捕鳥(niǎo)的少年;那個(gè)與“我”以兄弟相稱(chēng)的承載著“我”對(duì)故鄉(xiāng)的一切美好幻想的少年,已經(jīng)消失不見(jiàn)了。在多子、苛捐雜稅、官、紳、兵、匪的壓力下,他已經(jīng)變得麻木、沉默,如木偶人一般了。這無(wú)疑是對(duì)“我”的一種巨大打擊,本想著回鄉(xiāng)尋夢(mèng),結(jié)果無(wú)夢(mèng)可尋、無(wú)路可走,不由得讓人黯然神傷。
芬妮之所以會(huì)回到自己的家鄉(xiāng)樸次茅斯,是在經(jīng)過(guò)托馬斯爵士的深思熟慮之后作出的決定。當(dāng)時(shí)亨利·克勞福德先生對(duì)芬妮表達(dá)內(nèi)心的情意,為了獲得芬妮的愛(ài),還幫助了芬妮的哥哥威廉在海軍中謀得了一個(gè)軍銜。他所做的這一切讓芬妮感到很矛盾,一方面,她應(yīng)該感謝克勞福德先生幫助了自己的哥哥;另一方面,在排練話劇《山盟海誓》的過(guò)程中,芬妮作為局外人清醒地看到了克勞福德與她的兩位表姐之間的感情糾葛,認(rèn)為他是一個(gè)玩弄情感、不負(fù)責(zé)任、生活不檢點(diǎn)的人。因此,芬妮對(duì)他實(shí)在喜歡不起來(lái)。但出于上述的恩情,芬妮又很難做到對(duì)克勞福德先生惡語(yǔ)相向、斷然拒絕,她唯一的做法就是逃避,以及等待著克勞福德兄妹的離開(kāi)。托馬斯爵士認(rèn)為在克勞福德先生離開(kāi)之后,芬妮肯定會(huì)意識(shí)到情人的奉承和愛(ài)意對(duì)自己的重要性。但當(dāng)克勞福德真的離開(kāi)后,托馬斯爵士并沒(méi)有如愿以償,因此,他決定讓芬妮回一趟自己的家,讓她明白財(cái)產(chǎn)與地位對(duì)她未來(lái)的幸福生活有多么重要。因?yàn)橥旭R斯爵士堅(jiān)信,芬妮在豐衣足食的曼斯菲爾德莊園生活了八九年,已經(jīng)喪失了比較和判斷的能力,而她的父親將會(huì)使她清醒。
對(duì)于芬妮來(lái)說(shuō),能回到那個(gè)年幼時(shí)以自己為中心的家庭,與長(zhǎng)期分離的家人團(tuán)聚,在路途中有威廉的陪伴并且能暫時(shí)逃離克勞福德兄妹是最開(kāi)心不過(guò)的事情了。但是當(dāng)芬妮的馬車(chē)停在家門(mén)口的時(shí)候,她才能意識(shí)到現(xiàn)實(shí)中的家庭與她想象中的家是如此不同。她的家庭是如此的擁擠、破舊,家庭的秩序混亂不堪,環(huán)境與生活用品都是不潔凈的,家庭里的吵鬧聲仿佛沒(méi)有停止的時(shí)候,更重要的是,除了剛下車(chē)母親給了自己一個(gè)親切的擁抱,好像沒(méi)有人關(guān)注她。這與她想象中的充滿愛(ài)意與歡樂(lè)的家庭是毫不相關(guān)的。芬妮在這里沒(méi)有獲得想要的幸福與滿足,相反,她認(rèn)為待在這里純粹是一種煎熬。
三、“再離去”的毅然決然
魯迅回到故鄉(xiāng)面對(duì)這樣一種令人驚異窒息的悲慘景象,面對(duì)著以楊二嫂為代表的被生活異化了的尖酸刻薄的村民,面對(duì)著以閏土為代表的老實(shí)干活謀生計(jì)的農(nóng)民,卻依舊在帝國(guó)主義與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喘不過(guò)氣來(lái)的境況,“我”才明白原來(lái)“我”心中的那個(gè)明亮的故鄉(xiāng)只是“我”的一種想象而已,“我”徹底無(wú)家可歸,儼然成了社會(huì)的過(guò)客與棄兒。“我”想要在故鄉(xiāng)獲取精神力量、追求歸屬感的夢(mèng)破碎了,但是夢(mèng)醒了卻無(wú)路可走的悲涼又涌入心頭。但魯迅并沒(méi)有就此消沉與絕望,因?yàn)椤敖^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他堅(jiān)信“希望是本無(wú)所謂有,無(wú)所謂無(wú)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shí)地上本沒(méi)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他毅然決然地選擇再離去,把希望寄托于青年一代身上,他不是一個(gè)虛無(wú)主義者,他堅(jiān)信在一代代人的努力下,美好的明天一定會(huì)來(lái)臨的。
芬妮在這樣一個(gè)幾乎每個(gè)方面都與自己所盼望的截然相反的家里,更是一刻都不想停留。因?yàn)樗募彝ナ且粋€(gè)粗俗、吵鬧、混亂的場(chǎng)所,沒(méi)有一個(gè)人懂得如何把事情做得合情合理以及怎樣待人接物,尤其是她父親的粗鄙和無(wú)禮更是讓芬妮無(wú)法忍受。與鄉(xiāng)村新鮮的空氣隔絕,芬妮的身體也變得不如從前,她開(kāi)始想念曼斯菲爾德莊園,想念那里的人與物,甚至她把曼斯菲爾德莊園稱(chēng)作她的家。當(dāng)她收到埃德蒙的寫(xiě)著要帶她回莊園的信時(shí),她的興奮是難以比擬的,因?yàn)椤半m然曼斯菲爾德莊園可能有一些痛苦,樸次茅斯卻沒(méi)有快樂(lè)”。在芬妮自己家中,她是一個(gè)可有可無(wú)的人,每天靠著用托馬斯爵士給她的錢(qián)出去買(mǎi)面包充饑,家里的一切仿佛都與她格格不入;而在莊園,芬妮是不可缺少的人物,伯特倫姨母需要她,那里的一切都秩序井然、美好安寧。因此,芬妮對(duì)于自己家庭的再離去是非常主動(dòng)的,而且這種離開(kāi)的意念非常強(qiáng)烈,毅然決然。
四、小結(jié)
綜上所述,雖然魯迅的《故鄉(xiāng)》和簡(jiǎn)·奧斯汀的《曼斯菲爾德莊園》在內(nèi)容上看起來(lái)毫無(wú)關(guān)聯(lián),但是在小說(shuō)的情節(jié)敘述模式上都采用了“離去-歸來(lái)-再離去”,對(duì)小說(shuō)意義與主旨的建構(gòu)都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