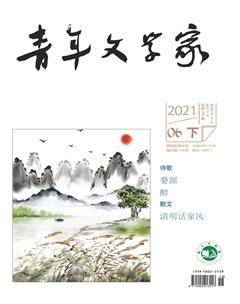論杰斯·斯圖亞特《愛(ài)》的敘事策略
賈鵬瑋
杰斯·斯圖亞特(1907—1984)出生在美國(guó)肯塔基州格里納普縣,是美國(guó)當(dāng)代著名的小說(shuō)家、詩(shī)人,但國(guó)內(nèi)關(guān)于他的介紹和譯作卻很少。他的作品主要描寫(xiě)肯塔基州東北的鄉(xiāng)村生活。斯圖亞特的短篇小說(shuō)《愛(ài)》講述了“我”和父親在玉米地里看到一條即將產(chǎn)卵的母黑蛇,在父親命令獵狗將其咬死的第二天,一條公黑蛇盤(pán)繞在死去的母蛇周圍,仿佛在為伴侶的不幸而悲傷。父親被此情景所觸動(dòng),最終改變態(tài)度放走了公蛇。小說(shuō)通篇簡(jiǎn)潔凝練,作者借敘述者“我”之口將故事向讀者娓娓道來(lái)。本文將從敘事視角、敘事距離、敘事空間三個(gè)方面探討小說(shuō)的藝術(shù)審美特征,并試圖挖掘小說(shuō)所蘊(yùn)含的主題意義。
一、第一人稱內(nèi)聚焦的敘事視角
斯圖亞特的短篇小說(shuō)《愛(ài)》中所運(yùn)用的第一人稱內(nèi)聚焦這一限知視角使得讀者通過(guò)敘述者正在經(jīng)歷事件時(shí)的眼光來(lái)觀察體驗(yàn)故事,不但降低了故事的虛構(gòu)性,而且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第一人稱內(nèi)聚焦通常涉及回顧性視角和體驗(yàn)性視角,小說(shuō)中體驗(yàn)性視角的使用大于回顧性視角,這一視角安排增強(qiáng)了讀者閱讀過(guò)程中的情感體驗(yàn),容易激起讀者對(duì)母蛇遭遇的同情與憐憫。
小說(shuō)《愛(ài)》中第一人稱敘述者“我”與人物聚焦者“我”重合,構(gòu)成第一人稱內(nèi)聚焦這一獨(dú)特的敘事視角。敘事視角指敘述時(shí)觀察故事的角度(申丹,2010:88)。所以敘事視角包含兩個(gè)方面:一是敘述時(shí)的角度,二是觀察時(shí)的角度。敘述的角度涉及“誰(shuí)說(shuō)”,觀察的角度涉及“誰(shuí)看”。兩者有時(shí)分離,有時(shí)重合。熱奈特把聚焦分為三類:零聚焦、內(nèi)聚焦和外聚焦(1990:129—130)。小說(shuō)《愛(ài)》中講述故事的人與觀察感知故事的人同為“我”,所以小說(shuō)第一人稱敘述者“我”和人物聚焦者“我”重合,構(gòu)成第一人稱內(nèi)聚焦。“我”既是故事的講述者,又是故事的參與者。當(dāng)故事以 “我”的親身經(jīng)歷展開(kāi)時(shí),讀者隨著敘述者“我”的切身體會(huì)而感同身受,在情感上容易引起與讀者的共鳴。第一人稱內(nèi)聚焦屬于限知視角,讀者只可以窺探敘述者“我”的想法,卻無(wú)法得知故事中父親的內(nèi)心。這樣故事的虛構(gòu)性被降到最低,而故事的真實(shí)性與可信性被更大程度地突顯出來(lái)。
第一人稱聚焦涉及回顧性視角和體驗(yàn)性視角,兩者通常融合在一起。因?yàn)閿⑹稣咴跀⑹龉适聲r(shí)故事往往是已經(jīng)發(fā)生了的,而非做現(xiàn)時(shí)性報(bào)道。在小說(shuō)《愛(ài)》中,開(kāi)頭敘述者便告訴我們故事是發(fā)生在昨天的事情,雖是回顧性視角,但小說(shuō)實(shí)際上體驗(yàn)性視角的運(yùn)用大于回顧性視角。“血從它弧度優(yōu)美的喉嚨噴射而出。什么東西擊中了我的胳膊,像小球一樣。”(斯圖亞特:22—23)此處敘述者明顯運(yùn)用體驗(yàn)性視角。既是發(fā)生在昨天的事情,那么“我”便早就知道擊中“我”胳膊的小球是蛇蛋。但敘述者沒(méi)有直接告訴讀者,而是帶領(lǐng)讀者仿佛親身經(jīng)歷了母蛇被狗撕裂的場(chǎng)面。這樣的安排加強(qiáng)了讀者的內(nèi)心震撼與對(duì)母蛇的同情效果,增強(qiáng)了下文讀者對(duì)“我”成功勸說(shuō)父親放生公蛇后的情感體驗(yàn)。
小說(shuō)《愛(ài)》中第一人稱內(nèi)聚焦這一視角的使用,不但降低了故事的虛構(gòu)性,而且拉近了作品與讀者之間的距離,使讀者在情感上更容易產(chǎn)生共鳴。作者通過(guò)敘述者“我”來(lái)講述“我”在玉米地上目睹的慘案來(lái)激起讀者對(duì)母蛇遭遇的憐憫之情,從而呼吁我們保護(hù)動(dòng)物、熱愛(ài)生靈,并間接傳達(dá)了作者“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生態(tài)思想。
二、動(dòng)態(tài)變化的敘事距離
小說(shuō)《愛(ài)》在敘事距離的調(diào)控方面,表現(xiàn)在敘述者與作者、敘述者與作品人物間的距離呈動(dòng)態(tài)變化的局面上。敘述者與作者時(shí)近時(shí)遠(yuǎn)的距離,不僅表達(dá)了作者熱愛(ài)土地、熱愛(ài)自然的生態(tài)思想,而且諷刺了人與自然二元對(duì)立和以人類為中心的利己主義思想。此外,敘述者與故事人物間距離的疏離共存在給讀者帶來(lái)戲劇性的審美體驗(yàn)的同時(shí),也暗示了小說(shuō)中父親生態(tài)意識(shí)的覺(jué)醒。
小說(shuō)中敘事距離的變化首先體現(xiàn)在敘述者與作者之間。根據(jù)韋恩·布斯,敘事距離主要體現(xiàn)在敘述者身上,通過(guò)敘述者的情感、道德、智力等方面展示出來(lái),主要表現(xiàn)為敘述者與隱含作者、讀者還有作品人物之間的距離。(布斯:175—177)敘事距離往往并非單一停滯,而是動(dòng)態(tài)變化的。小說(shuō)《愛(ài)》中敘述者“我”與作者及隱含作者的距離既相近又時(shí)而遠(yuǎn)離。敘述者為第一人稱時(shí),這種天然的代入感讓敘述者和隱含作者的敘事距離無(wú)限縮小(胡小玲2015:49)。縱觀全文小說(shuō)《愛(ài)》中第一人稱敘述者“我”的價(jià)值觀念與隱含作者的價(jià)值觀念是一致的。布斯認(rèn)為隱含作者是作者的第二個(gè)自我,那么隱含作者的價(jià)值觀念蘊(yùn)含著作者的道德意識(shí)。斯圖亞特曾贊美他家鄉(xiāng)的那片土地猶如肌膚般親近(David,2003:14)。文中隱隱透露出的美麗鄉(xiāng)村氣息,以及敘述者對(duì)蛇這一普遍被認(rèn)為是邪惡的生靈產(chǎn)生憐愛(ài)之情,表達(dá)了作者熱愛(ài)土地、熱愛(ài)自然之情。
但小說(shuō)中敘述者與作者的距離并非總是那么近。第一人稱內(nèi)聚焦屬于限知視角,它帶有的主觀性導(dǎo)致了敘述者有時(shí)并不是那么值得信賴。《愛(ài)》中“我”既扮演故事中的特定角色,又承擔(dān)著向讀者講述故事的功能,那么“我”所描寫(xiě)的只是“我”所感知和看到的,“我”所表達(dá)的只是“我”自己的內(nèi)心想法。“這就是生活,弱肉強(qiáng)食,即使在人類之間,也是如此。狗殺死蛇,鳥(niǎo)兒殺死蝴蝶。人類征服一切,為取樂(lè)而殺戮。” 這是“我”看到獵狗撕裂母蛇后的心理活動(dòng)。此處敘述者與作者的距離變大。“人類征服一切,為取樂(lè)而殺戮”,這與作者熱愛(ài)自然的道德信念相悖,所以此處敘述者“我”又與作者拉開(kāi)距離成為不可靠敘述,因而導(dǎo)致反諷。作者諷刺了以人類為中心的利己主義思想,并且抨擊了對(duì)動(dòng)物進(jìn)行不負(fù)責(zé)任的獵殺行為。
其次小說(shuō)中對(duì)敘事距離的調(diào)控也體現(xiàn)在敘述者與故事人物間的疏離共存中。小說(shuō)《愛(ài)》中敘述者“我”與父親之間的情感價(jià)值距離是由遠(yuǎn)及近轉(zhuǎn)換的。故事開(kāi)頭“我”與父親持相反態(tài)度。父親討厭蛇,并指使自家獵狗將其咬死。而“我”站在保護(hù)蛇的立場(chǎng)上勸說(shuō)父親黑蛇無(wú)毒。父親與“我”之間的價(jià)值距離使得讀者對(duì)父親的行為產(chǎn)生質(zhì)疑與不滿。后來(lái)父親在“我”的勸說(shuō)下被兩條蛇的愛(ài)情所感動(dòng)并放走公蛇,實(shí)現(xiàn)了父親與“我”的價(jià)值距離的一致。父親從憎恨蛇到對(duì)蛇的放生,體現(xiàn)出了小說(shuō)題目“愛(ài)”的深刻含義。作者不僅描寫(xiě)兩條蛇之間的愛(ài)情,更試圖言說(shuō)一種人類與自然萬(wàn)物之間的大愛(ài)。父親態(tài)度的轉(zhuǎn)變體現(xiàn)著敘述者與作品人物間距離的變化,這一安排暗示了父親生態(tài)意識(shí)的覺(jué)醒,給予了作者對(duì)人與動(dòng)物間關(guān)系的積極思考。
三、具有象征意義的敘事空間
小說(shuō)《愛(ài)》在敘事空間的建構(gòu)中賦予了其深刻的象征含義。小說(shuō)中的物理空間是故事發(fā)生的地點(diǎn)—玉米地,這一地域性的物理空間不但交代了故事發(fā)生的背景,而且象征著在這片土地上人類與動(dòng)物之間因生存而產(chǎn)生的矛盾沖突最終會(huì)通過(guò)人性的溫暖得以解決。小說(shuō)敘事的心理空間通過(guò)主人公即敘述者“我”的心理活動(dòng)所建構(gòu)。 “我”對(duì)母蛇遭遇所流露出的同情與無(wú)奈和對(duì)母蛇與分娩的女性相類比,表達(dá)了作者“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生態(tài)理念。
小說(shuō)塑造的“玉米地”這一物理空間,不僅具有地域性的指示意義,而且蘊(yùn)含著作者對(duì)人與自然界復(fù)雜關(guān)系的思考和對(duì)重建人與自然和諧關(guān)系的向往。米歇爾·德塞都在《日常生活的實(shí)踐》中指出每一個(gè)故事都是一種空間實(shí)踐,他強(qiáng)調(diào)物質(zhì)空間與隱喻空間的結(jié)合。(程錫麟,2007:26)物理空間不僅是一種物質(zhì)性器皿,它往往承載社會(huì)中隱性的復(fù)雜關(guān)系。小說(shuō)開(kāi)篇講述了“我”和父親在新開(kāi)墾的玉米地里,為防止牛群踐踏玉米地,準(zhǔn)備做一個(gè)柵欄。這一開(kāi)頭蘊(yùn)含了人與動(dòng)物之間的沖突。人類為了利益不斷“新開(kāi)墾”土地,而牛群為了生存不得不踏足“屬于人類的土地”。一道柵欄便成了人與動(dòng)物之間和諧相處的屏障。被松鼠吃掉種子從而枯萎脫水的玉米苗也是這片土地上人與自然界存在著矛盾的真實(shí)寫(xiě)照。從空間上來(lái)看,小說(shuō)的故事情節(jié) “昨天”和“今天”發(fā)生在同一地理場(chǎng)所,即玉米地。在這片土地上,“昨天”的情景是“牛群啃玉米,松鼠吃谷粒,父親因私利而殺害無(wú)害的母蛇”。“今天”的情景是“公蛇被拯救,父親被感動(dòng),人性的光芒煥發(fā)四射”。在這片土地上,過(guò)去存在著人與動(dòng)物相對(duì)立的情景,但在今天,隨著人性的回歸,人類打破與自然二元對(duì)立的藩籬并達(dá)到與自然界其他生物和諧共處的狀態(tài)。
小說(shuō)敘事的心理空間是通過(guò)主人公“我”的心理活動(dòng)所建構(gòu)的。“心理空間一般指抽象的精神空間,在敘事作品中以人物的心理活動(dòng)描寫(xiě)呈現(xiàn)。”(趙晨霞,2016:26)小說(shuō)《愛(ài)》塑造的心理空間通過(guò)故事的敘述者即主人公“我”的心理活動(dòng)呈現(xiàn)出來(lái)。“我”作為一個(gè)孩童,對(duì)父親無(wú)故殘害動(dòng)物這一行為的思考體現(xiàn)了主人公對(duì)人性的反思。當(dāng)“我”察覺(jué)母蛇被獵狗咬住但并沒(méi)有攻擊獵狗的意圖時(shí),“我”在想“它(蛇)為什么會(huì)爬到這黑土地上來(lái)”。“我”的心理活動(dòng)表征出“我”對(duì)懷孕的母蛇即將被殺死的命運(yùn)的無(wú)奈和惋惜。之后,“我”又將蛇為保護(hù)自己的孩子的行為同女性分娩時(shí)的痛苦聯(lián)系起來(lái),想到她們?yōu)榱苏群⒆訉⒃鯓咏吡範(fàn)帯P睦砜臻g是人的內(nèi)心對(duì)外部世界的投射,動(dòng)物的行為激起了主人公對(duì)人性的共鳴,動(dòng)物界的母愛(ài)同人類的母愛(ài)一樣偉大。作者把蛇與人進(jìn)行類比,表明人類與動(dòng)物同為地球上的生靈,他們是平等互通的,表達(dá)了作者“人與自然是命運(yùn)共同體”的生態(tài)觀。
小說(shuō)中作者塑造的物理空間和心理空間都具有深刻的內(nèi)涵意義。小說(shuō)敘事的物理空間“玉米地”不僅是地域上的指稱,它還象征著作者對(duì)重建人與自然和諧關(guān)系的希冀。小說(shuō)的心理空間在表征作者對(duì)人性思考的同時(shí),也暗含了作者“人與自然命運(yùn)共同體”的生態(tài)觀。
四、結(jié)論
小說(shuō)《愛(ài)》中作者對(duì)敘事策略的精心安排,不僅在形式上增強(qiáng)了小說(shuō)的藝術(shù)審美特征,而且在主題上有助于表達(dá)小說(shuō)的思想意蘊(yùn)。小說(shuō)中第一人稱內(nèi)聚焦體驗(yàn)性視角的運(yùn)用、動(dòng)態(tài)變化的敘事距離安排和富有象征含義的敘事空間,不僅給讀者在閱讀過(guò)程中帶來(lái)戲劇性審美體驗(yàn),而且表達(dá)了作者對(duì)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的否定,對(duì)重建人與自然和諧關(guān)系的希望和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生態(tài)理念。總而言之,通過(guò)探討斯圖亞特短篇小說(shuō)《愛(ài)》中的敘事策略,可以發(fā)現(xiàn)小說(shuō)不僅描繪了兩條蛇之間的愛(ài)情故事,作者更試圖通過(guò)動(dòng)物間的愛(ài)來(lái)喚醒人與自然間的愛(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