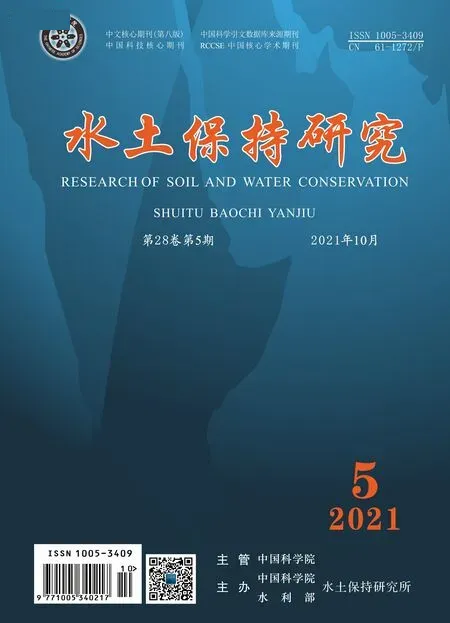城鎮空間擴張與景觀生態風險的耦合關聯
——以江西省袁州區為例
王杰云, 羅志軍, 齊 松
(1.江西農業大學 國土資源與環境學院, 南昌330045; 2.江西省鄱陽湖流域農業資源與生態重點實驗室, 南昌 330045)
城鎮化會對國家經濟、社會結構和生產、生活方式造成深刻變革,涉及城鄉結構調整、產業發展轉型、基礎設施建設、環境資源支撐等諸多方面[1]。近年來國家大力推行新型城鎮化建設,追求區域協調發展,提高城鎮發展質量,以實現區域統籌協調、產業升級轉型、生態文明高效、體制改革創新為重點的嶄新城鎮化過程[2]。城鎮化主要地理表現形式是空間擴張,城鎮空間擴張造成自然生態環境的損失破壞,區域生態安全將受到嚴重威脅[3-5]。生態風險是指受到外界脅迫作用下,某種群、生態系統或景觀的正常功能受到干擾或毀損,從而造成系統健康、生產力、遺傳能力、經濟和美學價值降低的一種狀況[6]。生態風險上升主要體現在大量生態資源被侵占,生態系統失衡等方面,例如森林斑塊消失、破碎化嚴重,水資源稀缺,生物多樣性退化等[7-8],而城鎮空間擴張是導致發生的關鍵因素之一。因此深入探索城鎮擴張與景觀生態風險之間復雜而緊密的聯系,對于科學理解城鎮擴張與生態風險耦合內涵,實現區域可持續發展意義深遠[9-11]。
城鎮化與生態環境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耦合聯系[12],大量學者從不同角度和方法對此進行廣泛而深入的探討。從城市發展的角度出發,城市擴張模式對生態環境造成的擠占影響因城鎮規模及其增長率的不同有所差異[13]。劃定城市增長邊界過程中,研究者們通常都會考慮生態環境效應,或通過識別生態風險空間、評估生境質量進行生態適宜性評價[14-15],或選擇生態阻力因子作為剛性約束條件與城鎮擴張模擬耦合[16-18],最終得到顧及生態安全的綜合城鎮增長邊界。從景觀生態學角度出發,以生態保護優先,通過構建綜合生態安全格局,識別生態安全與城鎮建設沖突區域,實現生態保護與城鎮擴張協調發展[19-20]。基于景觀格局的生態風險分析方面,許多研究者目光聚焦在流域環境上[21-24],研究地方區市景觀生態風險總體相對較少[25-26]。但也有研究者們開始定量的探索城鎮化與生態風險的內部關聯關系,通過選取景觀格局指數構建景觀生態風險模型,然后采用空間分析方法研究區域內景觀生態風險時空分異,最后將城鎮化水平與生態風險進行線性回歸擬合[27-28]。以上研究對城鎮化和生態環境及其之間的耦合聯系做出了初步探索。在相關研究基礎之上[29-31],本研究首先以城鎮擴張強度指數來表征袁州區2000—2018年城鎮擴張時空特征變化,然后利用景觀格局指數構建景觀生態風險模型,再以地統計方法分析生態風險空間異質結構并通過插值得到袁州區景觀生態風險等級時空分布可視化圖,最后通過構建GWR模型,探索城鎮擴張與景觀生態風險耦合聯系。
1 研究區與數據來源
1.1 研究區概況
袁州區位于江西省宜春市西南部,處于113°54′—114°37′E,27°33′—28°05′N,東西跨度約68 km,南北跨度長約58 km,土地總面積2 541.90 km2。袁州區自然資源十分豐富,林地面積所占比例最大,植物物種多種多樣,森林覆蓋率達62.7%,轄內明月山被列為國家森林公園。區內地貌以丘陵、山地為主,東部和袁河兩岸分布部分平原地帶。氣候條件優越,屬中亞熱帶季風性濕潤氣候,降水充沛,熱量豐富。袁州區轄區內含17個鎮,3個鄉,8個街道。人口總數為107.92萬人,其中包含城鎮人口62.44萬,農村人口45.48萬。2000年以來,袁州區處于經濟發展快速時期,2018年全區生產總值達300.78億,增長率7%。城市和鄉鎮用地面積猛增,2000年城鎮用地面積39 km2,2018年城鎮建設用地面積達到103.48 km2,增長64.48 km2,用地面積大幅上升。隨著經濟發展,人口快速增長和新型城鎮化的加速推進,未來城鎮建設用地面積將持續擴張,袁州區需要同時兼顧城鎮發展、生態保護和經濟增長等多方面因素,走生產、生態、生活協調發展道路。
1.2 數據來源
本研究從美國地質調查局USGS官網上(https:∥www.usgs.gov/)獲取Landsat TM/ETM+/OLI衛星影像數據,選取2000年、2010年和2018年成像時間在6—9月且平均含云量低于10%的影像,各期影像空間分辨率均為30 m。結合袁州區當地地類實際情形,將土地利用類型分為耕地、林地、水域、建設用地和未利用地5類。在ENVI 5.1軟件中對影像進行大氣校正、幾何糾正、影像增強、影像鑲嵌與裁剪等預處理,采用監督分類法與人機交互結合方法進行解譯判讀,最終利用混淆矩陣和Kappa系數對分類結果進行精度檢驗,總體分類精度均超過85%,解譯結果精度較好,滿足相關研究分析的需要。此外水系數據和路網數據通過OpenStreetMap官方網站(https:∥www.openstreetmap.org/)獲取。
2 研究方法
2.1 城鎮擴張強度系數
城鎮擴張強度系數是城鎮擴展數量特征研究的常用指標,用以表征城鎮擴張程度和速度。城鎮擴張強度指數是指城鎮用地空間在研究期內其拓展面積占區域土地總面積的百分比[32]。結合相關研究成果[33],以袁州區中心城區、圩鎮中心、工業園區等建成區作為城鎮用地空間,研究袁州區城鎮擴張的時間和空間變化特征,其公式見式(1)。
(1)
式中:I表示城鎮擴張強度系數;Sk表示第k年城鎮建設用地面積;Sk-Δt表示距第k年時間間隔Δt年份的建設用地面積;S表示研究區域內總面積。
2.2 景觀生態風險模型
2.2.1 景觀生態風險小區劃分 綜合考慮景觀類型的種類、斑塊平均面積和研究區總面積等因素,將研究區劃分為3 km×3 km的等間距單元網格,以每個網格作為研究樣本區,共得到349個景觀生態風險小區。通過公式計算研究樣本區內各地類景觀格局指數并得到景觀生態風險值,以此值表示研究區景觀生態風險水平。
2.2.2 景觀生態風險指數 景觀損失度反映在自然和人為干擾作用下,不同景觀類型自然屬性損失的相對大小,可以用來定量衡量景觀生態風險水平。通過計算各景觀組分面積比重,同時引入景觀損失度來描述各研究樣本區的景觀生態風險指數ERI,從而構建景觀生態風險模型。模型公式見式(2)。
(2)
式中:ERI表示第k個風險小區景觀生態風險指數;N為表示景觀類型種類;Ri表示景觀類型i的損失度指數;Aki表示第k個風險小區i類景觀組分的面積;Ak表示第k個風險小區的總面積。
模型中景觀損失度Ri由景觀脆弱度Si和景觀干擾度Ui進行積運算所得。其中景觀脆弱度Si基于MATLAB平臺,采用層次分析法得出,AHP權重結果如下:建設用地權重0.061 8,林地權重0.093,耕地權重0.159 9,水域權重0.262 5,未利用地權重0.418 5。景觀干擾度Ui由景觀破碎度Ci、景觀分離度Fi、景觀優勢度Di進行加權累加所得,相應權重通過專家咨詢法,分別賦予景觀破碎度權重0.5,分離度權重0.3,優勢度權重0.2。相應計算景觀格局指數的公式及生態含義見表1。

表1 景觀格局指數計算方法及其生態含義
2.3 地統計分析
景觀生態風險指數作為區域化變量,其空間異質性可以通過地統計學來分析。本研究通過構建半變異函數模型對區域化變量的空間變異結構進行研究,半變異函數公式見式(3)。

(3)
式中:γ(h)為半變異函數h表示步長,即配對樣本之間的空間距離;Z(xi)和Z(xi+h)表示在位置x和xi+h處的景觀生態風險指數的觀測值;N(h)為間隔距離為h的樣本總配對數。
半變異函數模型常用來研究變量空間變異結構,探索其空間相關性與空間異質性的規律,其參數主要包含塊金值(Nugget),基臺值(Sill)和變程(Range)。塊金值(Nugget)指當配對樣本空間間隔h=0時,半變異函數值卻不等于0,這種由于測量誤差及空間變異導致的隨機性的發生就表現為塊金值。隨著空間距離h逐漸增大,半變異函數值γ(h)達到相對穩定的常數時,此時這個穩定常數值即為基臺值(Sill)。從塊金值到基臺值之間的空間距離變化大小即為變程(Range),它體現配對樣本觀測值之間空間相關性的變化范圍。此外,塊金值和基臺值之比,多用來表示系統變量之間的空間相關程度[26]。它表示由隨機因素造成的空間異質性比例大小,其值越小,則觀測值之間空間自相關性造成的空間變異占比越大。
為實現可視化形式直觀地表現景觀生態風險指數的空間分布,本研究以普通克里金插值方法對袁州區景觀生態小區的景觀生態風險指數進行插值,從而獲得全區景觀生態風險等級空間分布圖。
2.4 地理加權回歸模型
地理加權回歸模型(GWR)在傳統最小二乘回歸模型(OLS)基礎上進行擴展,將變量的地理位置嵌入到回歸參數中,利用局部加權最小二乘方法進行逐點參數估計[34]。GWR充分考慮到空間變量的局部特性,解決變量關系隨著地理位置的改變產生的空間非平穩性問題,體現了變量的空間異質性。其模型公式見式4。
(i=1,2,…,n)
(4)
式中:yi為因變量,(ui,vi)為采樣點i的坐標;β0(ui,vi)為截距項;βk(ui,vi)為i點上第k個回歸系數,是與地理位置相關的函數;p為解釋變量個數;xik為解釋變量xk在i點的值;εi表示隨機干擾項。
地理加權回歸模型核心是構建空間權重矩陣,本研究選取高斯函數作為距離衰減函數,計算空間權重值。高斯函數公式見式5。
Wij=exp[-(dij/b)2]
(5)
式中:dij為樣本點i,j之間的距離;b為帶寬,是描述權重與距離之間函數關系的非負衰減參數,帶寬越大,權重隨距離的增加衰減的越慢,帶寬越小,權重隨距離的增加衰減越快[32]。研究采用最小信息準則(AIC)方法評價模型擬合優良性,計算最適宜帶寬。
3 結果與分析
3.1 袁州區城鎮擴張特征分析
從2000年以來,袁州區城鎮用地面積總體保持增長、2000—2010年擴張面積28.28 km2、擴張強度系數0.11%。2010—2018年擴張面積達到36.20 km2、年均擴張速率達4.53 km2/a、增幅較快。從2000—2018年整個發展周期來看、袁州區一直處于發展增長期、2000年城鎮用地面積為39 km2、2010年為67.28 km2、2018年達103.48 km2、城鎮用地面積是2000年的2.65倍、城鎮擴張強度指數為0.14%、總體而言、袁州區新時期城鎮化發展迅猛,發展速度大幅提升,處于城鎮化發展快速期。不同時期城鎮建設用地擴張面積見表2。

表2 袁州區不同時期城鎮建設用地擴張情況
從2000—2018年、城鎮建設用地擴張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區、金園街道、下浦街道三處、呈現較為明顯的往北和東西方擴張的倒“T”形擴張形狀。袁州區城區作為區域發展中心、建設用地需求強烈、呈現急速向外擴張的趨勢。往北擴張、金園街道從2000年以來建設用地擴張十分明顯,由于緊靠中心城區北部,區位條件優越,同時擁有便捷的交通,與三陽鎮、柏木鄉形成向北發展廊道,與萬載縣連通。往東西方向擴張,滬昆高速從東向西連接新余市、袁州區、萍鄉市。沿線下浦街道、彬江鎮通過滬昆高速與分宜縣,新余市相通,湖田鄉、西村鎮沿滬昆高速與萍鄉市相連,滬昆高速為袁州區城鎮擴張提供了良好的交通條件,沿線地區城鎮建設擴張面積顯著高于全區其他地方。同時袁河自西向東從西村鎮流向彬江鎮,沿途經過中心城區,為城鎮發展提供良好的水資源條件。由此袁州區形成了東西方向沿滬昆高速、袁河發展,往北沿萬宜公路發展的倒“T”形城鎮擴張發展格局。
此外,西北方向慈化鎮城鎮擴張現象較為突出,這主要是因為慈化鎮沿交通干線城鎮發展水平較為迅速。新坊鄉位于東南方向,與安福縣連通,近年來隨著工業發展水平上升,城鎮用地面積增長較大。溫湯鎮因為明月山國家級森林公園坐落于鎮西南角,隨著地方旅游業的蓬勃發展,景區基礎設施不斷加大建設和完善,經濟發展迅速,城鎮用地擴張較為明顯(圖1)。

圖1 袁州區2000-2018年城鎮建設用地時空分布
3.2 景觀生態風險時空變化分析
3.2.1 景觀格局指數分析 由表3得出,從2000—2018年以來、林地作為袁州區優勢度最高的景觀類型面積一直在減少,從2000年的1 949.803 2 km2減少到2018年的1 321.515 km2,景觀優勢度也從0.671 5下降為0.565 4。林地破壞問題嚴重很大部分原因是城鎮化和人口快速增長導致的,通過毀林建房,毀林耕種等手段,造成林地景觀破碎度顯著增加,斑塊數上升,破碎化明顯加重。景觀分離度從0.093 6增加到0.160 4,景觀損失度也由此增大。袁州區水域面積較小,景觀優勢度較低,從2010—2018年、受退耕還湖,保護濕地等政策影響,面積稍有增加,景觀破碎度和分離度也有所下降,由于其特殊景觀生態地位,景觀脆弱度指數較高,景觀損失度稍有下降,從0.260 1下降為0.235 6。受農業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影響,耕地面積出現大幅上漲,耕地面積從2000年的314.002 8 km2增加到2018年859.016 7 km2,景觀優勢度也達到0.490 4。耕地景觀破碎度和分離度都明顯減小,干擾度從0.375下降到0.244 6,景觀類型表現更為集聚,景觀損失度也較低。從2000—2018年、城鎮用地面積大幅增加,景觀分離度從0.825 2減小到0.428 2,破碎度從0.041 8減小到0.029 9,干擾度減小,表現出連續和聚集形態。其他建設用地景觀優勢度有所上升、2010—2018年景觀損失度下降明顯。未利用地在2000—2010年面積大幅減少,從80.481 6 km2減少到20.997 3 km2,這段時間主要由于袁州區城鎮化發展初期呈現無序狀態,對荒草地、沙地等潛力資源開發較為嚴重。未利用地景觀破碎度下降較大,斑塊數從9 956個減少到772個,此外未利用地由于受到人為干擾影響最大,景觀脆弱度指數也最高。

表3 袁州區2000-2018年景觀格局指數
3.2.2 景觀生態風險時空分布 通過ArcGIS 10.2中地統計分析工具對景觀生態風險指數進行探索性數據分析,然后以普通克里金插值方法對景觀生態風險指數進行插值,通過計算半變異函數并構建經驗模型,研究發現3個時期指數模型擬合結果較好,相關參數見表4。
由表4可以得出:(1) 2000年、2010年和2018年半變異函數模型塊金值都接近于0,表明由隨機因素造成的空間異質性作用較小;(2) 變程從2000年14 984 m增加到2018年17 564 m,說明空間相關性導致的空間異質性作用范圍變長,主要是由于各種景觀類型相互轉化造成的。同時發現基臺值逐漸減小,說明生態風險空間變異隨著時間的推移有所減小;(3) 通過對比3個年份的塊金/基臺值,隨機因素引起的空間變異均遠小于空間自相關引起的。同時發現2000年的塊金/基臺值>25%,表明該時期空間變異由隨機因素影響較為顯著。2010年、2018年塊金/基臺值均小于25%,表明此時空間異質特點主要取決于自身空間相關程度。總體來看、從2000—2018年、塊金值/基臺值呈現先減小后稍有增加的趨勢。這主要是因為2000年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相對較慢,生態風險空間變異由自然隨機因素引起的比重較大,2010年時期處于社會經濟發展高漲期,空間變異結構主要由于自身相關性引起。近年來,國家政府十分注重保護生態環境,受此影響自然隨機變異所占比重稍有增加。

表4 景觀生態風險指數半變異函數及其參數
通過對349個景觀風險小區的景觀風險指數進行克里金插值,得到2000年、2010年、2018年景觀生態風險空間分布。為便于直觀展示和比較生態風險變化情況,結合自然斷點法分布區間,以自定義間隔將其劃分為5個風險等級:Ⅰ級低生態風險區(ERI<0.032),Ⅱ級較低生態風險區(0.032≤ERI<0.046),Ⅲ級中等生態風險區(0.046≤ERI<0.060),Ⅳ級較高生態風險區(0.060≤ERI<0.074),Ⅴ級高生態風險區(≥0.074)。袁州區不同時期景觀生態風險等級分布見圖2。
由圖2看出,2000年高和較高生態風險區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區、金園街道、下浦街道、湖田鄉、西村鎮和飛劍潭水庫等處,中心城區和周圍街道景觀生態風險較高主要由于該時期內,城鎮化發展處于相對無序狀態,城區和城郊劃出大量的未利用土地,景觀脆弱度高,同時受到人類干擾因素強,生態風險等級因此也最高。西村鎮、湖田鄉和彬江鎮由于袁河的流經,飛劍潭鄉存在飛劍潭水庫,均由于水域的景觀脆弱度較高,受自然和人為干擾因素影響大,生態風險指數因此也較高。低生態風險區主要存在于南邊和西北方鄉鎮,如溫湯鎮,洪江鄉、慈化鎮、楠木鄉等,溫湯鎮因為林地覆蓋率高,植被成片,景觀類型規整,同時鎮域內坐落著明月山國家風景旅游區,注重生態保護,因此生態風險等級也最低。

圖2 袁州區2000-2018年景觀生態風險等級分布
2010年以后袁州區城市發展重心往金園街道方向靠攏,與2000年相比較,高生態風險區往金園街道方向發展,同時湖田鄉,彬江鎮也在城鎮化進程中生態風險等級升高,這兩處鄉鎮生態風險高的原因與2000年中心城區相同,均是由于城鎮化快速發展初期的相對無序擴張,同時城鎮周郊存在較大面積的未利用地,為后期發展提供資源。飛劍潭鄉由于水庫的影響生態風險依然很高。對比2000年,袁河流經的鄉鎮如西村鎮、湖田鄉、彬江鎮生態風險等級有很大部分由較高生態風險區轉化為中等生態風險區,這體現了當地保護河流生態的意識在提高。低和較低生態風險區在西北邊和南方范圍有所擴大,主要體現在楠木鄉、天臺鎮、洪塘鎮等地。
與2010年相比,2018年高和較高生態風險區主要分布在金園街道和湖田鄉,高風險區范圍顯著減小,飛劍潭水庫景觀生態風險等級也下降為較高生態風險區。中心城區由于城市化發展達到末期,城市建設用地集中連片,斑塊完整,景觀類型十分穩定,因此部分地區下降為較低生態風險區,大部分地區降低為中等生態風險區。同時袁河流經鄉鎮如彬江鎮、下浦街道生態風險等級也由較高風險降為中等風險。低生態風險區范圍進一步擴大,變化較為明顯地區分布在新坊鄉、洪塘鎮、水江鄉和天臺鎮。同時對不同時期景觀生態風險等級分布進行面積和比例統計,得到面積和比例見表5。
結合圖2和表5,從2000—2018年以來,袁州區高和較高生態風險區范圍出現較大幅度減小,低生態風險區面積分布逐漸擴大。高風險和較高風險區所占比例逐漸下降,占比從2000年的20.53%下降為2018年的4.17%,較高生態風險區面積從407.61 km2減小到61.21 km2,面積減少尤為顯著。中等生態風險區面積也出現顯著減小,面積從606.21 km2減小為264.8 km2。低生態風險區面積出現明顯擴大分布,面積從614.5 km2增長到1 237.9 km2,所占比例也增加到48.7%。

表5 袁州區景觀生態風險等級面積及比例統計
得出總體結論:2000—2018年以來,袁州區中等及以上生態風險級別分布范圍均顯著減小,低生態風險區范圍明顯增大,景觀生態風險呈逐漸下降趨勢。其中原因主要是城鎮化和人口增長造成建設用地擴張顯著,耕地面積增加較大,景觀斑塊更加完整,損失度減小,景觀生態風險度降低,同時近年來袁州區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既注重保護生態環境,又要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因此景觀生態風險整體呈下降趨勢。
3.3 城鎮擴張與景觀生態風險耦合關系
3.3.1 城鎮建設用地面積與生態風險指數耦合分析 研究以生態風險指數為因變量,城鎮建設用地面積為解釋變量,通過進行地理加權回歸(GWR)分析,探索兩者之間的耦合聯系。在ArcGIS 10.2中通過GWR工具建立回歸模型,模型以高斯函數為內核作為距離權重衰減函數,采用AICc值評價模型優良度,尋找最佳帶寬。對比發現選擇Adaptive核類型具有較好的擬合優度,其通過選定最近鄰點個數來表示帶寬變化,相應模型參數見表6。
表6中,帶寬大小通過最近鄰點個數(Neighbors)來表示,由于研究區樣本均勻分布,點個數越多,函數擬合相對更為平滑,空間權重隨距離衰減更為平緩。R2表示模型擬合優度,其值范圍在[0,1],值越大擬合越好,2000年模型擬合精度相對較好,其他兩個時期擬合結果相對較差。由GWR標準化殘差分布圖(圖3)可以得出,各景觀風險小區97%以上局部回歸模型標準化殘差落在[-2.5,2.5]區間內,模型總體構建較好。

表6 地理加權回歸模型檢驗參數

圖3 地理加權回歸(GWR)模型標準化殘差空間分布
由回歸系數分布圖所示(圖4),總體來看,3個時期城鎮用地面積與景觀生態風險指數呈正相關關系,但是從2000—2018年回歸系數逐漸減小說明這種正向影響關系正在逐漸減弱。隨著城鎮化發展不斷推進,城鎮建設用地面積不斷擴張,導致城鎮中心斑塊集中成片,景觀破碎度和分離度不斷下降,同時由于城鎮用地狀態相對穩定,脆弱度指數較低,因此景觀生態風險指數上升幅度也較小。3個時期中心城區的回歸系數與同期其他地區相比都較低,主要是由于中心城區城鎮化程度較高,城鎮用地面積增長對生態風險指數的影響幅度較小,生態結構穩定性較高。但是總體而言隨著城鎮化進程向前推進,袁州區景觀生態風險一直在增加,給當地的生態環境造成了不小壓力。

圖4 城鎮用地面積與生態風險指數回歸系數分布
3.3.2 城鎮擴張指數與生態風險變化指數耦合分析研究同時以2000—2018年的景觀生態風險指數變化率作為因變量,城鎮擴張強度指數作為解釋變量,進行地理加權回歸(GWR)建模,相應模型參數設置和模型檢驗方法同上。
由表7可得,2000—2010年的R2值為0.692 6,擬合優度相對較好,其他兩個時間跨度擬合結果相對較一般。GWR標準化殘差超過95%的采樣區標準化殘差值在[-2.5,2.5],總體來看模型構建較好。同時對每個研究單元回歸系數進行可視化表達,GWR回歸系數空間分布圖見圖5。

表7 地理加權回歸模型檢驗參數
由圖5可得,2000—2010年、城鎮擴張強度指數與景觀生態風險變化率兩者回歸系數總體有正有負、正值集中于中心城區附近、表明城鎮擴張強度增加會導致生態風險指數變化率上升、造成生態壓力加大。負值主要分布于飛劍潭和天臺等西部鄉鎮、這些地區城鎮化程度相對來說較低、發展較慢、城鎮擴張強度增加、生態風險變化率減小、但結合圖4生態風險依然處于增長趨勢。2010—2018年、總體來看在大部分區域內城鎮擴張強度指數和生態風險指數變化率仍是正相關關系、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區往金園街道方向、但在天臺、竹亭和遼市等鄉鎮仍處于負相關區域。整體2000—2018年、中心城區、下浦街道和金園街道等地區城鎮擴張強度指數與景觀生態風險變化率之間表現為正向關系,城鎮化強度增加導致景觀生態風險變化加劇,生態壓力也逐漸增加。負值區域分布在溫湯、新坊和洪江等鄉鎮,這些地區植被覆蓋范圍較為廣泛,生態風險變化幅度因此較小。

圖5 城鎮擴張指數與生態風險變化率回歸系數分布
4 結 論
(1) 2000—2018年、袁州區城鎮擴張面積達到64.48 km2、擴張強度系數為0.14%、城鎮用地面積是2000年的2.65倍。城鎮擴張空間分布呈現東西方向沿滬昆高速、袁河發展、往北沿萬宜公路發展的倒“T”形發展格局、同時西北方慈化鎮、西南方溫湯鎮、東南方新坊鄉擴張也較為明顯。
(2)從2000—2018年景觀格局指數分析中得出、林地作為袁州區優勢度最大的景觀類型正在逐漸喪失優勢、受人口增長和城鎮化等影響耕地和建設用地面積增長十分顯著。未利用地和水域景觀脆弱度較高,同時受外界干擾因素影響大,因此未利用地和水域景觀損失度也很高。
(3) 對景觀生態風險半變異函數構建模型并分析參數得出結論,袁州區2000年、2010年、2018年景觀生態風險指數存在較強的空間自相關性,隨機因素造成的空間異質作用較小。同時由景觀生態風險等級分布圖和統計表、2000—2018年期間,袁州區中等及以上生態風險級別分布范圍均顯著減小,低生態風險區范圍明顯增大,其原因主要是城鎮化和人口增長導致的建設用地和耕地擴張,景觀斑塊更加完整,損失度減小,景觀生態風險度降低。同時由于近年積極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和打造“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體,生態環境得到改善生態風險因此降低。
(4) 通過構建GWR模型,分析得出2000—2018年袁州區城鎮建設用地與景觀生態風險總體呈正相關關系,且隨時間推移回歸系數在逐漸減小。中心城區的回歸系數與同期其他地區相比都較低,主要是由于中心城區城鎮化程度較高,生態穩定性更高。城鎮擴張強度系數與景觀生態風險變化率相關關系有正有負,中心城區、下浦街道和金園街道等地區城鎮擴張強度指數與景觀生態風險變化率之間表現為正相關,城鎮化強度增加導致景觀生態風險變化加劇。負值區域主要分布在溫湯、新坊和洪江等鄉鎮,這些地區植被覆蓋范圍較為廣泛,生態風險變化幅度因此較小。
研究通過對袁州區2000—2018年城鎮擴張和景觀生態風險進行分析,然后探尋兩者之間耦合關系并得出相應結論,但研究也存在諸多不足之處。構建景觀生態風險指數模型過程中,僅僅從土地利用的角度考慮了各景觀類型的面積權重,沒有考慮其他生態因子如地形、降水、土壤類型等影響,因此景觀生態風險指數缺乏一定的生態涵義。此外深入探討城鎮擴張與景觀生態風險之間耦合關系時,并未將GWR與其他回歸模型進行對比[35],因此模型最優性值得商榷,需進一步完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