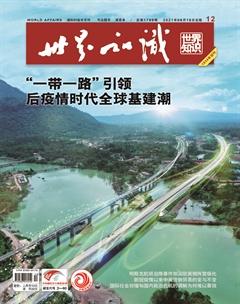美國的制衡阻擋不了“一帶一路”前進方向
趙明昊
“一帶一路”合作前景光明,但也面臨不容忽視的阻力,一些西方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負面認知根深蒂固,尤其是近年來美國全面加大對華戰略競爭,給“一帶一路”合作帶來壓力。拜登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特朗普時期的對華政策,明確將中國視為“最嚴峻的競爭者”,強調戰略競爭是美中關系的“本質”。今年3月,拜登在與英國首相約翰遜通電話時特別提出,為應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挑戰,應考慮提出由“民主國家”牽頭的類似倡議,“幫助世界各地需要幫助的群體”。這一表態意味著,在拜登政府力圖與中國展開“長期性、戰略性競爭”的背景下,美國對“一帶一路”的制衡將會進入新的階段。
美國對“一帶一路”的負面認知
隨著美國對華戰略發生以“大國競爭”為導向的范式轉變,與“一帶一路”相關的全球基礎設施建設已成為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焦點領域之一。
“一帶一路”倡議成為美國對華認知“威脅膨脹”(threat inflation)現象的重要推動因素。美方一些人刻意夸大“一帶一路”的安全和戰略性影響,誣稱中國欲借“一帶一路”對歐亞大陸進行控制并謀求“全球霸權”。前總統特朗普本人曾在私下場合稱,“一帶一路”倡議“可能擾亂全球貿易并具有冒犯性”。蓬佩奧等特朗普政府高官施壓巴基斯坦、巴拿馬、以色列等國警惕使用來自中國的投資,減少與中國的經濟合作。
美國軍方領導人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認知頗為消極。美軍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維德森妄稱,中國通過“一帶一路”想要“塑造一個與它自己的威權模式相符合的世界,并破壞國際規范,比如商業和信息的自由流動。” 美軍非洲司令部司令托馬斯·沃德豪森、南方司令部司令庫爾特·蒂德等也公開質疑“一帶一路”向非洲和拉美地區的擴展。
美國國會議員也在炒作“一帶一路”問題,并要求美國政府加大對中國的抗衡。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參議院金融委員會等多個國會內設機構,以及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多次針對“一帶一路”倡議舉行聽證會。共和黨籍參議員托德·揚(Todd Young)等人對“一帶一路”進行無理指責,大肆渲染所謂中國的“掠奪性經濟活動”,以及對美國經濟、安全、外交利益的威脅。2018年8月,16名聯邦參議員聯名致信時任財政部長姆努欽和國務卿蓬佩奧稱,“一帶一路”倡議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在經濟上最終由中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美國必須對此加以抗衡。
除了美國政府行政部門和立法部門,美國智庫和戰略界人士對“一帶一路”的關注也在不斷上升。美國國內主要智庫紛紛設立專門研究項目,對“一帶一路”的相關進展和信息加以跟蹤研判。如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設立“連接亞洲”項目,全國亞洲研究局(NBR)設立“新絲路經濟走廊”項目等。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就“一帶一路”撰寫專題報告,深入分析其經濟、政治和外交影響。蘭德公司則圍繞“一帶一路”如何影響中國與中亞國家關系以及中國在中東地區的角色變化等問題發布研究成果。
總體看,美國戰略界人士對“一帶一路”的看法較為負面。他們認為,“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的“馬歇爾計劃”,中國意欲借此將經濟實力轉化為地緣政治影響力,建立和鞏固自身對歐亞大陸的控制,并在國際秩序方面“另起爐灶”,推動中國版本的“全球化”。美國戰略界對“一帶一路”的關切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更加注重研判“一帶一路”建設的軍事安全影響;二是更為關注“數字絲綢之路”以及所謂“數字威權主義”問題;三是誣稱中國通過制造“債務陷阱”等方式加大對沿線國家的控制;四是憂心中國企業和金融機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不合規經營和腐敗行為對美國的利益造成損害;五是擔心中國借“一帶一路”倡議推動人民幣和中國技術標準的國際化。
當然,也有一些美國前政要和專家主張,不要過度夸大“一帶一路”的“威脅”,美國不必以對抗性方式應對“一帶一路”。比如,前助理國務卿謝淑麗等人建議美國政府全面審視中國的全球治理政策,對中國提出的倡議要進行深入研究而不是動輒拒絕,要考慮美國的利益,也要考慮這些倡議在提供國際公共產品方面的積極作用。前美國貿易談判代表巴爾舍夫斯基和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史蒂芬·哈德利稱,美國需要重視中美圍繞全球基礎設施建設的競爭,但當中國企業承擔的相關項目符合透明度、可持續、韌性、財政責任和社會責任方面的標準,就應受到歡迎。
美國的實際制衡及拜登政府動向
為了應對“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挑戰”,美國政府除了言辭抹黑之外,還采取若干政策舉措,力圖對“一帶一路”合作進行干擾和阻礙,實施“成本強加”,將對沖“一帶一路”作為美國對華戰略競爭大棋局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的對華博弈日益彰顯全面性、跨域性和全球性等特征,試圖將對華經濟圍堵、技術封控、軍事安全遏制與意識形態打壓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這在“一帶一路”問題上得到集中體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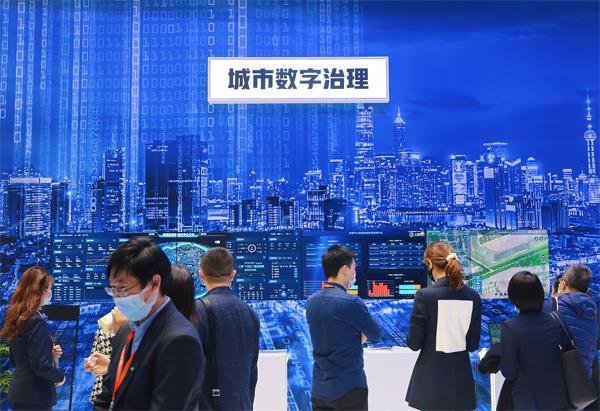
2021年4月15日,由商務部、科技部、國家知識產權局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第八屆中國國際技術進出口交易會在上海世博展覽館開幕。
首先,不斷充實、細化“印太戰略”,從經濟、安全、民主治理等方面推出若干政策舉措,將“印太戰略”打造為制衡“一帶一路”倡議的主要平臺。特朗普政府提出要構建“自由而開放的印太”,維護“基于規則的印太秩序”,推動“負責任的互聯互通”,支持符合透明、法治、環保等原則的“高質量基礎設施建設”。在經濟上,美國聚焦數字經濟和網絡安全、能源和基礎設施發展這三大領域,試圖深化與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等國的協作,為印太國家提供更多低息貸款,用于發電站、道路、橋梁、港口等基礎設施的建設。美日印三國還成立“印太基礎設施三邊論壇”等機制,旨在充分挑動私營企業和資本的力量,與中國展開競爭。
其次,重視“一帶一路”倡議在歐洲地區的擴展,欲聯手歐盟等力量共同對中國實施制衡。“一帶一路”倡議的主要目標是,將活躍的東亞經濟圈與發達的歐洲經濟圈更加緊密地聯系起來,歐洲在“一帶一路”合作格局中占據著特殊重要地位,尤其是希臘、捷克、匈牙利等南歐和中東歐地區國家對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較為積極。在此背景下,蓬佩奧等特朗普政府高官極力阻撓中歐開展“一帶一路”合作,包括要求意大利政府不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合作文件。此外,美國還通過支持波蘭、克羅地亞等國發起的“三海倡議”(波羅的海、黑海和亞得里亞海)等,對“一帶一路”倡議以及“17+1合作機制”進行反制,2020年2月,特朗普政府宣布為“三海倡議”提供10億美元的資金支持。
第三,將國際發展領域視為大國競爭的“角力場”,通過組建美國國際發展金融公司(USIDFC)、推動“藍點網絡計劃”等對中國進行反制。一方面,試圖通過多邊援助審查,加強對世界銀行等現有國際發展機構的控制,阻撓國際組織參與“一帶一路”合作。另一方面,根據《善用投資促進發展法案》(BUILD Act),將海外私人投資公司(OPIC)、美國國際開發署發展信貸部等機構重新整合,組建美國國際發展金融公司,為相關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融資等提供針對中國的“替代性選擇”。此外,美國還與日本、澳大利亞合作發起“藍點網絡計劃”,對大型基礎設施項目進行所謂國際認證,用市場化、債務可持續、環境保護等方面的高標準與“一帶一路”項目做出區隔。
第四,將“數字絲綢之路”作為對華制衡的重點領域,借助“清潔網絡計劃”“敏感技術多邊行動”等機制與中國展開“數字地緣競爭”。為了打壓華為公司在5G、海底光纜等領域的國際業務,美國政府推動“清潔網絡計劃”,要求成員國在建設本國數字基礎設施時不使用中國企業提供的設備和技術。再者,通過推動實施“數字互聯互通和網絡安全伙伴關系”“美國—東南亞智慧城市伙伴關系”等,加快構建應對“數字絲綢之路”的“全政府”機制,并完善相關的資源配置,力圖增強美國對發展中國家“數字未來”的塑造能力。此外,美國還推動對華“規則制衡”,以“美日數字貿易協定”“東盟—澳大利亞數字貿易標準倡議”等為基礎,將反對數據本地化、支持企業采取加密技術等條款擴展到美國與其他國家商簽的貿易協議中,進而影響國際數字貿易規則。

2020年10月25日,巴基斯坦拉合爾軌道交通橙線地鐵開通運營,這是“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巴經濟走廊首個簽約實施的大型軌道交通項目。
拜登政府總體上繼承了特朗普政府針對“一帶一路”倡議構建的政策體系,通過舉辦美日印澳四國峰會、創建關鍵和新興技術工作組等方式升級美國的“印太戰略”,而“數字互聯互通和網絡安全伙伴關系”“藍點網絡計劃”等具體機制也得到延續。4月,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民主黨參議員鮑勃·梅內德斯(Bob Menendez)等人提出的“2021戰略競爭法案”,要求為“數字互聯互通和網絡安全伙伴關系”追加一億美元的資金支持。除了“繼承”,預計拜登政府在如何制衡“一帶一路”倡議方面還會有“創新”,比如更加重視打“環境牌”,將氣候變化問題與“一帶一路”框架下的能源類、交通類項目聯系起來,對中國加大施壓力度。
面對來自美國的壓力,中國需要保持戰略定力。一方面,繼續堅守“一帶一路”促進共同發展、合作發展、共贏發展的初心,針對后疫情時期國際經貿、金融等領域的形勢變化,對“一帶一路”合作進行必要的調整和完善,更加重視落實高質量發展的原則和要求。另一方面,在各國面臨抗疫情、穩經濟、保民生艱巨挑戰的情況下,“一帶一路”合作的重要意義將會進一步彰顯,美國對“一帶一路”的打壓、破壞不得人心。拜登政府如何應對“一帶一路”仍在謀劃之中,中國需主動作為,引導美方客觀理性看待“一帶一路”,盡可能地引導美方抑制競爭和對抗的沖動,不放棄探索中美在國際發展領域的合作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