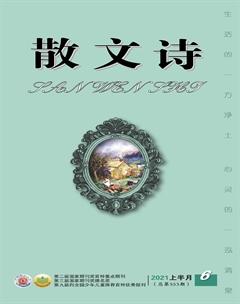經驗感知、命運認領與身體詩學
劉波
當一具殘缺的身體被意志所喚醒,究竟是什么在主導一個人用寫作來完成最終的精神救贖?這在歸馬的文字中似乎可以找到答案。如果說之前在史鐵生的作品中我們看到了作家與殘疾身體博弈的典范,那么,這種典范在其他人那里有沒有可復制性?能不能獲得同樣的效果?也許正是在心志的作用下,歸馬將那些體驗和思索轉化成了具有宗教感的文字,它們是對身體感知世界的一種審美和思想強化,同時也符合行動的邏輯。
歸馬的《單拐關鍵詞》確實很形象,對于早年失去一條腿的她來說,依靠強大的意志戰勝了世俗意義上的身體“失敗”,而那些曾經的受挫與陰霾,都被后來的不屈化成了對生活積極主動的探索。我們可以將其當作勵志典型,然而,勵志背后還是隱藏著歸馬將身體之痛進行轉換的審美沖動。她的文字看似是情緒激蕩的結果,但又不無理性的深度;她在強調修辭之美時,更注重形而上的思想錘煉。她通過文字來編織一張命運之網,滲透其中的哲思性與力量感,既立足于對身體經驗的異質性重構,又從更深層的思考中還原身體所感知到的內在風景,她在將這些風景書寫成內心的“格言”時,其實就暗示了自己所希望達到的美學維度。
歸馬所解析的每一個關鍵詞,都與她殘缺的身體相關,她從不同側面來審視自己失去一條腿之后的生活,而它們又反向呈現為經驗的哲理性升華。“我每天以拐杖的語言叩問世界與生活,叩問道路與遠方。”(《叩問》)失去了一條腿,這種身體之痛演化成了悲劇,而如何穿透現實的悲劇來抵達命運的奇跡,則是她面臨的又一挑戰。“認領厄運,是它把我行走的平仄加大了尺幅。”當抱怨從日常中被漸漸消解掉時,她抗衡生活的姿態是不是變成了無奈的接受?世俗的經驗已經固化了情感認知,但她沒有就此放棄自己,雖然她也知道,“我的平仄中充滿了悲劇色彩,充滿了不確定性。”(《平仄》)為此,她要付出比正常人更多的耐心和精力來應對生活的困擾,她依然選擇迎難而上,“我是一件受難的樂器,殘而不廢且緩緩升華。”(《樂器》)她不是對于殘缺身體的抵制,而是一種擁抱,在對生命的認同中重建了自身的主體性。當失去的那條腿曾經像空氣一樣被懸置時,她確實感到了某種空無,那是恐懼的,不安的,而只有意識到這種空無乃真實處境,她才真正找準了自己的位置,將身體那一部分的虛空用意志的力量填補起來,從而進行了屬性的拓展。
就像歸馬有著極強的抽象歸納能力,她甚至將自己的身體從一種具象化的呈現轉變為抽象的言說,繼而處理成寓言化的表述。在諸多身體與生活的矛盾沖突中,二元對立思維會左右她對問題的看法,這種影響在其文字中也有所反映:她那些富有張力的措辭,更多就是這種思維的外化。因此,身體的較量被并置到哲思范疇時,一種恢復自我主體性的功能就被歸馬自己詢喚出來,它讓其表達變得更為透明,更趨智性。“我的確失去了一部分肉體,但也在同時獲得了一部分虛無的身體。”(《抽象》)這種虛無看起來是抽象的,而對于歸馬來說,則又是切實的,它被置換成了一種內心定力,時刻提醒她身體的缺失會加持另一種能力的提升。比如她借助拐杖的單腿行走,這種體驗成為習慣之后,她并不會太在意失去的那部分軀體,因為,它可能已經被強力的思想裝置替代了。歸馬意識到身體失重會觸及她敏感的神經,“我不幸而有幸,讓身體長期葆有了不請自來的失重狀態。”(《失重》)這種失重雖然是常態,但也只有敏銳之人才能夠感受到失重對于自身所具有的超越性,它是身體的烏托邦,指向的不僅是過去,也可能是未來的存在。
歸馬的《單拐關鍵詞》雖然都是對過去身體的總結,但她憑借記憶、體驗和感知捕捉到了殘缺的身體所釋放出來的信號,不管是求助的,還是在毅力中溢出來的滿足感,她都總是在尋求身體與內心的平衡,這可能是命運賦予她的一種價值認同。她在變幻的修辭中復現了自己投射在所有關鍵詞上的意義定位,這又是別樣的詩性圖景。“當兩行腳印濃縮為一行,孤獨的腳掌對大地和道路的撫摸平衡之力,就會變得異常敏感。”(《足跡》)這種體驗性和領悟性表達里,暗藏著作者在創造中融入自身經驗后的審視意識。她發現了身體殘缺的風景不僅可能通向悲劇,也可能化為一束生命的微光,照亮一度被晦暗所籠罩的生活。此時,生活內部的循環同構于身體對外界司空見慣的接納,這是由時間帶來的潛移默化的改變,也是歸馬將身體作為一種參照來反思生活的前提。就像她因單腿而造成的身體的不平衡,讓她找到了重新認識自我的路徑,“我生命與生活的不對稱,是從身體的不對稱開始的。擁有不對稱的身體,是一種命運的特權。”(《對稱》)她運用詞語對身體進行剖析與提煉,從而獲得身心相對的安寧,乃至于達到某種“最低限度的美”。
歸馬在創作談《獨腿與窄門》中如此感慨:“我被命運刪減了一部分身體,恰是因此,我得以側身穿過命運的窄門,看到與眾不同的遠方。”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這也印證了一個人身體與命運之間的平衡。就像她對于身體傾斜的認識,“我越來越諳熟這種風雨中身姿的傾斜,并將其轉化成一種美麗前進的不竭勢能。”(《傾斜》)在此,轉化體現為心態和能力,它也是自我革新的佐證。而一個單腿人如何體驗飛翔的感覺,騎馬幫她完成了這一心愿,“我,一個獨腿人,借助馬兒的奔跑而抵近了飛翔。”(《飛翔》)這種大膽的挑戰正是努力改變自我所帶來的轉化之功,它或許就是歸馬長期自我教育的結果。
歸馬以單拐關鍵詞來檢視自己的人生命運,其實,最終還是要回到身體,她也由此在書寫中建構了自己的身體詩學。雖然身體詩學也會出現悖論,但樂觀式的認同在她的文字里敞開了希望之門,這一視角會讓其寫作獲得更多元的美學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