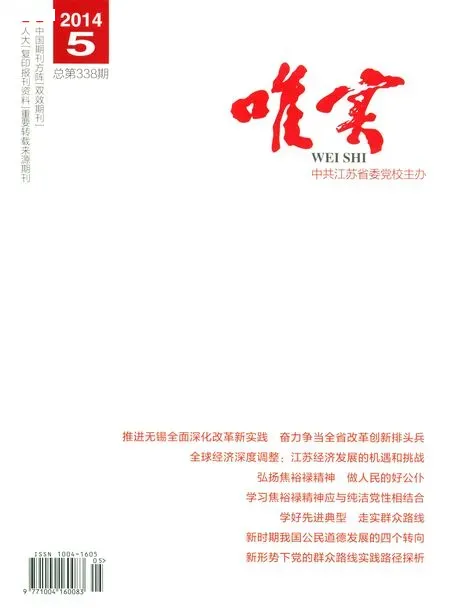揚(yáng)州刊刻《全唐文》二三事
馬俊
盛世修文,有清一代,康雍乾三朝以其文治武功,蔚為盛世。其間,作為盛世文治的重要標(biāo)志——官方大型文獻(xiàn)總集的編纂,如叢書《四庫(kù)全書》、類書《古今圖書集成》《佩文韻府》、文集《全唐詩(shī)》等為代表的皇皇巨著,不僅反映出當(dāng)時(shí)政治文化政策的轉(zhuǎn)變,交織著乾嘉學(xué)派的形成,而且折射了與文化重鎮(zhèn)揚(yáng)州的淵源——在上述清廷諸部重要文籍的采輯、編修、刊刻、典藏中,揚(yáng)州均傾盡全力、襄助有功。至嘉慶朝,雖然時(shí)勢(shì)日見(jiàn)盛衰轉(zhuǎn)捩,但其克紹箕裘、佑文圖治,卻是一道同風(fēng)。嘉慶親自主持編纂《全唐文》,并多次剖陳:“敬思圣祖仁皇帝欽定《全唐詩(shī)》風(fēng)行海隅,操觚家或睹初、盛、中、晚源流,有裨詩(shī)教甚大。茲《全唐文》(指內(nèi)府舊藏本)弆藏中秘,外間承學(xué)之士無(wú)由與窺美備,允宜頒示寰瀛,以昭盛軌”[1],“皇考?xì)J定《四庫(kù)全書》,嘉惠士林,頒行海宇,固已家弦戶誦,久道化成,無(wú)遠(yuǎn)弗被矣。予近得《唐文》一百六十冊(cè)(即內(nèi)府舊藏本),幾暇批閱,覺(jué)其體例未協(xié)、選擇不精,乃命儒臣重加釐定”[2],其踵武父祖、崇文重道的心跡直露顯豁。而這部《全唐文》的刊刻同樣與揚(yáng)州有著千絲萬(wàn)縷的聯(lián)系。
一、作為底本的“內(nèi)府舊藏”
與康熙朝編修《全唐詩(shī)》一樣,《全唐文》的編纂也以內(nèi)府舊藏為底本,關(guān)于這部底本的來(lái)歷,《全唐文》總纂官之一法式善在其《校全唐文記》中云:“內(nèi)府《全唐文》鈔本十六函,每函十冊(cè),約計(jì)成篇,蓋萬(wàn)有幾千矣。前無(wú)序例,亦無(wú)編纂者姓氏,首鈐‘梅谷二字私印。相傳海寧陳氏遺書,或云玲瓏山館所藏,或云傳是樓中物。大約抄非一手,藏非一家,輯而未成,僅就人所習(xí)見(jiàn)常行采摭為卷,唐人各集亦錄從近代坊本。”法式善提及的“海寧陳氏”,葛兆光先生根據(jù)陳調(diào)元《庸閑齋筆記》等考訂系浙江海寧人陳邦彥,康熙朝二甲進(jìn)士,歷任翰林院編修、左中允、侍讀學(xué)士等,雍正朝曾任《古今圖書集成》副總裁,陳氏編纂此書是出于其侍讀南書房時(shí)親睹《全唐詩(shī)》進(jìn)呈的主觀自愿,還是出于康熙本人的特別授意,已難考證,但此書確實(shí)對(duì)嘉慶朝編纂《全唐文》有奠基之功。
法式善還提及“或云(小)玲瓏山館所藏,或云傳是樓中物”,小玲瓏山館即清代著名鹽商、藏書家揚(yáng)州馬曰琯、馬曰璐兄弟的藏書樓,傳是樓即清初學(xué)者、藏書家昆山徐乾學(xué)的藏書樓,可以推知陳氏之《全唐文》雖編纂未竟,但此后傳于江浙,售于書賈,并借此由特定人物進(jìn)呈,從而成為嘉慶朝欽定《全唐文》的底本。法式善在相關(guān)記述中亦有所謂“內(nèi)府所藏唐文原本十六函,每函十冊(cè)……第一葉有‘梅谷圖記,為海寧陳氏裒輯未完之書。蘇大司空官兩淮鹽政時(shí)以重價(jià)購(gòu)得,進(jìn)呈乙覽”[3]等語(yǔ),記述的正是底本《全唐文》自揚(yáng)州轉(zhuǎn)呈京師、上達(dá)內(nèi)廷的這層關(guān)節(jié)。蘇大司空即蘇楞額,滿洲正白旗人,乾隆六十年轉(zhuǎn)赴揚(yáng)州,出任兩淮鹽政。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諭“內(nèi)府舊存《全唐文》寫本系由蘇楞額呈進(jìn)”,亦言及此事。彼時(shí)揚(yáng)州私家藏書之富、市肆?xí)Z之盛、鹽政要員遴選進(jìn)呈文籍之功由此可窺一斑。
二、兩處設(shè)立的“全唐文館”
《全唐文》的編修始于嘉慶十三年(1808年)十月,嘉慶親自下詔“著將此書(指內(nèi)府舊藏本)交文穎館,通行抄錄,并詳稽載籍有應(yīng)補(bǔ)入者,一體編輯,校勘完善,進(jìn)呈乙覽后,刊刻頒行”[1],編修處設(shè)于故宮西華門內(nèi)。康熙朝為編修《皇清文穎》設(shè)立的文穎館,時(shí)人亦稱之“全唐文館”。編修官則有包括總裁官董誥、總閱官阮元、提調(diào)兼總纂官徐松、總纂官法式善等在內(nèi)的88人,大多為當(dāng)世朝廷重臣、館閣耆舊和新晉進(jìn)士。諸人在普查群籍近600部之后,歷經(jīng)六年的努力,于嘉慶十九年(1814年)閏二月修成《全唐文》,董誥奏請(qǐng)“伏念江南為人文淵藪,其間績(jī)學(xué)之彥、藏書之家堪任校讎者不少,且揚(yáng)州文匯閣貯有《四庫(kù)全書》,刊叢籍鴻編,勘校尤為至便。懇仰天恩將全書頒發(fā)兩淮刻印”[4],同年六月發(fā)往揚(yáng)州,由兩淮鹽政阿克當(dāng)阿監(jiān)刊。
揚(yáng)州承辦欽定《全唐文》刊刻事宜,并不局限于刻印工作。在歷時(shí)兩年多的時(shí)間里,阿克當(dāng)阿督率眾人,認(rèn)真查照文穎館原奏事宜,悉心酌定章程,延致就近各省熟諳校勘書籍之士,翻檢文匯閣藏有的《四庫(kù)全書》,并博采揚(yáng)州藏書之家的有關(guān)唐文善本,詳細(xì)謹(jǐn)慎予以校對(duì)。[5]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刊校也設(shè)立了“全唐文館”,參與校訂的梅曾亮有《揚(yáng)州唐文館即事二首》,其《題王夢(mèng)蘭校書圖》又有“唐文開館昔揚(yáng)州,簪筆西園憶舊游”云云,此唐文館所在的天寧寺西園亦是文匯閣所在,而入館諸人又有吳鼒、秦恩復(fù)、孫星衍、顧廣圻等碩儒文彥。
揚(yáng)州唐文館的入館學(xué)士對(duì)于文穎館諸臣的“正本”并非盲從、無(wú)所作為,而是以其嚴(yán)謹(jǐn)?shù)闹螌W(xué)態(tài)度和深厚的文史學(xué)養(yǎng),對(duì)其中文字的錯(cuò)訛、衍脫之處,通過(guò)校語(yǔ)一一注明并繕寫歸檔,即所謂“其中篇章字句有一二重復(fù)偽脫之處,陸續(xù)將改移抽補(bǔ)各條分別存檔”[5],雖然語(yǔ)帶謙恭,但是諸人在《全唐文》勘誤上用功甚勤,卓有成效。
三、倚仗“鹽羨”的揚(yáng)州書局
自康熙朝,揚(yáng)州多次承擔(dān)內(nèi)府刻書之責(zé):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五月,江寧織造兼兩淮鹽政曹寅奉旨在揚(yáng)州天寧寺設(shè)立“揚(yáng)州詩(shī)局”,主持刊刻《全唐詩(shī)》;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三月,江寧織造曹寅又奉旨設(shè)立“揚(yáng)州書局”[6],主持《佩文韻府》繼武英殿本之后的二次刊刻(同年七月曹寅染病身故,內(nèi)兄蘇州織造李煦繼之)。由于江寧織造、蘇州織造以及杭州織造均屬內(nèi)務(wù)府主管,因此《全唐詩(shī)》《佩文韻府》可視作內(nèi)府刻書,揚(yáng)州詩(shī)局、揚(yáng)州書局亦可視作內(nèi)府刻書的臨時(shí)派出機(jī)構(gòu)。而“詩(shī)局”“書局”的名稱之別主要在于刊刻分屬詩(shī)集、文籍的類型之別。至嘉慶朝,揚(yáng)州再次設(shè)立書局,負(fù)責(zé)刊刻《全唐文》,并在刊刻完畢后,由嘉慶褒獎(jiǎng),將其中一部《全唐文》與《古今圖書集成》《四庫(kù)全書》一起恭藏于文匯閣,以嘉惠士林,便于士人查閱研讀。
近代版本學(xué)家陶湘在其《清代殿版書始末記》中提出:“兩淮鹽政曹寅以鹽羨刻《全唐詩(shī)》,軟字精美,世稱揚(yáng)州詩(shī)局刻本,以奉敕,亦稱內(nèi)府本……(嘉慶)十九年敕纂《全唐文》,亦由揚(yáng)州詩(shī)局承辦。”[7]雖然“揚(yáng)州詩(shī)局承辦”說(shuō)法稍稍有誤,應(yīng)為“揚(yáng)州書局”,但是陶湘之說(shuō),一方面,指明了揚(yáng)州以其鹽業(yè)財(cái)力和雕版技藝承印內(nèi)府刻本的史實(shí);另一方面,也勾勒出奉敕刊刻《全唐詩(shī)》以至《全唐文》的迭代承繼關(guān)系。其間,鹽政官員和鹽商群體在內(nèi)府刻書活動(dòng)中的積極參與應(yīng)屬必然,正如阿克當(dāng)阿在《全唐文》刊刻完成后的幾次上呈嘉慶的奏折中所說(shuō):“督率運(yùn)司及承辦官商等(校勘刻印《全唐文》)”[5],以及懇請(qǐng)“遴委妥員同該管官商(恭藏《全唐文》于文匯閣)”。
所謂“鹽羨”,即鹽稅扣除運(yùn)銷損耗外的盈余稅款。自古以來(lái),揚(yáng)州繁華以鹽盛,憑借鹽業(yè)的巨額收入、鹽商的傾力襄助及其崇文風(fēng)尚,促成了揚(yáng)州雕版印刷的精美和文籍出版的繁榮,以至“同治四年,署鹽運(yùn)使李宗羲開養(yǎng)賢館,以收恤寒畯。八年,鹽運(yùn)使方濬頤議設(shè)(淮南)書局……其經(jīng)費(fèi)仍于裁減成本項(xiàng)下開支,書成平其值售之”[8]。從揚(yáng)州詩(shī)局,到揚(yáng)州書局,再到淮南書局,依托鹽業(yè)收入的揚(yáng)州書業(yè)之盛不絕如縷。
在對(duì)揚(yáng)州刊校清廷內(nèi)府刻本的歷史考察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所謂“人文淵藪”,不僅素有績(jī)學(xué)之彥,集聚了一批出經(jīng)入史、博古通今的飽學(xué)之士;而且富有藏書之家,涌現(xiàn)了“下規(guī)百年地,上蓄千載文”的私人“借書樓”或稱公共圖書館;此外更有匠心之作,無(wú)數(shù)不曾留下姓名的工匠手中玉成了代表古代雕版印刷最高技藝的“康版”“曹本”“馬版”“秦刻”等藏書精品。而最為重要的是,集成以上優(yōu)勢(shì)資源,積極參與具有重要政治意義和時(shí)代意義的國(guó)家大型文化工程建設(shè)之中。唯有如此,人文淵藪、文化重鎮(zhèn)才愈顯實(shí)至名歸。
參考文獻(xiàn):
[1]中國(guó)第一歷史檔案館.嘉慶朝上諭檔:第十三冊(cè)[Z].南寧: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8:599.
[2]董誥,等.全唐文:第一冊(cè)[Z].北京:中華書局,1983:1.
[3]法式善.陶廬雜錄:卷一[Z].北京:中華書局,1959:7.
[4]翁梁溪.清內(nèi)府刻書檔案史料匯編:下冊(cè)[Z].揚(yáng)州:廣陵書社,2007:466.
[5]中國(guó)第一歷史檔案館,揚(yáng)州檔案館.清宮揚(yáng)州御檔選編:第四冊(cè)[Z].揚(yáng)州:廣陵書社,2009:328-330.
[6]中國(guó)第一歷史檔案館,揚(yáng)州檔案館.清宮揚(yáng)州御檔:第一冊(cè)[Z].揚(yáng)州:廣陵書社,2010:159.
[7]書目叢刊[M].沈陽(yáng):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65-66.
[8]中國(guó)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Z].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226-227.
(作者單位:中共揚(yáng)州市委辦公室)
責(zé)任編輯: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