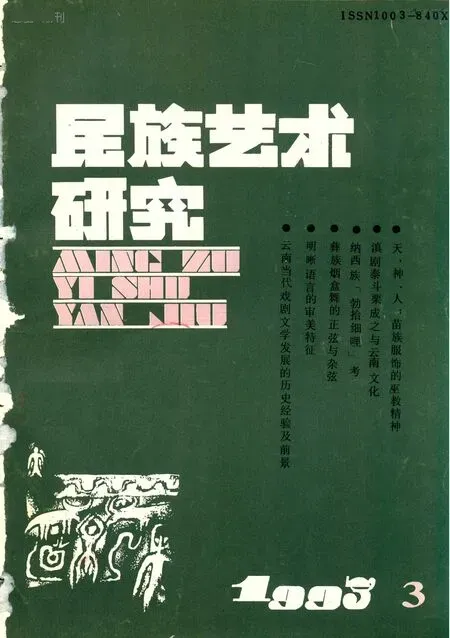民族地區鄉村經濟與傳統文化共同振興的協同效應研究
——白族大型民俗文化活動“秧賩會”與“田家樂”的啟示
石黎卿,石裕祖
2020年,我國取得了脫貧攻堅戰的全面勝利。在各貧困縣、貧困鄉鎮、貧困村一一摘帽后,如何防止返貧,是脫貧后時期的新任務。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印發的《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振興促進法》(2021年4月29日),對于鞏固脫貧成果、實現鄉村振興提出了明確的目標。推動民族地區鄉村的經濟振興和傳統文化振興是這個大目標下具有一定難度,同時又具有一定特殊性的目標。而在資源有限、任務緊迫的情況下,如何推動民族地區鄉村經濟與傳統文化共同振興就成為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課題。
通過多年持續考察,發現數百年來在白族聚居地水稻生產中自發結成的“秧賩會”及與之緊密結合的民俗文化活動“田家樂”,在特定的時期有效地推動了白族地區鄉村經濟與文化協同發展。“秧賩會”是經濟的范疇,“田家樂”是文化的范疇,兩者相互作用實現經濟與文化協同發展的機制正是上述協同效應的體現。這對于目前解決民族地區鄉村經濟與文化共同振興的問題有什么啟示呢?這正是案例所關注并試圖解決的問題。
一、白族“秧賩會”與“田家樂”——經濟組織與傳統文化活動的緊密結合
(一)大理白族“秧賩會”
分析“秧賩會”需要從更一般形式的“賩會”說起。“賩會”或簡稱“賩”①參見《康熙字典》“賩:[正字通]同‘賨’,[說文]南蠻賦也。[廣雅]稅也”。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210頁。,是云南西部一些少數民族在貨幣、生產資料、勞動力等方面進行互幫互助的一種自發組織,例如納西族的“化賩”和回族、漢族的“打賩”就是一種貨幣性的輪轉互助儲蓄組織,屬于“錢賩”的范疇;而“秧賩會”則是白族在水稻栽插時節進行生產資料和勞動力互助的一種組織。
本質上,“秧賩會”是一定數量的村民自發地組成的一個勞動互助組織,在“秧官”統一安排下、搶在有限的時令內依次完成會員的栽秧任務。“秧賩會”在每年大春栽秧時組建,栽秧完成后即解散,如果合作順利,來年栽秧時節可以原班人馬再組“秧賩會”。根據《云南民族民間舞蹈集成》②包括《洱源縣卷》《大理市卷》《云龍縣卷》《劍川縣卷》和《賓川縣卷》等。等文獻記載,“秧賩會”僅在以水稻種植為主的白族聚居地區出現。具體地點包括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大理市、洱源縣、云龍縣、劍川縣、賓川縣和麗江市玉龍縣的部分鄉鎮。
“秧賩會”運行的基本過程包括:第一,組會。一般延續往年的編制,亦有部分新老勞動力的更替。第二,開秧門。正式開始栽秧之前的一個儀式,主要內容是請出“本主”③“本主”即本主崇拜,是白族獨有的一種多神崇拜。起源于原始社會社神的崇拜和農耕祭祀,是南詔大理國時期白族先民的一種重要的民俗信仰,歷經千余年的發展,文化內容豐富。白族人認為本主就是村社保護神,掌管本地區、本村寨居民的生死禍福之神,能保國護民,保佑人們平安吉祥、風調雨順、五谷豐登、六畜興旺,白族村寨幾乎都建有本主廟。或其他神仙,并將該“秧賩會”的標志——“秧旗”插入勞動場地,增強“秧賩會”勞動的儀式感,并調動勞動的積極性。第三,從事集體栽秧勞動。分組進行栽秧,或進行栽秧比賽,其中穿插各種民俗文化活動和聚餐。第四,關秧門。活動規模較大時,稱為“田家樂”,指勞動結束后的多種民俗歌舞、戲劇(白劇、白族花燈)、曲藝、雜耍的慶祝儀式,并解散當年的“秧賩會”。
“秧賩會”中的勞動者進行分工合作。核心人物為“秧官”和“副秧官”。“秧官”相當于總指揮,統籌整個栽秧過程的流程與安排;“副秧官”相當于會計出納,負責重要事項的記錄和資金的進出。其余勞動者大致分為幾組:女性勞動者是栽秧的主力軍,男性勞動者負責平整田地、挑秧苗等,另有部分成員負責敲鑼打鼓、吹嗩吶,吶喊助興,調動氣氛并掌握節奏。
(二)伴隨“秧賩會”的獨特民俗文化活動事項——“田家樂”④“田家樂”的白族語名稱為“撒直”,直譯即為“解散秧賩會”。本文所述“田家樂”泛指各種規模的解散“秧賩會”的民俗文化活動,而不限于名稱為“田家樂”的活動。
在栽秧勞動結束后,“秧賩會”的使命即已完成,此時會員們聚集起來通過民俗文化儀式活動和多種民間文藝表演的形式進行慶祝,并宣布“秧賩會”的解散,屬于“秧賩會”的“關秧門”重要環節。不同鄉村的慶祝活動在內容、形式和規模上有所不同,但主要目的是相同的——慶祝栽插圓滿結束,以進一步增進會員感情。會員們則通過自娛娛人,各顯神通,展露個人藝術才華,借此凸顯本“賩會”社會地位和文化價值,并彰顯本“秧賩會”的經濟實力和厚重的民族傳統文化藝術積累。
其中內容最豐富、規模最大、歷史最悠久的要數大理州洱源縣鳳羽鄉的“田家樂”活動。除了祭祀酬謝“本主”等活動外,還包括“耕、漁、樵、讀、士、工、商”等十余種內容形式的戲曲歌舞表演。有的鄉村的表演規模略小一些,如大理喜洲鎮的表演主要是“耕、漁、樵、讀”的情節;劍川縣各鄉鎮只通過“耍牛舞”的表演來體現“耕”的情節。還有些鄉村一般都沒有文藝表演,只是通過一些簡單的儀式完成“關秧門”的任務,并以“打拼伙”聚餐來結束“秧賩會”。
以下為最具有代表性的大理州洱源縣鳳羽鄉“田家樂”田野調查個例。主要角色與活動內容包括:
1.秧官和副秧官:由“秧賩會”的兩位負責人扮演。秧官:統管栽秧勞動全盤;副秧官:主管經費收支賬目、后勤生活。
2.霸王鞭舞隊:由30或40多個男女青年組成。霸王鞭舞在嗩吶的伴奏聲中,圍圓循環地跳起20余種舞蹈傳統套路,以表現和渲染“田家樂”歡樂、熱烈的情緒和氣氛。
3.“耕”:在“犁田老漢”教授“來興”(啞子)和“來妹”(啞女)如何耕作、教猴子種地以及捉懶漢等情節中,表演者以唱、念、做相結合及詼諧的藝術手法,進行夸張表演,引起觀眾捧腹大笑,放松身心,散發出濃郁淳樸的白族鄉土生活氣息。使青少年從中學習農業耕作技能、提升道德修養,能夠寓教于樂。
4.“漁”:夸張地表演“漁翁”垂釣時的樂趣。
5.“樵”:“樵夫”肩挑柴擔,口唱白族山歌,沿街叫賣。
6.“讀”:由一位“教書先生”率一群兒童圍繞場地四周邊走邊唱,吟誦《三字經》。
7.“士”:護衛手執“五尺棍”維護場地秩序,差役負責抓“懶漢”“賭徒”和“吸毒人”;間或表演白族傳統刀槍棍武術套路;“士”還兼任扛“栽秧旗”的旗手。
8.“工”:肩挑補桶、修甑子和修鍋碗瓢盆的工具,在場中四周邊唱花燈小調,邊吆喝表演。
9.“商”:肩挑貨郎擔,手搖“撥浪鼓”,口唱山歌、變小魔術、念快板書。
10.還有裝扮成“懶漢”“賭徒”“吸毒人”的角色。他們服裝襤褸,臉上、手腳上還滿畫著爛瘡。
11.其他文藝表演:雜耍、板凳戲、百鳥朝王(巫舞)、白鶴舞、耍虎、刀槍棍棒等。
洱源縣鳳羽鄉的大型民俗歌舞戲劇儀式活動“田家樂”一直延續至今,其文化影響力遠播國內外,歷經數百年而不衰。
二、民族地區鄉村經濟與傳統文化協同發展的協同效應
(一)“秧賩會”對白族地區鄉村經濟發展的推動
“秧賩會”的組織形式和生產方式有利于提高生產效率,有利于增強集體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通過對相關縣、鄉鎮有“秧賩會”農民人均純收入均值的統計數據能清晰地看出其差異。為了分析“秧賩會”對鄉村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在各縣市內對比研究有“秧賩會”鄉鎮和無“秧賩會”鄉鎮的農民人均純收入。項目在研究時考慮了以下因素:
第一,由于機械化水稻種植方式生產在2000年前后逐漸進入云南,很多鄉鎮的“秧賩會”開始逐漸消失,因此選擇2000年的數據進行對比;
第二,由于大理市是大理州府所在地,機械化引入時間更早,且受旅游業等因素影響較大,數據統計剔除大理市的情況;
第三,由于縣府所在地人均純收入受影響因素與非縣府所在地不同,所以在對比時剔除了縣府所在地的數據。
對比結果見下表:

農民人均純收入對比
從數據統計表可以看出:
第一,從單一縣市來看,有“秧賩會”鄉鎮的農民人均純收入均值都高于無“秧賩會”的鄉鎮。洱源、劍川、云龍和賓川四縣,有“秧賩會”鄉鎮的農民人均純收入均值高于無“秧賩會”的鄉鎮分別為3.75%、2.79%、0.88%和6.39%。其中,賓川縣和洱源縣的兩類鄉鎮差距更為明顯,體現了賓川縣和洱源縣的“秧賩會”和“田家樂”的活動規模更大,活動內容也更完整。
第二,四個縣作為總體來看,有“秧賩會”鄉鎮的農民人均純收入均值高于無“秧賩會”的鄉鎮。兩類鄉鎮的差距達到3.45%。
上述數據統計結果表明,“秧賩會”在推動白族地區經濟增長方面,確有顯著的提升作用。
(二)“田家樂”對白族地區鄉村文化繁榮的作用
“田家樂”最初的內容形式較為簡單,只是對水稻“耕”作勞動的藝術再現和傳頌。其后,隨著社會的發展其內容不斷擴充,包括了“漁、樵、讀”,甚至還融入了“士、工、商”等內容情節;藝術樣式上也不斷拓展,包括了舞蹈、戲劇(吹吹腔、啞劇、白族花燈、板凳戲)、山歌、小調、曲藝(本子曲、白曲)、魔術、詩文、武術、雜耍、巫舞、刀劍棍武術,插科打諢(大頭和尚)等各種藝術門類,真正推動了白族地區鄉村文化藝術的繁榮,成為一種在白族地區深受群眾喜愛的民間民俗活動。可以說,“田家樂”儼然是一臺集白族歌、舞、樂、戲、“百戲”等于一體的白族民間傳統文化藝術的大展演。為此,因其較高的文化歷史和民族傳統藝術價值,“田家樂”被入選為《云南省第四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根據非物質文化遺產價值評價框架,白族“田家樂”的文化價值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第一,歷史價值。據考,白族地區早在約三千年前就已開始從事稻谷生產,①考古發現,大理州劍川海門口遺址所出土的稻、粟、麥等多種碳化谷物遺存證明:早在新石器晚期至青銅器早期,白族先民已經普遍栽種稻、粟、麥等多種谷物。而“田家樂”的原始雛形大致在春秋戰國后形成②參考《云南民族民間舞蹈集成——洱源縣卷》第111—113頁。,后經千百年的融匯、借鑒和發展,形成了內容豐富飽滿、藝術形式多樣、藝術門類眾多的大型傳統民俗藝術活動。“田家樂”“秧賩會”呈現了早期白族先民水稻農耕經濟社會的歷史創舉。為此,在知名度、參與性和歷史傳承等方面的民族學、考古學和經濟學研究中具有較高的學術參考價值。
第二,審美價值。“田家樂”之所以有很強的群眾娛樂性,正是因為“田家樂”的活動符合白族群眾的傳統審美觀。參與活動的村民既是勞動者又是編創人員,同時還是表演者,他們均為本民族傳統文化的持有者。這就必然使得“田家樂”具有獨特的民族文化藝術個性,并反映白族地區的特定地域特征。例如“吹吹腔”“霸王鞭舞”“耍牛舞”“耍馬舞”“百鳥朝王”“白鶴舞”“老虎舞”“白族調”等這些“田家樂”中不可或缺的歌舞戲曲表演,以及“秧官”“犁田老漢”“來興”(啞子)和“來妹”(啞女)差役等角色的裝束、道具和“秧旗”的形制等等,都是“田家樂”典型的地域特色文化代表符號。
第三,精神價值。“田家樂”在白族地區具有極強的文化認同感。“田家樂”的活動融入了白族地區獨特的“本主”信仰,白族人民以此祈求風調雨順以及好的收成。這種文化認同感使得“田家樂”活動在很多白族地區鄉村都有開展,甚至遠在湖南的桑植白族也通過向洱海邊的白族學習這一民族習俗來實現民族認同。1980年,有日本學者認為日本的插秧節源自云南,紛紛到云南來考察尋根,這也體現了“田家樂”的一種精神價值。
第四,社會價值。“田家樂”中耕田老漢教授來興和來妹耕種田地的情節,是“田家樂”活動最有代表性的核心情節,由于詼諧、夸張的啞劇表演方式,使其成為最受青少年喜歡的表演情節。人們在歡笑聲中普及了生產勞動的知識,充分體現了“田家樂”的教育價值。“田家樂”活動中穿插融入各種懲惡揚善的鄉規民約,如:懲懶、勸賭、戒毒等。這亦是對村民和青少年實施有效的社會道德教育。正因為“田家樂”在自娛自樂中潛移默化地施行具有傳統道德教化、技能傳授以及“耕讀傳家”、勞動光榮、抨懶頌勤、勸賭戒毒、勤儉節約的諸多價值,于是,“田家樂”理所當然地成為白族民俗傳統文化中的一筆璀璨耀眼的精神瑰寶。
(三)“秧賩會”及“田家樂”推動白族地區鄉村經濟與文化協同發展的協同效應
一般的民間文化活動,可以通過旅游和文化產業等途徑為鄉村帶來經濟收益,形成一個創造經濟收益的來源,可以把文化給經濟帶來的這種影響稱為單向效應。然而,植根于農業生產活動的白族“田家樂”可以帶來的經濟增量卻不僅僅止于此。
第一,“田家樂”自然誕生于“秧賩會”之中。“秧賩會”把大家聚攏到一起進行勞動生產,使得勞動結束之后大家聚在一起勞逸結合、自娛自樂一番是一件很自然的事。“田家樂”活動開展的時間、地點、人員和內容等安排,也都明確地被“秧賩會”所決定。所以“田家樂”這一傳統民俗文化活動與“秧賩會”這一經濟組織具有天生的內在聯系,密不可分。
第二,“田家樂”滿足了“秧賩會”功能上的多種需求。“田家樂”自起源于“秧賩會”,本身就具有服務于經濟活動的功能,其中包括勞動之余的身心放松、情感交流、勞動技能的教育與傳播、親友關系的融洽、鄉規民約的鞏固等。一方面,“秧賩會”規模越大,參與人數越多,組織紀律性越強,就會要求“田家樂”提供更多的活動內容和表演形式與之相匹配,進而推動民俗藝術品種、藝術樣式的遞增與繁榮;另一方面,“田家樂”的服務功能越有效,經濟生產活動的需求得到更大的滿足,經濟活動的收效也越高。
第三,勞動者與文化持有者合為一體,是生產活動和文化活動相結合的天然潤滑劑。“秧賩會”和“田家樂”的參與者,在生產時是勞動者,在文化活動時是藝術表演者,實現了勞動者與文化持有者合為一體。而且表演內容就是特定的農耕勞動生產和白族的生活內容,這便使得參與者具備了一種素質:在勞動時具備表演者的生動、詼諧;在表演時具備勞動者對勞動的理解和勞動技能。這使得在生產勞動效率得到提高的同時,文化活動的參與性、趣味性和自信心也得到提高,生產活動與文化藝術活動渾然一體。例如,“秧官”對栽秧動作落后者,以幽默和善意的方式進行催促,大家在笑聲中放松的同時,又不會有損落后者的臉面。這種能力是從“秧官”同時擔任“田家樂”主持和管理栽插中獲得的。“田家樂”中老農夫婦教授啞子啞妹的過程詼諧而有趣,教授的內容和技能來源于經濟活動,以寓教于樂的形式教育了青少年,有效地提高了“秧賩會”的栽秧勞作效率。
第四,“田家樂”活動富有精神感染力,擴大了勞動和藝術的參與范圍。“秧賩會”的栽秧活動只有青壯勞動力參與,但是“田家樂”活動老少均可參與,最大限度地提高了民眾對勞動的熱愛,并實現了對民眾精神的代際傳播。另外,“田家樂”活動深受群眾喜愛,會吸引尚未加入“秧賩會”的村民們參與進來,擴大“秧賩會”的規模和影響,使生產力得到提高。再者,“田家樂”受邀到鄰近的村莊進行表演,則增進了鄉村間的文化和生產合作,甚至還增進了民族間的和睦與團結。例如麗江九河鄉白族村的“秧賩會”和“田家樂”活動就吸引了其他村寨很多納西族、漢族村民的參與,成為民族團結的紐帶。
第五,獨特的白族人文資源與豐厚的民族地域文化積累,其影響力具有提振旅游經濟開發的作用。“田家樂”民俗文化活動通過其所具有的民族性、地域性和多種休閑養生綜合資源①如洱源鳳羽鎮白族傳統文化保護區的徐霞客兩度游過的清源洞、“百鳥朝鳳”的鳥吊山、白石江瀑布。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三教宮,有鶴林寺、帝釋山寺觀群、靈鷲寺、積慶寺、玉皇閣、武廟、魁閣,以及鎮風塔、鎮水塔、鎮蝗塔、文筆塔、渚安塔、留佛雙塔等圣跡靈地。,以及輕松愉悅的參與性極強的自娛自樂特征,能吸引大批來客參與其中,于此獲得身心健康,促進村民與游客互動。同時,“田家樂”活動中的一些文化藝術元素也提供了極豐富的文化產業資源,有利于經濟開發。例如秧旗、升斗、荷包、銅鈴、鳳羽硯和鳳凰帽、鳳尾鞋等特色手工藝品。這些旅游和文化產業資源都可以直接推動經濟的繁榮。
綜上可以看到“田家樂”活動在第五個方面發揮了與一般民間文化活動同樣的單向效應,有利于創造一定的經濟效益。但從前四個方面看,由于“田家樂”活動與“秧賩會”之間的密切聯系,形成類似于螺旋狀的相互推動,使得經濟發展與文化發展實現了良好的互相推進的作用。如此,經濟搭臺,文化唱戲,經濟與文化互動雙贏,便有效地實現了白族地區經濟與文化的協同發展。這種螺旋式推進給鄉村發展帶來的影響可以形象地稱為協同效應,以區別于一般民間文化活動帶來的單向效應。
三、推動民族地區鄉村經濟與傳統文化共同振興的思考
(一)“秧賩會”與“田家樂”的興、衰與再復興
由于協同效應的存在,在以勞動力為主的農耕時代,“秧賩會”與“田家樂”曾經有效地推動了白族地區經濟和文化的協同發展。其繁盛程度之高,一度吸引了外界的高度關注。丘恒興(1988年)②丘恒興:《中日民俗的異同和交流——訪鐘敬文先生》,《民俗研究》1988年第3期,第18—21頁、57頁。在對鐘敬文先生的訪談中稱,日本的“插秧節”與云南的“秧賩會”很相似,甚至有日本學者到云南來為日本的水稻文化尋根。楊國才(2001年)③楊國才:《中國大理白族與日本的農耕稻作祭祀比較》,《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期,第64—71頁。進而將大理白族的“秧賩會”和“田家樂”與日本稻作文化中的“花田植”和“田樂”進行了系統地比較研究。
但是隨著農耕機械化在白族地區的推進,大大提高了水稻的栽插效率,家家戶戶可以獨立地完成栽秧任務,而不需要鄉鄰的互助,因此“秧賩會”這一傳統的合作勞動方式就失去了優勢。從大理壩開始,“秧賩會”這一方式逐漸消失,而與“秧賩會”相生相伴的“田家樂”也一并消失④金少萍:《大理白族稻作祭儀及其變遷》,《中南民族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3期,第48—51頁。。
出于對傳統民俗活動中蘊含的優秀文化藝術形式的保護和傳承,“秧賩會”和“田家樂”被列入《云南省第四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⑤以“栽秧會”的名稱入選云南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得到政府的支持,使得其中傳統文化的部分得以重現,進而得到“復興”。程志君(2001年)⑥程志君:《大理周城白族栽秧會風俗變遷淺析》,《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1期,第7—11頁。對大理周城“秧賩會”的“傳統復興”過程中的難點和痛點進行了分析;高峰(2019年)⑦高峰,劉彥:《散雜居民族的族群認同與文化再造:合群經驗的視角》,《長江師范學院學報》2019年第4期,第10—17頁。從族群認同的角度,分析了桑植白族通過復興“秧賩會”進行文化再造的過程。但是所謂“復興”后的民俗活動雖然保留了原有的表現形式,但是其原生態的服務于經濟生產的功能卻已不復存在。曾經具備的協同效應也不復存在,只剩下單向效應。
(二)啟示與建議
白族地區“秧賩會”與“田家樂”的興、衰與復興的過程,以及協同效應在其中發揮的作用,為新時期推動民族地區鄉村經濟與傳統文化的共同振興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第一,傳統文化活動有不同的起源,只有源于經濟活動的文化活動才會與經濟發展產生協同效應。民族文化活動主要有兩種起源,一是來自生產生活,例如“田家樂”產生于生產勞作當中;大理“三月街”①大理“三月街”:古稱“觀音市”,是西南地區具有1000多年歷史的古老的貿易集市,被譽為“千年趕一街”,亦是大理州各族人民一年一度的民間文藝體育大交流的盛大節日。1991年起,三月街被確定為大理州各族人民的法定節日。產生于經貿活動當中,可以不斷地根據生產生活的特點進行創新,實現經濟和文化的協同效應;二是來自宗教祭祀等,過去這一類的民俗文化多是由權利階級用以限制大眾的思想行為,這一類的民俗文化雖然也包藏豐富多彩的文化藝術資源,但這一類民俗文化與經濟發展之間聯系不大,多是獨立于經濟而存在的。因此,即使通過旅游和文化產業等手段進行開發,充其量就是實現文化對經濟的單向效應。
當今在推動民族地區鄉村經濟與文化共同振興的任務目標下,上述第一類的民族文化活動可以實現與經濟的協同發展,應該作為地方政府重點扶持,進行挖掘、保護、傳承和創新的對象。
第二,經濟與文化互相推動才能實現協同效應。正如“秧賩會”與“田家樂”的鼎盛時期,以“秧賩會”為代表的經濟組織與以“田家樂”為代表的文化藝術活動互相推動,一度在白族鄉村實現了協同效應。而一旦兩者不再保持同步時,這種協同效應也不復存在。正如“秧賩會”生產方式消失后,“田家樂”這種民俗活動對于經濟發展的協同效應也就消失了。
文化的積累和沉淀可能需要比較長的時間,但經濟發展的速度卻快得驚人。想要實現經濟和文化同步互相推動,就需要對文化建設提出更高的要求,施以更為有效的舉措,特別是在文化的教育功能、知識傳播功能和文化信仰等方面,使得文化服務于經濟的功能可以跟得上經濟發展的腳步。
第三,優秀文化藝術需要傳承,更需要創新,有生命力的文化藝術才能實現協同效應。從“田家樂”的發展歷程來看,就是一個不斷創新的過程。其表演情節從最初的“耕”開始,到“耕、漁、樵、讀”,再到“耕、漁、樵、讀、士、工、商”,就是本民族的文化持有者堅持不斷創新,不斷融入外來文化精華的過程。因此保護優秀傳統文化并非墨守成規、一成不變,而是需要文化持有者自覺參與,不斷地吸收、融合、創造的過程。同時,對于外來文化也不是直接拿來主義,而是通過交流互鑒,為我所用。這樣的文化藝術才更具有生命力,從而推動協同效應的實現。
因此,扶持保護民族傳統文化藝術的方式,應當包括鼓勵文化持有者創新,特別要鼓勵與當前勞動生產水平相適應的文化創新。政府出資在鄉村組織的脫離生產的傳統民間文化藝術活動固然有其傳承的價值,但是如果能讓傳統文化藝術活動融入新的生產勞動方式,文化才會是歷久彌新的。
第四,勞動者直接參與文化創新可以更好地實現文化藝術對經濟的協同效應。前述文化藝術的發展可能會滯后于經濟快速發展提出的功能需求,“秧賩會”和“田家樂”的案例顯示,要更好地使經濟和文化和諧發展,由勞動者,同時也是文化持有者直接參與文化藝術創新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誠然,勞動者直接參與文化創新需要有堅實的群眾文化基礎和平臺,舞臺化的陽春白雪固然賞心悅目,但是要實現民族地區鄉村經濟與文化振興的文化藝術創新,需要發生在生產勞動的場地,形成于片刻的閑暇休息之時,如果勞動者有文化參與和創新的經驗,以及堅實的民族文化自信心,就能更有效地潛移默化推動文化創新。
結 語
“秧賩會”和“田家樂”在一定的歷史時期有效地推動了白族地區鄉村經濟和文化的協同發展。回顧并探析這一典型案例,有助于在新時期找到能夠實現民族地區鄉村經濟與文化共同振興的有效路徑。
在外來文化襲來之際,如何在保護民族傳統文化的同時,推動民族文化藝術創新,有效鞏固脫貧成果,防范返貧,服務于經濟發展,實現協同效應,通過透析白族“秧賩會”和“田家樂”的案例獲得啟示和思考,以期對促進民族地區鄉村經濟和文化共同振興,實現民族文化繁榮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