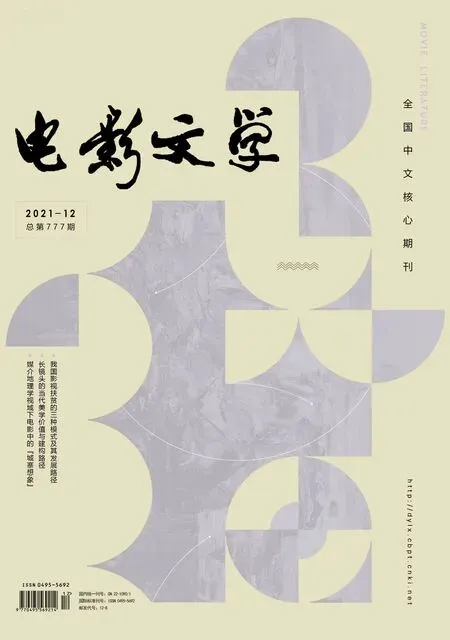型構社會學視域下觀影特殊化現象研究
阿柔娜 王 松(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北京 100084)
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觀影并非如現代一般是廣大社會公眾的一種休閑娛樂方式,而是有閑階級或者社會分層之上層人特權在休閑娛樂領域彰顯的一個縮影。透過觀影特權看新中國成立30多年來突出的“等級特權問題”,或許觀影行為僅是被深度“政治化”的諸多行為中的一個較為顯性的案例,體現出鮮明的階層劃分與等級秩序。新中國成立以來,觀影特殊化現象主要體現在什么階層的人具有觀影權力,具有觀影權力的階層觀影范疇如何區分,區分觀影范疇后享受的觀影方式是什么,諸如此類,觀影特權的有力體現。從埃利亞斯的角度看,觀影特殊化現象不是伴隨電影的產生而與生俱來的,是一個漫長的觀影演變過程,而后演變出的特殊化現象離不開型構的社會發生與心理發生,進而映射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分層現象的社會發生。
一、以過程為導向的方法論:埃利亞斯型構社會學理論框架
埃利亞斯的型構社會學方法論首先應建構研究者的觀點(Researcher’s Perspective)即埃利亞斯的理論與個人視角,要厘清社會理論與社會方法相互依賴的關系即確定“理論—實證”的研究方案。根據解釋的范式,理論和數據在社會研究中緊密相連:數據是建立和檢驗理論的主要來源,而理論框架則是選擇和解釋數據的遵循。因此,作為“理論和經驗導向”的埃利亞斯所依賴的社會理論是以過程為導向的方法論即型構社會學,幫助埃利亞斯確定研究所需要的實證數據及其選擇合理的研究設計;其實證方法包括通過敘事、經驗和定性的方法(如民族志、文獻、文件、地圖等)獲取數據的直接重建,與以文明的進程、宮廷社會和局內人—局外人等實例的間接重建,“理論—實證”重建埃利亞斯的理論與個人視角即研究者的觀點,以闡釋埃利亞斯提出的具體問題及其理論基礎并闡明型構社會學理論框架的研究步驟。
對于埃利亞斯而言,型構社會學理論框架理應包含三大步驟見圖1:第一步,型構的規則與社會結構(宏觀維度)。型構(configuration/figuration)是由位置、規則、規范和價值相互聯系的個體組成的社會結構,是一個集體和個體行動的框架,用于調節和確定他們的行為和交流的方向。個體(或集體)在型構中有不同的位置,且每個位置都能促進某些類型的行為并抑制其他行為。在既定(觀影特殊化)的型構中個體(或集體)都有一定的約束和選擇的權力,而權力比例則取決于其在型構的位置。即是,不同階層的觀影權力完全不同,并且存在誰可以享受觀影特權以及誰可能不享受觀影特權的規則。第二步,個體所處的位置、感知和改變型構的能力(微觀維度)。型構設定個體的行動框架,即根據個體在型構的位置,決定其行動的權力比例,或多或少具備采取行動的能力,但并不意味著型構的個體確實在行動。在既定(觀影特殊化現象)的型構中,個體如高官能夠影響到觀影型構,改變其在觀影型構享有的權利,如首長席、紅票席、送票等,同時亦可改變觀影型構本身(涉及的規則和社會結構)。要考慮到個體在型構中的位置、個體的行為如何與其他成員一起融入型構中,以及如何或為何改變其型構。第三步,型構的社會發生。根據埃利亞斯的型構社會學,微觀個體(Individual)和宏觀型構(figuration)總是在變化,同時又相互交織。合理的社會學研究需要面向過程導向,著重于對社會過程的解釋的同時超越“時間維度”而達到“觀古論今”,即社會學研究要回顧過去即具備歷史邏輯,剖析宏觀型構與微觀個體之間的關系,即“型構的規則和社會結構不僅會重新出現而且還會終止,個體可能進入或退出型構,或者可能更改其在型構的位置”。此外,亦要兼備反觀當下的現實邏輯與展望未來的啟示邏輯。

圖1 埃利亞斯型構社會學理論框架的研究脈絡圖
一言以蔽之,埃利亞斯過程導向的型構社會學方法論的理論框架,注重社會過程(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的觀影過程)的實證分析,并通過社會過程的實證分析來發展中級理論(從數據中提取理論,并使用數據檢驗這些理論),與“不脫離歷史性和社會動態的”社會理論(通過全面和整合的理論指導經驗研究,并通過實證研究對這些理論檢驗)。因此,埃利亞斯的型構社會學方法論是開拓超越歷史社會學和靜態社會學之外的社會科學,即一種宏觀(型構)和微觀(個體)如何在時間上交織在一起的方法。可見,時間性是埃利亞斯型構社會學的核心要義,因此埃利亞斯重建型構的社會發生,即“社會和人格結構的長期發展”。
二、觀影特殊化現象:20世紀50—80年代
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觀影特殊化現象,呈現出觀影“政治化”“階層性”“等級制”等表征,其根本原因在于觀影者擁有的權力比例的不對等。從埃利亞斯的角度來看,電影人和觀影人的相互依賴通常是不平等的,因此二者之間的權力比例也就不平等,但是這種權力比例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至今一直在變化,尤其以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最為突出,這種權力比例的變化絕非偶然的,而是發生在結構性的進程之中,即觀影的文明的進程。
1957年,“等級特權問題”突出。囿于觀影特權問題,星期六司局長干部可帶家屬小孩同去和平賓館看電影,政協常委、人大常委還有汽水喝,其特權在于官員行政級別(司局長級別是享受觀影特權的門檻)、攜帶家屬小孩(一人帶多人的觀影特權)、和平賓館(觀影地點的特權)、汽水(觀影待遇的特權),即不同等級的政府官員享受的觀影權力比例不同。正所謂“上行下效”在這個觀影“政治化”的特殊環境是極大的諷刺,自“上”觀影特權成為一件用于階層區隔的外衣,通過設置“首長席”“紅票席”“送票”的方式控制其他人的權利范圍顯示自己的與眾不同,他們的看“限量”電影、不排隊觀影、包場電影等無不體現出享有獨占權或優先權的觀影特權,就如同資產階級精英排斥人與人爭斗的民眾階級的體育運動如足球、拳擊而偏愛網球、高爾夫等無身體接觸的貴族式運動一般,追求的是休閑娛樂的“個體化”和“距離感”的審美心態而非“聚眾式”的休閑娛樂。而“下”基層干部領導雖不及“上”之觀影權力比例大,如無法涉及所謂的“內參片”,但仍有與社會公眾區別開來的觀影特權。1958年全國推行人民公社制度,農村在獲得生產和分配的自主權后,紛紛自辦電影隊以縮小城鄉休閑娛樂差距。為社會公眾豐富業余文化生活的同時,“享奢電影”的觀影特權在基層干部中蔓延,如觀影地點的隱秘化、觀影消費奢侈化、觀影生活亂倫化等。這種“自上而下”的觀影特殊化現象與布迪厄所說的那些統治階層喜歡購買最昂貴劇院的最昂貴座位,并將觀劇變成一次炫耀消費的行為不謀而合。
1966年—1976年間,正值“文化大革命”,中國電影也因此進入“乏片”時代,全國電影界總共僅發行70部長片,包括6部故事片、12部舞臺紀錄片、36部外國影片以及16部恢復發行的影片,其數量、題材、主題難以滿足中國社會公眾的休閑文化生活。在這段時間內,以美國電影為代表的“內參片”在“免稅放行”政策的庇護下迅速獲得中國電影市場準入,根據行政官員的電影偏好或影星偏好“搜購”影片資料成為中國電影公司的主要業務。然而,這些被作為“資料片”搜購回來的西方電影并未普遍流入市場,供應中國社會公眾“觀影”,反倒是以“內參片”的身份或角色在這個特殊的年代出現乃至盛行,其觀影特殊化現象更是明顯。這種“內參片”的觀影文化無疑放大并加劇了那個年代觀影特殊化問題,普通社會公眾觀影機會更是少有,但是這也不完全拘泥于“少數人”的日常休閑娛樂,也成為政治高層的國際文化交流、國際政治態勢、國際問題決策的重要借鑒,因為西方不同國家的一些題材電影也反映出該國家這個年代的一些休閑文化與意識形態。除此之外,電影業務人員也是“內參片”觀影特權享用者,因為觀摩學習非公映外國影片提升電影業務員的文化素養的傳統在此期間未曾斷過。因此,電影人也享有著業務范圍內的觀影特權。
1976年之后,享有觀影特權的群體開始逐漸被控訴,社會公眾通過揭發、抨擊、斥責等手段宣泄并治愈被不平等對待的心靈。然而,短暫的“觀影特權批判”風波過后,觀影特殊化現象并未得到根除,其享有觀影特權的群體猶在。政府官員仍然能夠觀到“內參片”,獲得一些未引進中國的影片的觀影特權,如1979年美國電影《根》、1986年美國電影《非洲之旅》等。于社會公眾而言,1976年觀影禁忌正式解除,其觀影文化開始步入正軌。城鄉觀影如日中天,農村公眾自帶板凳露天觀影無可厚非,城市公眾電影院一票難求需與政治關聯。改革開放后中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開始解凍,觀影限制消除、很多禁映電影復映或重映,就連“內參片”也開始公映。進入20世紀80年代,電視和錄像帶的出現及其普及,中國進入技術/機器為代表的現代觀影時代,徹底改變著中國社會公眾的觀影方式,社會觀眾的自由觀影權利也隨之歸位,其觀影特權現象蕩然無存。迎來互聯網時代,以網絡為媒介的觀影方式盛行,新媒體時代短視頻等簡約化觀影方式開始,進一步打破觀影特權的復發。當然,觀影特權的消逝,電視、錄像帶、網絡等媒介的出現也創造了資本收益最大化的現代觀影方式。這在埃利亞斯看來,觀影的人數和結構的復雜性內容增加了,而競爭中(社會文化與政治力量的博弈)的權力差別則減少了,即社會公眾自由觀影權利復位后,其觀影人數眾多的群體其權力比例越是相對平等,而這個過程埃利亞斯稱之為“功能性民主化。
三、型構社會學理論框架下的觀影特殊化現象分析
在宏觀層面,型構主要強調相互依賴,型構中的行動主體必須遵守規定著相互的行為期待的規范的要求。新中國成立初期,經過土地改革、工業恢復等措施,到1952年全國經濟基本穩定。在經濟階層區隔喪失合法性和目的理性的活動系統還未革新的時代,階層區隔更多的與政治權力關聯。這一時期政治化滲透在方方面面,政治權力直接影響社會諸系統。在社會文化系統中,政治化的“觀影特殊化”體現在政治身份或精神嘉獎的肯定與觀影權力密切相關,政治身份或精神嘉獎是獲得觀影特權的重要渠道,成為一種建構階層和體現等級秩序的表現方式。十年的“乏片時代”對于普通民眾而言,是“觀影特殊化”更為嚴重的年代,利用非公映外國電影做領導人、制片人和技術人員內參或觀摩學習的傳統并未間斷,并且愈演愈烈。70年代末期中國政府放開觀影限制,普通民眾終于可以有權力觀看電影,但電影片的購買還是建立在政治關系的基礎之上。直到80年代之后,電視、錄像帶、錄播機等技術手段真正使大眾觀影成為可能。這些技術使得生活中無法光顧影院的人們能夠觀看到經典的影視作品,目的理性彌漫在文化傳統中,但至少瓦解了傳統的對于普通民眾觀影權力剝奪的政治力量。這一時期,技術規則引致的補償綱領,伴隨著平等與民主等觀念進入社會文化系統,對觀影特殊化造成了沖擊。
在微觀層面,埃利亞斯認為文明的進程最初發生在一些特殊群體內,逐漸擴展到更廣泛的階層,個體在社會發展中是處于“彼此在聯系中的被分離和被隔絕”,有些看似習以為常的行為的最初狀態都是因為彼此依賴而對本能的放棄和改變。而這種改變基于心理發生的“指向性”(即指向與他人交往的自律)和可塑性(即心理會隨著對各種聯系的極強的適應性而不斷地調整),現在看似習以為常的觀影習慣實則也是一些特殊群體對本能的放棄和改變。在特殊化觀影現象的發展中,擁有政治權力的個體也同時擁有與普通民眾無身體接觸的距離式的觀影權力,“特殊化”體現在“首長席位”“私自調看”“特需翻譯”,甚至到“獨自觀影”等,而在80年代后,為促進全民消費、拉動經濟、穩定國家,特權群體做出了放棄和改變,并且在技術力量的推動下,觀影特權化已從“空間特權”逐漸轉向“時間特權”,并且與經濟實力相聯系,比如現在的“首映禮”,擁有了觀影的權力,但擁有經濟實力或政治實力的群體仍然擁有提前觀影的權力,從特權群體到普通民眾都為關系的穩定做出了妥協和讓步,因為彼此的依賴性。
社會發生和心理發生在型構中是朝向同一方向的,穩定的國家提供了制度基礎,職能分工得以發展,人的行為受到規范和法律的制約,使得和諧成為可能和必要的現象,上下層之間的行為反差會逐步縮小,個體的心理強制機制逐漸強大,人將自身的偏愛隱藏起來,這種有意識的自我控制和自我監督更加穩定了自我控制的社會機制。新時代,這種觀影特權逐漸消退,觀影人群得以逐漸平衡。
結 語
20世紀80年代以后,中國電影發展史上發生的“觀影特殊化現象”逐漸從空間層面消逝,其根本原因在于技術/機器時代的到來,因此技術創造出的無差別商品磨平了個體與個體之間的等級差異。那么,是否可以推斷“技術是消除社會等級、重建民主型社會文化格局的工具”?當然,正如埃呂爾所言,技術進步都是有代價的,影視作品的易觀看性和娛樂性也對社會文化造成了沖擊。由此,“觀影特殊化現象”的消除不能僅僅依靠技術,更要依靠穩定的社會關系網絡,牢固可靠的相互依賴的社會關系網絡會使處于其中的人們為了互惠互利而從心理上淡化特權,這離不開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如良好的政治環境、有力的政策支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