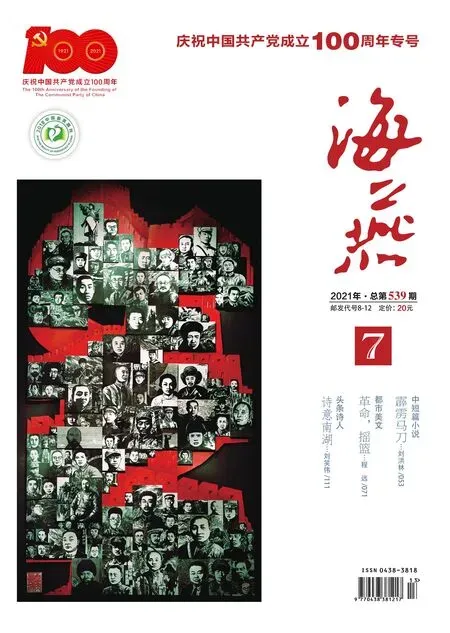阿哆哥
管朝濤
2013年,酷暑中父親打來(lái)電話,興沖沖地告訴我,他找到了一個(gè)很重要的朋友,準(zhǔn)備前去探望。他準(zhǔn)備明天一早翻越浙閩古道前往福建壽寧乘坐班車,取直道前來(lái)溫州泰順縣,叫我去接他。他在電話里很激動(dòng),聲音有些顫抖,這讓我十分詫異。我那段時(shí)間在執(zhí)行一個(gè)比較重要的項(xiàng)目,正忙得不可開(kāi)交。但思量片刻后,還是順從了他的意見(jiàn)。
老家是浙江省慶元縣一個(gè)省界山村,翻越村南的蝮蛇林古隘口便是福建省壽寧縣地界。壽寧、溫州泰順、麗水景寧三縣是明景泰年間,官府為防閩浙礦工私斗析置而成。蝮蛇林是洞宮山余脈,山頂常年被云霧籠罩,山間的泉水在山腳匯集成溪,出了村北山谷后流向左溪、景寧畬族自治縣,再?gòu)那嗵飬R集繞行一大圈到甌江前往東海。這里是世間一隅,千百年間,歸屬管轄的行政區(qū)域在臨海郡、處州(麗水)、溫州,青田縣、景寧縣、龍泉縣、慶元縣間交替更迭。最近的一次,是1973年7月17日劃歸麗水慶元縣。
如今,慶元與壽寧交界的兩個(gè)隘口下方山底的公路邊,不僅有漢白玉壘砌而成的高大的省際界碑,有一個(gè)路口還立了一塊藍(lán)色路牌,上書(shū):“浙江省最偏遠(yuǎn)山村”八個(gè)大白字,告知旅客這里離省會(huì)杭州近千里。
這里的人們?cè)陂L(zhǎng)期生活中,前往不同的屬地管理處辦事或外出營(yíng)生,必須學(xué)會(huì)使用十余種方言與不同的人溝通。各種方言之間并無(wú)互通之處:蠻講、畬客話、吳語(yǔ)、閩東語(yǔ)……在日常生活中隨機(jī)使用,“同村不同音,跨村不同語(yǔ)”是這里的一大特色。這里融合了浙西南、閩東北兩區(qū)的各類民俗:畬族采茶歌、“乞丐節(jié)”、絕技“蓋十三樓”、迎神、浙閩墟會(huì)、吃新等地方特色節(jié)日在四季中演繹。當(dāng)季之時(shí),喧嘩直沖云霄,人們用熱情烘燃著寂靜山谷間的村落。
這里的人,除卻繞道過(guò)甌江放排至溫州外,極少往北前去浙江省域內(nèi)縣市謀生。他們習(xí)慣于翻越各處山嶺、隘口前往福建寧德、三明、福州等地拓山做蕈(香菇)、做石(石匠)營(yíng)生。
這里的人出門在外經(jīng)歷風(fēng)霜雨雪,而外地做篾、箍桶、彈棉、鐵匠等手藝人也紛至沓來(lái),在連綿不絕的山巒下的山村中攬活兒。當(dāng)然,所有人都不例外,他們都要找一個(gè)東家作為落腳點(diǎn)。祖母告訴我,1945年冬,日本鬼子投降后不久,沉寂許久的山間游匠又逐漸多了起來(lái)。早年落戶于我們家的瑞安篾匠邱順發(fā),相隔多年,喪妻后帶著他的兒子阿哆前來(lái)山中做篾器營(yíng)生,依然落腳至我們家。如今,家里已經(jīng)包漿的篾匾、籮筐、米篩見(jiàn)證著他們?cè)?jīng)精湛的篾技。
經(jīng)歷了戰(zhàn)爭(zhēng)的困苦后,從溫州放排回來(lái)的祖父再遇故知,自然是欣喜不已,把酒言歡的同時(shí)也不斷地給他攬活兒。邱順發(fā)十歲的兒子阿哆,也和我的伯伯們整日嬉戲于鄉(xiāng)間。隨后五年,他滿口的文成話,也變成了地道的蠻講,這是一種僅存在浙閩邊境的一支百越語(yǔ)種。
1946年12月,邱順發(fā)的老家從泰順、瑞安、青田三地邊區(qū)析置地界合并為文成縣;1949年5月17日,兩百里外的慶元縣城解放,7月13日,一山之隔的福建壽寧縣解放。邱順發(fā)在攬游活兒的時(shí)候,也娶了毗鄰洋寨寡居的水蘭,算是正式落戶。
1950年,在身為“農(nóng)會(huì)長(zhǎng)”的祖父的幫助下,他順利分到了房、地。為此,他欣喜萬(wàn)分,恰逢次子出生,取名圣喜,小名阿喜。
但阿喜這個(gè)名字并未給他帶來(lái)好運(yùn)。就在落戶當(dāng)年的初夏里的一天,邱順發(fā)清早勞作回來(lái),早餐吃了菜粥后便大喊腹痛,之后不久便渾身抽搐身亡。已經(jīng)在外村攬活兒的阿哆得知信息趕回后痛哭流涕,最終在我祖父的幫助下,買了棺具將其父親安葬在黃土崗。水蘭隨后攜帶阿喜改嫁給了祖父的一位遠(yuǎn)房堂侄,阿喜也隨之改名朝喜。朝喜比我父親年長(zhǎng)一歲,卻按照鄉(xiāng)俗喚我父親叔叔,而三十一年后出生的我,亦稱阿喜為堂兄。
阿哆一直認(rèn)為他父親死得蹊蹺,因?yàn)樗诜孔油獾乃疁侠铮l(fā)現(xiàn)了一團(tuán)被搗碎的“青暗草(斷腸草的一種)”殘?jiān)彝龉矢赣H的手臂、指甲、腳全是黑色的。但是他還是強(qiáng)忍悲痛,按照鄉(xiāng)俗,三年后揀回骸骨挑回了文成東龍老家安葬。
父親說(shuō),阿哆后來(lái)還回來(lái)過(guò)許多次,但并沒(méi)有前往他的繼母家落腳,只是來(lái)看他的弟弟阿喜。他給了阿喜許多買不到的冰糖、餅干之類的東西吃。當(dāng)然,他也會(huì)分給與阿喜玩耍的我父親一些糖,然后又挑著篾擔(dān)游走于各地?cái)埢顑骸?/p>
父親說(shuō),從那以后,阿喜常常會(huì)在村口等待著他的哥哥前來(lái)。為此,水蘭經(jīng)常責(zé)罵他,并不許他再去見(jiàn)阿哆。從那以后,阿哆也在隨后的七八年間都沒(méi)怎么出現(xiàn)。直到1964年秋天,阿喜十四歲時(shí),成了家的阿哆又挑著篾刀工具前來(lái)做篾。這次,他還帶了許多東西給繼母水蘭,并大大方方地住進(jìn)她的家。他白天出去攬活兒,晚上則殷勤地幫忙修理破損的曬谷墊和籮筐。水蘭在我祖母的勸說(shuō)下,也不好拒絕,但是始終陰沉著臉。阿哆在沒(méi)有活兒的時(shí)候,都會(huì)在我祖母家吃飯,并親切地呼喚我父親為東家小叔叔,阿喜和哥哥在相處中漸漸親密起來(lái)。
“大概是住了三個(gè)多月吧,還沒(méi)到過(guò)年的一天傍晚,那天正落著大雪,我沒(méi)有鞋子穿凍得直打哆嗦,于是生了火盆在取暖。突然聽(tīng)到水蘭嫂在哭喊:‘朝喜不見(jiàn)了,朝喜不在了,一定是被阿哆帶走了,快幫我追啊,我就知道他沒(méi)安好心,這個(gè)天煞的!’我想也是這樣,阿喜總歸是阿哆的親弟弟嘛,再說(shuō)了,我堂哥和水蘭嫂對(duì)他也不好,走了也直息(清爽)。”父親喝了一口水,扭頭笑著對(duì)我說(shuō)。
“那阿伯和水蘭大娘他們沒(méi)有去追嗎?”
“怎么追啊,雪落得又大,阿喜本來(lái)就不是你堂伯親生的,他才不管呢!水蘭嫂在雪地里嚎了幾聲后,也只能悻悻地回去了——她屋里還有兩個(gè)孩子吶。”

插圖:李雨薇
“我從那以后二十多年都沒(méi)有見(jiàn)到阿哆。”父親坐在副駕座上,扭了扭身子看了看窗外。車子在盤山公路上順勢(shì)而下,我一言不發(fā),腦海里出現(xiàn)了一幕場(chǎng)景:昏暗的天空下,一位年輕人挑著擔(dān)子在浙閩古道上艱難地行走,身后跟著年幼的弟弟,兄弟倆的腳印落在了雪地上。他們應(yīng)該在路邊的亭子里過(guò)夜,然后相擁取暖度過(guò)大雪紛飛的夜晚。在那個(gè)沒(méi)有通車的時(shí)代,他們要先路過(guò)福建壽寧,再前往泰順,然后抄小道返回文成東龍老家,這在雪地里至少要行走四天以上。
從我去泰順接了父親的時(shí)候,一路經(jīng)過(guò)廊橋之鄉(xiāng),又再次踏入福建地界。從我家到這里是由西南向東南,一路齒輪狀的省界地域,讓我接到了不少同樣的提示短信。通常,一個(gè)縣城也是縣域的中心,但泰順縣城卻緊緊地挨著壽寧邊界,而從泰順縣府所在地到縣域最東面的分水關(guān)高速路口,卻足足要駕駛一個(gè)半小時(shí)以上。
父親在過(guò)泰順的途中還講了一個(gè)廣泛流傳的民間故事。他說(shuō),當(dāng)年浙江泰順和福建壽寧解決邊界紛爭(zhēng)的時(shí)候,兩個(gè)縣令議定好啟程日,以兩人相逢的地點(diǎn)作為兩縣分界。壽寧一方的縣令入夜后即刻上路,清早到泰順縣衙后,泰順縣令還在睡夢(mèng)中,醒來(lái)后驚訝萬(wàn)分,遵守約定同時(shí)難堪地說(shuō)道:“總不能以縣衙門口作為分界線吧?”最后,壽寧縣令退步,以縣衙五里之外作為浙閩分界線。后來(lái),我在馮夢(mèng)龍縣令所著的《壽寧待志》中,也找到了類似的記載:“浙之景寧、泰順、慶元與閩之福(壽寧)四縣……并設(shè)時(shí),壽寧與泰順爭(zhēng)疆不決,乃期面議,各以某日展行,即相遇處為鴻溝。壽寧令夜行直達(dá)泰順城內(nèi),登其室,泰順令猶未出,繇(由)是城以外盡屬壽焉。”
其實(shí)寫到這里,本來(lái)是可以結(jié)束了,阿哆帶著弟弟阿喜回到了文成,再未踏入我的家鄉(xiāng)半步。而且,阿喜只是父親的一個(gè)玩伴而已,我的工作又非常繁忙和棘手,這他是知道的。這談不上清早風(fēng)風(fēng)火火地從遠(yuǎn)處的山里趕來(lái)相見(jiàn)吧?
父親似乎知道了我的想法,咳嗽了一聲,松了下安全帶繼續(xù)說(shuō)道:“阿喜長(zhǎng)大娶親后回來(lái)過(guò)很多次,畢竟他生在那里,阿奶(蠻講母親的稱謂)也在我們那里,水蘭去世后沒(méi)幾年,阿喜也因哮喘復(fù)發(fā)早早過(guò)背了。我?guī)闳ヒ?jiàn)見(jiàn)阿哆,那個(gè)叫我東家叔叔的侄子,你一會(huì)兒記得叫他阿哆哥啊!”
已近晌午,父親掏出紙巾,擦拭了下眼睛后繼續(xù)講述。車子在沈海高速上飛馳,從父親緩慢的言語(yǔ)中,我才知世間的事,總會(huì)不經(jīng)意間展現(xiàn)另一段溫情。
原來(lái),1986年,我五歲那年,父親借錢與人合伙“判山”,那是一種在看山林時(shí),以樹(shù)林綠濃度判定成木存量定下砍伐合同,類似于“賭石”的生意模式。到了伐木時(shí),木工發(fā)現(xiàn)蔥郁的森林下全是陡峭的小石壁,成木彎曲多枝且難以運(yùn)輸出山,結(jié)果自然是血本無(wú)歸。生意做到最后,只剩下政府給予的伐木補(bǔ)貼——幾十擔(dān)尿素化肥,而且沒(méi)有人購(gòu)用。大戶人家出身的母親忍受不了山中的困苦,一氣之下帶著我和姐姐返回了五百里之外的娘家,留下父親孤身一人。
父親說(shuō),那會(huì)兒山里的年輕人娶親不易,年輕時(shí)他和同伴在外販木的時(shí)候,以美好的前景和生活條件吸引了母親和她的伙伴。當(dāng)她們從浙中金華跋山涉水到達(dá)浙閩邊界的時(shí)候,失望已為時(shí)過(guò)晚。正因如此,父親一直對(duì)母親深懷愧疚。
其實(shí),這種狀況一直持續(xù)到現(xiàn)在,只不過(guò)我的伙伴們比父輩走得更遠(yuǎn)。我的發(fā)小們陸續(xù)從越南、緬甸、柬埔寨這些飽經(jīng)戰(zhàn)火摧殘的國(guó)家娶回了自己的女人,這也讓我們這里成為了有名的“國(guó)際村”。每年春節(jié),來(lái)自東南亞各國(guó)的洋媳婦在村聯(lián)歡晚會(huì)上,展現(xiàn)出了非凡的異域風(fēng)采。
母親寫信來(lái)說(shuō),以目前的經(jīng)濟(jì)條件是無(wú)法帶好兩個(gè)孩子的,他告知父親她在娘家會(huì)更有條件將我們養(yǎng)大,請(qǐng)他安心。母親的來(lái)信讓父親非常難受。恰巧阿喜回鄉(xiāng)探望他的母親水蘭,他告知父親溫州瑞安一帶的農(nóng)民已經(jīng)會(huì)使用化肥。父親思考許久后,再次借錢雇了人將肥料翻山挑到壽寧,雇車過(guò)泰順到文成百丈口,準(zhǔn)備順飛云江而下文成、瑞安販賣。
可能是時(shí)機(jī)已晚,亦或是父親運(yùn)氣不好。到了瑞安之后,季節(jié)已過(guò),另外父親也是初來(lái)乍到,這一船肥料自然是滯銷。為此,父親不僅要擔(dān)憂夏季的雨水打濕尿素,還要每日支付船租,這讓他憂心忡忡。
車輛即將到達(dá)平陽(yáng),我從余光中,看到他微微地低下了頭。下了高速后我打開(kāi)了車窗給他遞了一支煙,父親接后,點(diǎn)上大口吸了起來(lái)。煙味被窗外呼呼的大風(fēng)吹回,灌入我的口鼻,讓我打了個(gè)大大噴嚏。父親見(jiàn)狀,打開(kāi)空瓶子想熄滅了它,我擺擺手示意不要緊。天空飄起細(xì)雨,輕輕地落在前擋玻璃上。路上積累的塵土和雨水,在雨刮器的晃動(dòng)下形成了一道道渾濁的弧線,我急忙按了噴水器并順勢(shì)揉了下發(fā)熱的眼眶,眼前逐漸清晰了起來(lái)——那時(shí)的父親該是多么的無(wú)助啊!
無(wú)奈之下,父親吩咐船工調(diào)頭,溯江而上返回,一路吆喝,寂靜的兩岸并無(wú)人回應(yīng),這更令他心急如焚。
正當(dāng)父親一籌莫展的時(shí)候,忽然聽(tīng)見(jiàn)有人喊著他的名字“茂叔——茂叔!”煙雨朦朧的夏初,岸邊有兩個(gè)身影在向他招手,當(dāng)船逐漸靠近埠頭的時(shí)候,他看見(jiàn)了多年未見(jiàn)的阿哆。原來(lái),阿喜返家后,告知了兄長(zhǎng)我父親運(yùn)肥來(lái)賣時(shí),阿哆就知道此行肯定不暢。于是每日在江邊等候著他。當(dāng)疲憊不堪的父親走上岸時(shí),我能想象得到他那踉踉蹌蹌的腳步。
“這是我一生最為艱難的時(shí)候,我并不怪你母親,你舅舅是干部,家庭生活條件更好,能讓你們更好地成長(zhǎng)。”父親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雨迅速大了起來(lái),路邊的高樓在疾馳的車窗外掠過(guò),雨點(diǎn)順著后視鏡拉出一道道水珠。我在想,我在職場(chǎng)上的煩躁和挫折,相對(duì)于他們來(lái)說(shuō),只是人生旅途中極小的一個(gè)漣漪。
車子到達(dá)平陽(yáng)與瑞安交界的飛云江南岸,兩岸是當(dāng)年為建造珊溪水庫(kù)遷來(lái)的移民村,阿哆就住在那里。從地圖上看,大致還有十五分鐘車程。
阿哆帶著弟弟阿喜,從船上卸下無(wú)人問(wèn)津的肥料運(yùn)送至家中。夜晚,他顧不得敘舊,立刻召集了他的本家?guī)资恍值荛_(kāi)會(huì)。這位比我父親年長(zhǎng)十六歲,歷經(jīng)滄桑的中年男人緩緩說(shuō)道:“這位茂叔,是我和你們大伯當(dāng)年在慶元落戶東家的兒子,他們以前對(duì)我很好。這樣——雖然已經(jīng)過(guò)季了,但他的肥料很好,是政府供應(yīng)的,尿素含量足。你們每人扛一袋回去分售,按照市價(jià)每市斤加五分結(jié)算……”所有人都一言不發(fā),飛快地扛起肥料回了家……第二天傍晚,他們將一摞摞零鈔送到了阿哆手中。
飛云江岸邊的木房中,火架子里的松精燈火光忽而跳躍,橘黃色的火焰下,阿哆認(rèn)真地?cái)?shù)著鈔票,然后一疊疊摞好后交給了我父親。窗外蟲(chóng)鳴蛙聲連綿響起,堂前的燕窩里那一群毛絨絨的雛燕,它們?cè)诟改傅某岚蛳拢匠鲱^來(lái)發(fā)出“唧—唧—唧”的囈語(yǔ)聲。
父親拿著這筆錢,又南下瑞安,買了一些山里緊俏的物資帶回家鄉(xiāng)售賣——后來(lái)他因此開(kāi)了一家商店,從日用品到五金件和肥料一應(yīng)俱全,小店一直運(yùn)營(yíng)到現(xiàn)在。父親在當(dāng)年秋天,就前往外婆家,將我和姐姐接回了老家,和母親此后再未有爭(zhēng)吵。1997年,國(guó)務(wù)院批準(zhǔn)文成珊溪水庫(kù)為第三批新開(kāi)大中型項(xiàng)目。阿哆帶著弟弟攜家?guī)Э诎徇w到了平陽(yáng)縣移民村,父親從此與他們失去聯(lián)系。
2013年8月20日,當(dāng)父親輾轉(zhuǎn)找到阿喜的聯(lián)系方式時(shí),是他兒子接的電話,說(shuō)阿喜早幾年已過(guò)世。他兒子在電話中說(shuō),父親臨別之際,念念不忘的是沉在水底的老家,還有出生地浙閩邊邑的伙伴。
次日,車子在飛云江入海口邊的一個(gè)村前廣場(chǎng)停了下來(lái)。我遠(yuǎn)遠(yuǎn)地看到一位耄耋老人,帶著妻子、侄子撐著雨傘,顫顫巍巍地走向前來(lái)迎接我們。
經(jīng)歷過(guò)戍邊風(fēng)雪的我,大步越過(guò)積水走上前去,彎下腰緊緊握住那雙干枯的雙手,怯生生地喊了一聲:“阿哆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