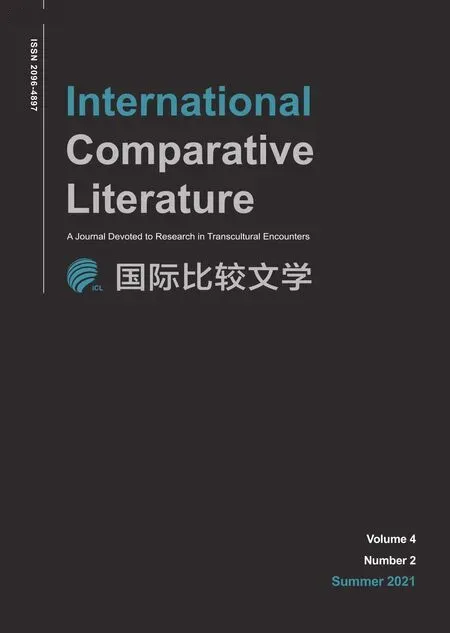時間修辭與亞洲書寫:《東方志》的政治宇宙學*#
周云龍 福建師范大學
一、作為官方調查報告的《東方志》
試圖反寫“歐洲中心論”的歷史學文本在討論印度洋中心的國際貿易體系時,共同的出發點是把大西洋中心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作為參照系。早在這些歷史學文本之前,還存在一個與印度洋中心的國際貿易體系屬于同一時代的重要旅行書寫文本,對這個出現于大西洋中心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之前的貿易體系進行了近讀細查。它就是葡萄牙在16世紀初首次遠遣亞洲的大使多默?皮列士獻給國王曼努埃爾一世(Manuel Ⅰ)的《東方志》。雖然在《東方志》寫作的年代,葡萄牙人已經開始介入這一貿易體系,但根據《東方志》所記敘的內容,至少在16世紀初,葡萄牙人并沒有給印度洋的貿易體系帶來結構性的改變。《東方志》的重要性可能正好體現于其長期以來的“湮沒無聞”。因為“葡萄牙國王曾在16世紀施行過封鎖非洲的發現及其貿易活動信息的政策,這一點似乎相當確鑿。當曼紐爾王在1504年頒布的法令被取消以后,保密的政策可能延伸到了有關印度和遠東的信息中去。根據目前所知的情況,在1500年到這個世紀中期這段時間內,沒有一部關于亞洲地理發現的著作在葡萄牙出版,……多默?皮列士(Tomé Pires)的《東方志》(Suma oriental
)和杜阿爾特?巴爾博薩(Duarte Barbosa)的《書籍》(Book
)都寫就于1520年之前,二者的主題都是關于葡萄牙的東方帝國,直到1550年意大利編者賴麥錫打印了兩本書稿之后才得以出版。甚至在印刷時,賴麥錫還不知道皮列士的名字,無法得到討論香料的那部分章節。”《東方志》長期不為人所知,可能正是因為它對葡萄牙王室東方擴張事業有著無可比擬的重要性。與20世紀下半葉以來志在反寫歐洲中心主義的史學著作不同,這部旅行文獻沒有后來的歐洲全球霸權作為參照。當然,這并非就是說《東方志》對印度洋的記述是“客觀”或“真實”的,《東方志》的敘事風格是展示、呈現式的,這部著作本身就是歐洲進入印度洋國際貿易體系的“導言”與表征。就辭采而言,《東方志》的可讀性很差。正如葡萄牙學者科提松(Armando Cortes?o)對其人其文的評價:“多默?皮列士首先是一個熱心的觀察者,一個敏銳探索的學者,并且是一個忠實、準確和不知疲倦的撰述人—盡管他語言貧乏,甚至不能在早期歐洲記述東方的作家中占有一席之地。”皮列士作為葡萄牙官方委派的大使,其寫作從性質上說屬于官方調查報告。因為《東方志》行文中多次出現“陛下”的稱謂,由此可知其預設的讀者就是葡萄牙國王。皮列士對自我的身份意識頗為自覺:“我不是以大膽的想象力來撰寫這部書,因為那會有失真實,但我要求,在發現我有所缺失之處,要給予原諒,因為我的撰述是誠實的。我曾看到許多大事的發生,以至于不得不得罪某些從事寫作的人,他們的著作需要改正。”皮列士的自陳,特別能使人想起《馬可?波羅行記》或《曼德維爾游記》中引人入勝的異域書寫。比如,其中對巴布亞島人的評論:“例外的是,聽他們說,在巴布亞島,大約距班達80 里格,有長著大耳的人,他們用耳朵遮蔽自己。我從未見過曾目睹大耳的人,這個傳說不值得重視。”這段話幾乎可以視為是在和《曼德維爾游記》進行間接地對話。再如,對同時代人瓦爾塔馬、巴波薩和卡斯特涅達等人記述的坎貝國王蘇丹穆扎法沙身體的毒性問題,皮列士絕不人云亦云,他在《東方志》中堅定地表態:“但我不相信這個,盡管人們都這么說。”
枯燥蒼白的語言未必就是作者辭采欠缺或“貧乏”,它毋寧更加暗示了對想象力的抑制和對忠實性的謀求,因為它預設的接受對象是尋找長老約翰(Prester John)領地和香料群島的葡萄牙國王。在一切都要講求言之有據、謹慎謙遜的前提下,沒有修辭性的語言本身就是最好的“真實”修辭。本文的任務不在于考據其“真實”樣貌如何,而是從《東方志》的文本出發,解讀它所呈現的印度洋國際貿易體系以及對早期近代歐洲與亞洲關系的跨文化想象。
二、亞洲敘事與時間的空間化
在時間緊迫、紙張匱乏的工作環境中,《東方志》所載之事理應都很重要,諸如亞洲諸國的物產財富,風土人情,政治制度,軍事歷史等,但其重中之重卻是商業貿易。在“第二前言”里面,皮列士對整部著作的內容有明確說明,同時也表達了對商品貿易的禮贊:“在這部《東方志》中,我將不僅談地域、省份、王國和地區的劃分及其疆界,還將談到它們彼此間進行的貿易,這種商品交易是如此必要,以至于沒有它,這個世界就不能前進。”的確如“第二前言”所強調的,《東方志》涉及的縱向地理路線相當綿長,對各地的橫向觀察描述又細致入微,但這些由縱橫交叉點連續而成的敘事線索所凸顯的,正是印度洋的國際商品貿易網絡與體系。這完全符合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在16世紀初期的戰略設計—把國家建設的中心設定在貿易方面。《東方志》的亞洲敘事是自成一體的,而不是區域貿易狀況的簡單羅列與疊加。皮列士對此相當自覺,他曾自喻其寫作為裁縫剪裁。所以,其中的縱向地理路線不能忽視,縱向的地理路線賦予了不同區域以整體的結構性意義,它發揮著有機的編織性功能。
關于敘述的縱向地理路線,皮列士“先從亞洲開始敘述,從非洲起,到第一印度;第二部將從第一印度到中印度結束;第三部將是恒河另一邊的印度高地,……;第四部將談中國及屬于它的省份以及高貴的琉球(Lequeos)島、日本(Janpon)、浡泥、呂宋和望加錫(Macaceres);第五部將詳述各島”。還有皮列士在“前言”里面沒有說出的“第六部馬六甲”,全書以此作結。這一敘述架構分配事實上也是將亞洲不同地域體系化的方式。至于這一縱向的地理路線是否就是皮列士的旅行路線,不得而知。根據與皮列士生平相關的片段性資料,《東方志》的寫作順序很可能不是其旅行路線,因為他最終卒于中國,而且這個問題也沒有那么重要,觀念的地理要比現實的地理更加值得探究。盡管皮列士在寫作中直陳放棄了想象,也放棄了對前人地志的依循,轉而倚重于自身的第一手訪談、觀察和體驗,但《東方志》作為呈現給葡萄牙國王的“亞洲戰略”調查報告,在極其有限的時間和紙張的限制下,必然需要一個敘述的框架與剪裁,把不同區域的狀況組織進來,而不可能是一種完全自然主義式的照錄。對皮列士而言,這一矛盾帶來的壓力可能尤其嚴重,因為他對第一手的經驗和真實有著近乎傲慢的“實證主義—實用主義”偏執。
我們不懷疑《東方志》作者皮列士的慎重嚴謹與實證精神,但在今天的知識系統中,重新面對該文本時,無論是匍匐在皮列士無比忠誠的“真實”之前,還是簡單套用“(前)東方主義”的論調,可能都是一種知識上的懶惰。具有啟發性的閱讀方式,也許需要把《東方志》視為一種復雜的跨文化文本,在早期近代的歐亞關系脈絡中,討論其中的“反實證—實用”的實證主義—實用主義敘事,并解析其中的“政治宇宙學”(politic cosmology)把亞洲納入知識的對象領域的具體操作方式。“政治宇宙學”即“用時間的術語界定(自我)與他者的關系”。這種閱讀方式,對我們思考早期近代乃至當代作為知識的世界意識的再生產機制將不無益處。
皮列士書寫亞洲的框架安排,既具有空間意味,同時又暗示著某種時間意義。前文已經指出,《東方志》中涉及的地理區域順序安排與皮列士本人的旅行足跡并不重合。在葡萄牙海外拓殖信息嚴格保密的制度背景中,可以說《東方志》預設的唯一讀者就是國王曼努埃爾一世。《東方志》的敘述是第一人稱的,具體行文中,敘事者“我”不斷跳出文本與“陛下”、“您”或“你”進行想象的對話。比如,在談及馬拉巴爾時,皮列士寫道:“我不必深入談馬拉巴爾,陛下對它已很熟悉,……馬拉巴爾百姓的皮膚是黑色的,有的是黑褐色。國王都是婆羅門,那是他們教士的種姓。”這段引文在《東方志》里面具有非常典型的代表性,它不是一般性的介紹文字,而是一個生動的交流情景:一位虔誠、謹慎的書記官在向國王呈述其位于地球遙遠的另一邊的疆域的調查情況。這種交流情景在《東方志》里比比皆是。從這段引文可以看出,《東方志》的時態是現在時,即“在現在時態中對他者文化和社會作出描述的實踐”。《東方志》在書寫亞洲時采用的正是這種時態。
當《東方志》的敘事者說“馬拉巴爾百姓的皮膚是黑色的”的時候,這種具有主導性的現在時態已經暗示了文本的修辭目的,而無論皮列士在主觀上如何想極力做到客觀。類似的表述組成了《東方志》的主要句型與時態。我們可以信手拈出幾個例句:交趾支那國“有瓷器和陶器—有的很值錢—從那里把它們運往中國售賣。……”“馬六甲有四個沙班達,他們是市政官員。”首先,諸如“馬拉巴爾百姓的皮膚是黑色的”和《東方志》中涉及的諸多亞洲地理區域的各個層面的描述一樣,是一個極其粗糙而無效的命題,因為在敘事者的視界中,永遠不可能把所有的觀察統計對象進行一網打盡。因此,這一實踐在邏輯上的困難在于,作者以其所見的部分代替某個文化整體;其實體論方面的問題在于,不斷發展變化的某個文化族群被作者凍結在其觀察的時間之內,呈現為靜態的分類學敘事。也就是說,從《東方志》第一部到結尾的馬六甲,涉及的地理區域的文化、社會、歷史、政治、貿易,都被敘事者封存進了一個想象的博物館,它們是靜態的,完成的,永恒的。敘事者使用語言修辭的魔力,制作出一張以《東方志》為名稱的、以旅行書寫為文體樣式的“圖表”(tableau),把“亞洲”不同區域的知識進行分隔,然后填充在其中。這張圖表“使得思想去作用于存在物,使它們秩序井然,把它們分門別類,依據那些規定了它們的相似性和差異性的名字把它們組集在一起。有史以來,語言就是在這張圖表上與空間交織在一起”。《東方志》涉及的地理區域之間是不同的,它們有著不同的名稱和社會特質;《東方志》涉及的地理區域之間又是相似的,它們共享著同一個“亞洲”的名稱和永恒的現在時間。
《東方志》里面還存在著另一種時間。正如前面引用的有關“馬拉巴爾”的記述,這些靜態的現在時態嵌套在另一個時間框架內,這個時間框架就是敘事者與葡萄牙國王共享的、交流的時間。“事實上,緊跟著環球航行,‘普遍性的時間’在文藝復興時期,就因為政治的原因,得以具體地構建,以回應古典哲學和地理大發現時代產生的認知挑戰。”“普遍性的時間”就是世俗化了的猶太—基督教時間觀。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把《東方志》里面的時間分為亞洲表述主體與葡萄牙國王共存的抽象“普遍性的時間”,以及為這個時間框架所封存的亞洲—印度洋時間。因此我們可以說,《東方志》在書寫亞洲時,其邏輯起點是“時間空間化”(spatialized time)。
《東方志》就好像是一個基督圣徒在與其國王陛下講述其在亞洲各個不同的地理區域獲得的世俗知識的情景。在這個講述的過程中,原本神圣的宗教“時間”世俗化為“普遍性的時間”。因此,《東方志》中的旅行者“我”既是在空間中旅行,也是在時間中旅行,更是在觀念中旅行—隨著“我”的步履遷移,時間流逝,有關亞洲的世俗知識得以累積,“我”/歐洲完成現代的蛻變,成為抽象的“普遍”。異域旅行成為世俗的朝圣。不僅是《東方志》,包括早期近代的其他旅行文本,其中的旅行書寫均可以在修辭上指涉歐洲自身的變遷,所以,其中的旅行者無論走得多遠,最終必然折返歐洲。甚至可以說,遠走他鄉就為了更徹底地回歸自身。就像《東方志》里面的敘事者向國王轉述域外的亞洲知識,原本屬于旅行者過去的經驗,但在文本中卻統一采用現在時態。表面上,亞洲的時間與敘述者和國王共享的“普遍性時間”一致,實際上,這個現在時態像恐怖的詛咒一樣把亞洲社會靜態化了—它一直如此,而且被“普遍性時間”涂抹上了防腐劑,像處理標本那樣凍結并封存。這種時間操縱有效地把歐洲的旅行者從亞洲景觀中分離出來,知識在福柯式的“圖表”中得以分配、安置并秩序化,文化的距離就誕生了,從而凸顯了時間的空間化意義。而這個過程中的亞洲,則被凍結在敘事者“我”的講述中,僅僅是作為歐洲旅行/蛻變的空間/時間參照而永恒存在的。
三、《東方志》的敘述空間架構
《東方志》涉及的地理疆域相當宏闊。敘事者對“東方”的書寫從埃及開始,然后一路向東,經過阿拉伯地區,再向東南方,到達廣袤的印度,越過浩瀚的印度洋,進入東南亞地區,再北上進入中國、日本,又突然折返南下到亞洲最南部的浡泥、菲律賓、爪哇、莫鹿加等群島,最后終止在馬六甲。《東方志》完成于在皮列士抵達中國之前,所以,出現在《東方志》中的部分國家,他根本沒有抵達。葡萄牙人的商業貿易滲透到中國和日本是16世紀后半葉的事情,而且民間貿易成分占了相當大的比重。因此,《東方志》里面呈現的不同地理區域順序頗為怪異。在那個交通不便,語言不通,政治阻隔的年代,這條有點南轅北轍意味的線路,作為山長水遠的旅行設計可能既不經濟,也不完善。這顯然不可能是皮列士的旅行路線,因為皮列士最終卒于中國,而且《東方志》所記述的各區域之間也不是一個連續的物理空間序列,但它的確又是作者刻意規劃設定的,這就意味著該路線在文本層面是完全可行的。從性質上看,《東方志》對亞洲各個地理區域的定位是一種空間排序法,是在歐洲知識“圖表”或坐標中框定亞洲的實踐方式。
《東方志》中敘事者觀念旅行的地理區域順序,盡管不太可能在現實層面付諸實施,但是其序列清晰地遵循了一種具有“后設地理學”(metageography)意味的空間圖式。在《東方志》的地理坐標作為敘事的前提下,其中的整個路線首先呈現為從歐洲到“中近東”(埃及、阿拉伯地區),再到“遠東”(印度、中國、日本、東南亞等)。《東方志》的敘述立足點就是歐洲,站在這個立足點上面向亞洲/東方觀察、想象世界,距離歐洲越遠的地方就被敘事者放置在文本空間的遙遠的末端。“近東”、“遠東”雖然是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構建的文化空間概念,但是在漫長的歐洲世界秩序想象中,“將波斯和埃及之間的區域視作東西方過渡地帶的觀點可追溯到許多年以前歐洲人探索印度洋的時期。”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看到《東方志》作為歐洲構建“現代世界秩序”的某一級知識階梯的意義。這種想象世界的方式,“黑格爾在其表述里面把方向具體化了,他指出在穿越歐亞大陸的過程中,越向東便越能感受到東方的本質。”然而,這樣一種“從歐洲大西洋海岸來觀察世界的視角,造成了嚴重的空間扭曲”,因為黑格爾所謂的“東方的本質”,就是亞洲相對歐洲的“停滯狀態”。“停滯”用來描述一個文明空間時,其中包含著明顯的時間操作的意味,即這個被描述的空間是靜態、永恒的,它來自歐洲觀察者的眼睛,是被歐洲的“普遍性時間”所封存、凍結了的。敘述的時間在歐洲與亞洲之間畫出知識的疆界,并確立了歐洲作為觀察被隔離的亞洲的地位。因此,《東方志》書寫亞洲時使用的現在時態與其地理空間序列安排,是一組一體兩面的“時間空間化”操作。
《東方志》與這一時期的其他多數旅行書寫文本相比較,有著與眾不同的特征—它不是在一種美學的觀照下去書寫作為異域他鄉的亞洲,而是把情感克制壓抑到了幾乎令人感受不到的程度,軍事征服和經濟商貿則被凸顯到了特別重要的地位。這正如前文所提及的,作為一份官方調查報告,作者皮列士非常自覺地在《東方志》中貫徹了一種“實證主義—實用主義”的寫作態度。然而,《東方志》的敘事者同時又用一種“反實用”的旅行路線來布局、呈現他所觀察到的印度洋國際貿易體系,這一矛盾的狀況值得深思。
16世紀,葡萄牙人就其環繞非洲頂端航行的漫長規劃,積極地發起了一輪新的、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探險,這是前往印度十分必要的第一步。瓦斯科·達·伽馬、卡布拉爾、阿爾梅達(Almeida)和以及阿方索·德·阿爾伯克基(Afonso de Albuquerque)等人率領的艦隊進入印度洋國際貿易體系和皮列士《東方志》的寫作,均以此為歷史的地平線。這就是歷史學家所謂的“歐洲的商業重新定位”的年代—直到阿爾伯克基去世的1515年,“葡萄牙帝國已經成功創建了從馬六甲到卡利卡特、果阿、莫桑比克,再回到里斯本這樣一條海上線路的霸權”。然而,作為歐洲的“遠東”的中國與日本依然在葡萄牙海上霸權航線的外緣位置,此時尚處于葡萄牙帝國嘗試性的接觸或想象性的規劃狀態。
在16世紀初期的歐亞關系脈絡中,我們可以看到皮列士在《東方志》里面的設置的縱向“反實用”旅行路線的合理性所在。《東方志》的地理敘事起于埃及,終于馬六甲,從空間上隱喻般地投射了彼時葡萄牙帝國的亞洲戰略構想與拓殖欲望。16世紀初,曼努埃爾王重啟葡萄牙的海外冒險事業,他在探索前往印度洋的貿易路線方面,熱切地呼應了亨利王子十五世紀上半葉在非洲一系列的探險行為,并成功地開拓了亞洲的香料貿易市場。“亨利王子在很多方面的發現都構成了葡萄牙人后來在地理學和歷史學上的理論基礎,”在這個意義上,曼努埃爾王才是亨利王子真正的繼承人,埃及也正是曼努埃爾王海外探險功業的起點。空間書寫從埃及開始的《東方志》,作為一份承奉給曼努埃爾王的官方報告,也共享了這一集體欲望與意識形態氛圍。
四、帝國的欲望地理
如果說埃及是葡萄牙介入印度洋的前哨,印度的果阿是基地,那么馬六甲則是葡萄牙在亞洲的貿易樞紐和終端。早在1511年,勤勉而悲情的“帝國主義夢想家”阿爾伯克基的艦隊就成功地驅逐了馬六甲的蘇丹。這一重要的歷史條件給了皮列士很多可能,比如他獲得了馬六甲香料貿易管理人的身份。馬六甲在《東方志》中單獨占了整整一部的篇幅,皮列士對其歷史、鄰國、行政、貿易以及與葡萄牙的關系等各方面的敘述,也是不厭其詳。關于馬六甲的戰略地位和商業重要性,皮列士有其相當深刻的觀察和認識:“馬六甲的貿易無疑極其重要,……它位于季風的終點,在那里你能找得到你需要的東西,有時超過你的期望。……馬六甲是一個為商品而設的城市,比世上任何其他城市都適宜……。”在《東方志》里面,埃及和馬六甲之間,是廣袤的東(南)亞,很多區域是皮列士從未親自涉足的空間。因此,在《東方志》“第三前言”里,皮列士一方面強調著作所記載的一切,他都“體驗過并且眼見到他們”,另方面又以“裁縫”剪裁布塊自喻其寫作過程。如果說前者凸顯出一種科學的、實證主義的傾向,而后者卻表現出一種虛構的、剪輯組合的寫作手法。這種看似矛盾的亞洲書寫狀況,與其說是在向曼努埃爾王匯報其對亞洲的調查,還不如說是為曼努埃爾王勾畫了一幅葡萄牙帝國在亞洲擴張的想象性地圖。
《東方志》架構中,馬六甲是作為壓軸部分出現的。其前面各個部分涉及的區域間貿易都與馬六甲發生聯系,比如在“第一部”述及坎貝的商業活動時,皮列士就注意道:“坎貝伸出兩條手臂,右臂伸向亞丁,左臂伸向馬六甲,這些是航行最重要的目的,而別的地方被認為是次要的。”“我在談馬六甲時將詳述它的商品。如果割斷坎貝與馬六甲的貿易,它就不能生存,因為它將無商品可出口。”《東方志》中的各個地理板塊看上去松散且不連續,事實上是一個此呼彼應的敘述整體,它們因馬六甲的商業活動而緊緊扭結在一起,共同型構了一個帝國之眼中的印度洋國際貿易互動體系。因此,可以說馬六甲是印度洋國際貿易體系運作的動力源,也是葡萄牙帝國在亞洲殖民規劃和航海探險的輻射點。《東方志》的寫作時段正處在葡萄牙人攻占馬六甲與謀劃遠東之間,事實上,皮列士本人后來就是乘坐西芒?德?安德拉德的船艦前往中國的。所以我們可以把《東方志》里面一系列實際上并不連續的地理排序,尤其是遠東地區被整合、放置在從埃及到馬六甲之間已被征服的區域鏈中(最終托付于歐洲/里斯本),視為帝國欲望和秩序想象在遠東地理上的投射—空間圍堵與時間封存相互協調合作。
正如拉赫所觀察的那樣:“雖然葡萄牙的編年史家們把東方大部分地域都包括進了各自的探討范圍,但他們對海島世界的討論很不充分,爪哇尤其如此。”雖然拉赫沒有明確提及《東方志》,但作為葡萄牙帝國在16世紀關于亞洲的重要文獻,《東方志》同樣有其主觀性。不過,拉赫對16世紀的歐洲有關亞洲/“東方”的綜合性評價,依然建立在“反映論”的基礎上—這些文獻可以作為紀實性的信息來參考。在本文的立論基礎上,《東方志》的反“實證主義”并非拉赫所謂的“局限和民族偏見”,而是一種文本的“政治無意識”,其中的“偏見”恰恰最真實地表達了某種歷史欲望。
五、時間與政治宇宙學
當然,倚重“時間空間化”修辭的《東方志》里面的普遍性時間并非一個密不透風的敘事囚牢。皮列士在《東方志》里面多次提到曼努埃爾王權杖所及的印度洋國際貿易狀況是如何地和平、有序、繁榮。比如,德坎“是一個富庶和高貴的停泊港,有許多船只,陛下對這些港口很不關心,所以它們遭到了破壞;而第烏,因陛下的支持,從荒涼變得強大。”關于葡萄牙人占領后的果阿,“從今以后,果阿將成為比過去更大的停泊港,商人在我們的管治下將比在摩爾人治下更加愉快。”當葡萄牙人占領馬六甲之后,“馬六甲又開始歡迎商人,有很多人到來”。事實上,這類敘述使《東方志》的時間嵌套,即敘事者采用現在時態構造的普遍性時間包裹亞洲時間的敘述結構,出現了一個幾乎無從補救的敘述裂口:《東方志》表達赤裸裸的帝國愿景時必然要涉及葡萄牙人介入印度洋的壯舉,其敘事每當到了這一環節,現在時態設定的靜態的亞洲時間與歐洲的普遍性時間之間的區隔關系就變得復雜起來。如果敘事者對此無動于衷,“時間空間化”的修辭就會產生危機,對歐洲與亞洲進行區別對待的非共時性就無法實現。
為了討論該問題,我們有必要把介入印度洋國際貿易體系的葡萄牙人在與當地人發生實質性交接的瞬間進行放大,并與時間嵌套中的其他兩種時間,即普遍性時間與亞洲時間進行比較:

敘述(例證)時態時間人稱在這果阿國,流行的風俗是每個異教徒的妻子在其夫死后活活自焚。他們自己對此評價極高(It is mostly the custom in this kingdom of Goa for every heathen wife to burn herself alive on the death of her husband.Among themselves they all rate this highly,……)。(皮列士49,Pires 59)現在時態永恒的、靜態的亞洲時間第三人稱如果陛下沒有把此城據為己有,那么現今它會是摩爾人的,因為有個馬摩勒·梅卡爾(Mamalle Mercar),開始變得極強大(If Your Highness had not taken this kingdom under your rule,it would be Moorish by now,because a certain Mamalle Mercar was beginning to be very powerful.)。(皮列士59,Pires 77)虛擬時態(假設、愿景)、過去正在進行時態多變的、動態的普遍性時間第一、第二人稱果阿正準備使基督徒遭受重大損失,但上帝的裁決反使他們受創,當果阿被攻占時,摩爾人痛苦地呻吟(Goa was preparing to inflict great losses on the Christians,but God’s judgement turned the loss upon them,for there is no doubt that Moors groaned when Goa was taken.)。(皮列士47,Pires 56)過去時態與當下互為參照的、有生命的時間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
前文已經論證了《東方志》里面的兩種敘述時間及其關系。正如上表任意摘錄的引文所示,當敘事者在用現在時態論及亞洲各區域的居民制度或風俗物產時,就像在講述一個從來如此的古老故事那樣,其暗示的時間意識總是一種永恒的靜態感,過去如此,現在如此,以后仍將如此;而敘事者以“我”的姿態,打斷文本中的亞洲風物展示場景,與想象中的葡萄牙國王交流時,我們感受到的是另一種有生命的、現實感特別鮮明強烈的多變時態—多種時態組合、交織,共同營造出一個僅屬于當下的交流情景和氛圍。這種交流的氛圍把亞洲的各個區域的敘述納入其中,而敘事者是自由的,那個歐洲的“我”可以在任何覺得有需要的時間和地方直接現身或隱身,中止或繼續關于亞洲的任何話題。這種時間修辭的操縱,最重要的(空間)效果之一就是設定了亞洲與歐洲在文本中的非共時性關系,相對歐洲,亞洲像是一個死去的、靜止的地理板塊或文明單位。
那么,當葡萄牙帝國與亞洲發生實質性互動的時刻,敘事者又是如何處理其中的時態與時間的呢?《東方志》的敘事主干是一場交流,即一位葡萄牙駐外使官對國王講述他在亞洲的經驗與見聞,亞洲其實是被排除在敘事主干也就是交流情景之外的,是外在于“我們”的“他們”。然而,當敘事者以葡萄牙使官的身份述及“我們與他們”時,雖然這些內容依然被嵌套在普遍性時間/“我們”的交流時間之內,但至少可以看到兩種特殊的處理:一是靜止的現在時態被轉換為動態的、表示發生過的過去時態;二是封存在普遍性時間之內的葡萄牙人借助人稱代詞鋪就的通道,直接參與到普遍性時間中來了。過去時態之所以屬于過去,它參照了敘事者所在的當下,換句話說,過去時態的敘事效果是動態的,過去時態才真正顯現敘事者對所述之物的自信。相對而言,現在時態類似于一種文學敘事,它的靜態處理方式,是避免敘事者因無法完全掌控其所述之物而導致的尷尬的有效手段。因此,這里的過去時態潛在參照的不是亞洲的永恒、靜態的現在時態,而是敘事者講述的當下,即普遍性時間。由此,這個用過去時態敘述的葡萄牙人與亞洲交接的瞬間,仍然是有生命的、動態的。除此之外,這兩句引文中包含的人稱也值得考察。“果阿”“摩爾人”和其他關于亞洲地理區域的敘述一致,毫無疑問是第三人稱的;“基督徒”“上帝”在純粹的語法意義上也是第三人稱,但“果阿被攻占時”里面省略的部分告訴我們,這句話完整的表述是“果阿被我們葡萄牙人攻占時”,于是,“基督徒”“上帝”在文本的敘事意義上就等同于“我們葡萄牙人”,而獲得了第一人稱的敘事效果。同樣,“阿豐索·德·奧布魁克,大船長和印度總督,在……”里面的阿豐索·德·奧布魁克自然是第三人稱,但是其同位語“大船長和印度總督”明確暗示了他是“我們”的“大船長和印度總督”,由此,第三人稱的語法獲得了第一人稱的效果。通過這樣一種人稱代詞的置換通道,第三人稱的葡萄牙被敘事者成功引渡出時間的囚牢,順利回歸到屬于“我們”的普遍性時間中。當然,這條借助人稱代詞鋪就的通道只歡迎敘事者的同胞葡萄牙人,過去時態中的“他們”仍被阻隔在外。
- 國際比較文學(中英文)的其它文章
- ICL人物
- 投稿須知
- 一流國際化期刊建設與中國期刊人的責任擔當*
——第二屆一流期刊建設高峰論壇暨人文青年學者學術研討會綜述 - 吳真:《孤本說唱詞話〈云門傳〉研究》
- Charles William Johns.The Irreducible Reality of the Object:Phenomenological and Speculative Theories of Equipment
- An American Scholar’s Research on Chinese Wome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An Interview with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Gail Hersha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