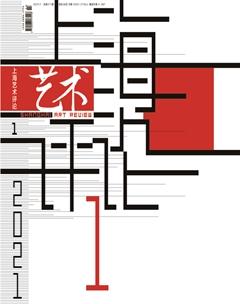略談“藝起前行
胡曉軍
“藝起前行—優秀新創舞臺作品上海展演”于2020年11月中旬圓滿閉幕。作為全國抗疫任務最艱巨、表現最出色的城市之一,上海以自信而又審慎的態度、熱情而又冷靜的行動,完成了這場歷時一個多月的大型展演活動,讓寂寥多時的上海舞臺重現歷年金秋盛況,讓渴盼多日的上海觀眾得享戲劇審美盛宴。
嚴格防控作為本次展演的頂層設計,在具體的運作中得到了自始至終的踐行。在劇目的性質、新創的標準、觀演的規約等各方面,都有縝密的預案、嚴謹的實施,尤其在劇目的選擇、演出的場次上更到了精挑細察的程度。綜觀所有參演劇目,兩大共性十分明顯,一是均為近年原創、多次打磨、受重點扶持的精品力作;二是均涉及了新時代的重要題材和重大主題,包括革命歷史、精準扶貧、生態文明、共奔小康、科技強軍、反腐倡廉等。多樣的題材,不同的題旨,一起匯聚到一個大的主題—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展現出歷史與社會發展要求相通的時代潮流,文藝與人民群眾期待相應的精神面貌。可以推想,隨著“十三五”收官和“十四五”開啟,隨著“五位一體”戰略格局的展開與收獲,隨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識成立與扎實構建,“主旋律”的文藝疆域會越拓越廣,“正能量”的創作路徑會越走越寬。與此相應,在幾十年的不斷堅持和不懈探索下,“主旋律”的創作理念愈趨成熟,“正能量”的藝術呈現愈發精美,對此喜聞樂見、津津樂道的觀眾數量也愈加增長。《亮劍》《潛伏》《戰狼》系列等熱門影視劇姑且不談,僅舞臺藝術便俯拾皆是,例如話劇《郭明義》《谷文昌》,豫劇《焦裕祿》《重渡溝》,舞劇《永不消逝的電波》等均巡演全國各地、廣受觀眾贊譽。因此,我們有必要對本次參演的外地劇目做一次梳理,分析它們在題材選擇、主題呈現、藝術風格上的堅持與變化、守正與創新,為上海的舞臺藝術創作提供參考和借鑒,此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展演已經結束,卻堪比那繽紛花事雖過,空中猶有余香存焉。筆者僅以所觀略談感受,猶如品其余香,既當過往的回味,又作未來的期待。
就地取材,深耕厚植本土原創。此次外地展演劇作的一個明顯特點是,題材多為本土,人物多為本地,故事大多圍繞本土本地開展,同時向外輻射。北京京劇院京劇《李大釗》、廣西壯族自治區戲劇院彩調劇《新劉三姐》、西安話劇院話劇《長安第二碗》等均如此,從而形成了一種現象級景觀。可以看到,主創們懷著對本土人物、故事、風土人情的熱烈情感和強大自信,作了深入的思考、深度的解讀和深遠的開發,并以獨特的戲劇構思及藝術手段展現出來。例如川劇《草鞋縣令》演繹清嘉慶年間什邡縣令紀大奎勤政廉政的故事,這是川地真人真事,以家鄉劇表現可謂理順、情暢而藝達。又如話劇《深海》以相似的戲劇結構,表現了“中國核潛艇之父”黃旭華的事跡,隨著時間的推移,相關事件的解密,中國強軍的艱苦歷程與偉大成就,奉獻一生卻默默無聞的前輩英雄正陸續被文藝作品加以挖掘和表現,成為激勵民族精神、鼓舞群眾心志的重要文化資源。黃旭華院士是廣東省汕尾市人,他的幾十年心路歷程由廣州話劇院來演繹,自是順理成章—君是本鄉人,最知本鄉事,這是“生活是創作的唯一源泉”的更切近、更鮮明的體現。
在眾多再現日寇攻占南京、中華民族遭遇浩劫的文藝作品中,江蘇大劇院的話劇《朝天宮下》顯得特立獨群。該劇并未表現戰斗場面,也不展示屠殺慘狀,而是演繹了幾位文化人在南京朝天宮中守護一批“南遷文物”的故事。這臺以“文化抗戰、文脈抗戰”為核心主題的話劇,之所以顯得極罕見而又極必要,顯然仰仗于江蘇本土、南京當地曾發生過的一段真人真事。概言之,歷史的“地氣”撐起了創作的底氣、藝術的勇氣和戲劇的場氣。更可貴的是,《朝天宮下》百分之百地使用了本土編導演員,實現了“就地取材、就地用人、就地生產、凸顯江蘇原創水平”的追求。所謂“文章腳下做,不須遠方求”,正是“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的具體表現。要注意的是,在互聯網時代的當下,這一創作現象及趨勢已與固步自封無關、與畫地為牢無關;恰恰相反,而是與本土文化自覺、文化自信的增長有關,與文化開放同步、藝術信息共享的現實有關。這與十幾年前曾一度風行的戲劇創作,在題材上好高騖遠、在主創上舍近求遠的狀態形成了鮮明的反差,也從某一個側面反映出浮躁的創作心態、虛空的“大作”思維正逐漸消散,而“各顯其能”“各出新招”正成為戲劇創作的新格局,并通向“百花齊放”的好局面。
守正創新,立足本體拓疆擴域。許多外地劇目在深挖并呈現本土歷史、人物和事件的同時,又根據劇本實際,在思想性上拓寬廣度、在藝術性上嘗試突破、在觀賞性上進行強化,力求使作品既具備扎根本土的魅力,又擁有走向全國的能力。仍以《朝天宮下》為例,主創借助祝同禮假造文物清單的情節,以大篇幅介紹了具有代表性的中華文物,最后以臺詞“文物一毀,文化一忘,民族國家永無復興之望”;主題歌詞“記住這一刻,記住這一切,血脈與文脈相連,文脈與國脈相接”,彰顯了全劇的意旨。這一劇情設計,可謂匠心良苦。《草鞋縣令》作為原創作品,既保持了主唱腔和“幫打唱”,又特意以名角為核心,添加了不少超出傳統程式的唱做手段,更摻雜了一些當代詞匯。此舉效果優劣,暫時不談,卻可看到外地戲曲原創勇于革新的膽量及踐行能力,這無疑是將歷史故事與當代現實相勾連,主動實現“以古鑒今”的有力嘗試。
京劇《李大釗》的戲劇結構,也采用了片段法,將全劇劃分為教導學生、營救同志、組織罷工、創建我黨、從容就義等幾個重場戲,并以重點唱段作為各場戲的“重中之重”。此舉為名角提供了充足的發揮空間,代價是損失了人物完整的交代和塑造,故而難以稱其為一部人物傳記劇,而應視為一部抒情詩歌劇。主創之所以如此選擇,既可能基于人物及事件的戲劇性較弱,原創尤其是虛構的著力點較小;但也可能基于“以表演為中心”的戲曲觀,于是在唱詞的通俗、板式的正宗、音樂的調和尤其是流派的表現上著力最大。不重戲劇結構的嚴謹和唱詞邏輯的縝密,而更注重音韻的流暢性和演唱和舒適度,這是京劇在早期和全盛期的突出表征,《李大釗》的主創將其用于紅色現代題材,似可視為對這一傳統的“回歸”。甚而言之,在戲曲創作思維基本被納入整體戲劇思維的當代,戲曲唱腔藝術完全服從于戲劇文學的當下,這種“回歸”因其稀缺,竟也有了幾絲“創新”的意味。另外,《李大釗》還創造性地將《國際歌》旋律與皮黃腔結合起來,奉獻了一段酣暢淋漓、震撼人心的曲子,成為全劇的一大亮點。彩調劇《新劉三姐》的音樂主體采用了“老劉三姐”曲調,卻屢有翻新,主要是基于不同人物的性格、心情加以靈活的變化,在大樂團的伴奏下呈現出介于山村和都市間的多樣化聽覺審美感。該劇的歌詞寫作也頗具特色,編劇采用了大量比興、隱喻和諧音、頂針等技巧,在體現少數民族民歌特點的同時,又加入了唐詩宋詞的詞句和意象,再加上當代網絡語匯,呈現出純粹與綜合、傳統與時尚、生活與哲理并存共揚的美感。與之異曲同工的是歌劇《扶貧路上》,該劇采用了壯歌旋律和比興風格,歌詞猶如潺潺溪水,在政治性與文藝范之間蜿蜒流淌,營造出既莊重又活躍的時代氣質,流露出既嚴肅又輕快的青春氣息。
常州市滑稽劇團的《陳奐生的吃飯問題》,將本屬于話劇的沉重主題與本屬于滑稽戲的詼諧風格,十分完美地結合了起來,完成了一次對滑稽戲本體的有力且有效的突破。該劇以時間為線索,演繹一個農民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五十多年的悲歡遭際,反映改革開放前后農民生活、命運、觀念、情感的巨大變化,進而全景式地映現中國在“三農”問題上走過的彎路以及反思糾偏、改革進取、發展成功的歷程。該劇視角獨特,開掘深刻,表現曲折,笑料充足且有的十分巧妙。最關鍵的是,主創對這一劇種作了明顯的改造或大量的拓展,諸如主演一演到底、臺詞全部用普通話、取消“什錦戲”等。盡管對演員作了偶戲化裝的處理,并加入了眾多人偶的舞蹈場面,但該劇依然難以阻止觀眾產生“名為滑稽戲,實為話劇”的印象。筆者的看法是,該劇主創借用了滑稽戲的軀殼,注入了北方話劇的厚重質感,卻也保留了滑稽戲的鬧劇質地,再加上人偶戲提供的夸張因子,產生了傳統戲曲性的間離效果,營造了類似荒誕派的滑稽風格。該劇的步子貌似邁得很大,但從歷史上看,滑稽戲正是由話劇派生而來的新劇種,因此該劇仍以滑稽戲命名,也不能算名實悖離。筆者不禁想起,十幾年來確有不少原創戲劇,尤其是原創戲曲因“本體不可絲毫毀傷”的觀念束縛,多少遏制了主創的想象力和演員的創造力。其間,盡管有人試圖以多媒體、歌舞隊等予以補救,卻只能算是表面文章,所謂“突破”僅在浮面。真正的高手,能根據題材、觀念、情感的需要,利用原創適度拓展劇種本體,以求獲得出人意料的好的效果。當然,這樣做是有風險的,不僅成敗難料,而且口碑叵測。其中關鍵之一,在于劇種本身須具有較大的可塑性和靈活度—滑稽戲自是其中最合適的突破對象、最自由的創造載體。總之,《陳奐生的吃飯問題》既堅持了“滑稽戲的生命是笑”(童雙春語)之說,又堅持了“話劇絕不是由人來白相的”(田漢語)之言,是一臺公認的好戲。我們與其多爭論其在劇種定位上的“錯位”,倒不如多欣賞其對本體的一次卓有成效卻難仿效的突破,一次度身定制而難以復制的成功。
精益求精,呈現精美文化食糧。此次參演的外地劇目,演出規模都比較大,最大者如《新劉三姐》,演職人員達近三百名,包括了當地最好的彩調劇演員、山歌手以及實力強勁的特邀演員,滿臺歌舞幾乎找不到短板或弱項。眾所周知,戲劇表演貴在“一棵菜”,所謂“主角配角,角色不分大小;大戲小戲,戲份不問多少”,所有人都為全劇服務,都為全劇奉獻。在“一棵菜”精神的統領下,該劇回旋往復的歌聲配上平衡車的自由滑行,婉轉變化的旋律配上山清水秀的舞美渲染,令觀眾的耳朵和眼睛就像懷了孕那般幸福。彩調劇是一種由多個少數民族的山歌、民謠發展壯大而成的地方戲,本體十分開放自由。作為原創劇目,《新劉三姐》充分地體現了彩調劇在“勾兌”“混雜”上的能力及水平,并很好地延續了彩調劇通過好看、好聽、好玩的審美,傳達積極、健康、樂觀的價值取向的特點。在參演的上海劇目中,與之相呼應、相媲美的,是上海越劇院以云南扶貧為題材的《山海情深》,既表現了少數民族的能歌善舞,又展示了越劇的青春靚麗,堪稱雙璧合一。
筆者認為,任何藝術創作—包括了“主旋律”創作、特別是“主旋律”創作,對觀賞性的注重和投入是極重要和極必要的。若觀賞性低下,主題思想再好也無法感染觀眾、贏得人心;若觀賞性上佳,則其義自顯、其意必彰。這在上海近幾年出品的舞劇《永不消逝的電波》、雜技劇《戰上海》等身上已有了最鮮明的印證。至于戲曲,我們可再回顧一下“以歌舞演故事”的定義。筆者認為,王國維對“歌舞”與“故事”的地位和比重,并沒有孰輕孰重的判定,而是均衡、統一、互為的整體。若兩者差距過大,則很容易出現不匹配,導致文學性不足、技藝性過剩或相反—這正是彩調劇《新劉三姐》、越劇《山海情深》這樣的劇作主創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難點。
歌劇《扶貧路上》和話劇《山海情深》則從另一條路線達成了它們的觀賞性。《扶貧路上》以廣西百色市樂業縣百妮村第一書記黃文秀的事跡為中心,以小見大地展示了全國精準扶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收官之年,在各地脫貧攻堅戰線上奮斗、奉獻、犧牲的黨員干部群像。該劇的結構、情節顯得頗為簡約,唱詞、音樂則非常優美,舞臺裝置更是令人眼睛一亮—多個幾何框架組合,按照戲劇情境或人物心情變化內容及色調,主演、配演及歌隊、舞隊就在這些幾何框架中或佇立、或行進、或穿梭,電腦燈和多媒體則隨之而變化,顯得立體而鮮活,將鄉土氣息與現代氣質有機地融為整體。由此可見,科技進步為舞臺藝術提供了更多更新的呈現理念及手段,劇作的思想情感在技術的支持下獲得了更廣的意境時空和更高的觀賞價值。《山海情深》擁有震撼力十足的多媒體動態畫面、金屬感飽滿的舞臺機械裝置,對該劇特定的題材、傳統的結構、質樸的人物言行都起到了很好的“包裹”“涂色”、渲染作用。難得的是,兩劇的演員們在如此強大的舞臺裝置、如此多變的多媒體動態背景下,神采絲毫不減,無論形象、歌喉還是臺詞,都展示完美、演繹厚重甚至動人心魄,實現了將劇作的思想性、藝術性與舞臺觀賞性的高度統一。
綜上所述,筆者所觀“藝起前行—優秀新創舞臺作品上海展演”的外地參演劇作,在上述三個方面表現出了很高的智慧和很強的能力,取得了較好的成效。歸根結底,這是因為有了廣闊的生活基礎、開放的創作觀念、豐富的表達手段,使“主旋律”找到了思想提升的平臺、藝術突破的可能、爭取觀眾的資本。盡管這些劇目守正創新的程度各有不同,取得的成效見仁見智,但從廣義和長遠看,都是意義深長、意味深遠的—正所謂“藝”起前行,這是舞臺藝術工作者對傳統、對藝術的主動探索,對社會、對觀眾的應有回應,對新時代新征程的一次昂揚奮發的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