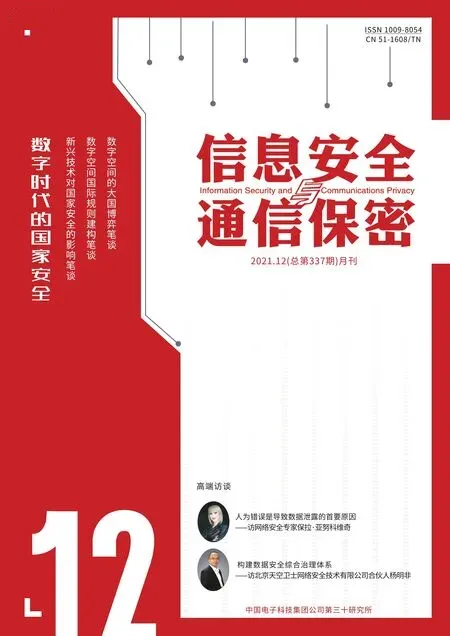數字空間國際規則建構筆談*
郎 平,李 艷
0 引 言
隨著大數據、云存儲、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當今世界正在從網絡時代邁向數字時代。如果說網絡時代的“網絡空間”是指基于一種基于分布廣泛、互聯互通技術的人造空間,那么數字時代的“數字空間”則有著更加廣泛的數字技術作為人類活動的根基。與網絡時代相比,數字時代既延續了前者的發展脈絡,又有著不同的演進動力和核心問題。在數字時代浪潮撲面而來的當下,重新審視網絡空間國際規則的制定進程,展望其未來發展的特點與趨勢,有助于我們在歷史的長河中加深對這一進程的理解與把握。
1 對數字空間國際規則構建的重新審視①郎 平(1972—),女,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網絡空間國際治理與大國關系。本文作者排名不分先后。
談到數字空間國際規則的構建,首先要思考的是,近年來,當我們開始更多地使用“數字時代”和“數字空間”來取代“網絡時代”和“網絡空間”時,我們所賦予這兩對詞的內涵究竟有何不同?從概念上看,隨著網絡空間的內涵和外延不斷擴大,網絡空間的概念界定被逐漸泛化,這兩對詞也常常被互換使用,但同時,當我們選擇其中之一時,背后又有著明顯不同的側重和邏輯。韓國互聯網之父、國際互聯網名人堂入選者全吉南認為,和網絡空間相比,數字空間是一個更加中性的詞匯,前者常常與網絡安全和網絡戰爭聯系在一起,后者則更多與數字經濟和數字社會的語境相適應;數字空間是一個以互聯網和其他網絡為基礎設施,涵蓋人工智能、數據、物聯網、網絡安全和社交媒體等不同層面的數字經濟和社會空間[1]。
接下來,回到治理的三個基本問題——治理什么?由誰治理?在哪兒治理?——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從網絡空間治理到數字空間治理的時代變遷。從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10年代中期,網絡空間國際治理從域名和IP地址等基礎資源層的治理逐漸向社會、經濟和安全領域擴展,例如個人信息保護、網絡攻擊、網絡犯罪、網絡空間負責任國家行為規范,治理框架主要包括IETF、ICANN、IGF、UNGGE等;治理模式主要遵循多利益相關方框架由政府、私營部門、非政府組織、技術社群等共同參與治理,但隨著議題的政治性和安全性逐漸增加,政府在多利益相關方框架中的主導地位也隨之升高,政府間雙邊和多邊合作機制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
21世紀10年代中期之后,以特朗普政府上臺為標志性節點,網絡空間不僅是大國競爭的重要領域,更成為大國謀求其戰略目標的重要工具,特別是數字科技的技術標準、人工智能倫理、數據和數字貿易、供應鏈安全、信息操縱等問題正在成為大國博弈的焦點,亟待制定相應的國際規則來規范國家間的互動。上述問題的治理模式是以國家行為體為主導、非國家行為體參與的多邊、多方治理模式,但是相比較前一階段,私營部門和技術社群等非國家行為體基于其自身掌控的資源和權力逐漸擁有越來越大的話語權。
那么,回到當下數字時代的起點上再來審視網絡空間國際規則的制定進程,我們可以看到兩類進程:一類是技術社群主導的互聯網基礎資源層的治理進程,這類進程具有較為確定和穩定的治理機制和模式;另一類主要是政府間圍繞經濟和安全規則的談判進程,由于大國利益的沖突,在治理機制和路徑上還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尚未達成較為普遍的全球規則。從國際關系的視角看,第二類規則制定進程無疑更值得關注和研究,其中又可分為三種情況:一是聯合國框架下有關維護國際安全與和平的議程,如UNGGE、OWEG以及UNIEG。這些治理機制已經持續較長的時間,具有較強的穩定性,在規則制定方面已經形成了某種共識,未來的進程走勢有較強的可預期性;二是數字經濟規則制定進程,如WTO、APEC、G20等。這些治理進程都具有“老平臺”“新議題”的特征,機制具有穩定性,但是成員國之間的博弈還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結果如何還不可預期;三是有關新興技術標準、供應鏈安全、數據安全等新議題,到哪里去制定規則目前還在爭議之中。這些新議題的談判進展與中美兩國的競爭態勢直接相關,最終走向取決于雙方在全球治理理念和實施路徑層面的博弈。
在國際秩序構建的理念上,中美目前圍繞什么是真正的多邊主義正展開激烈交鋒:與特朗普政府更多依靠單邊和雙邊機制不同,拜登政府上臺后美國雖然宣布回歸多邊主義,但其更強調要依靠盟友和民主價值觀相同的國家來制定多邊規則,而中國則主張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主義,認為以聯合國憲章和原則為基礎的、平等相待、合作共贏才是真正的多邊主義。這種理念和路徑沖突將會直接影響到網絡空間國際規則的制定。2021年9月,美國總統拜登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演講,表示美國正在加強關鍵基礎設施以抵御網絡攻擊、破壞勒索軟件網絡,并努力制定適用于所有國家的明確的網絡空間規則;美國不能再繼續打過去的戰爭,而是要將目光集中于和將資源全部投入對未來具有關鍵意義的挑戰上,包括在貿易、網絡和新興技術等關鍵問題上塑造世界規則;同月,美歐貿易和技術委員會(TTC)發表首份聯合聲明,宣布達成六項共同承諾,涉及投資審查、出口管制、人工智能系統、半導體供應鏈伙伴關系、全球貿易政策等內容,都與中國展開科技競爭直接相關。
進入數字時代,科技與網絡空間成為數字空間國際治理的兩條軌道,而這里的“網絡空間”又重新回歸文初的狹義界定。全球治理的本質是為了應對共同挑戰,通過相互協商來達成集體行動,從而實現共同發展或維護國際安全與和平。網絡空間國際規則的制定也遵循同樣的邏輯,由解決問題或避免沖突的動機所驅動,一方面是由于網絡空間的虛擬屬性而帶來的安全威脅如何應對的問題,其核心是網絡空間安全問題;另一方面是大國競爭背景下數字科技創新所帶來的利益分配和秩序重塑,其核心是科技創新和發展問題。從規則制定的進程來看,這兩個軌道目前呈現出既相對獨立又彼此關聯的態勢:因為解決問題的性質不同而相互獨立,同時又因為兩個空間的元素存在相互交叉而彼此關聯,例如數據之于前者是互聯網平臺治理的重要一環,之于后者則是數字經濟競爭的重要內容。
2 數字空間治理體系初探①李 艷(1976—),女,博士,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科技與網絡安全所副所長,主要研究方向為網絡安全戰略與國際治理。本文作者排名不分先后。
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應用不斷驅動信息社會發展進入新階段,特別是在全球疫情影響下,“線上”形態的社會活動更加普及,使得國際社會對于未來可能社會形態的具象更加清晰,“數字空間”的概念得到更多的關注與呼應,并且開始探討數字空間治理體系的構建與發展。
2.1 理解“數字空間”
一般而言,“空間”是人們對所處客觀環境的一種感知和客觀描述。著名的社會學家蘇賈提出:“空間可以分為物理空間(第一空間);精神空間(第二空間);第三空間既是生活空間又是想象空間,是人們進行社會活動和選擇的場域”[2]。在他看來,空間既可以是現實存在的,更可以是人們“選擇”或創造出來的空間,但無論如何,具有社會學意義的“空間”更加關注人類社會活動的開展與社會關系的存續,并進一步認為所有空間的共性都在于是人類利用技術與應用手段獲取資源與拓展活動范圍并形成社會關系的空間。比如人類對于海洋空間的探索離不開航海技術,對于太空的探索離不開航天技術,對于網絡空間的探索離不開互聯網技術等。
正是對于空間的這些認知和理解,奠定了當前對各種技術與應用催生下“新空間”探討的基礎,從之前的“網絡空間”到當前的“數字空間”皆遵循這樣的認知邏輯:一是觀察技術與應用的不斷創新對傳統空間的變革性影響;二是分析技術與應用“創造”什么樣的人類活動新空間;三是研判這些“空間”中人類社會生產活動與社會關系的互動與變化。
2.2 “空間”的數字化轉型與升級
目前國際社會學界與政策界對于“數字空間”并沒有明確的界定,中國的科學家們較早明確提出“數字空間”的概念。中國科學院院士魏奉思認為,從字面講,“數字空間”指地球之上空間的認知與應用通過數字化構建的空間。他在一次發言中提到:“近10年來,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把對空間的認知與應用納入信息化發展軌道,實現科技與經濟的融合,更好地為人類社會發展謀福祉。‘數字空間’無疑是一個好載體、好抓手,這是擺在我們面前亟待起步的一個重要戰略新領域。隨著空間科技的進步、認知水平的提高、利用能力的增強、應用開發的拓展以及現代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所有這些都向我們呼喚:‘數字空間’時代要到來了。”[3]他還特別強調,“數字空間”是將空間的科學、技術、應用和服務融入現代信息技術發展軌道的一個空間科技前沿交叉新領域。
由此可見,在科學家眼中,“數字空間”是經過數字化,即依托衛星探測、通信導航等空間通信網絡,融入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處理技術,將各種包括傳統意義上的海、陸、天、空以及“網絡空間”在內的所有空間“數字化”的結果。其目的是利用新一代信息技術提升人類空間利用開發能力與效益。因此,與其說“數字空間”是一個新空間,不如說是所有空間的數字化“轉型”與“升級”。
正如2021年6月28日中國移動董事長楊杰在世界移動通信大會上的主旨演講中所言:“隨著以5G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加速融入經濟社會民生,一個與現實世界映射共生的數字空間正逐漸形成。未來,伴隨人們娛樂、溝通、交易等各項生活、生產活動加快向數字空間遷移,信息技術、數據要素對傳統人力、資本要素價值的放大、疊加、倍增效應將日益顯現,進而推動人類突破發展瓶頸,實現生產力躍升。可以說,數字空間的拓展過程,本質就是經濟社會數智化轉型的過程,即以信息技術、數據要素改造現實世界的過程”[4]。由此可見,數字空間不僅是現實社會的映射,更是一種共生,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會伴隨著進一步的數字化與智能化轉型,從而形成一種新的社會形態。鑒于此,科學家們將“數字空間”的發展提升到打破當前世界空間格局的重大戰略舉措的高度。
2.3 數字空間國際治理面臨重大挑戰
數字空間的良性、有序發展的戰略重要性不言而喻,能否跟上形勢發展需要,實現有效治理,使得數字空間保持良性發展,真正造福于人類,是信息時代背景下,國際社會共同面臨的重大挑戰。但人類歷史發展實踐證明,任何新生事物發展的規律都是機遇與挑戰并存。數字空間作為所有人類空間的“數字化”轉型,它帶來的挑戰更是前所未有。
一方面,數字空間會是一個與現實世界映射共生的關系,這就意味著現實空間的諸多治理問題將在數字空間得以延伸。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延伸不是簡單的“照搬”,而是會因為“數字化”而產生一些新的運轉特點,從而不斷帶來新的問題。典型代表如數據的權屬問題,現實空間中確定權屬是實現權益和有效保護的基礎。但在數字空間,數據的產生、存儲、流轉與交易無時不刻不在發生,數據的權屬難以照搬現實空間的運轉邏輯,從而使得權益主張與安全維護都面臨很多現實困難。目前國際社會各方均在實踐中不斷摸索,試圖從理論與實踐中找到能夠真正適用于數據治理的有效解決之道。
另一方面,數字空間并沒有消解傳統現實空間,而是會不斷給現實空間帶來變革性影響,這種影響反過來又會不斷反饋到數字空間。典型代表如AI發展與應用的問題,雖然AI的社會應用總體上還處在發展初期,但其對現實傳統空間的變革性影響已經初露端倪。在經濟領域,AI技術正在帶來產業與勞動力結構變化;在軍事領域,AI技術正在掀起新一輪軍事革命,極有可能重塑各國軍事力量格局; 在社會領域,AI技術應用帶來的系列倫理問題,尤其是著眼于人類未來可能面臨的“人機雙智”共存的前景,AI發展應遵循怎樣的倫理其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人類對未來的選擇。
2.4 數字空間治理體系的不確定性
影響治理體系的因素有很多,評估治理框架的要素也有多重選擇。如果基于全球治理框架下去思考這一問題,可以發現,從當前發展態勢看,未來數字空間治理體系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
首先,數字空間治理的理念不確定。在國際社會開始探討網絡空間國際治理問題時,正值互聯網的全球普及,邏輯起點是網絡空間的技術架構,強調其互聯互通的價值,因而形成一種主流共識,即“沒有哪一個國家或哪一個主體能夠解決所有的互聯網治理問題”。國際合作,特別是多利益相關方的合作應該被看作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的必然選擇。雖然近年來,受地緣政治影響,該理念在實踐中受到相當沖擊。但客觀來講,國際合作的思維慣性還在,比如各主要大國仍然強調通過信任措施來控制沖突;比如國際社會在面對所謂網絡空間“巴爾干化”時,仍然呼吁要避免網絡空間的碎片化。中國更是提出要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5]。
但數字空間發展所處的歷史環境卻有顯著區別,它不是處在一個強調“互聯互通”的國際環境下,而是受到地緣政治博弈加劇的影響,數字空間從發展伊始似乎就充斥著競爭與博弈。縱觀當前圍繞5G、數據、人工智能以及各種所謂“前沿技術”,這些數字空間賴以存在與發展的技術架構與基礎,從一開始就是國際戰略競爭的重點,特別是美國出于遏制的需要,更是將這些領域作為“主戰場”。如果這樣的國際環境持續下去,可以想見未來數字空間治理難以形成基于基本共識的治理理念。
其次,數字空間國際治理機制不確定。同樣,參照網絡空間國際治理機制,相對成型或確定的治理機制會表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治理主體基本確定。比如網絡空間治理涉及問題多元且復雜,秉持多利益相關方共同參與,實踐中要基于議題發揮各自的優勢與作用;二是治理客體較為清晰。比如規范網絡空間各主體行為。國際社會普遍認為網絡空間的各種危害,如網絡犯罪、網絡恐怖主義以及網絡攻擊根源在于各主體的惡意利用網絡空間,因此強調有效約束各主體行為,如打擊網絡犯罪與恐怖主義,推進國際法在網絡空間的適用等;三是治理目標相對明確。國際社會認為,網絡空間存在的各種分歧根源在于發展問題。各國處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發展與安全訴求,因此,促進發展,尤其是幫助消除數字鴻溝,是實現發展與安全的必由之路。
當然,當前對于“數字空間”治理的探討剛剛開始,治理的主體、客體與目標還沒有共識。但以目前發展態勢來看,相關國家更加關注在新一輪技術與應用浪潮中如何占得先機,表現在國際治理層面,對于公共事務的關注更多集中在對各種技術標準與應用規范的規則制定權的爭奪上。以數據跨境流動規則為例,技術與數字經濟發達的國家更加偏好要讓數據流動起來;而欠發達國家則更關切數據的保護問題。因此,當前有關數據流動規則的構建更多呈現出雙邊或區域性安排的特點,尤其數據流動呈現“小圈子”態勢,美歐等國更是提出流動要基于信任,甚至基于共同價值。如果這種模式泛化開來,那么未來數字空間的規則體系與機制構建很有可能會呈現出“條塊化”甚至是“碎片化”特點。
綜上所述,數字空間的問題很復雜,數字空間的未來存在很大不確定性。目前對于數字空間治理的思考更多只是基于當前現實的觀察。但見微知著,未來數字空間的有效治理需要著眼于數字化轉型所帶來的技術與社會等層面的影響,需要理念與認知的轉變、磨合與塑造,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推進治理手段的重大創新,更需要加強國際合作與協調,積極探索適應形勢發展需要的治理框架。
3 結 語
從現有的發展趨勢來看,數字空間的規則博弈將成為大國博弈的焦點。與其他領域相比,數字空間仍然在快速發展之中,一方面,數字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前景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政策制定者對技術應用所蘊含風險的把握和認知還不成熟,在不存在迫在眉睫的重大安全風險的前提下,大國對達成具有約束力的國際規則通常會比較謹慎;另一方面,數字技術對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具有全局性和戰略性意義,而國際規則具有非中性的特征,為盡可能維護本國利益,大國間圍繞數字經濟領域的規則制定將會進行長期的博弈。在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當下,圍繞著數字空間國際規則制定展開的博弈將會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未來國際秩序重塑的關鍵推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