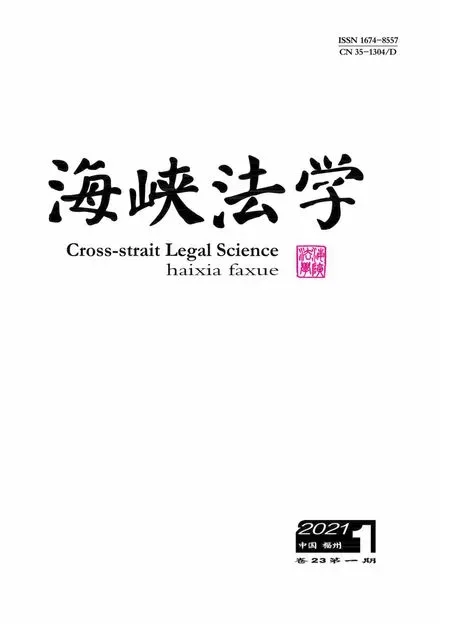員警誤擊拒捕通緝犯用槍過當?
——評“最高法院”2016年臺非字第88號判決與其歷審裁判
許福生
一、前言
近年來在臺灣地區一個備受實務矚目的阻卻違法事由,便是通緝犯拒捕員警開槍致該名通緝犯死亡的案例。此類案例討論的主要重點在于,員警在面臨急迫狀況下,其槍擊通緝犯的行為,是否符合依法令之行為或正當防衛?特別是“警察法”第9條第6款規定警察有依法使用警械之職權,同法“施行細則”第10條第1項第5款規定使用“警械依警械使用條例”之規定行之,“警械使用條例”第12條則規定警察人員依本條例使用警械之行為,為依法令之行為,而“刑法”第21條第1項規定依法令之行為,不罰。故警察人員依警械使用條例之規定使用警械之行為,為依法令之行為,而依法令之行為,不罰。至于員警是否依“警械使用條例”之規定使用警械,其判斷標準何在?倘若員警之開槍行為不符合“警械使用條例”之規定不能阻卻違法,而主張正當防衛時有無防衛情狀時如何判斷?又若是通緝犯拒捕當時有服用毒品會不會影響對防衛情狀成立與否之判斷?以及在警察誤認通緝犯有傷害或殺害自己的現在不法侵害時,應該如何判斷誤想防衛的法律效果?均值探討。
本此理念,本文即以“最高法院”2016年臺非字第88號判決與其歷審裁判為基礎,探討員警誤擊拒捕通緝犯是否真的用槍過當?因此,本文在結構上分為如下幾個部分:首先說明本文之動機與構想,接著論述本案例事實及相關爭點,之后探討歷審法院之實務判決并提出評析,以作為本文之結論。
二、案例事實
員警甲輪值轄區巡邏勤務,接獲值班警員通報疑似有人變賣贓物后到場,發現在場車輛之車主乙是通緝犯,且因竊盜案件通緝中,乃向附近住戶探詢是否有見到車主,住戶示意乙剛已返回車上,員警甲立即基于逮捕通緝犯之意思,趨前至該自用小客車左后方,并持警槍上膛警戒,惟此際乙已發動引擎并倒車準備離去,員警甲見狀旋即沖上駕駛座旁將該車前左側車門打開,乙見身著員警制服之員警甲開其車門,立即將車門拉回關上,員警甲再度打開該車門,喝令乙“停車”“不要動”,乙不聽制止,員警甲遂對空鳴開1槍示警,乙仍不理,續踩油門迅速倒車,以順時針方向倒車繞過員警甲欲逃離現場。
甲誤認乙倒車是要撞擊自己,故基于防衛自身及制止乙脫逃之意思,對乙之腿部近距離接續射擊3槍,乙遭受槍傷后,仍持續倒車拒捕,并于完成倒車后加速駛離現場逃逸,員警甲隨即騎乘警用機車沿乙逃逸之方向追捕,旋在距離上址約560公尺外,發現乙所駕車輛已偏離道路而墜入左側田埂間,乙坐在駕駛座內并陷入昏迷狀態,員警甲見狀隨即主動通知值班警員上情并請救護人員到場救治,后雖經救護車緊急送醫急救,仍因損傷下肢動靜脈血管出血致出血性休克死亡,惟事后鑒定通緝犯乙在事件發生當下有服用甲基安非他命。
三、相關爭點
(一)員警在執行職務面對拒捕犯人使用槍械導致其死亡結果,其屬于依法令行為正當化之界限為何?特別是比例原則判斷標準為何?
(二)倘若不能主張依法令之行為阻卻其違法性而主張正當防衛時,有無防衛情狀如何判斷?特別是犯人有吸毒是否會影響防衛情狀之判斷?
(三)現若客觀上不存在現在不法侵害,但主觀上卻誤認有不法侵害之情事存在之誤想防衛,其法律效果為何?
四、實務判決
(一)一、二審之判決
本案一①參照臺灣地區桃園地方法院2014年矚訴字第19號刑事判決。、二審②參照臺灣地區“高等法院”2015年度上訴字第787號刑事判決。事實認定與法律效果并沒有太大差別,因此就以二審判決作為整理重點如下。1. 員警甲槍擊造成乙出血休克是主要死因
針對乙之死亡,二審依鑒定意見,死者遭槍擊共致造成10個槍口,主要造成大腿血管破裂出血,內臟血液會流光達出血性休克,明確認定出血性休克為直接之主死因,并非因被害人服用甲基安非他命,而使原不可能發生死亡結果之被害人產生死亡結果之情形,被告此項辯解,為不足采。被告本件槍擊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系甚明。被告所辯因被害人施用高劑量甲基安非他命始造成死亡一節,不足采。
2. 用槍過當不得以依法令行為阻卻違法
縱使員警甲的槍擊行為是造成乙出血休克主要死因,接續需討論的是甲造成乙死亡的行為,能否適用任何阻卻違法事由?二審法院考量了“依法逮捕犯罪嫌疑人之公務員,遇有抵抗時,雖得以武力排除之,但其程度以能達逮捕之目的為止,如超過其程度,即非法之所許,不得認為依法令之行為(“最高法院”1941年上字第1070號判例參照)”。
由于甲在逮捕過程中使用了警槍,故法院進一步討論“警械使用條例”相關規定指出:按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遇有依法應逮捕、拘禁之人拒捕、脫逃時,得使用槍械,固為“警械使用條例”第4條第1項第3款所明定。惟同條例第6條亦規定:“警察人員應基于急迫需要,合理使用槍械,不得逾越必要程度。”二審法院并進而表示“比例原則”之內涵包括:“適合性原則”,即使用槍械必須基于急迫需要,且能有效達成行政目的;“必要性原則”,即依當時情況,必須沒有其他侵害法益較小之方式時,始得使用槍械,并非警察人員為逮捕拒捕或脫逃之現行犯即得毫無限制使用槍械,且縱有使用之需要,仍應選擇侵害人民法益最小之方式為之;“利益相當原則”,即所欲達成之行政目的,必須與不得不侵害之法益輕重相當。
至于“比例原則”之具體操作二審法院認為:被告欲將其逮捕,既遇被害人拒捕,不聽對空鳴槍之警告仍極力脫逃,于此急迫情形下,雖得依上述條例第4條第1項第3款規定使用槍械,且使用槍械亦能有效達成逮捕被害人之目的,惟當時被害人并未持械,也未對被告施以任何攻擊之行為,被告實際上未受到任何立即之危害,此業如前述,且欲執行逮捕,本應斟酌情形使用不致危及人命之追捕方式達成,衡以被害人倒車拒捕之過程中,被告始終站立于被害人車輛之駕駛座車門旁,距離甚近之情形,則被告原可選擇避開汽車,再迅速透過巡邏警網圍捕,或趁周遭無波及他人之危險而可持槍朝被害人車輛之輪胎射擊,以阻止被害人駕車逃離,并非有立即使用槍械對人身射擊之必要。
最終,二審法院認定:被告因積極執行職務以求行政目的之達成,其出發點固無不當,然其未選擇對被害人侵害最小之方式,即率而對人下肢連開3槍,用槍之方式逾越必要程度,致所欲達成之行政目的,與侵害之法益輕重失衡,是被告使用槍械之行為未合乎上揭“警械使用條例”第6條之規定,不為法律所容許,不得以依法令之行為主張阻卻其違法性。惟其逾越必要程度用槍,仍應審酌有無阻卻違法事由之錯誤情形。
3. 不能主張正當防衛但有誤想防衛情形
本案甲雖然不能主張依法令之行為阻卻其違法性,但仍可考慮正當防衛的阻卻違法事由,惟構成正當防衛必須先有防衛情狀,甲必須客觀上面臨現在不法侵害 。①許恒達:《員警槍擊拒捕通緝犯的正當防衛爭議——評“最高法院”105年度臺非字第88號刑事判決與其歷審裁判》,載《月旦法學雜志》2018年第276期,第26頁。二審調查相關證據后法院認為:被害人雖有倒車拒捕之舉動,然因現場有建筑物及雜物堆砌,被害人僅得以倒車方式退至后方聯外道路上始能逃離……觀諸其倒車行徑,系刻意以順時針方向繞過被告,顯然被害人當時意在離開現場,實際上并無對被告直接沖撞或攻擊之情形……且被害人以順時針方向倒車,避開左側車門外之被告,事實上并無對被告沖撞之故意,從而本案被害人之倒車拒捕行為,對被告實際上并未造成生命、身體之不法侵害,亦即事實上當時尚無現在不法侵害之情事存在,被告因而無從以正當防衛主張可以對被害人身體開槍射擊。
換言之,法院認為乙倒車行徑不會直接沖撞甲,且主觀上也無沖撞被告之故意,故無現在不法侵害之情事存在,惟法院接著論述甲主觀認知指出:當時被告與被害人二人短暫接觸,被告急于使被害人停車就范,被害人則急于駕車逃逸,緊急之間,被告本能性反應產生被害人極可能直線倒車(而非實際上之順時針方向倒車),預見立即有遭車門直接撞倒之危險,而有誤想防衛之情形,此想法,客觀而言,并無不合理之處。亦即法院認為甲開槍致乙死亡的行為構成誤想防衛。
至于誤想防衛的法律效果,二審法院認為:誤想防衛本非正當防衛,蓋其欠缺正當防衛要件之現在不法侵害,故誤想防衛不阻卻違法性,然而對于此種情形,即不知所實行者為違法行為,是否得以阻卻故意,因學說對于容許構成要件錯誤之評價所持理論的不同,而異其后果。在采限縮法律效果之罪責理論者,認為容許構成要件錯誤并不影響行止型態之故意,而只影響罪責型態之故意,亦即行為人仍具構成要件故意,但欠缺罪責故意,至于行為人之錯誤若系出于注意上之瑕疵,則可能成立過失犯罪。“最高法院”1940年上字第509號判例意旨以行為人出于誤想防衛(錯覺防衛)之行為,難認有犯罪故意,應成立過失罪責,論以過失犯,即與上述學說之見解相仿(參考“最高法院”2013年度臺上字第3895號判決)。
4. 負業務過失致人于死罪責且符合自首要件
最后二審法院認定被告員警甲:其傷害行為因欠缺違法性認識,阻卻犯罪之故意,而不構成傷害罪或傷害致死罪;惟被告對于依職權使用槍枝,仍有一定之注意義務,是應審酌被告是否違反該注意義務致造成被害人法益侵害之結果,而應負過失責任。且被告系警員,持警槍執行查緝犯罪勤務,為其日常業務之一部,系從事業務之人,其于執行業務中,因過失致被害人于死亡,核其所為,系犯“刑法”第276條第2項之業務過失致人于死罪。①“刑法”第276條規定已于2019年5月29日修正公布并于同月31日生效,將“刑法”第276條第2項之“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犯前項之罪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并科3000元以下罰金”之規定予以刪除,修正后“刑法”第276條規定為“因過失致人于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之下罰金”。至于本條之修正理由為:“1. 過失致死罪與殺人罪,雖行為人主觀犯意不同,但同樣造成被害人死亡之結果,惟原關于過失致死罪之法定刑為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二千元以下罰金,與殺人罪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落差過大,在部分個案上,顯有不合理,而有提高過失致死罪法定刑之必要。于是修正第一項法定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使法官依個案情形審酌違反注意義務之情節而妥適之量刑,列為本條文。2. 原過失致死依行為人是否從事業務而有不同法定刑,原系考慮業務行為之危險性及發生實害頻率,高于一般過失行為,且其后果亦較嚴重;又從事業務之人對于一定危險之認識能力較一般人為強,其避免發生一定危險之期待可能性亦較常人為高,故其違反注意義務之可責性自亦較重。因此就業務過失造成之死亡結果,應較一般過失行為負較重之刑事責任。惟學說認從事業務之人因過失行為而造成之法益損害未必較一般人為大,且對其課以較高之注意義務,有違平等原則,又難以說明何以從事業務之人有較高之避免發生危險之期待。再者,司法實務適用之結果,過于擴張業務之范圍,已超越立法目的。而第一項已提高法定刑,法官得依具體個案違反注意義務之情節,量處適當之刑,已足資適用,于是刪除原第二項關于業務過失致死規定。”又被告于開槍肇事后,隨即通知值班警員上情并請求救護人員到場救治被害人,此有流程時序表及通聯紀錄……足認被告符合自首之要件,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二)三審之判決
二審法院判決后,檢察官與被告均上訴至“最高法院”,乃因檢察官認為本案應構成故意犯而非過失犯且量刑過輕,而被告則主張應構成正當防衛且持槍射擊乙下肢,并未逾越必要程度。惟“最高法院”仍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并無違背法令之情形存在,且并無認定事實未憑證據之情形,屬事實審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既未逾法定刑度,且無違背公平正義情形,故直接駁回上訴,本案即告確定②參照“最高法院”2015年度臺上字第3901號刑事判決。(如表1)。
(三)非常上訴之判決
檢察總長在本案確定后,又針對乙在本案發生前,曾經施用甲基安他非命而喪失行車控制能力一事,認為原審并未詳細審視影響甲刑責的證據,而從提起非常上訴。檢察總長認為:上述鑒定報告所稱被害人達“中毒性休克”“意識不清”之狀況,是否表示被害人已無判斷行為之能力?若被害人已無行為判斷能力,則其遇警攔截,自己都未能控制、預測其下一步之舉動,能否排除其亦有沖撞被告之可能?以當時被告與被害人對峙時間甚短,能否由被害人駕車離開現場之情形于事后推論被害人之倒車拒捕行為對被告實際上并未造成生命、身體之不法侵害?此攸關被告是否正面臨生命、身體之不法侵害及被告應采取之防衛方法之判斷,原審未予查明,不無于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
不過,“最高法院”并未接受檢察總長意見,認為:羅某于案發前不僅能駕駛自用小客車至案發現場,于案發當時亦能辨識穿著警察制服之被告,并判斷自己因案遭通緝,惟恐遭被告逮捕,而能順利操作、啟動自用小客車,并以順時針方向倒車欲往聯外道路行進……況羅某當時是否有上述“中毒性休克”及“意識不清”之情形,僅系其當時主觀上之生理與意識狀況,尚不足以影響原確定判決依憑第一審勘驗筆錄,而據以認定“羅某當時并無駕車對被告沖撞或攻擊之動作,且羅某系以順時針方向倒車欲往聯外道路行進,并繞過左側車門旁之被告而急速駕車駛離現場,被告站立于開啟之駕駛座左側車門外,事實上并無遭碰撞或拖行之情形,其生命、身體并未遭受實際之傷害”之客觀事實,亦不足以改變原確定判決對于被告當時所為尚不符合正當防衛之判斷結果。基此“最高法院”認為并無應于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情形,故駁回非常上訴。③參照“最高法院”2016年度臺非字第88號刑事判決。

表1 歷審法院判斷員警誤擊拒捕通緝犯用槍是否過當思維
五、評析
(一)依法令行為正當化事由之界限
1. 依法令行為正當化之事由
警察人員依“警械使用條例”之規定使用警械之行為,為依法令之行為,而依法令之行為,不罰。又依“警械使用條例”第4條之規定:“警察人員執行職務時,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使用警刀或槍械:一、為避免非常變故,維持社會治安時。二、騷動行為足以擾亂社會治安時。三、依法應逮捕、拘禁之人拒捕、脫逃,或他人助其拒捕、脫逃時。四、警察人員所防衛之土地、建筑物、工作物、車、船、航空器或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財產遭受危害或脅迫時。五、警察人員之生命、身體、自由、裝備遭受強暴或脅迫,或有事實足認為有受危害之虞時。六、持有兇器有滋事之虞者,已受警察人員告誡拋棄,仍不聽從時。七、有前條第一款、第二款之情形,非使用警刀、槍械不足以制止時。前項情形于必要時,得并使用其他經核定之器械。”(本條例第3條第1款之情形為:協助偵查犯罪,或搜索、扣押、拘提、羈押及逮捕等須以強制力執行時。第2款之情形為:依法令執行職務,遭受脅迫時。)
換言之,警察人員在執行職務,客觀上有使用警刀或槍械之情事存在時,即得使用警刀或槍械,必要時得并使用其他經核定之器械。惟使用警刀或槍械時,仍應遵守如下使用警械之程序及注意事項①有關“警械使用條例”之詳細內容,可參閱黃清德:《警械使用條例與案例研究》,收錄于許福生主編:《警察法學與案例研究》,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20年版,第347~384頁。:
(1)事前:①出示身份(本條例第1條第2項);②使用警械因而致人受傷、死亡或財產損失之補償或賠償措施(本條例第11條)。 柯耀程:《用槍過當?——評“最高法院”一○四年度臺上字第三九○一號、臺灣“高等法院”一○四年度上訴字七八七號、桃園地方法院一○三年度矚訴字第一九號刑事判決》,載《月旦裁判時報》2016年第45期,第35頁。先命停止舉動或高舉雙手(本條例第5條);③柯耀程:《用槍過當?——評“最高法院”一○四年度臺上字第三九○一號、臺灣“高等法院”一○四年度上訴字七八七號、桃園地方法院一○三年度矚訴字第一九號刑事判決》,載《月旦裁判時報》2016年第45期,第36頁。判斷有無急迫需要(本條例第6條前段)。
(2)事中:①手段合理即使用警械應符合比例原則 (本條例第6條后段);②使用警械因而致人受傷、死亡或財產損失之補償或賠償措施(本條例第11條)。 柯耀程:《用槍過當?——評“最高法院”一○四年度臺上字第三九○一號、臺灣“高等法院”一○四年度上訴字七八七號、桃園地方法院一○三年度矚訴字第一九號刑事判決》,載《月旦裁判時報》2016年第45期,第35頁。警察人員使用警械之原因已消滅者應立即停止使用(本條例第7條);③警察人員使用警械時應注意勿傷及其他之人(本條例第8條);④警察人員使用警械時如非情況急迫應注意勿傷及其人致命之部位(本條例第9條)。
(3)事后:①應將經過情形,即時報告該管長官,但使用警棍指揮者,不在此限(本條例第10條);
按本案前提事實存在有二正當事由的可能情狀,一為依法令行為,一為正當防衛行為。然而,歷審判決法院均認定員警開槍致通緝犯死亡結果的情況,均無正當化事由之存在,其既已逾越“警械使用條例”用槍之界限;同時亦非屬于正當防衛的情形,故自應為有罪之認定。或許本案自始并非所謂正當防衛的問題,蓋通緝犯欲開車逃逸,并無想沖撞員警的具體情事,是以非屬現在不法之侵害,亦無“警械使用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警察人員之生命、身體、自由、裝備遭受強暴或脅迫,或有事實足認為有受危害之虞之情事,但員警系為逮捕欲行脫逃的通緝犯,且具體情況系屬于防止脫逃的急迫狀況,依法本得以使用槍械,此并非無依法令之事由,倘若遽以造成死亡之結果,而以結果遽然論以逾越法律授權的界限,恐論據上仍有未足②。
警察人員執行職務,知有犯罪嫌疑者,依“刑事訴訟法”第229條至231條之規定,應即開始調查,遇到通緝犯或是現行犯時,應以逮捕,又當其抗拒拘提、逮捕或脫逃者,得用強制力拘提或逮捕之,但不得逾必要之程度,此乃“刑事訴訟法”所授權警察人員之行為,原則上為“刑法”第21條第1項依法令之行為,阻卻違法。但是一旦逮捕行為超越侵害犯人人身自由,若使用警械施行逮捕行為以回應犯人之攻擊時,就不能單純只用刑事訴訟法判斷警械使用之合法性,此時應以“警械使用條例”之規定,認定警察人員使用槍械之情形是否在條例的許可范圍內。
依“警械使用條例”之規定,警察人員執行職務,在得使用槍械時,仍應基于急迫之需要,且不得逾越必要之程度,以防止濫用槍械而侵害人民權益。觀之本件具體事實,員警甲乃本于逮捕通緝犯之事由,遇有通緝犯正要倒車逃跑,且有沖撞員警之可能時,此時槍械之使用,在對應于“警械使用條例”第4條第1項第3款之前提事實上,應屬符合用槍時機;況且員警欲將其逮捕但仍拒捕不聽,并對空鳴槍警告卻仍極力脫逃時,在此急迫需要下,員警甲用槍亦遵守“警械使用條例”第9條的規定要求:勿傷及其人致命之部位而槍擊下肢,本質上應非必然性之致命部位,惟卻因該名通緝犯仍續踩油門迅速倒車脫逃,導致損傷下肢動靜脈血管出血致出血性休克死亡的結果,最后卻以結果論推翻行為之正當性,反推員警未選擇對通緝犯侵害最小之方式,即率而對人下肢連開3槍,用槍之方式逾越必要程度,而未合乎“警械使用條例”第6條之規定,如此恐有“反果為因”的錯誤邏輯存在。
因此,從本案員警使用槍械的行為觀察,員警具有得使用槍械的前提事由,且其使用警械之行為,合乎急迫需要與手段合理之法律要求,即先行警告對空鳴槍與不直接傷及致命部位(射擊下肢)之要求,在行為的要求上應屬合于“刑法”第21條第1項所規定之依法令行為,不罰。況且“刑法”依法令行為的正當與否,本非單以法益衡量作為是否逾越的單一標準,觀察具體行為是否有逾越法令授權的界限,應先從依法令的行為著眼,而非徑從結果遽認逾越界限③。
2. “比例原則”之判斷
本案所以論定用槍過當,而需承擔業務過失致人于死罪責,其主要論據,還是在于“比例原則”之判斷。本案歷審實務見解均認為“警械使用條例”第4條第1項第3款以及第6條是“比例原則”之展現,且進而表示“比例原則”之內涵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適合性原則”,即使用槍械必須基于急迫需要,且能有效達成行政目的。
(2)“必要性原則”,即依當時情況,必須沒有其他侵害法益較小之方式時,始得使用槍械,并非警察人員為逮捕拒捕或脫逃之現行犯即得毫無限制使用槍械,且縱有使用之需要,仍應選擇侵害人民法益最小之方式為之。
(3)“利益相當原則”,即所欲達成之行政目的,必須與不得不侵害之法益輕重相當。
確實,對于具有強制力授權的公務員,于執行職務時,雖得使用強制力,但干預的程度仍不得逾越必要之程度并符合“利益相當”原則,此為國家權力運作當然之理。惟對于具體情況下,所為權利干預的作用,并不能一概而論,倘若公權力的干預,僅屬于一般行政目的的干預,其自然須符合如判決所示“比例原則”的基本要求,但具體個案如系對于犯罪行為的問題,屬于實現國家刑罰權的認定,其層次并非僅屬于一般行政目的實現的目的,此觀之“行政程序法”第3條規定,刑事案件犯罪偵查程序不適用“行政程序法”之程序規定便知。此時若仍堅持對于拒捕通緝犯脫逃用槍,用槍結果必須符合用槍時預定之必要損害程度始能免責,倘若超出此程度而生“加重”結果,如本案因射中腿部造成通緝犯失血過多致死,便稱用槍之方式逾越必要程度且與侵害之法益輕重失衡,而不得以依法令之行為主張阻卻其違法性,相當不妥①黃朝義:《警察用槍規范與審查機制——兼論其他警械使用》,載《警大法學論集》2015年第29期,第33頁。。
如此,必然會發生是否即須容忍所有任由應逮捕拘禁之人脫逃,均不能使用警槍之事實發生,最后只能如判決所言:“再迅速透過巡邏警網圍捕,或趁周遭無波及他人之危險而可持槍朝被害人車輛之輪胎射擊,以阻止被害人駕車逃離,并非有立即使用槍械對人身射擊”。如此是否能實現國家刑罰權所賦予得使用強制力的目的?恐令人疑慮!②許福生:《增設警械使用審查機制執法有后盾》,載《臺灣法學雜志》2020年第395期,第10頁。
因此,對于對抗犯罪所允許的強制手段,其干預強度的授權,應較一般行政目的實現的行為,會有更大的寬容性;同時執行刑罰權所生的強制權力,原則上并非完全以“利益相當原則”作為界限判斷的基準,而是在“憲法”23條法律保留的前提下,所采取的強制處分手段,其背后均是以刑罰權,作為支撐的依據③柯耀程:《用槍過當?——評“最高法院”一○四年度臺上字第三九○一號、臺灣“高等法院”一○四年度上訴字七八七號、桃園地方法院一○三年度矚訴字第一九號刑事判決》,載《月旦裁判時報》2016年第45期,第37頁。。
況且,依“警械使用條例”之條文觀之,對拒捕人使用槍械,須符合“急迫需要”“手段合理”這二要件,又可槍擊人體致命處,僅限于“最急迫”時情況,方可為之。因而判斷時必須考量具體情況的急迫性以及個別手段的合理性,進行個案審查,“比例原則”雖然重要,但“比例原則”只能判斷手段和目的之間的妥適性,卻無法具體地處理個別情況的急迫性,尤其是當通緝拒捕時采取的反應方式更為強烈時,理論上應許可員警使用更為強大的警用火力回應,二審法院單憑比例原則,恐怕無法考量急迫性的需求④許恒達:《員警槍擊拒捕通緝犯的正當防衛爭議——評“最高法院”105年度臺非字第88號刑事判決與其歷審裁判》,載《月旦法學雜志》2018年第276期,第30頁。。
判斷員警用槍是否過當?應先從使用警械的法律授權條件觀察,若屬正當法律授權的范圍,即使于使用或不用之間,仍有具體選擇時,卻不能因有選擇用與不用之情狀,而遽認使用不當,應視為使用槍械屬于具有授權正當性的前提存在。又警械的使用,除授權條件之外,其使用行為是否遵守誡命上的要求(“警械使用條例”第6條至第9條規定),亦即使用槍械的行為是否正當,若具體所為的情狀若非逕為人命之剝奪,其行為乃屬正當行為,縱使所生之侵害結果,非屬預期,仍不能倒果為因而科以刑責,否則所謂依法令之行為不罰,將淪為空談①柯耀程:《用槍過當?——評“最高法院”一○四年度臺上字第三九○一號、臺灣“高等法院”一○四年度上訴字七八七號、桃園地方法院一○三年度矚訴字第一九號刑事判決》,載《月旦裁判時報》2016年第45期,第39頁。。
特別是作為“刑法”的正當化事由,包括依法令之行為、業務上正當行為及正當防衛行為等,但在層次上應有所差異,依法令之行為是依法律授權直接可以做;業務上正當行為必須遵守執行業務的作業程序方屬適法;正當防衛必須公權力來不及保護才可以防衛反擊。由于警械的使用時機,大部分出于緊急情形,“警械使用條例”授權警察人員得使用警械,如造成傷亡,司法必須以“寬容原則”來認定是否違法,較為適當,倘若法院的認定與正當防衛等正當事由同等視之,在法條的適用上不同,而無層次之分,其判決可能違背法令②方文宗:《警械使用正當性之刑法界限》,載《東海大學法學研究》2019年第57期,第51~61頁。。
3. 對比臺北市張姓員警案之判斷
相較于本案,另一受矚目的臺北市警察局漢中街所張姓員警,射擊不聽從喝令倒車試圖逃逸之黎員致死一案,最終法院認為本案案發當時確有使用警用槍械制止黎員拒捕倒車行為之急迫需要,被告用槍時機符合前揭“警械使用條例”相關規范,屬合理使用,且已注意勿傷及致命之部位,并未逾越必要程度,是被告客觀上并無違反注意義務,主觀上亦已盡其注意之能事,自難認有何過失可言,而判決張姓員警無罪。
至于本案法院對于“急迫需要”之認定,認為黎員其拒捕脫逃之意志甚堅,并承受極大之精神壓力,自不能以正常駕駛行為評估黎員,不能排除黎員在情急之下,會突然用力踩踏油門急速倒車以擺脫警方追捕之可能性,則在黎員所可能造成之危害甚巨,不可控制之風險甚高時,身為警員之被告自得依“警械使用條例”第4條第1項第3、4款之規定,采取使用警槍射擊黎員所駕之小客車等方式,以制止其倒車脫逃之行為。
另外,對于“手段合理”之認定,認為縱使被告系直接朝該擋風玻璃編號8彈孔位置射擊,因該處非常靠右,一般人之認知應不致于射中在車身左側之駕駛而造成嚴重傷害(實際上依前所述,乃系彈頭射中擋風玻璃后,因其材質特性產生彈道偏向而擊中黎員),可認為其已盡量注意勿傷及致命部位……是衡酌當時情況之急迫性,所可能造成危害之嚴重性等情后,法院認定縱使被告係開槍射擊該擋風玻璃編號8位置彈孔,亦屬合理,并未逾越必要程度……況此一風險之產生,乃系因黎員拒絕遵從執法警員命令下車,一再拒捕并欲倒車逃離致危害人群及用路人安全所致,理應自行承擔,而非由為保護民眾生命、身體安全而開槍制止之執法警員承擔此項注意義務,方屬事理之平③“最高法院”2019年度臺上字第1017號刑事判決;臺灣地區“高等法院”2018年上訴字第242號刑事判決。。
因此,員警執勤時使用槍械射擊,應以員警當下所處位置及面臨之具體情狀綜合加以判斷是否符合“警械使用條例”之規定,而非以其后面產生之結果來反面推斷衡量所侵害法益與使用之手段是否必要合理,否則員警將永遠無法判斷當下是否符合使用警槍之時機,而須以使用后所侵害法益的結果論斷,則國家法律將永遠無法告知警察人員何時為正確的用槍時機及方式,“警械使用條例”也將無法律明確性可言,也不符當初“警械使用條例”第12條規定:“警察人員依本條例使用警械之行為,為依法令之行為”之立法精神,系為保障警察人員依該條例行使使用警械之職權行為,不受國家刑罰權之處罰而列為專條,明確予以規定,以利公務,避免紛擾④“最高法院”2007年度臺上字第5765號刑事判決認為,警察人員執行職務,而得使用槍械時,仍應基于急迫之需要,且不得逾越必要之程度,以防止濫用槍械而侵害人民權益。至于是否合于急迫之需要及必要之程度,則須綜合全部之主、客觀情況資以判斷,而非僅以事后察知之客觀事實以檢討判斷其是否合于槍械之正當使用。如此看法,符合本文之主張。。
(二)正當防衛防衛情狀之判斷
本案雖然沒明確對員警居于國家的地位行使公權力,可否主張正當防衛這個爭點進行分析,但是法院從來沒有任何懷疑就討論正當防衛之態度中得知,是采取肯定說。至于學說上有肯定與否定二說,否定說認為警察乃執行公權力,其行為合法與否之判斷優先考慮以比例原則,檢視其行為是否符合法令,乃著眼點在于法治國原則對國家行為控制的效能,而不在于保護個別公務員;肯定說認為警察縱然在執行公權力,但也不可以排除警察有保護個人法益之需求,而且正當防衛的法條規定、“警察法”之規定都沒有排除國家機關的適用。多數見解是采取肯定說,乃認為在一般執行勤務之情形下固然要遵循比例原則,但正當防衛是發生在危及重要法益之特別情形,仍然應該認為警察有保護自我的需求,沒有理由要求警察放棄保護自身的反擊手段①許恒達:《警槍擊拒捕通緝犯的正當防衛爭議——評“最高法院”105年度臺非字第88號刑事判決與其歷審裁判》,載《月旦法學雜志》2018年第276期,第30~32頁。。
確認本案員警甲得適用正當防衛阻卻違法后,接下來需討論是否符合正當防衛的要件,首先須確認本案究竟有無現在不法侵略之防衛情狀存否?對于侵害人之行為是否侵害法益構成防衛情狀,向來分成事前判斷標準與事后判斷標準。事前判斷標準是指在事件發生當下,以一般人所能認知的事實情況,以及防衛者的特殊認知判斷之;事后判斷標準則是以法院所能收集的一切證據為基礎,從事后角度予以評價。在本案中,若以事前角度判斷乙的倒車行為,因為不能排除向員警甲駛去的可能,肯認存在防衛情狀。然而,歷審法院皆采取事后判斷之角度,基于事后調查得知乙有順時針倒車避過甲,否定存在防衛情狀。有學者同意上述實務見解,仍基于通說認為正當防衛具有對不法行動的法確證性效果,故在個案中必須確定侵害行為的不法性,若是無從確認其不法性,應無由賦予私人相應的合法施行暴力的權利。為了確認是否不法,應在事后依法院所能收集的一切證據為基礎判斷,始滿足法確證原則②同上,第32~33頁。。
然而,縱使采取事后判斷標準則,惟法院在其所能收集的一切證據為基礎在事后從事評價時,仍須審酌警察是否遭受立即危害存否防衛情狀時,應以身歷其境之“理性警察”的觀點加以判斷,而非后見之明。據此,“最高法院”1940年上字第509號判例謂“被告充當聯保處壯丁,奉命緝捕盜匪,正向被人誣指為匪之某甲盤問,因見其伸手撈衣,疑為取搶抗拒,遂向之開槍射擊,當時某甲既未對被告加以如何不法之侵害,則被告之防衛權,根本無從成立,自無防衛行為過當之可言。”即以事后調查得知某甲并未攜槍之資訊推斷被告開槍時情況并非急迫而系出于“誤想防衛”成立過失犯罪,未以當時“理性警察”客觀情況合理加以審酌,殊有檢討之必要③黃朝義:《警察用槍規范與審查機制——兼論其他警械使用》,載《警大法學論集》2015年第29期,第34~35頁。。
況且,縱使從事后角度判斷乙有順時針倒車避過甲,惟通緝犯車已發動駛駕中,下一秒方向盤會如何轉動真能準確預測?再加上事后驗出通緝犯乙在倒車當下有吸毒,而科學的證據也顯示吸毒者對自己的行為控制能力可能弱化,有較高的機率會損害他人,在此危急的場景下,一位“理性客觀的警察”真的會相信乙順時針方向倒車繞過員警甲逃離現場,不會有任何的反擊行為?在此危急的情況下,真的不存在防衛情狀?難道真的要等到通緝犯突然轉向沖撞員警而造成員警死傷才能判斷存在防衛情狀?故本案本文認為構成正當防衛且持槍射擊乙下肢,并未逾越必要程度。
(三)誤想防衛之法律效果
倘若依法院之認定,確認乙的倒車行為尚不構成現在不法侵害,惟主觀上卻基于防衛意思而對乙開槍以保護自己,乃是誤想防衛,或稱容許構成要件錯誤。針對誤想防衛的法律效果,學說上有下列三種見解:第一種是嚴格罪責理論,誤想防衛的行為人是出于故意侵害他人法益,就該當構成故意犯的不法行為,只是基于欠缺現實不法意識,必須比照禁止錯誤的法律效果處理,因而依“刑法”第16條,視其錯誤可否避免阻卻罪責。第二種是限制罪責理論,認為容許構成要件錯誤同是事實層面之錯誤,而類推適用構成要件錯誤之法理,評價為阻卻故意,只能轉論以過失犯。第三種是限制法律效果之罪責理論,主張容許構成要件錯誤并不影響構成要件故意,但會影響故意罪責,亦即在不法層次不受錯誤的影響,而是在罪責層次會阻卻故意之成立,而至多成立過失罪責,通說采此說①許恒達:《員警槍擊拒捕通緝犯的正當防衛爭議——評“最高法院”105年度臺非字第88號刑事判決與其歷審裁判》,載《月旦法學雜志》2018年第276期,第35~38頁。。
此件判決最后依通說見解,采取限制法律效果之罪責理論,認為容許構成要件錯誤并不影響行止型態之故意,而只影響罪責型態之故意,亦即行為人仍具構成要件故意,但欠缺罪責故意,至于行為人之錯誤若系出于注意上之瑕疵,則可能成立過失犯罪。至于甲是否成立過失犯,仍需處理構成要件階段有注意義務違反,罪責階段個人有遵守義務能力與預見可能性。縱使本案甲有違反“正確選擇因應手段”的執法義務違反,符合構成要件階段有注意義務違反,但在罪責上需具體考慮甲有無“正確認知無防衛情狀之能力”。現就本案判斷,甲雖然發生誤會,但這種發生于緊急狀態下的誤會,從甲個人能力以觀,實在無從避免,陷于突發狀態中的甲,在乙倒車當下,恐怕根本不可能正確且果斷地判斷乙根本無意撞甲,此時即可認為,甲對于構成“不存在防衛情狀”欠缺預見可能性,如此便無法構成過失犯的罪責,法院只能判甲無罪。而非只是像判決書簡單地交待“被告在誤想防衛及依法令執行逮捕而用槍之情形下,應注意、“能注意”采侵害人民法益最小之方式為之,卻未注意,而貿然對被害人之下肢連開3槍,致被害人下肢動靜脈血管出血致死,被告應負業務過失致死罪責”②同上,第38~40頁。。
六、結論
確實,警察人員執行職務,在得使用槍械時,仍應基于急迫之需要,且不得逾越必要之程度,以防止濫用槍械而侵害人民權益。最終本案法院的判決仍認為員警甲槍擊造成乙出血休克是主要死因,用槍過當不得以依法令行為阻卻違法,不能主張正當防衛但有誤想防衛情形,最后應負業務過失致人于死罪責。至于判決評價基礎是被告使用槍械之行為未合乎“警械使用條例”第6條之規定,即合法使用槍械須符合“急迫需要”“手段合理”這二要件,又可槍擊人體致命處,僅限于“最急迫”時情況,方可為之,況且基于事后調查得知乙有順時針倒車避過甲,否定存在防衛情狀,但有誤想防衛情形存在。誠然,國家授權公權力的強制作用,應以最小的侵害為準則,但最小之侵害,不能僅以結果論為判斷方式,否則若仍堅持對于拒捕通緝犯脫逃用槍,用槍結果必須符合用槍時預定之必要損害程度始能免責,倘若超出此程度而生“加重”結果,如本案因射中腿部造成通緝犯失血過多致死,便稱用槍之方式逾越必要程度且與侵害之法益輕重失衡,而不得以依法令之行為主張阻卻其違法性。如此,必然會發生是否即須容忍所有任由應逮捕拘禁之人脫逃均不能使用警槍之事實發生,而只能如判決所言:“再迅速透過巡邏警網圍捕,或趁周遭無波及他人之危險而可持槍朝被害人車輛之輪胎射擊,以阻止被害人駕車逃離,并非有立即使用槍械對人身射擊”。如此是否能實現國家刑罰權所賦予得使用強制力的目的?恐令人疑慮!對于對抗犯罪所允許的強制手段,其干預強度的授權,應較一般行政目的實現的行為,會有更大的寬容性。
因此,判斷員警用槍是否過當?應先從使用警械的法律授權條件觀察,若屬正當法律授權的范圍,且其使用行為也遵守誡命上的要求,則其行為便屬正當行為,縱使所生之侵害結果,非屬預期,仍不能倒果為因而科以刑責,否則所謂依法令之行為不罰,將淪為空談。此外,判斷是否逾越法令之授權,應從身歷其境“理性警察”的行為作為判斷基準,結果僅是參考輔助作用之一而已,而非已后見之明判斷。如同“警察人員使用槍械規范”,要求各機關對于警察人員使用槍械適法性之判斷基準,應以用槍當時警察人員之合理認知為主,事后調查或用槍結果為輔。同樣地,“最高法院”2007年度臺上字第5765號刑事判決,亦認為是否合于急迫之需要及必要之程度,則須綜合全部之主、客觀情況資以判斷,而非僅以事后察知之客觀事實以檢討判斷其是否合于槍械之正當使用。是以,本案之判決,仍有檢討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