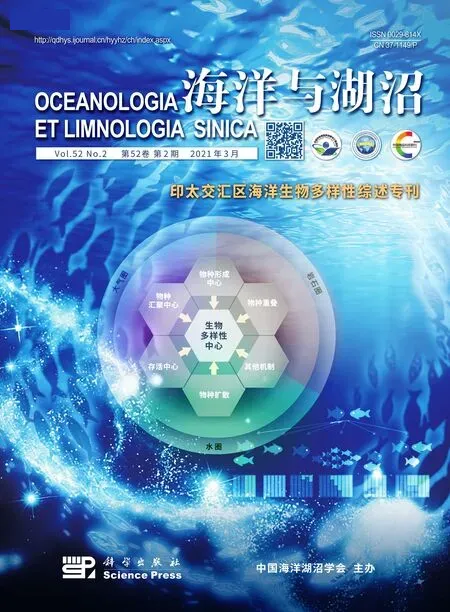印太交匯區(qū)海洋魚(yú)類多樣性格局與演化研究進(jìn)展*
劉 靜 肖永雙
印太交匯區(qū)海洋魚(yú)類多樣性格局與演化研究進(jìn)展*
劉 靜1, 2肖永雙1, 2
(1. 中國(guó)科學(xué)院海洋大科學(xué)研究中心 青島 266071; 2. 中國(guó)科學(xué)院海洋研究所 青島 266071)
印太交匯區(qū)不僅是熱帶物理海洋海氣能量匯聚中心、地質(zhì)板塊活躍中心以及生物多樣性中心, 而且也是用于開(kāi)展地球系統(tǒng)物質(zhì)能量交換與全球氣候變化以及海洋生物多樣性起源研究的理想靶區(qū), 因此一直受到世界科學(xué)家們的廣泛關(guān)注。作為全球34個(gè)生物多樣性熱點(diǎn)區(qū)域之一, 印太交匯區(qū)的珊瑚礁三角區(qū)孕育了全球76%的造礁珊瑚、75%的紅樹(shù)林、50%的珊瑚礁魚(yú)類和45%的海草物種數(shù)。魚(yú)類是珊瑚礁生態(tài)系統(tǒng)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 在整個(gè)印度-太平洋海域中珊瑚礁群落的組成和維持中起到重要作用。過(guò)去, 生物學(xué)家們圍繞熱帶珊瑚礁魚(yú)類多樣性格局與演化做了大量工作, 提出了許多生物地理學(xué)假說(shuō)模型, 如中心物種形成模型、匯聚中心模型、重疊中心模型和華萊氏線假說(shuō)等, 這些假說(shuō)在一些珊瑚礁魚(yú)類類群得到驗(yàn)證。但是, 相對(duì)于印太交匯區(qū)的熱帶珊瑚礁魚(yú)類多樣性研究, 深海的魚(yú)類區(qū)系和生物多樣性研究起步較晚, 仍缺乏時(shí)間序列的觀測(cè)數(shù)據(jù)和系統(tǒng)研究。目前對(duì)于印太交匯區(qū)深海與淺海生物多樣性中心形成演化機(jī)制以及深淺海生物之間的源匯關(guān)系認(rèn)知方面仍存在分歧。本文梳理了過(guò)去國(guó)內(nèi)外學(xué)者在印太交匯區(qū)魚(yú)類多樣性方面的研究工作, 綜述了該地區(qū)淺海熱帶珊瑚礁和深海魚(yú)類多樣性格局演化研究最新進(jìn)展, 提出在深海極端環(huán)境和生命過(guò)程研究對(duì)策, 以期為探討印太交匯區(qū)海洋生物多樣性中心形成演化過(guò)程及證實(shí)/證偽各種生物地理學(xué)假說(shuō)提出科學(xué)論據(jù), 并為戰(zhàn)略生物資源開(kāi)發(fā)利用提供新視角。
印太交匯區(qū); 珊瑚礁三角區(qū); 魚(yú)類; 生物多樣性; 分布格局; 演化
生物多樣性是地球上生命經(jīng)過(guò)幾十億年發(fā)展進(jìn)化的結(jié)果, 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zhì)基礎(chǔ)。由于全球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dòng)的雙重脅迫, 生物多樣性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遭受破壞, 特別是熱帶森林和珊瑚礁生態(tài)系統(tǒng)受到氣候干擾和人類活動(dòng)影響最為嚴(yán)重(Robert, 2002), 已經(jīng)引起國(guó)內(nèi)外生物學(xué)家的高度重視。早在1988年, 英國(guó)牛津大學(xué)著名生物多樣性與自然保護(hù)學(xué)家諾曼·麥爾首次提出“生物多樣性熱點(diǎn)(Biodiversity hotspots)”概念, 他提出雖然熱點(diǎn)生態(tài)系統(tǒng)占據(jù)的生態(tài)位空間有限, 但其包含了高豐度的物種多樣性。這個(gè)概念后來(lái)被“保護(hù)國(guó)際(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簡(jiǎn)稱CI)”組織在2000年又作了進(jìn)一步發(fā)展和定義。“保護(hù)國(guó)際”組織設(shè)定生物多樣性熱點(diǎn)地區(qū)的基本原則是: 受威脅最大的高豐度物種分布地區(qū)。Myers(2000)提出了“優(yōu)先保護(hù)的全球25個(gè)生物多樣性熱點(diǎn)地區(qū)”。2005年, “保護(hù)國(guó)際”組織宣布新增9個(gè)熱點(diǎn)地區(qū), 這使得全球生物多樣性熱點(diǎn)地區(qū)增加至34個(gè)。目前, 世界34個(gè)生物多樣性熱點(diǎn)地區(qū)雖然僅占地球表面積的2.3%, 但卻包含了地球75%以上的瀕危動(dòng)植物物種(Allen, 2008)。其中, 珊瑚礁生態(tài)系統(tǒng)因其高豐度的生物多樣性和極高的初級(jí)生產(chǎn)力特點(diǎn)被稱為“熱帶海洋沙漠中的綠洲”, 一直以來(lái)都是海洋生物學(xué)家們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問(wèn)題(Cowman, 2011)。
印太交匯區(qū)(Indo-Pacific Convergence Region, 簡(jiǎn)稱IPCR)位于亞歐大陸、太平洋、印度洋三大板塊的交匯處, 孕育了全球最大的海洋生物多樣性中心, 是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樣性熱點(diǎn)地區(qū)(Brooks, 2006)。印太交匯區(qū)的珊瑚礁三角區(qū)(Coral Reef Delta Region; Coral Triangle), 又稱“印澳群島Indo-Australian Archipelago, IAA”, 或者“印度馬來(lái)三角區(qū)Indo-Malayan Triangle”, 或者“東印度群島三角區(qū)East Indies Triangle”, 因其位于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巴布亞新幾內(nèi)亞和所羅門群島之間水域呈三角形, 且分布著種類繁多的珊瑚而得名。印太珊瑚礁三角區(qū)僅占印度-太平洋海域面積3%, 卻擁有印度-太平洋海域生物物種的52%, 是名副其實(shí)的海洋生物多樣性的中心帶(Allen, 2008)。印太高生物多樣性的形成起源和維持機(jī)制是當(dāng)今生物多樣性研究的全球焦點(diǎn), 形成了各種爭(zhēng)議較大的假說(shuō)(Carpenter, 2011)。比較系統(tǒng)發(fā)育地理學(xué)的興起, 為驗(yàn)證這些生物地理假說(shuō)提供了有效支撐。經(jīng)過(guò)數(shù)十年的系統(tǒng)發(fā)育地理學(xué)研究, 使得珊瑚礁三角區(qū)生物多樣性格局初現(xiàn)倪端。但是, 這種格局在5.4億年以來(lái)并非一成不變, 全球海洋生物多樣性的峰值區(qū)在過(guò)去5000萬(wàn)年經(jīng)歷了至少兩次轉(zhuǎn)移: 從古地中海到紅海等阿拉伯海域, 再到現(xiàn)代印太珊瑚礁三角區(qū), 峰值區(qū)轉(zhuǎn)移的時(shí)間和地點(diǎn)與構(gòu)造事件和氣候變化等具有關(guān)聯(lián)(Renema, 2008; Carpenter, 2011)。因此, 印太交匯區(qū)不僅是熱帶物理海洋海氣能量匯聚中心、地質(zhì)板塊活躍中心以及生物多樣性中心, 而且也是用于開(kāi)展地球系統(tǒng)物質(zhì)能量交換與全球變化以及海洋生物多樣性起源研究的關(guān)鍵區(qū)和理想靶區(qū)。
鑒于印太交匯區(qū)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獨(dú)特性及其在全球生態(tài)系統(tǒng)中的重要意義, 近些年來(lái), 印太交匯區(qū)海洋生物多樣性中心形成演化過(guò)程一直受到世界科學(xué)家們的廣泛關(guān)注, 目前國(guó)際間對(duì)于淺海珊瑚礁區(qū)生物多樣性格局形成與演變機(jī)制以及深海與淺海生物之間的源匯關(guān)系認(rèn)知方面仍存在分歧。因此, 加強(qiáng)該地區(qū)生物區(qū)系和多樣性研究, 不僅能夠獲得新的生命現(xiàn)象認(rèn)知, 還能揭示更多不為人知的生命過(guò)程及其與環(huán)境的互作關(guān)系, 為證實(shí)/證偽海洋生物多樣性中心形成演化的各種假說(shuō)提出科學(xué)論據(jù)。本文梳理了過(guò)去國(guó)內(nèi)外學(xué)者在印太交匯區(qū)魚(yú)類多樣性方面的研究工作, 綜述了印太交匯區(qū)魚(yú)類區(qū)系組成、多樣性格局形成與演化機(jī)制的最新研究進(jìn)展, 有助于對(duì)印太交匯區(qū)這種特殊生境生物多樣性格局和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整體認(rèn)識(shí), 為今后進(jìn)一步探討該地區(qū)生物多樣性演化機(jī)制、海洋生態(tài)系統(tǒng)和功能、極端環(huán)境和生命過(guò)程等學(xué)科研究提供新視角。
1 印太交匯區(qū)熱帶珊瑚礁魚(yú)類多樣性格局與演化
1.1 印太交匯區(qū)熱帶珊瑚礁魚(yú)類多樣性格局
珊瑚礁生態(tài)系統(tǒng)和魚(yú)類區(qū)系多樣性是海洋環(huán)境學(xué)領(lǐng)域國(guó)際前沿?zé)狳c(diǎn)問(wèn)題(Cowman, 2011)。印太珊瑚礁三角區(qū)的物種多樣性在整個(gè)印度-太平洋海域珊瑚礁群落的組成和維持中起到重要作用, 其物種多樣性格局和演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學(xué)意義(Mora, 2003)。珊瑚礁生態(tài)系統(tǒng)分布于營(yíng)養(yǎng)匱乏的熱帶海洋, 但卻擁有數(shù)量驚人的生物多樣性和極高的初級(jí)生產(chǎn)力, 被稱為“熱帶海洋沙漠中的綠洲”(王麗榮等, 2001)。
印太珊瑚礁三角區(qū)只是印度-太平洋海域的一小部分, 卻是全球海洋生物多樣性最高的區(qū)域, 孕育了全球76%的造礁珊瑚、75%的紅樹(shù)林、50%的珊瑚礁魚(yú)類和45%的海草物種數(shù)。有報(bào)道, 生活在這一地區(qū)的魚(yú)類超過(guò)3000種(Briggs, 2005)。Allen等(2003)評(píng)估印太交匯區(qū)的珊瑚魚(yú)類為3764種, 超過(guò)印度-太平洋珊瑚礁魚(yú)類物種總數(shù)的2/3及全球珊瑚礁魚(yú)類的1/2。而且, 在這一地區(qū), 每年還不斷有魚(yú)類新種發(fā)表(Briggs, 2005)。
Allen等(2012)對(duì)過(guò)去60多年來(lái)積累的魚(yú)類調(diào)查資料進(jìn)行了分類整理, 出版了《東印度群島的珊瑚礁魚(yú)類》一書(shū), 該書(shū)記述了生活在東印度群島的珊瑚礁魚(yú)類2631種, 包括25個(gè)首次發(fā)表的新種。其中, 米卡擬花鮨(Allen & Erdmann, 2012)、阿洛喉盤魚(yú)(Allen & Erdmann, 2012)、紅斑鰭塘鱧(Allen & Erdmann, 2012)和沙拉精美蝦虎魚(yú)(Allen & Erdmann, 2012)就是作者在印度尼西亞附近海域調(diào)查時(shí)發(fā)現(xiàn)的新種(圖1a, 1b, 1c, 1d)。
與陸地生態(tài)系統(tǒng)不同, 印太珊瑚礁地區(qū)的生物多樣性熱點(diǎn)在緯度和經(jīng)度分布上都存在一個(gè)顯著的梯度(Bellwood, 2009)。Connolly等(2003)和Mora等(2003)分別研究了印度-太平洋海域的1766種和1970種魚(yú)類的分布范圍, 他們得出幾乎相同的結(jié)論, 即魚(yú)類的緯度分布熱點(diǎn)(中心)在赤道附近, 支持“中域效應(yīng)”假說(shuō)。與此同時(shí), 上述研究也表明魚(yú)類的經(jīng)度分布熱點(diǎn)(中心)大約在東印度洋群島附近, 距離印度-太平洋海域中點(diǎn)以西較遠(yuǎn)的位置。Connolly等(2003)認(rèn)為這個(gè)獨(dú)特的物種分布中心(指偏離了兩大洋中點(diǎn)位置)以及這種物種分布模式可能是受到向西流動(dòng)的赤道流影響導(dǎo)致的。另一方面, Mora等(2003) 則認(rèn)為這是東印度洋諸島中的海洋生物種群種化并向外擴(kuò)散的結(jié)果, 他們指出東印度洋群島在印度-太平洋地區(qū)的生物群落形成中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
注: a. 米卡擬花鮨; b. 阿洛喉盤魚(yú); c. 紅斑鰭塘鱧; d. 沙拉精美蝦虎魚(yú)
從赤道向兩極物種數(shù)目逐漸減少是當(dāng)前海洋生物多樣性的一個(gè)基本格局, 熱帶海域的生物多樣性要比溫帶和兩極高得多。由于地理分布不均, 在印太珊瑚礁三角區(qū)魚(yú)類物種豐度最高, 沿著緯度和經(jīng)度向外緣輻射, 物種豐度趨向遞減。有的學(xué)者認(rèn)為之所以熱帶海域的生物多樣性比溫帶和兩極高, 是因?yàn)闊釒汉鹘腑h(huán)境有利于物種形成, 是進(jìn)化的中心。但是這種分布格局的演化和生態(tài)學(xué)原因一直存在爭(zhēng)議。Rabosky等(2018)基于硬骨魚(yú)類的遺傳數(shù)據(jù), 檢驗(yàn)了緯度、物種豐度和物種形成速度三者之間的關(guān)系。結(jié)果顯示物種形成速度最快的地區(qū)并不是在熱帶海域, 而是在熱帶海域以外、物種豐度低的高緯度海域; 緯度越高, 物種形成速度越快, 海水表層溫度越低, 特有種數(shù)越多。
最近研究人員發(fā)現(xiàn), 遠(yuǎn)古時(shí)期的珊瑚塑造了現(xiàn)代海洋魚(yú)類多樣性。Pellissier等(2014)采用印澳群島的沉積物巖芯重建過(guò)去3百萬(wàn)年以來(lái)全球古海洋環(huán)境及該地區(qū)珊瑚的分布, 并基于全球6316種珊瑚礁魚(yú)類的分布數(shù)據(jù), 為第四紀(jì)時(shí)期(即260萬(wàn)年前到現(xiàn)在)魚(yú)類物種豐度的歷史分布格局建立模型, 估算由于第四紀(jì)氣候波動(dòng)而導(dǎo)致的珊瑚礁魚(yú)類數(shù)量變化程度。結(jié)果顯示: 在這一時(shí)期, 與珊瑚礁隔離而造成的對(duì)珊瑚礁魚(yú)類物種多樣性的影響要遠(yuǎn)大于其他任何因子, 其中包括海水表層溫度和光照強(qiáng)度等。該研究還發(fā)現(xiàn), 珊瑚礁為海洋魚(yú)類的祖先提供了數(shù)百萬(wàn)年來(lái)氣候變化的避難所。這一發(fā)現(xiàn)提示, 珊瑚礁不僅在環(huán)境變化時(shí)保護(hù)海洋物種, 它們還會(huì)塑造未來(lái)的物種多樣性格局。在第四紀(jì)時(shí)期, 地球經(jīng)歷了至少30次冰期-間冰期周期, 但環(huán)繞印澳群島卻始終存在廣袤的珊瑚礁。因此, 印澳群島成為當(dāng)今全球魚(yú)類物種多樣性最高的地區(qū)之一, 與該地區(qū)的珊瑚礁不無(wú)關(guān)系(Williams, 2017)。
1.2 印太交匯區(qū)熱帶珊瑚礁魚(yú)類多樣性格局的演化
本世紀(jì)生態(tài)學(xué)家提出生物地理學(xué)的核心問(wèn)題是印澳群島生物多樣性中心的起源問(wèn)題(Read, 2006)。生物進(jìn)化和環(huán)境演變的復(fù)雜過(guò)程和機(jī)制, 至今仍有許多奧秘未被揭開(kāi), 特別是當(dāng)?shù)貙訑?shù)據(jù)不完整以及化石證據(jù)不足時(shí), 生物進(jìn)化和演變過(guò)程成為爭(zhēng)議的焦點(diǎn)。近幾十年來(lái), 由于分子生物學(xué)和生物系統(tǒng)地理學(xué)的飛速發(fā)展, 使得生物學(xué)與地質(zhì)學(xué)交叉融合, 借助于化石尋求生物學(xué)上的證據(jù), 能夠推斷物種的起源、遷移以及變異, 進(jìn)而可以驗(yàn)證板塊構(gòu)造學(xué)的理論。
過(guò)去, 圍繞“印太交匯區(qū)的珊瑚礁三角區(qū)生物多樣性高”的問(wèn)題, 前人提出過(guò)很多假說(shuō)。其中被普遍接受的生物地理學(xué)模型假說(shuō)有中心物種形成模型、匯聚中心模型、重疊中心模型和華萊氏線假說(shuō)等(Lourie, 2004; Gaither, 2011)。采用譜系生物地理學(xué)的原理和研究方法來(lái)驗(yàn)證生物地理隔離假說(shuō), 已經(jīng)在海洋魚(yú)類的生物地理學(xué)研究中獲得了廣泛的應(yīng)用, 極大地提升了人們對(duì)典型海洋區(qū)域內(nèi)魚(yú)類多樣性格局的形成及演化過(guò)程的認(rèn)知。
1.2.1 中心物種形成模型(Center of speciation model) 又稱為物種起源中心假說(shuō)。物種以赤道熱帶區(qū)域?yàn)槠鹪粗行南蚰媳眱蓸O進(jìn)行種化擴(kuò)散。當(dāng)?shù)厍蛱幱诒?間冰期波動(dòng)時(shí)期, 珊瑚礁三角區(qū)成為海洋生物的冰期避難所, 保護(hù)了海洋生物多樣性。該模型認(rèn)為熱帶生物多樣性熱點(diǎn)地區(qū)(包括珊瑚礁三角區(qū))環(huán)境能夠促進(jìn)海洋生物物種的產(chǎn)生和輸出, 在地理復(fù)雜性、生境異質(zhì)性和激烈的生態(tài)位競(jìng)爭(zhēng)條件下會(huì)導(dǎo)致種群發(fā)生隔離分化, 并推動(dòng)物種的形成。這個(gè)假說(shuō)在熱帶珊瑚礁魚(yú)類中得到了廣泛的驗(yàn)證。
磯塘鱧屬()是隱居在珊瑚礁中、擴(kuò)布能力較弱的珊瑚礁魚(yú)類類群, 其生活史和生態(tài)學(xué)有助于潛在的物種形成。Tornabene等(2015)采用分子系統(tǒng)學(xué)和生物地理學(xué)分析手段, 解析了磯塘鱧屬2個(gè)群體在珊瑚礁三角區(qū)物種起源的時(shí)間和過(guò)程。基于線粒體和核DNA序列分析, 重建磯塘鱧屬魚(yú)類的分子系統(tǒng)學(xué), 重點(diǎn)分析了絲鰭磯塘鱧(Lachner & Karnella, 1980)和黑腹磯塘鱧(Giltay, 1933)這2個(gè)在珊瑚礁三角區(qū)均有分布的物種。研究結(jié)果揭示了絲鰭磯塘鱧和黑腹磯塘鱧這一對(duì)復(fù)合體在遺傳學(xué)上明顯表現(xiàn)出在珊瑚礁三角區(qū)存在與體色相關(guān)的、新近物種分化的痕跡。分子鐘校正表明多數(shù)分化事件發(fā)生在更新世, 并且物種之間的遺傳間隙的地理格局與化石無(wú)脊椎動(dòng)物及其他海洋魚(yú)類的幾乎一致。由于海平面的升降導(dǎo)致的地理隔離可以很好地在這些魚(yú)類類群間得到詮釋。珊瑚礁三角區(qū)作為世界海洋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熱點(diǎn)區(qū)域的原因之一, 是由于該區(qū)域海洋生物物種在原地快速分化成種。
Briggs(2004)研究了印太交匯區(qū)6個(gè)科魚(yú)類的系統(tǒng)發(fā)育關(guān)系, 結(jié)果支持進(jìn)化流理論, 即魚(yú)類物種從生物多樣性中心向外圍擴(kuò)散。對(duì)于東印度群島, 這意味著起源于多樣性中心的優(yōu)勢(shì)種將替代即將滅絕的、或者被迫沉入到深海、或者水平遷移到邊緣的老物種。魚(yú)類的線粒體DNA序列分析有跡象表明, 從東印度群島向外輻射, 魚(yú)類群體遺傳多樣性逐漸降低, 觀點(diǎn)支持了他以前提出的假設(shè), 即印太珊瑚礁三角區(qū)是物種起源中心的假設(shè)(Briggs, 1966, 1999)。
1.2.2 匯聚中心模型(Center of accumulation model) 又稱為物種積累中心假說(shuō)。許多物種起源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孤立群島, 如夏威夷或馬爾代夫群島, 然后被洋流帶進(jìn)珊瑚礁三角區(qū)。一旦進(jìn)入珊瑚礁三角區(qū), 這些物種就會(huì)與已經(jīng)生活在該地區(qū)的物種混合, 并最終形成高生物多樣性。自東向西流動(dòng)的北赤道流是太平洋海盆的群島幼體擴(kuò)布匯集至交匯區(qū)的主要?jiǎng)恿υ? 而自西向東的北赤道逆流則可將生物向交匯區(qū)以外擴(kuò)布。這兩個(gè)海流成為驗(yàn)證印太交匯區(qū)高生物多樣性成因和源匯假說(shuō)的天然實(shí)驗(yàn)場(chǎng)。
阿南屬()魚(yú)類隸屬于隆頭魚(yú)科(Labridae), 全球共有12種, 廣泛分布于印度-太平洋熱帶珊瑚礁或巖礁海域, 其中40%以上都是特有種。Hodge等(2012)基于線粒體和核DNA序列分析, 通過(guò)分子鐘校正后得出結(jié)論: 阿南屬魚(yú)類在始新世中期開(kāi)始出現(xiàn), 在中新世逐漸分化成種。研究結(jié)果還顯示, 印太交匯區(qū)外圍的地理隔離導(dǎo)致阿南屬魚(yú)類分化成種, 同時(shí)在產(chǎn)生和維護(hù)魚(yú)類特有種以及對(duì)印太交匯區(qū)的高生物多樣性的貢獻(xiàn)起到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通常認(rèn)為在更新世, 由于海平面的升降導(dǎo)致了陸地露出, 露出海平面的陸地成為物種擴(kuò)散的屏障, 隔離分化是支撐物種形成的主要機(jī)制。
1.2.3 重疊中心模型(Center of overlap model) 該模型認(rèn)為珊瑚礁三角區(qū)的海洋生物多樣性起源于太平洋與印度洋兩大生物區(qū)系的交匯重疊。在上新世和更新世冰盛期, 海平面下降導(dǎo)致珊瑚礁三角區(qū)成為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地理屏障, 印-太兩洋海洋生物發(fā)生隔離分化。隨著間冰期的到來(lái), 海平面上升, 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洋生物通過(guò)珊瑚礁三角區(qū)發(fā)生了隔離后混合事件, 使得珊瑚礁三角區(qū)的生物多樣性得以增強(qiáng)。
Gaither等(2011)基于線粒體和核DNA序列分析, 研究了法屬波利尼西亞、太平洋中西部、印度-太平洋交匯區(qū)、東印度洋、西印度洋5個(gè)區(qū)域的斑點(diǎn)九棘鱸(Bloch & Schneider, 1801)的遺傳變異, 斑點(diǎn)九棘鱸在研究區(qū)域內(nèi)具有明顯的種群分化。研究人員發(fā)現(xiàn)了斑點(diǎn)九棘鱸種群向珊瑚礁三角區(qū)遷移、擴(kuò)張的證據(jù)。線粒體Cyt基因序列單倍型分為2個(gè)分支, 分別對(duì)應(yīng)太平洋和印度洋區(qū)域, 且除兩大洋交匯區(qū)外, 二者基因互滲程度較低。冰期期間, 由于海平面較低而形成的印度-太平洋屏障是決定斑點(diǎn)九棘鱸親緣地理模式的首要因素。斑點(diǎn)九棘鱸在長(zhǎng)達(dá)10萬(wàn)年的冰期周期中被隔離的種群經(jīng)歷向珊瑚礁三角區(qū)擴(kuò)張, 并最終在印度-太平洋邊界處混合, 這個(gè)隔離后分化并最終混合的種群歷史可能是導(dǎo)致珊瑚礁三角區(qū)的高生物多樣性的原因之一, 生物多樣性在印度-太平洋交匯區(qū)多樣性最高, 因此支持“重疊中心模型”假說(shuō)。
1.2.4 華萊氏線假說(shuō)(Wallace’s line hypothesis) 華萊氏線是動(dòng)物地理區(qū)劃中東洋區(qū)與澳洲區(qū)的分界線。東南亞作為世界上地理特征最復(fù)雜的地區(qū)之一, 蘊(yùn)藏著豐富的生物多樣性水平和生物多樣性格局。英國(guó)博物學(xué)家華萊士通過(guò)實(shí)地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位于東南亞龍目海峽和望加錫海峽兩側(cè)的陸生動(dòng)物區(qū)系存在很大差異, 進(jìn)而劃定了著名的華萊氏線(Wallace’s line)。研究人員發(fā)現(xiàn), 除了陸生動(dòng)物存在東西生物區(qū)系分化外, 海洋生物動(dòng)物區(qū)系同樣遵循華萊氏線原則。
在更新世冰期, 由于海平面下降導(dǎo)致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間形成陸橋, 進(jìn)而導(dǎo)致印太兩洋的海洋生物基因交流發(fā)生中斷, 有可能造成分布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洋生物間在種、亞種或者群體水平上發(fā)生生物地理上的不連續(xù)性。為了檢驗(yàn)這種假說(shuō), Lourie等(2004)基于線粒體Cyt基因序列分析研究了東南亞的三斑海馬(Leach, 1814)的分子系統(tǒng)地理格局。研究發(fā)現(xiàn)在三斑海馬分布范圍內(nèi)檢測(cè)到2個(gè)明顯分化的譜系分支, 這2個(gè)譜系分支的地理分布與華萊氏線假說(shuō)相吻合。這些結(jié)果表明: 東南亞海域的海洋魚(yú)類遺傳格局復(fù)雜而多樣, 其形成及演化過(guò)程反映了復(fù)雜的生物地理事件, 并不能簡(jiǎn)單地用冰期海平面下降導(dǎo)致的印太兩洋之間的隔離來(lái)詮釋。
為了深入探討這個(gè)問(wèn)題, Lourie等(2005)采用比較譜系生物地理學(xué)的原理研究了東南亞海域的4種海馬的譜系地理格局, 結(jié)果發(fā)現(xiàn)4種海馬的譜系格局各不相同, 進(jìn)一步驗(yàn)證了作者上述提出的假設(shè)(Lourie, 2004)。
2 印太交匯區(qū)深海魚(yú)類多樣性
海洋面積約占地球總表面積的71%, 全球海洋的平均水深超過(guò)3500 m, 水深大于1000 m的深海區(qū)域超過(guò)全球海洋面積的90%。19世紀(jì)40年代以前, 人們對(duì)深海海洋認(rèn)知少之又少。自19世紀(jì)末英國(guó)“挑戰(zhàn)者號(hào)”第一次實(shí)現(xiàn)環(huán)球海洋科學(xué)考察以來(lái), 深海海洋科學(xué)研究才引起國(guó)際科學(xué)家的注意, 并且已經(jīng)成為國(guó)際海洋研究領(lǐng)域的前沿和孕育重大科學(xué)發(fā)現(xiàn)的搖籃。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 以美國(guó)、英國(guó)、德國(guó)等歐美國(guó)家為代表的世界海洋強(qiáng)國(guó)高度重視“藍(lán)海戰(zhàn)略”, 極大促進(jìn)了深海海洋科學(xué)和技術(shù)研究, 催生了一系列突破性研究成果(李超倫等, 2016)。
深海作為海洋系統(tǒng)的重要組成部分, 不僅包含了獨(dú)特的深海生態(tài)系統(tǒng)和極端生命過(guò)程, 而且還可能對(duì)上層海-氣能量交換產(chǎn)生深遠(yuǎn)影響。因此, 深海研究在整個(gè)地球科學(xué)和全球變化研究中都處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張素萍等, 2017)。深海蘊(yùn)藏著豐富的礦產(chǎn)資源, 同時(shí), 深海海底生物物種十分豐富, 據(jù)估計(jì)生活在深海的未知生命類群超過(guò)1000萬(wàn)種(李超倫等, 2016)。深遠(yuǎn)海極端環(huán)境中的海洋生物認(rèn)知及起源和演化研究是一直備受關(guān)注的前沿科學(xué)問(wèn)題。據(jù)報(bào)道, 全球尚有約20%的海洋未被勘測(cè), 特別是深海及遠(yuǎn)洋的中、下層深海珊瑚、海山、海溝、冷泉、熱液等未知區(qū)域(邵廣昭, 2011)。關(guān)于深遠(yuǎn)海魚(yú)類研究, 國(guó)外只有零星報(bào)道。隨著深海探測(cè)技術(shù)的進(jìn)步, 海洋科學(xué)研究已由近海逐漸向深遠(yuǎn)海發(fā)展, 不斷取得新的發(fā)現(xiàn)和認(rèn)知。
地球上絕大部分生態(tài)系統(tǒng)是利用光合作用來(lái)維持生命循環(huán), 但深海中缺乏陽(yáng)光和靜水壓力大, 形成黑暗、低溫和高壓的環(huán)境。深海生態(tài)系統(tǒng)中缺少光合作用的植物, 因而不能進(jìn)行光合作用, 也沒(méi)有植食性動(dòng)物, 只有碎食性和肉食性動(dòng)物、異養(yǎng)微生物和少量濾食性動(dòng)物。目前人類已發(fā)現(xiàn)的深海生態(tài)系統(tǒng)包括: 深海化能合成生態(tài)系統(tǒng)、深海海山生態(tài)系統(tǒng)、深淵生態(tài)系統(tǒng)、海底火山生態(tài)系統(tǒng)和海底湖泊生態(tài)系統(tǒng)等。
2.1 深海化能合成生態(tài)系統(tǒng)
深海化能合成生態(tài)系統(tǒng)是國(guó)際海洋生物多樣性研究計(jì)劃“國(guó)際海洋生物普查計(jì)劃”的現(xiàn)場(chǎng)研究項(xiàng)目之一。深海化能合成生態(tài)系統(tǒng)主要包括熱液、冷泉、鯨骨生態(tài)系統(tǒng)以及由其他高度還原型生境形成的生態(tài)系統(tǒng), 其中熱液和冷泉為典型的深海化能合成生態(tài)系統(tǒng), 也是近年來(lái)國(guó)際海洋科學(xué)研究的熱點(diǎn)。熱液和冷泉不僅有非常特殊的化能生態(tài)系統(tǒng), 還顛覆了人們“萬(wàn)物生長(zhǎng)靠太陽(yáng)”的認(rèn)知, 而且熱液區(qū)和冷泉區(qū)都具有豐富的礦物資源和生物多樣性, 但二者成因和分布不同, 環(huán)境特征也有較大差別(Cheng, 2019)。
熱液生物群落是深海化能合成生態(tài)系統(tǒng)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生物多樣性和生產(chǎn)力可與陸地?zé)釒в炅窒噫敲馈R曰茏责B(yǎng)細(xì)菌為基礎(chǔ)的管狀蠕蟲(chóng)、貝類、甲殼類、魚(yú)類等生物生活在不同類型的熱液區(qū), 通過(guò)化能營(yíng)養(yǎng)繁衍。
熱液動(dòng)物區(qū)系與一般深海海底生物區(qū)系相比, 有著低物種數(shù)、高優(yōu)勢(shì)度的特點(diǎn), 即熱液口周圍動(dòng)物區(qū)系物種多樣性低, 但是某一種的個(gè)體數(shù)量會(huì)很高, 同時(shí)密度往往很大。目前在已發(fā)現(xiàn)的50個(gè)活躍的海底熱液口中, 只有20個(gè)左右發(fā)現(xiàn)有魚(yú)類, 魚(yú)類的物種多樣性很低, 特有魚(yú)類非常多, 它們基本具有典型的熱液區(qū)系特征。2015年, 中國(guó)科學(xué)院海洋研究所依托先進(jìn)的“科學(xué)”號(hào)海洋科學(xué)考察船, 搭載“發(fā)現(xiàn)”號(hào)無(wú)人遙控深海機(jī)器人(ROV), 在沖繩海槽熱液區(qū)域進(jìn)行綜合調(diào)查時(shí)獲取的新幾內(nèi)亞火綿鳚(Machida & Hashimoto, 2002)(圖2)。

圖2 新幾內(nèi)亞火綿鳚Pyrolycus manusanus
注: a. ROV原位截圖; b. 外形圖
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lái), 美國(guó)、德國(guó)、法國(guó)、日本、澳大利亞等國(guó)家先后開(kāi)展了大規(guī)模的熱液口生物群落調(diào)查。據(jù)Desbruyères等(2006)報(bào)道, 已采集并描述典型熱液口大型動(dòng)物540種, 包括魚(yú)類19種, 隸屬2綱6目10科15屬。從物種數(shù)目看, 6個(gè)科最具代表性, 它們是角鯊科(Squalidae)、鼬鳚科(Ophidiidae)、長(zhǎng)尾鱈科(Macrouridae)、深海鱈科(Moridae)、合鰓鰻科(Synaphobranchidae)、綿鳚科(Zoaridae)。這些深海生境中的魚(yú)類物種多樣性很低, 以深海特有種占絕對(duì)優(yōu)勢(shì), 且具有典型的熱液區(qū)系和深海區(qū)系特征。
綿鳚科魚(yú)類是非常特殊的一個(gè)類群, 無(wú)論從物種數(shù)量還是生物量, 它們?cè)谒{(diào)查站位獲得的樣品中占絕對(duì)優(yōu)勢(shì)。綿鳚科魚(yú)類全球已知種類超過(guò)220種, 絕大多數(shù)屬于深海特有種, 這個(gè)科的魚(yú)類從淺海大陸架到5000 m深海均有分布, 它們之所以能夠適應(yīng)從近海到深海的熱液環(huán)境, 不僅與內(nèi)部器官構(gòu)造和食物鏈結(jié)構(gòu)的適應(yīng)進(jìn)化有關(guān), 而且與對(duì)熱液口周圍的化學(xué)環(huán)境適應(yīng)有關(guān)(Desbruyères, 2006)。
冷泉是深海中的另外一種極端環(huán)境。來(lái)自海底以二氧化碳、硫化氫或碳?xì)浠衔?甲烷或其他高分子量的碳?xì)錃怏w)為主的流體以噴涌或滲漏方式從海底溢出, 溫度與海水接近時(shí), 稱為冷泉。長(zhǎng)期以來(lái)深海被認(rèn)為是生命的禁區(qū), 在那里由于缺少陽(yáng)光, 海洋植物無(wú)法進(jìn)行光合作用, 導(dǎo)致深海環(huán)境氧氣匱乏, 同時(shí)還缺乏必要的食物來(lái)源。然而, 在海底冷泉噴口, 則存在以化能自養(yǎng)細(xì)菌為初級(jí)生產(chǎn)者的食物鏈, 衍生成群落結(jié)構(gòu)獨(dú)特的生態(tài)系統(tǒng), 形成了一片深海海底的“沙漠綠洲”, 且這可能就是生命的起源地之一。
冷泉生態(tài)系統(tǒng)與熱液生態(tài)系統(tǒng)中的生物群落相似, 物種生物量高, 而多樣性較低。科學(xué)家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的冷泉生物有600多種(German, 2011; 沙忠利, 2019)。但是冷泉生態(tài)系統(tǒng)中的生物生長(zhǎng)較慢。與冷泉中的無(wú)脊椎動(dòng)物相比, 人們對(duì)冷泉中的魚(yú)類認(rèn)知比較少, 原因在于深海魚(yú)類誘捕非常困難。
熱液和冷泉被發(fā)現(xiàn)也只有40多年歷史, 人類對(duì)于熱液和冷泉生態(tài)系統(tǒng)還缺乏深入了解, 需要不斷探尋和認(rèn)知。2013年以前, 中國(guó)科學(xué)家對(duì)深海化能生態(tài)系統(tǒng)這一前沿科學(xué)領(lǐng)域研究幾乎是空白。自2014年中國(guó)科學(xué)院海洋先導(dǎo)專項(xiàng)實(shí)施以來(lái), 先后執(zhí)行了沖繩海槽熱液區(qū)、馬努斯熱液區(qū)和南海冷泉區(qū)科學(xué)考察, 獲得了一些重要發(fā)現(xiàn)和一批有價(jià)值的生物樣品, 促進(jìn)了我國(guó)科學(xué)家對(duì)深海化能生態(tài)系統(tǒng)的了解, 為深海生物多樣性保護(hù)及資源開(kāi)發(fā)利用提供科學(xué)依據(jù)。
2.2 海山
海山(Seamount)又稱海底山, 狹義上是指海面以下高度超過(guò)1000 m的海底隆起, 廣義上將海底隆起高度500—1000 m的海丘和低于500 m的小山均稱為海山。海山是深海大洋中的顯著生態(tài)景觀, 以其獨(dú)特的生物群落、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和巨大的資源價(jià)值, 成為深海生物多樣性保護(hù)的國(guó)際熱點(diǎn)(徐奎棟, 2020)。據(jù)估計(jì), 全球海洋中有33452個(gè)海山和138412個(gè)海丘, 約占全球海底面積的21% (Clark, 2010)。
特殊的地理、地貌和水文特征, 形成了獨(dú)特的深海大洋中的海山生態(tài)系統(tǒng)。與周邊深海環(huán)境相比, 海山生態(tài)系統(tǒng)具有高生產(chǎn)力、高生物量和高生物多樣性等特點(diǎn), 成為深海研究中最為關(guān)注的生態(tài)系統(tǒng)之一。在中高緯度及少數(shù)低緯度的海山中, 常可見(jiàn)到成片的珊瑚林和海綿場(chǎng)生境, 因此, 海山又有“海底花園”之稱, 成為大洋遷徙動(dòng)物的驛站和海洋生物的避難所。
海山作為深海中的一種特殊生境, 已成為全球關(guān)注的熱點(diǎn)。海山涉及生物門類多, 物種多樣性非常豐富。但是, 我國(guó)開(kāi)展深海及海山生物探測(cè)和研究起步較晚。近些年來(lái), 我國(guó)陸續(xù)建成“蛟龍”號(hào)載人潛水器(HOV)和“發(fā)現(xiàn)”號(hào)無(wú)人遙控深海機(jī)器人(ROV)等探測(cè)設(shè)備, 在南海和西太平洋等海域開(kāi)展了海山探測(cè), 取得了第一手生物樣品和影像資料。然而, 由于地形復(fù)雜, 海山中的生物樣品獲取非常困難。目前全球已開(kāi)展的200個(gè)海山探測(cè)中, 多以生物影像為主, 生物樣品相對(duì)較少(徐奎棟, 2020)。圖3為2014—2017年中國(guó)科學(xué)院海洋研究所實(shí)施海洋專項(xiàng)開(kāi)展西太平洋雅浦海溝-馬里亞納海溝-卡羅琳洋脊交聯(lián)區(qū)海山調(diào)查獲取的魚(yú)類代表種原位圖像。
海山不僅是深海大洋中具有高生產(chǎn)力和高物種多樣性的特殊生境, 也是大洋漁場(chǎng)所在地。中高緯度的海山往往蘊(yùn)藏著豐富的漁業(yè)資源。據(jù)統(tǒng)計(jì), 已有調(diào)查取樣的全球海山中, 具有經(jīng)濟(jì)價(jià)值的魚(yú)類有80余種, 估算每年的漁獲量達(dá)到200多萬(wàn)t (Clark, 2007)。在全球已知的3萬(wàn)多個(gè)海山中, 已開(kāi)展生物取樣調(diào)查的僅占1%, 因此, 海山生態(tài)系統(tǒng)被認(rèn)為是人類最不了解的生物棲息地之一, 其作用機(jī)制值得我們?nèi)パ芯亢吞接憽?/p>

圖3 西太平洋雅浦海溝-馬里亞納海溝-卡羅琳洋脊交聯(lián)區(qū)海山魚(yú)類代表種原位圖像
注: a. 軟首鱈; b. 異鱗海蜥魚(yú); c. 合鰓鰻屬未定種sp.; d. 柯氏鼠鱈; e. 貢氏深海狗母魚(yú); f. 單棘躄魚(yú)
3 展望
印太交匯區(qū)熱帶珊瑚礁三角區(qū)的海洋生物多樣性高, 是古地質(zhì)和極端氣候事件、地殼運(yùn)動(dòng)過(guò)程、海洋水文環(huán)境與生命過(guò)程等多圈層、多界面與海洋生物物種互作形成的結(jié)果。珊瑚礁三角區(qū)的海岸生境為人類提供寶貴的漁業(yè)資源、庇護(hù)珍稀物種、保護(hù)海岸線免受侵蝕和能成為有效的“碳匯”區(qū)。然而, 近年來(lái), 隨著全球極端氣候變化和漁業(yè)捕撈量快速增加對(duì)印太交匯區(qū)海洋生物多樣性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影響, 未來(lái)該區(qū)域的海洋生物多樣性如何演變以及將會(huì)產(chǎn)生何種資源和環(huán)境效應(yīng)都有待深入研究。
長(zhǎng)期以來(lái), 人們都認(rèn)為深海是無(wú)生命的沙漠。然而, 隨著近年來(lái)大量研究發(fā)現(xiàn), 深海孕育著極其豐富的生物多樣性。熱液、冷泉、海山是地球上典型的極端環(huán)境, 支撐著區(qū)域性特有的海洋生物區(qū)系, 成為研究物理和生物過(guò)程相互作用造成物種隔離、分化和擴(kuò)散的絕佳研究場(chǎng)所(Shank, 2010)。由于受到深海探測(cè)技術(shù)、設(shè)備和研究經(jīng)費(fèi)的限制, 人類對(duì)這些極端環(huán)境下的深海生命過(guò)程研究不夠深入。近些年來(lái), 深海大洋的生態(tài)系統(tǒng)一直受到世界各國(guó)政府、科學(xué)界和社會(huì)公眾的廣泛關(guān)注。自2013年以來(lái), 我國(guó)自主設(shè)計(jì)、自主集成研制的“蛟龍?zhí)枴陛d人深潛器和最先進(jìn)的綜合科學(xué)考察船“科學(xué)”號(hào)的下水, 并搭載先進(jìn)海洋探測(cè)設(shè)備, 標(biāo)志著我國(guó)已經(jīng)具備深海探測(cè)與研究的能力(張均龍等, 2013)。鑒于深海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獨(dú)特性及其在全球生態(tài)系統(tǒng)中的重要意義, 深海環(huán)境和生命過(guò)程的探索與認(rèn)知是當(dāng)前和將來(lái)國(guó)際地球與生命科學(xué)的前沿和重要研究?jī)?nèi)容之一。
印太珊瑚礁三角區(qū)是全球海洋生物多樣性最高的區(qū)域, 相對(duì)于淺海, 迄今對(duì)深海的生物多樣性和地理格局的認(rèn)知更加匱乏。對(duì)于該區(qū)域深海生物多樣性的起源、演化與擴(kuò)布機(jī)制, 以及深海的生物多樣性分布格局是否具有類似淺海的特點(diǎn)尚不明確。相較于近海環(huán)境的動(dòng)蕩, 深海環(huán)境更為穩(wěn)定, 因此被認(rèn)為是重大滅絕事件中海洋生物的避難所, 同時(shí)也可能保存了古老物種(Newman, 1985; Tunnicliffe, 1998)。基于化石記錄能夠重現(xiàn)生命演化歷史, 改變?nèi)祟悓?duì)古生代海洋生物多樣性演化的認(rèn)知。但是, 超過(guò)1億年歷史的已知深海化石記錄的數(shù)量非常少。由于古代深海生物記錄的稀缺, 科學(xué)家們往往認(rèn)為深海生物群落起源于近海淺水區(qū)。針對(duì)熱液、冷泉和海山等深淵區(qū)域的代表性物種的系統(tǒng)進(jìn)化分析結(jié)果表明, 在這些極端環(huán)境中, 多數(shù)生物類群位于進(jìn)化節(jié)點(diǎn)的末端并發(fā)生了單向特化, 即起源于近海(Lorion, 2013)。然而, 近期發(fā)現(xiàn)的1.8億年深海生物化石或?yàn)楹Q笊锲鹪刺峁┬碌目茖W(xué)證據(jù), 深海在產(chǎn)生和保存海洋生物多樣性方面所起的作用遠(yuǎn)比之前預(yù)想的要大得多(Thuy, 2014)。
環(huán)境變化背景下生物的適應(yīng)性進(jìn)化是生物多樣性產(chǎn)生的重要機(jī)制。隨著分子生物技術(shù)和基因組學(xué)的蓬勃發(fā)展, 讓生物學(xué)家能夠檢測(cè)到新物種起源與演化的信號(hào), 并且將物種形成過(guò)程中產(chǎn)生的變異格局能在基因水平上得到詮釋。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jì), 全球已完成350余種硬骨魚(yú)的全基因組測(cè)序工作, 主要涉及魚(yú)類物種起源進(jìn)化、重要性狀形成機(jī)理以及選擇育種等研究。Wang等(2019)通過(guò)全基因組學(xué)分析, 結(jié)合關(guān)鍵性狀調(diào)控基因(骨鈣素基因、三甲胺N-氧化物以及hsp90伴侶蛋白基因等)突變研究, 揭示了生活在馬里亞納海溝6000 m深處以下的獅子魚(yú)(Gerringer & Linley, 2017)適應(yīng)深海極端環(huán)境的遺傳基礎(chǔ), 對(duì)脊椎動(dòng)物的形態(tài)、生理和分子進(jìn)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見(jiàn)解。全基因組數(shù)據(jù)分析顯示海馬(Cantor, 1849)是目前已獲得全基因組魚(yú)類中進(jìn)化速率最快的物種, 并且海馬與環(huán)境適應(yīng)相關(guān)的基因在長(zhǎng)期的進(jìn)化過(guò)程中發(fā)生了明顯收縮(Lin, 2016)。該研究還進(jìn)一步發(fā)現(xiàn)了海龍科魚(yú)類118個(gè)基因與胎盤類哺乳動(dòng)物趨同進(jìn)化, 這些基因參與了育兒袋內(nèi)細(xì)胞增殖與凋亡、血管增生及胚胎發(fā)育等生命過(guò)程(Zhang, 2020)。生物對(duì)環(huán)境的適應(yīng)是一種復(fù)雜的機(jī)制, 基因組高通量測(cè)序技術(shù)及多組學(xué)聯(lián)合的生物信息技術(shù)的發(fā)展將為物種的起源機(jī)理、演化規(guī)律和適應(yīng)性研究提供有力的數(shù)據(jù)支撐。
王麗榮, 趙煥庭, 2001. 珊瑚礁生態(tài)系的一般特點(diǎn). 生態(tài)學(xué)雜志, 20(6): 41—45
李超倫, 李富超, 2016. 深海極端環(huán)境與生命過(guò)程研究現(xiàn)狀與對(duì)策. 中國(guó)科學(xué)院院刊, 31(12): 1302—1307
沙忠利, 2019. 西太平洋深海化能生態(tài)系統(tǒng)大型生物圖譜. 北京: 科學(xué)出版社, 1—205
張均龍, 徐奎棟, 2013. 海山生物多樣性研究進(jìn)展與展望. 地球科學(xué)進(jìn)展, 28(11): 1209—1216
張素萍, 張樹(shù)乾, 2017. 軟體動(dòng)物腹足綱分類學(xué)研究進(jìn)展-從近海到深海. 海洋科學(xué)集刊, 52: 1—10
邵廣昭, 2011. 十年有成的“海洋生物普查計(jì)劃”. 生物多樣性, 19(6): 627—634
徐奎棟, 2020. 西太平洋海溝洋脊交聯(lián)區(qū)海山動(dòng)物原色圖譜. 北京: 科學(xué)出版社, 1—239
Allen G R, 2008. Conservation hotspots of biodiversity and endemism for Indo-Pacific coral reef fishes. Aquatic Conservation: Marine and Freshwater Ecosystems, 18(5): 541—556
Allen G R, Adrim M, 2003. Coral reef fishes of Indonesia. Zoological Studies, 42(1): 1—72
Allen G R, Erdmann M V, 2012. Reef Fishes of the East Indies. Volumes I-III. Perth: Tropical Reef Research, 1—1292
Bellwood D R, Meyer C P, 2009. Searching for heat in a marine biodiversity hotspot. Journal of Biogeography, 36(4): 569—576
Briggs J C, 1966. Zoogeography and evolution. Evolution, 20(3): 282—289
Briggs J C, 1999, Modes of speciation: Indo-West Pacific. Bulletin of Marine Science, 65: 645—666
Briggs J C, 2004. A marine center of origin: reality and conservation. In: Lomolino M V, Heaney L R eds. Frontiers of Biogeography. Sunderland: Sinauer Associates, 255—269
Briggs J C, 2005. The marine East Indies: diversity and speciation. Journal of Biogeography, 32(9): 1517—1522
Brooks T M, Mittermeier R A, da Fonseca G A B, 2006. Glob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priorities. Science, 313(5783): 58—61
Carpenter K E, Barber P H, Crandall E D, 2011. Comparative phylogeography of the Coral Triangle and implications for marine management.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s, 2011: 396982, doi: 10.1155/2011/396982
Cheng J, Hui M, Sha Z L, 2019. Transcriptomic analysis reveals insights into deep-sea adaptations of the dominant species,(Crustacea: Decapoda: Anomura), inhabiting both hydrothermal vents and cold seeps. BMC Genomics, 20: 388
Clark M R, Koslow J A, 2007. Impacts of fisheries on seamount. In: Pitcher T J, Morato T, Hart P J Beds, 2007. Seamounts: Ecology,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Ltd, 413—441
Clark M R, Rowden A A, Schlacher T, 2010. The ecology of seamounts: structure, function, and human impacts. Annual Review of Marine Science, 2: 253—278
Connolly S R, Bellwood D R, Hughes T P, 2003. Indo-Pacific biodiversity of coral reefs: deviations from a mid-domain model. Ecology, 84(8): 2178—2190
Cowman P F, Bellwood D R, 2011. Coral reefs as drivers of cladogenesis: expanding coral reefs, cryptic extinction even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iodiversity hotspots.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Biology, 24(12): 2543—2562
Desbruyères D, Segonzac M, Bright M, 2006. Handbook of Deep-Sea Hydrothermal Vent Fauna. 2nd ed. Linz: Biologiezentrum der Ober?sterreichischen Landesmuseem, 1—544
Gaither M R, Bowen B W, Bordenave T R, 2011. Phylogeography of the reef fish(Epinephelidae) indicates Pleistocene isolation across the Indo-pacific barrier with contemporary overlap in the coral triangle. BMC Evolutionary Biology, 11: 189
German C R, Ramirez-Llodra E, Baker M C, 2011. Deep-water chemosynthetic ecosystem research during the census of Marine life decade and beyond: a proposed deep-ocean road map. PLoS One, 6(8): e23259
Hodge J R, Read C I, van Herwerden L, 2012. The role of peripheral endemism in species diversification: evidence from the coral reef fish genus(Family: Labridae). Molecular Phylogenetics and Evolution, 62(2): 653—663
Lin Q, Fan S, Zhang Y, 2016. The seahorse genome and the evolution of its specialized morphology. Nature, 540: 395—399
Lorion J, Kiel S, Faure B, 2013. Adaptive radiation of chemosymbiotic deep-sea mussel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80(1770): 20131243, doi: 10.1098/rspb.2013.1243
Lourie S A, Green D M, Vincent A C J, 2005. Dispersal, habitat differences, and comparative phylogeography of Southeast Asian seahorses (Syngnathidae:). Molecular Ecology, 14(4): 1073—1094
Lourie S A, Vincent A C J, 2004. A marine fish follows Wallace’s Line: the phylogeography of the three-spot seahorse (, Syngnathidae, Teleostei) i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Biogeography, 31(12): 1975—1985
Mora C, Chittaro P M, Sale P F, 2003. Patterns and processes in reef fish diversity. Nature, 421(6926): 933—936
Myers N, Mittermeier R A, Mittermeier C G, 2000. Biodiversity hotspots for conservation priorities. Nature, 403(6772): 853—858
Newman W A, 1985. The abyssal hydrothermal vent invertebrate fauna: a glimpse of antiquity? Bulletin of the Biological Society of Washington, 6: 231—242
Pellissier L, Leprieur F, Parravicini V, 2014. Quaternary coral reef refugia preserved fish diversity. Science, 344(6187): 1016—1019
Rabosky D L, Chang J, Title P O, 2018. An inverse latitudinal gradient in speciation rate for marine fishes. Nature, 559(7714): 392—395
Read C I, Bellwood D R, van Herwerden L, 2006. Ancient origins of Indo-Pacific coral reef fish biodiversity: a case study of the leopard wrasses (Labridae:). Molecular Phylogenetics and Evolution, 38(3): 808—819
Renema W, Bellwood D R, Braga J C, 2008. Hopping hotspots: global shifts in marine biodiversity. Science, 321(5889): 654—657
Roberts C M, McClean C J, Veron J E N, 2002. Marine biodiversity hotspots and conservation priorities for tropical reefs. Science, 295(5558): 1280—1284
Shank T M, 2010. Seamounts: deep-ocean laboratories of faunal connectivity, evolution, and endemism. Oceanography, 23(1): 108—122
Thuy B, Kiel S, Dulai A, 2014. First glimpse into Lower Jurassic deep-sea biodiversity:diversification and resilience against extinction.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81(1786): 20132624
Tornabene L, Valdez S, Erdmann M, 2015. Support for a ‘Center of Origin’ in the Coral Triangle: cryptic diversity, recent speciation, and local endemism in a diverse lineage of reef fishes (Gobiidae:). Molecular Phylogenetics and Evolution, 82: 200—210
Tunnicliffe V, McArthur A G, McHugh D, 1998. A bio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of the deep-sea hydrothermal vent fauna. Advances in Marine Biology, 34: 353—442
Wang K, Shen Y J, Yang Y Z, 2019. Morphology and genome of a snailfish from the Mariana Trench provide insights into deep-sea adaptation. 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 3(5): 823—833
Williams S L, Ambo-Rappe R, Sur C, 2017. Species richness accelerates marine ecosystem restoration in the Coral Triangl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4(45): 11986—11991
Zhang Y H, Ravi V, Qin G, 2020. Comparative genomics reveal shared genomic changes in syngnathid fishes and signatures of genetic convergence with placental mammals.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7(6): 964—977
PROGRESS IN FISH DIVERSITY PATTERN AND EVOLUTION IN THE INDO-PACIFIC CONVERGENCE REGION
LIU Jing1, 2, XIAO Yong-Shuang1, 2
(1. Center for Ocean Mege-Science,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China; 2.Institute of Ocean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China)
The Indo-Pacific Convergence Region is not only the center of sea-air energy convergence, tectonic movement, and biodiversity in the tropical ocean, but also an ideal area for studying the exchange of material and energy in the earth system,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origin of marine biodiversity. Therefore, it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 by scientists all over the world. Specifically, as one of the 34 global richest biodiversity hotspots and a relatively small part of the Indo-Pacific Convergence Region, the Coral Triangle harbors about 76% reef-building coral species, 75% mangrove species, 50% coral reef fish species and 45% seaweed species of the world. Among them, fishes ar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group and play a major role in the assemblage and maintenance of coral reef communities throughout the Indo-Pacific Convergence Region. In the past, biologists have done great works on fish diversity pattern and evolution of tropical coral reef in the shallow marine ecosystem. Several hypotheses, including the Center of Speciation Model, the Center of Accumulation Model, the Center of Overlap Model, the Wallace’s Line Hypothesis, etc., have been verified in some fish groups in the Coral Triangle. However, compared with the researches on fish diversity of tropical coral reefs in the Indo-Pacific Convergence Region, studies on deep-sea waters started relatively late, and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long-time observation data and systematic research.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controversies in the respects of mechanisms of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marine biodiversity centers and the source and pool between the marine organisms from tropical shallow water and deep-sea water. We summarized the latest research progresses o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fish diversity in both tropical coral reef and deep-sea water, and propose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deep-sea extreme environments and life processe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processes of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biodiversity center in the Indo-Pacific Convergence Region and to provide scientific evidence to substantiate/disprove various biogeographic hypotheses and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strategic biological resources.
Indo-Pacific Convergence Region; Coral Triangle; fishes; biodiversity; distribution pattern; evolution
* 國(guó)家自然科學(xué)基金項(xiàng)目, 31872195號(hào); 中國(guó)科學(xué)院戰(zhàn)略性科技先導(dǎo)專項(xiàng), XDB42000000號(hào); 中國(guó)科學(xué)院國(guó)際合作局國(guó)際伙伴計(jì)劃資助項(xiàng)目, GJHZ2039號(hào)。劉 靜, 博士, 研究員, E-mail: jliu@qdio.ac.cn
2020-09-07,
2020-11-16
Q178.53; Q951; S932.4
10.11693/hyhz20200900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