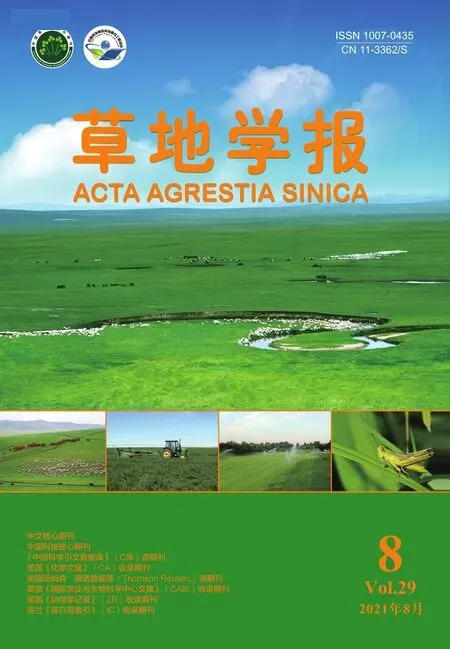中國草原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現狀及展望
岳方正, 高書晶, 程通通, 徐林波, 韓海斌*, 丁 偉, 柴守權*
(1.國家林業和草原局森林和草原病蟲害防治總站, 遼寧 沈陽 110034;2.中國農業科學院草原研究所, 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3.寧夏固原市涇源縣大雪山林場, 寧夏 固原 756400)
草原是我國面積最大的陸地生態系統,是干旱半干旱和高寒地區的主要植被類型,與森林共同構成了我國生態安全屏障的主體。我國有天然草原4億hm2,占國土面積的40.9%,是耕地面積的2.91倍、森林面積的1.89倍[1]。草原生態系統十分脆弱,群落結構相對單一,食物鏈結構相對簡單,被過度利用后形成的次生裸地加快了風蝕和沙化,面積不斷擴大[2]。在全球變暖大環境下,過度利用引起草原退化,植被群落發生巨大變化:水源涵養能力下降,形成的裸地為蝗蟲繁殖提供了良好條件[2-3];植被高度和蓋度大幅降低,有利于嚙齒動物的生存,從而引起種群密度增長造成鼠害[4-5];草地植被蓋度降低也為毒害草繁殖提供了空間,毒害草環境適應能力強,種間競爭力強,顯著降低草原生物多樣性,降低草原生態系統的自我修復能力[6]。
草原生態系統中生產者數量的減少,降低了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的效率,食物網結構受到破壞,最終引起草原生態系統的持續性惡化[2,7],特別是受氣候、人為等因素影響,我國草原的退化和沙化嚴重,導致鼠、蟲、毒害草及病害滋生蔓延,形成草原生物災害,而生物災害又再次加劇了草原生態環境惡化,形成惡性生態循環[8-9]。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指出:“要提升生態系統質量和穩定性”。因此,加強草原生物災害防治工作,是加快草原生態修復的重要舉措,事關生態文明建設、民族團結、邊疆穩定和牧區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1-2,7-8]。
本文在廣泛調查基礎上結合文獻資料,全面回顧了我國草原有害生物為害情況,客觀評價了防治工作取得的成效,并科學分析當前制約草原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瓶頸問題,面向行業發展需求系統提出加強草原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展望。
1 我國草原有害生物為害現狀
1.1 為害草原的有害生物種類多
我國草原有害生物災害包括鼠、蟲、毒害草及病害4大類[2]。草原害鼠為嚙齒動物,有兔形目和嚙齒目兩大類100余種,常見的草原害鼠有20多種,已開展監測與防治的為害鼠種有高原鼠兔(Ochotonacurzoniae)、高原鼢鼠(Eospalaxfontanierii)、大沙鼠(Rhombomysopimus)、布氏田鼠(Lasiopodomysbrandtii)等[4]。為害草原的害蟲包括蝗蟲類、草原毛蟲類、夜蛾類、葉甲類、草地螟(Loxostegesticticalis)、蚜蟲類、葉蟬類、盲蝽類和薊馬類等,已開展監測和防治的草原害蟲只有草原蝗蟲、草原毛蟲、白茨夜蛾(Leiometononsiyrides)等[9];世界上目前已知的蝗蟲有10 000余種,我國有1 000余種,造成危害的蝗蟲有20余種[10]。草原有毒有害植物有101科1 000種,已開展監測和防治的物種只有豚草(Ambrosiaartemisiifolia)、三裂葉豚草(Ambrosiatrifida)、紫莖澤蘭(Eupatoriumadenophorum)、瑞香狼毒(Stellerachamaejasme)、烏頭(Aconitumcarmichaeli)、棘豆、少花蒺藜草(Cenchrusspinifex)等為害面積較大的種類[9]。我國草原病害調查主要針對牧草,以生態為導向的草原病害調查尚未開展,缺乏文獻資料。
1.2 草原有害生物為害面積大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草原有害生物總體上呈偏重發生態勢,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末期至本世紀初期,草原有害生物災害連年高發[2,7]。據統計,2011—2018年草原鼠害年均為害面積3 232.40 萬hm2,2011—2018年草原蟲害年均為害面積1 432.33萬hm2,鼠蟲害為害面積約是林區的5倍[2,5]。2019年草原鼠害為害面積3 737.26萬hm2,嚴重為害(種群密度是為害指標的2倍以上)面積1 461.46 萬hm2;草原蟲害為害面積1 038.40 萬hm2,嚴重為害面積455.25 萬hm2;全國9個省份發生草原毒害草為害面積1 644.25 萬hm2,嚴重為害面積225.73 萬hm2[11]。
1.3 草原有害生物為害損失大
從鼠蟲害造成經濟損失方面來看,按照每公頃牧草損失450 kg、每公斤鮮草0.3元計算,2011—2018年每年平均發生鼠蟲害4 664.73 萬hm2,年均損失牧草約210億公斤,造成直接經濟損失62億元[2,12]。從鼠蟲害造成的生態環境的破壞來看,害鼠打洞造穴,推土造丘覆蓋地表,破壞草皮和地表土層,造成地面塌陷、水土流失、礫石裸露和沙化,嚴重者造成寸草不生的次生裸地,即“黑土灘”,降低了草原防風固沙能力,增加沙塵暴發生風險[5]。從鼠害對人類社會的為害來看,鼠類是很多疾病發生和流行的傳播媒介,能傳播鼠疫、流行性出血熱、鉤端螺旋體病等30多種疾病[2]。2000—2010年青海省發生13起鼠疫,2004年囊謙縣暴發的肺鼠疫致死6人,2009年興海縣子科灘爆發的肺鼠疫致死3人[4]。2019年內蒙古多地發生鼠疫病例。鼠蟲害的爆發嚴重降低牧民生活質量,拖慢脫貧攻堅步伐,危及邊疆穩定[11]。
2 我國草原有害生物防治現狀
2.1 工作機制不斷完善
經過多年努力,全國已建立比較完善的年度草原有害生物防治工作機制。每年的1月份,有關省區上報全年的防治計劃;3月份,有關省區召開鼠蟲害發生趨勢會商會議,發布災害發生趨勢分析報告,預測全年鼠蟲害為害程度、區域和面積;4月份,召開全國草原鼠蟲害防控工作部署會,研判草原鼠蟲害發生形勢,部署防控工作;在災害發生和防控關鍵時期,有關省區運行“定位監測、路線調查、牧民監控、應急值班”四位一體的監測預警工作機制,對關鍵時期、重點區域、重點物種開展監測,發布監測預警信息,適時開展新藥物篩選和新技術試驗示范;6—8月份,有關省區每周上報蟲害發生和防治情況,實行24小時值班和“零報告”制度;7—8月份,有關省區草原站領導專家組成督查組,開展省際間的草原生物災害防控工作檢查;9月份,召開全國草原鼠蟲害防控工作總結會,總結上報年度防治工作成效報告。
2.2 生物防治比例逐步提高
近年來,各級草原部門堅持“預防為主、綜合防治”的植保方針,牢固樹立“科學植保、公共植保、綠色植保”理念,草原有害生物綠色防治比例不斷提高。2014年全國鼠蟲害綠色防治比例分別為82%和57%,2016年分別達到82%和59%。2019年草原鼠害共完成防治面積532 萬hm2,綠色防治面積468.52 萬hm2,綠色防治比例達到89%,較2016年提高7個百分點;草原蟲害完成防治面積356.07 萬hm2,綠色防治面積297.80 萬hm2,綠色防治比例達到84%,較2016年提高25%[11-13]。
2.3 綜合防治技術集成化
草原生物災害防控工作由單一防控技術向多項技術轉變,初步構建了生物防治、化學防治、天敵防治、生態治理相結合的治理技術體系。用于防治鼠害的微生物制劑主要包括C型肉毒素、D型肉毒素等;用于防治害蟲的微生物制劑有蝗蟲微孢子蟲、阿維菌素·蘇云金桿菌、綠僵菌等;用于防治鼠蟲害的植物源農藥主要包括雷公藤甲素、印楝素、苦參堿、煙堿·苦參堿等;用于防治鼠蟲害的天敵動物主要包括招鷹控鼠、野化狐貍控鼠;用于防治蟲害的天敵動物包括雞和鴨等;草原鼠害的物理防控主要包括世雙鼠靶、鼠夾、鼢鼠箭、洞道箭等;生態調控為利用政策法規改善生態環境,提高環境的耐害性,包括禁牧、休牧、劃區輪牧、飛播種草等[14-16]。
2.4 綜合防治模式逐步形成
近年來,各地草原推廣機構因地制宜,組織開展了防治技術試驗示范,形成了一批效果較好的綜合防治模式。在鼠害防治方面,形成了“弓箭滅鼠+圍欄禁牧”“運—5飛機投餌+招鷹控鼠+圍欄禁牧”“機械投餌+野化狐貍控鼠+圍欄禁牧”“人工投餌+圍欄禁牧+補播改良草場”“弓箭滅鼠+圍欄禁牧+補播改良草場”“人工投餌+招鷹控鼠+圍欄禁牧+補播改良”和“三角翼飛機投餌+招鷹控鼠+圍欄禁牧”等綜合配套技術[17]。在蟲害防治方面,形成了“飛機防治+地面機械+牧雞防治”三機(雞)聯動防控,“大型機械+生物制劑+植物源農藥”和“人工招引紅椋鳥+牧雞、牧鴨”等綜合防控模式[18-20]。
2.5 防治投入有所增加
2010—2018年累計投入防治經費25億元[3,21-22]。2019年全國草原生物災害防治工作投入經費23 282.22萬 元,其中內蒙古、遼寧、云南、西藏、新疆、新疆兵團,青海7個省(區)地方自籌經費共1629.51萬 元,占投資總額7%。2010—2018年省級草原鼠、蟲害防治標準平均約為15元·ha-1,2019年草原鼠、蟲害防治標準分別增加為19.65元·ha-1,36.15元·ha-1[11]。
3 我國草原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
近年來,我國草原有害生物防治工作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與當前國家草原保護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的需要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面臨一系列突出問題和現實困難,遠不能滿足草原保護和草原防災減災工作客觀需求。
3.1 防治法規及理念滯后
涉及草原有害生物防治的法律法規、政策普遍陳舊,在草原有害生物防治的計劃申報、監測預警、藥物安全使用、防治機械管理、應急防治組織、防治工程管理、防治效果調查和監測預報等方面,沒有最新的、具體的法規制度[8]。另外,草原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具有很強的社會性,其工作開展需要全社會的大力支持,但由于資金投入少、草原區地廣人稀、思想觀念落后等因素,社會化防治服務機制還不健全,社會化防治服務組織數量較少,草原有害生物防治的市場化、社會化程度極低,遠遠不能滿足草原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實際需要。
3.2 防治資金投入滯后和不足
由于大部分草原地區經濟發展滯后,地方財政財力有限,完全依賴于中央財政補助資金開展草原鼠蟲害防治工作,加之近年來運輸成本、油料開支、勞務支出等基本防治成本大幅上漲,導致實際防治成本遠大于目前的中央財政補助標準[20]。同時,中央財政草原鼠蟲害防治資金下達較晚,錯過最佳防治適期[11]。鼠害防治一般在春季、秋冬季開展,6—7月為蝗蟲最佳防治期,而鼠蟲害防治資金7月份才能到達縣級防治部門,錯過了鼠蟲害的最佳防治期。
3.3 監測預警能力較低
目前,草原有害生物的監測站點少,盲區多,不能滿足有害生物監測預警的需求,不能有效實現災前預報,延誤最佳防治時機,往往成災后再救災,導致防治費用成倍增加[23-24]。隨著草原生態環境整體惡化,草原有害生物宜生區域不斷擴大。雖然2017年以來按照《全國動植物保護能力提升工程建設規劃》[25],啟動實施了一批監測站建設,但監測預警體系建設還相當不完善,省、市有害生物監測預警中心建設未實現全覆蓋,監測預警信息覆蓋面和時效性亟待提高。基層草原站普遍缺乏野外監測車輛,原有害生物監測與防治數據上報軟件已基本停用,目前也無新軟件替代使用。數據預測預報方法落后,主要鼠害、蟲害的發生趨勢預測模型數量少,可用性差,只能依靠人為經驗、氣象數據、有限的地面調查數據進行預測。
3.4 基本防治能力嚴重不夠
據統計,“十三五”期間全國草原有害生物年均防治面積1 138.88萬ha,僅占為害面積的28.44%[12],巨大的應防未防區域為翌年暴發埋下隱患,造成“年年防治,年年爆發”的尷尬處境。長期以來,由于沒有草原有害生物防治的基本建設項目,導致基礎設施建設十分滯后。各地區均無專用的物資儲備設施,缺乏必要的應急物資儲備,缺少大、中型施藥機械,現有機械普遍陳舊、老化,應對突發性草原災害能力薄弱,使防治工作被動。草原牧區地廣人稀,勞動力缺乏,機械化專業化防治隊伍不足,組織農牧民進行人工防治難度大,飛機和機械防治僅可在北方典型草原地區開展,高寒草甸草原地區大多依靠人工投餌和捕捉。尤其是青藏高原等藏區,受宗教信仰的影響,防治工作主要依靠外來人員,難以形成穩定的技術隊伍,致使防治效率低和防治成本高,無法及時遏制草原鼠蟲害爆發。
3.5 科技支撐力度有限
長期以來,從事草原有害生物研究的人員較少,科技支撐能力薄弱,研究內容不系統、研究深度和廣度不夠。受研究項目、方法等因素制約,草原有害生物災害的發生規律、監測預警、防治等關鍵技術研究不夠深入;有害生物的中長期災變規律不清;生物生態防治技術非常有限,適用先進技術較少,研究成果產業化步伐過慢[11]。受氣候變化等因素影響,一些草原有害生物種類的生物學特性、發生規律、成災機制發生了新的變化,但相應的防治方法的研究未跟進、防治機制尚未形成。草原有害生物防治的科技貢獻率遠遠低于草業發達國家。
4 我國草原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展望
4.1 落實防治責任,進一步理順管理體制
草原有害生物災害與林業有害生物災害、森林和草原火災、洪澇,以及臺風、風雹、高溫熱浪、海冰、地震等災害一樣,屬自然災害范疇,但也有人為災害特征,如因人為過度放牧所導致的草原有害生物災害等。草原有害生物防治屬于公共服務范疇,具有普惠性和公益性。因此,同樣需要納入防災減災體系,予以同等重視。在我國,政府在防災減災中承擔著主導作用,這是我國的國情和優勢。根據《草原法》的規定和我國防災減災體制,草原有害生物防治工作中政府應起主導作用。因此,應堅持“政府主導,屬地管理,分級負責”的工作機制,督促和引導地方政府關注和重視草原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強化組織領導,盡快落實盟州、旗縣兩級草原有害生物防治機構歸屬問題。
4.2 創新防治機制,推進社會化防治
機制創新是解決事業單位改革后基層防治力量弱的有效手段,特別是對于沒有獨立的草原有害生物防治機構的縣市區,更要通過機制創新,確保草原有害生物防治不弱化、不斷檔。社會化防治組織形式是一種適應市場經濟的防治草原有害生物的組織形式,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市場化防治機制。在具備條件的地區,開展防治機制創新試點,積極探索政府購買防治服務方式的社會化防治。在推進社會化防治工作過程中,各級草原主管部門應重點研究制訂社會化防治組織資質和從業人員資格認定制度,完善社會化防治的招投標制度、作業監理制度、防治效果評估和第三方防治成效核查評價制度;建立起政府、部門、企業、公眾共同參與的社會化防治監督機制,規范社會化防治市場,暢通公眾監督渠道,依法查處違約、違規行為;加強防治協會建設的指導,支持行業協會等社團組織參與林業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發揮其應有的積極作用。
4.3 突出防治重點,爭取啟動實施工程治理
為實現草原生物災害應防盡防或者全面防治,借國家高度重視草原工作的機遇,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積極爭取國家支持,在重要生態區域,針對重大生物災害,集中人力、財力、物力啟動實施重大草原生物災害工程治理,建立持續有效的防控機制,以此推動整個草原生物災害防治工作的開展。啟動實施重大草原生物災害工程治理,不僅可有效控制草原有害生物嚴重為害的局面,最大程度最大可能地降低損失,而且還可以增加國家資金投入的使用效率。
4.4 加強草原有害生物防治人才隊伍建設
加強草原有害生物防治機構人員隊伍培訓,提升從業人員業務素養,是做好草原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基礎。各級防治機構應著力提高植物保護、草地保護等相關專業人員比例,加強教育培訓,提高工作人員的防治管理水平和服務能力,為全面加強林業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奠定堅實基礎。國家應建立全國技術師資庫,指導省級防治機構做好防治、測報技術人員的培訓工作。認真制訂行業人員隊伍培訓計劃,逐級定期開展防治技術培訓,切實提高基層技術人員、生態管護員、兼職測報員和農牧民的防治技能,形成一支結構合理、素質優良、專業過硬的草原有害生物防治人才隊伍。
4.5 加強基礎設施和體系建設,提高綜合防治能力
認真落實《全國動植物保護能力提升工程建設規劃(2017—2025年)》,抓好國家發改委和原農業部已批復的基礎建設項目的銜接與實施,推進草原有害生物監測預警中心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實施,整合包括生態定位站在內的現有力量建立和完善監測預報體系;結合當前草原有害生物防治實際,實施區域應急防控設施及物資儲備庫等新建項目,配備生產防治急需的大中型植保機械,提升災變的應急、防控能力。在國家《“十四五”林業和草原發展規劃》中增加“草原有害生物防治基礎設施建設”相關內容,積極引導和推動各地政府將“草原防災減災基礎設施建設”納入地方政府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中,將草原有害生物防治經費納入地方財政預算,加大投入力度,逐步建立起中央、地方和企業相結合的草原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長效投入機制。根據各地實際防治投入,應重新制定可行的防治投入標準,進一步擴大鼠蟲害和毒害草防治面積,新增牧草病害防治任務,積極爭取使中央財政增加草原有害生物災害防治投入經費總額。重新修訂發布草原有害生物防治資金管理辦法,優化資金用途等。
4.6 健全監測預報,提升災害預警水平
重建和完善國家、省、市、縣、鄉村五級草原有害生物監測預報網絡體系。在保持現有固定監測點的基礎上,按照主要為害區域的主要有害生物種類設置固定監測點的原則,查漏補缺,科學設置監測點數量,逐步完善固定監測點布局。采用航空遙感監測等新型監測技術,開展固定監測點監測工作,制定完整的監測方法標準體系,提高監測工作的準確性和高效性。制定監測數據資料的管理辦法,保證監測數據的長期性和延續性。開發和應用高效數據報送軟件,促進有害生物發生防治信息的保存、查詢與互通。同時開展草原有害生物人工調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固定監測點涉及區域范圍不全的缺點。加強草原農牧民測報員機制,將農牧民測報員作為鄉村級抓手,連通草原有害生物監測預報網絡體系與天然草原之間的最后一公里,為地面網格化監測提供人員保障。搭建“天空地”一體化的立體監測網,利用雷達和衛星遙感技術,將雷達信號特征分析與遙感信息技術建立的多個時序光譜特征量與紋理特征量相結合,搭建草原生物災害智能監測遙感網絡;通過無人機攜帶多光譜/高光譜相機獲取圖像,對采集到的圖像進行分類識別,建立相關的耦合模型,搭建草原有害生物智能監測的空中監測網絡;利用地面智能識別監測、手持智能終端設備識別等技術,突破基于照片深度學習的草原生物災害智能識別算法模型,研發智能終端系統,搭建草原生物災害智能監測的地面識別監測系統,實現草原生物災害的實時監測、準確預報和及時預警的目標。嚴格落實災情24小時值班制度和“零報告”制度。
4.7 完善應急預案,加強應急防控能力
突發的草原有害生物災害,其應急管理是國家公共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構建反應靈敏、運轉高效、結構完整、功能齊全、資源共享和保障有力的應急機制,對于全面提升災害應急處置能力和水平尤為重要。結合當前草原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實際,應自上而下,按“預防為主、常備不懈”的方針和“統一領導、分級負責、反應及時、措施果斷、依靠科學、加強合作”的原則,進一步完善重大草原有害生物災害應急預案,構建科學、完善的應急組織體系和規范有序的運作程序,以及反應靈敏、運轉高效、結構完整、功能齊全、資源共享、保障有力的應急機制。按照合理布局、突出重點、依災配置、規模適度、有效保障的原則,在各省按一定比例,選擇草原資源相對集中、交通便利、輻射性強的重點區域,設立跨地區、服務周邊的儲備應急防控器物資中心儲備庫。
4.8 創新防治技術,提高科學化防治水平
創新技術手段是草原有害生物防治事業發展和成效持續的基本保證。在草原有害生物防治工作中,應牢固樹立向科技要生產力、要成效的思想,積極轉變防治思路,改進防治技術手段,推動防治工作創新發展。必須立足現有條件,將提高草原有害生物防治科技含量作為一項基礎性工作抓好、抓實、抓出成效,切實加快由人工、地面防治為主向利用航天、航空遙感、物聯網等先進技術手段防治并重的轉變。重點在綠色防治新技術研發、防治新模式推廣方面發力,堅持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并重,著力解決科學研究與行業應用脫節的問題、科技立項和評價制度錯位的問題。籌建成立草原有害生物防治標準化技術委員分委會,推進草原有害生物防治標準體系建設,加快監測預警、防治通則、損失評估等綜合性標準的制修訂。針對不同草原類型的不同有害生物種類,制定合理的防治指標。
4.9 加大宣傳培訓力度,構建群防群治格局
應高度重視草原有害生物防災減災教育宣傳基地、科普基地建設,使之成為公眾了解防治知識、增強防治意識的平臺。充分發揮廣播電視、報刊雜志、網絡平臺等媒體優勢,在各級林草網站、官方微信群等新型媒體上,發布草原鼠蟲害災情信息,宣傳防治成效,推廣典型經驗做法,營造良好工作氛圍。加大對牧民防控技術知識的宣傳和推廣力度,充分調動牧民群眾參與滅治草原鼠蟲害的積極性,強化農牧民群眾的防災減災意識,共同參與鼠蟲害防治,有效保護天然草原植被,改善草原生態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