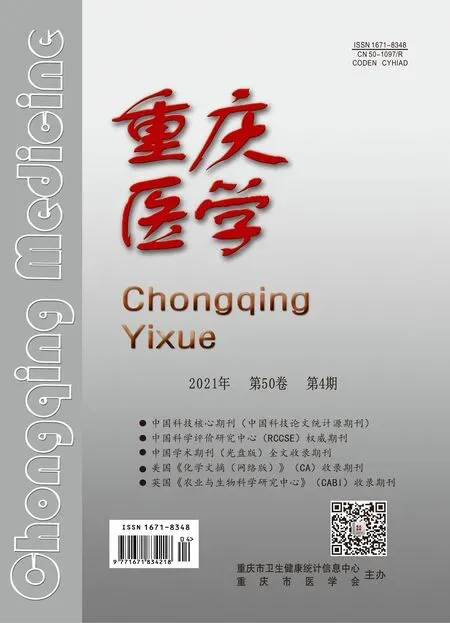結直腸癌肺轉移的研究進展*
朱萬莉,張潤冬 綜述,張亞陸,艾開興 審校
(同濟大學附屬上海市肺科醫院普外科,上海 200433)
結直腸癌(colorectal cancer,CRC)是最常見的消化系統惡性腫瘤之一,盡管對CRC的早期篩查和診療技術不斷完善,但近年來其的發病率和病死率仍呈居高不下。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癥中心團隊在2018年發表的最新全球癌癥統計數據顯示[1],CRC的發病率和病死率分別居全球癌癥發病和病死的第3位(19.7/10萬)和第2位(8.9/10萬),我國的發病率和病死率分別為23.7/10萬和10.9/10萬[2],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術后的復發和轉移是導致CRC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發生率約50%。肺作為CRC第二常見轉移部位,10%~25%的患者會發生肺轉移,CRC根治術后也常發生肺轉移,發生率約10%。CRC肺轉移患者的無病生存期更短,如不加以治療,其發生肺轉移后的中位生存時間為8個月,1年生存期為30%,僅有5%的患者可以生存5年以上[3]。
CRC肺轉移根據不同的標準有如下分類[4]:按照肺轉移和原發灶的出現時間,分為同時性肺轉移和異時性肺轉移;按照肺轉移和其他遠處轉移的先后順序,分為初發肺轉移和非初發肺轉移;按照是否伴有肺外轉移,分為單純性肺轉移和非單純性肺轉移。
1 CRC肺轉移的高危因素
直腸癌較結腸癌更易出現肺轉移,這主要與直腸的靜脈回流相關,直腸中下段的腫瘤細胞可以隨直腸中、下靜脈經髂靜脈直接引流入下腔靜脈而進入肺臟[5]。而結腸癌的腫瘤細胞經門靜脈首先進入肝臟,但部分患者僅表現為單純性肺轉移,這提示CRC肺轉移受到某些高危因素的影響。
多項回顧性研究表明,CRC發生肺轉移的危險因素有:CRC原發灶位置(直腸)、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水平升高、淋巴結轉移、脈管瘤栓、種族(亞裔及太平洋島民)、女性等[6-7]。ZHOU等[8]研究表明,在直腸癌中,中下段直腸癌較上段直腸癌更易發生肺轉移。術前CEA異常和術后CEA水平升高與肺轉移的發生密切相關,因此,常用于CRC預后的監測。此外,術前高水平CA19-9(>24 U/mL)也和CRC肺轉移的發生顯著相關[9]。因此,對于具有上述危險因素的患者,應加強術后的隨訪和胸部的復查。
眾所周知,吸煙是CRC發生和死亡的重要危險因素。隨著近年來研究的深入,吸煙同樣也是CRC肺轉移發生的一大危險因素。YAHAGI等[10]研究證實,吸煙狀態(當前吸煙)是CRC發生肺轉移的獨立危險因素。細胞因子或有毒化學物質及吸煙本身刺激物引起的微環境炎性改變在CRC肺轉移的發病機制中更為關鍵。DINO等[11]研究表明,香煙煙霧提取物可減少細胞壞死,并增加miR-21、Claudin-1和鈣黏附蛋白E(E-cadrin)的表達,香煙煙霧提取物暴露后,細胞通透性、肌動蛋白聚合和癌細胞遷移均增加,癌細胞的侵襲性增強,進一步揭示了吸煙在促進CRC轉移中的可能作用機制。因此,對于吸煙狀態的CRC患者,應當加強對其肺轉移的隨訪,并建議戒煙以減少肺轉移的發生。
2 CRC肺轉移的機制
2.1 基因異質性
原發腫瘤的基因特征是決定是否發生轉移的重要因素。MOORCRAFT等[12]將肺轉移灶與CRC原發灶的基因分子圖譜進行對比后發現,兩者的突變狀態具有一致性,最常見的突變基因分別為APC(71%)、Kras(58%)和TP53(46%)。而隨著基因測序技術的發展,研究人員在對TCGA數據庫中CRC相關數據進行綜合分析后,確定了一組與結腸癌轉移相關的關鍵候選基因(REG1B、TGM6、NTF4、PNMA5、HOXC13等)[13]。這提示可能還有更多的基因參與了CRC肺轉移,但具體的生物學功能和潛在分子機制還需要進一步研究證實。
Kras是一種小GTPase,在腸上皮表皮生長因子受體家族的通路中起中心作用,其激活與血管侵襲和血源性轉移相關[14]。Kras還可以激活磷脂酰肌醇3激酶α亞單位(PI3KCA)-絲氨酸蘇氨酸蛋白激酶(Akt)-乳動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等信號通路,調節細胞生長、存活、細胞周期和遷移[15-16]。研究表明,Kras突變可作為Ⅱ、Ⅲ期CRC肺轉移的獨立預測因子,且Kras突變后發生肺轉移的時間更短[17-18]。Kras通路中其他基因亦可能參與了CRC肺轉移,如PIK3CA突變、PTEN缺失等[19-20],而DACT2過表達可減少CRC肺轉移的發生[21]。最近的一項研究顯示基因突變還與CRC肺轉移切除術后復發有關,Kras和TP53突變增加了復發的風險并與較短的生存期相關,而APC突變則降低了復發的風險[22]。
2.2 靶向性遷移
趨化因子介導的循環腫瘤細胞(circulating tumour cell,CTC)靶向性遷移是CRC肺轉移的重要機制之一。CTC上的趨化因子受體與靶器官中的配體之間的相互作用決定了CTC對靶器官趨向性。CXCL12-CXCR4軸是參與腫瘤轉移最具代表性的趨化因子信號之一,其在CRC中與肝轉移的發生密切相關。類似的機制在肺轉移中也存在。YAMAMOTO等[23]研究證實,Smad4的缺失通過CCL15-CCR1軸促進CRC肺轉移,且CCL15在肺轉移中的表達是CRC患者預后較差的獨立預測因子。CXCR7受體特異性介導了CRC肺轉移[24]。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CXCR7和CXCL12在CRC肺轉移灶中的表達顯著高于配對的原發灶,且 CRC肺轉移灶癌旁組織中CXCL12的表達也明顯增高,且CXCL12在CRC轉移前表達即增高[25],提示CXCL12-CXCR7軸促進了CRC肺轉移的發生。
2.3 轉移前生態位的形成
肺部腫瘤微環境(tumour microenvironment,TME)的建立,即轉移前生態位的形成是CRC肺轉移的另一個重要發生機制。在CTC實際到達靶器官之前,通過分泌細胞因子和外泌體等重組肺部轉移前TME,以宿主免疫性與炎性細胞、器官特異性趨化因子、生長因子與細胞外基質-修飾蛋白為特征,提供支持滲出與定殖環境[26]。
外泌體是大小在30~100 nm的小囊泡,內含蛋白質、脂質及各種類型的核酸,包括DNA、RNA和miRNAs。腫瘤來源的外泌體可誘導轉移前生態位的形成,并增加特定靶器官轉移的風險[27]。WANG等[25]研究顯示,外泌體參與了CRC肺轉移前生態位的形成。最新的幾項研究表明,CRC細胞通過分泌包含miR-25-3p、miR-106b-3p和ITGBL1的外泌體誘導轉移前生態位形成,促進CRC遠處轉移[28-30],但其是否與CRC肺轉移相關仍需進一步研究證實。
除腫瘤細胞可分泌外泌體外,M2型巨噬細胞也能分泌外泌體并介導CRC的遠處轉移,其通過分泌富含miR-21-5p和miR-155-5p的外泌體介導CRC細胞的遷移和侵襲[31]。腫瘤相關巨噬細胞(tumour-associated macrophage,TAM)作為TME中主要浸潤的炎性細胞,通過多種途徑參與腫瘤生長,不但可通過分泌細胞因子介導腫瘤的遠處轉移,同時也可通過參與CTC的形成介導遠處轉移。CAI等[32]研究表明,在CRC中,TAM通過分泌轉化生長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激活Smad2/3/4 Snail通路誘導上皮間質化(EMT),從而促進其發生遠處轉移。
3 結直腸癌肺轉移的治療
3.1 手術治療
對于可切除的CRC肺轉移,肺轉移切除術是首選治療手段。接受手術治療的患者其中位生存期可達36~50個月[33]。
肺轉移灶切除的最佳時機是目前討論的一個熱點。在早前的兩項研究中,研究者根據肺轉移診斷和切除的間隔時間對患者預后進行了分析,發現當間隔時間較短時,術后早期復發的風險增加,同時,延遲手術患者的生存率明顯升高,并建議從發現肺轉移到切除的間隔時間至少為3個月[34-35]。而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研究者在對CRC肺轉移患者的手術時機和預后進行分析后發現,當發現肺轉移到切除間隔時間為9個月時,患者5年無復發生存率顯著改善(45.8%vs.85.6%),因此,他們建議,當目前的轉移數目小于或等于9個月前的影像學檢查時,是早期行轉移灶切除術的良好指征[36]。
對于肺轉移灶切除術術式的選擇,與原發型肺癌不同的是,解剖肺切除并不能獲得更好的生存率[37]。在一項對CRC肺轉移楔形切除后局部復發危險因素的研究中,研究者發現只要獲得至少腫瘤大小一半的病理切緣長度,楔形切除術可以獲得足夠的局部復發控制率[38]。還有研究表明,胸腔鏡手術與傳統開胸手術的同側復發率和生存率相當[39]。因此,對于CRC肺轉移患者,胸腔鏡下肺楔形切除術在保證足夠的切緣長度時可獲得最佳治療效果。淋巴結清掃雖對改善患者預后無明顯益處,但淋巴結轉移情況對預測患者的預后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建議可在手術時對淋巴結進行采樣以指導患者的后續治療[40]。
3.2 放(化)療
對于不可切除的CRC肺轉移,化療、立體定向放療、射頻/冷凍/微波消融等治療手段的單獨或聯合應用是有效的治療手段,臨床上能獲得較滿意的治療效果[40-41]。
對于可切除的CRC肺轉移,盡管早期的一些研究認為,在其圍術期輔助化療并不能改善預后,但目前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與單純手術相比,圍術期聯合化療能顯著改善CRC肺轉移患者的生存率[42-44]。RAPICETTA等[45]在對CRC單純性肺轉移行根治性手術的患者進行回顧性分析后認為,以CEA水平、正電子發射計算機斷層顯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CT結果、既往胸外轉移切除和無瘤間期對患者進行圍術期化療的風險和獲益評估,可進一步使治療方案科學化、合理化。
3.3 其他輔助治療
多學科規范化綜合診療模式是當前惡性腫瘤治療的發展趨勢,為患者提供科學合理、規范化及個體化的治療方案對提高生存質量、延長無進展生存期有重要意義。中醫藥作為CRC的綜合治療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在降低化療藥物的毒副作用、提高免疫力、改善生存質量等多方面的療效已取得相關研究證實[46-48],這提示中藥在改善CRC肺轉移患者預后方便具有潛在優勢。
隨著對腸道菌群研究的不斷深入,腸-肺軸的提出為CRC肺轉移的綜合治療提供了新思路[49]。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腸道菌群參與了癌癥的發生,同時也調節了抗腫瘤治療的活性、有效性和毒性[50]。TIAN等[51]發現,益生菌制劑與化療藥物聯合應用于肺癌患者可減輕化療藥物的副作用。因此,鑒于腸-肺軸的作用及益生菌對免疫系統的有益影響不斷顯現,在CRC肺轉移的患者中應用益生菌輔助治療將成為一項有價值的探索。
4 總 結
綜上所述,隨著對CRC肺轉移臨床和基礎研究的不斷開展,對其發生機制研究的不斷深入,以分子機制為基礎指導的多學科綜合治療,將使患者獲得更加科學合理個體化的治療,進一步提高生存率和生存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