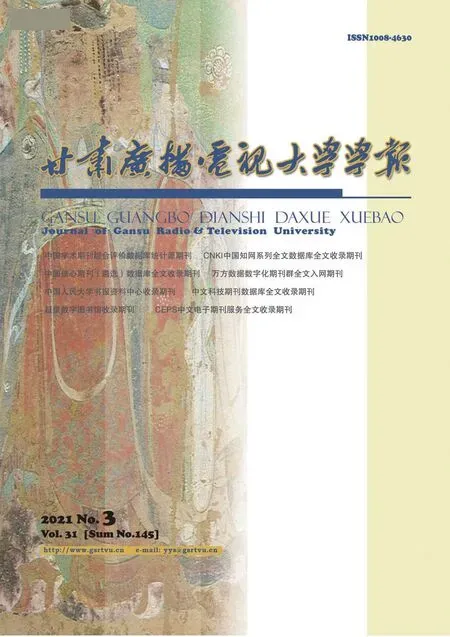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寺院的節料
徐秀玲
(河南大學 文獻信息研究所,河南 開封 475001)
20世紀早期出土的敦煌文獻中有關于節料的記載。對此,高啟安先生解釋說,有時也叫“節糧”,多出現在飲食文獻中的節日食物原料支出中,不惟寺院節日支出的飲食原料稱為“節料”,歸義軍衙內節日支出的食品原料也叫作“節料”,因此可以判斷出它是“專為節日支出的飲食原料”[1]。關于敦煌文獻中的節料研究,趙紅、高啟安曾提到敦煌寺院一般為諸色人等發放的節料是麥、粟、油等糧食或酒之外[2],并未對敦煌寺院領取節料人員的構成、節料的等級性進行探討。筆者擬從以下四個方面對敦煌寺院的節料作進一步的探討,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批評指正。
一、從敦煌寺院領取節料的附屬人員
從敦煌寺院領取節料的附屬人員,從名字上看有黑女、安三娘、五娘、六娘子、員住、恩子、再兒等人,但是他們的身份又各不相同,試析如下。
(一)黑女、安三娘、五娘、六娘子
黑女、安三娘、六娘子出現的文書僅S.6233lv《年代不明(9世紀前期)付諸色斛斗破歷》,轉錄文如下:
廿八日,付天養麻子□麥肆斗,溥。五月四日,付麥伍斗與黑(女)□充節糧,(溥)。同日,付黑女酥壹升,折麥貳斗,溥。十日,付面叁斗,付黑女,折麥貳斗,溥。十一日,付黑女豆貳斗,糧食,溥。十三日,付黑女麥貳斗,充糧食,溥。同日,付黑女豆貳斗,充糧食,溥。十九日,付黑女粟伍斗,充糧食,溥。廿四日,付黑女麥兩斗,粟貳斗,充糧食,溥。廿五日,付黑女粟叁斗,對付……溥。六月三日,付安三娘粟貳斗,麥壹斗,溥。五日,付安三娘……溥。十六日,付安三娘青麥伍斗,廿三日,付安三娘青麥貳碩,……□月四日,付黑女五娘青……溥。七日,付黑女及六娘子青麥共陸碩,溥。[3]174
本件文書記載了黑女等三人從寺院領取斛斗的記錄。在整個五月份黑女計領取麥9斗、面3斗、酥1升(折麥2斗)、豆4斗、粟8斗,小計麥粟面豆等斛斗2碩6斗。六月沒有黑女領取糧食的記錄,但是六月安三娘從寺院領取糧食粟2斗,麥2碩6斗,計2碩8斗。七月,黑女兩次領取糧食,第一次數目不明。第二次是七月七日與六娘子兩人領取青麥6碩。按人均計算黑女兩次領取糧食總數至少3碩以上。從黑女、安三娘、六娘子三人領取糧食的數目來看,人均每月領取糧食至少麥粟2碩8斗5升。
李正宇指出,唐宋時期敦煌人對女子往往按其排行,稱之為“一娘子”“二娘子”“三娘子”“四娘子”等。莫高窟第107窟女供養人題名見有“二十一娘”。呼之既久,約定俗成。于是“厶娘子”也就成了該女名號。貴族女子,取有雅名,則以名行,但仍習慣在名前冠以“厶娘子”,以示行輩,如莫高窟第98窟女供養人題名有“第十一小娘子延勝”“第十二小娘子延蔭”[4]。S.6233lv文書中的安三娘、六娘子、五娘等人與黑女一起領取糧食。如黑女五月、七月兩個月內領取糧食5碩6斗以上,也高于一般莊頭人的食糧,極有可能是她們也如“某頭”一樣作為某項活動的負責人,從寺院領取糧食。可見黑女等人的身份應高于一般的當寺女人。
(二)員住、再兒等人與恩子的身份比較研究
員住是人名,但是在敦煌文書中,有叫李員住、安員住、令狐員住、康員住者多人,唯獨有名無姓叫員住的人僅出現在S.1398v《壬午年(982)酒破歷》[3]227與S.4642v1-8《年代不明(10世紀)某寺諸色斛斗入破歷算會牒殘卷》[3]548兩件文書中。前者出現在酒破歷的后面雜寫兩行,后者出現員住之名較多,一起出現的還有再兒、任婆等人。在后件文書中員住與任婆、再兒等人一起從寺院領取月糧、節料,甚至員住與妻子治病、再兒妻子祈禱平安都是寺院出資。為明白起見,轉S.4642v1-8《年代不明(10世紀)某寺諸色斛斗入破歷算會牒殘卷》部分錄文如下。
麥壹碩,付員住月糧用。麥壹碩,董和通月糧用。麥伍斗,任婆月糧用。粟兩碩捌斗,付員住再兒月糧用。(大歲)面叁斗,付員住、任婆節料用。面伍斗,員住妻將病用。(寒食)面貳斗,付員住、任婆節料用。(冬至)面捌斗,員住、再兒節料用。連麩面叁斗,員住、再兒節料用。連麩面叁斗,員住、任婆、和通節料用。(大歲)油貳勝,再兒、員住節料用。油壹勝,員住將病用。(寒食)油壹勝,員住、再兒節料用。油貳勝,再兒妻平安用。(冬至)油壹勝,員住、再兒節料用。[3]548-554
由本件文書可知,員住、再兒、任婆等人在敦煌某寺領取月糧、節料以及家人費用麥粟連麩面油等物品。如員住領取月糧麥1碩,另一次是與再兒兩人領取粟2碩8斗,人均1碩4斗。在晚唐五代宋初的某段時期,麥粟比例為1:1.4,員住領取月糧麥1碩即相當于粟1.4碩,可知員住常年月糧為麥1碩,全年為12碩。此外,員住從寺院領取節料,本人及妻子生病,寺院又支出面及油等1碩6斗5升,員住全年收入可達13碩6斗5升。
再兒月糧如員住一樣同為折合麥1碩或是粟1碩4斗。全年月糧12碩,再兒妻平安以及再兒節料還從寺院領取連麩面、油等,寺院支給再兒一家的斛斗也超過12碩。
董和通從寺院領取月糧及節料的資料僅有三條,董和通的月糧為麥1碩,節料是與員住、任婆領取一起的連麩面3斗,人均1斗;和通還從寺院領取面6斗,可知董和通一年從寺院支取的糧食也超過12碩。
任婆的月糧每月麥5斗,全年6碩,任婆從寺院領取節料有3斗5升。全年收入6碩3斗6升,遠遠低于員住、和通以及再兒等人。
可見,敦煌寺院支付給黑女、義員、恩子、再兒、任婆、員住等人在大歲日、寒食、端午、冬至等節日的節料有麥、油、面、連麩面等。麥的數量一般較少,僅黑女在端午節前夕得麥5斗,其他的人的節料一般是面或油,其中摻雜著連麩面。如員住、再兒任婆、和通、恩子等人都得到過連麩面。
關于他們的身份。如恩子,謝和耐將之稱為難以解明的恩子,可能是奴隸階級[5]。池田溫認為恩子是人名[6],北原薰認為恩子不見于凈土寺以外,恩子不表示身份[7]。姜伯勤從寺院供給恩子年糧、節料,家庭特殊用途、住房,以及恩子在寺院長役等幾個方面認為恩子確是一個人名,地位是當寺廝兒,身份相當于寺奴婢[8]182-183。黃英認為恩子可能是“僧奴”的別名,不同寺院對僧奴的稱呼不同,是供養的具有使用價值的一類人的總稱。寺院為其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每逢節歲時還有額外的補貼[9]。筆者以為,黃英指出恩子為敦煌寺院某一類人的別稱,其觀點有誤。其一是姜伯勤認為恩子從凈土寺領取的糧食:春秋糧、節料以及其他收入每年最多9.4碩[8]180-181,按照唐宋時期人均每年食糧最少7碩2升計算,恩子每年的食糧總數僅夠一人吃用。若恩子是某一類人的總稱,凈土寺關于恩子食糧的支出斷不能每年不到10碩。從這角度來看,黃英把“僧奴”這個群體等同于恩子并非正確。
唐代官奴婢給糧,“男子入于蔬圃,女子入廚膳,乃甄為三等之差,以給其衣糧也。(注:四歲已上為小,十一已上為中,二十已上為丁。春衣每歲一給,冬衣二歲一給,其糧則季一給。丁奴頭巾一,布衫、袴各一,牛皮靴一量并氈。官婢春給裙、衫各一,絹裈一,鞵二量;冬給襦、複袴各一,牛皮靴一量并氈。十歲已下男春給布衫一、鞋一量,女給布衫一、布裙一、鞵一量;冬,男女各給布襦一、鞵襪一量。官戶長上者準此。其糧:丁口日給二升,中口一升五合,小口六合。諸戶留長上者,丁口日給三升五合,中男給三升)。凡居作各有課程。(注:丁奴三當二役,中奴若丁婢二當一役;中婢,三當一役)[10]。“其糧則季一給”,很顯然,恩子屬于奴婢。但是員住等人與恩子是不一樣的,他們是按月領取糧食。張弓指出,寺奴婢的月糧標準沒有明確記載。唐代官奴口糧,丁口日給二升,中口一升五合,小口六合,寺奴婢與此相差不多。作者以“僧奴”為例,說明僧奴的取糧方式似乎反映著某種常規:凡稱“牧羊人僧奴”取者,所取有粟,有面,品種較好;所取凡稱“月糧”或僅署“僧奴”而不稱“牧羊人”者,品種則以粗劣的連麩面為多,細糧較少。這表明:(1)有的僧奴每年僅在春、夏、秋放牧季節充做收羊人;(2)在僧奴做牧羊人時,寺院供給的口糧品種有時稍好;若不放羊則仍取一般寺奴所受的月糧,品種亦粗劣[11]。但是僅從某月節料員住、再兒、任婆、董和通人均1斗連麩面,屬于粗糧外,其他時間里,員住、再兒和通等人領取的月糧、節料以及自身、妻子生病或祈求平安時領取的麥粟面油等均屬于細糧可知,敦煌寺院中的勞動者以領取月糧質量的好壞作為評判他們是否屬于一般寺奴婢的標準不準確。我們從寺院員住等人領取全年的糧食高于恩子等人領取的春秋冬糧推測員住等人的身份應該高于寺院奴婢,或者他們即使屬于寺院奴婢,其身份也應歸屬于寺院奴婢中的上層。
綜上所述,黑女、安三娘、六娘子、員住、再兒、和通以及任婆等人,他們從寺院領取糧食、節料,生病、祈禱平安時可從寺院支取糧食。他們的身份有的屬于寺院某項勞動時的“某頭”,負責勞動時從寺院支取糧食,有的是寺院的附屬人員,在寺院中承擔各項具體的勞動,領取春秋糧、冬糧以及節料等,身份等同于或高于奴婢。
二、領取寺院節料的僧官、眾僧
晚唐五代宋初敦煌寺院的僧官、眾僧在節日期間也會獲得節料。寺院支出的節料有白面、油、麥、粟等,其中麥、粟一般用于臥酒。
S.3074v《吐蕃占領敦煌時期某寺白面破歷》第42行載“廿四日,出白面叁碩,付利珍,充冬至眾僧節料”[3]171。S.1519(1)《辛亥年(891或951)某寺諸色斛斗破歷》第9行載“十九日,麥酒壹甕、粟酒兩甕,僧錄僧政節料用”[3]177。S.1519(2)《辛亥年(891或951)十二月七日后某寺直歲法勝所破油面等歷》第12行載“(大歲日)又酒肆甕,諸和尚節料用”[3]178。P.2049v《后唐長興二年(931)正月沙州凈土寺直歲愿達手下諸色入破歷算會牒》第175行載“麥玖斗,冬至臥酒僧官節料及徒眾等用”。第176至177行載“麥玖斗,歲臥酒僧官節料及眾僧等用”。第318至319行載“油貳斗伍勝,歲付眾僧節料用”[3]377,383。P.2032v《后晉時代凈土寺諸色入破歷算會稿》第236行載“麥九斗、粟壹碩二斗,冬至節料及眾僧等用”。第247行載“粟壹碩貳斗,和上眾僧法律等歲(付)節料用”。第251行載“油肆斗陸勝,歲付眾僧節料用”[3]467-468。P.2040v《后晉時期凈土寺諸色入破歷算會稿》(乙巳年正月已后)第308行記載“油五升,歲付眾僧節料用”[3]419。
上述文書記載了敦煌諸寺領取或享用節料的僧人,有眾僧或徒眾、僧錄、僧正、法律、諸和尚等人。眾僧或徒眾一般屬于本寺僧人。僧錄、僧正、法律及諸和尚的身份可能比較復雜,有的可能屬于敦煌佛教教團的成員,如僧錄或僧正等,有的可能是本寺的僧官。當冬至、大歲日等節日期間時,這些僧官也從寺院領取一部分節料。但是相對于一般的僧眾,僧官從寺院領取的節料,基本上都有酒,而普通的僧眾,僅有麥、粟、白面等。可知敦煌寺院僧官與普通僧眾領取或享用的節料具有等級性。
三、敦煌寺院中酒戶的節料
在唐宋時期的中原地區買官曲的酒戶一直存在,即“明年(崇寧四年),改令磨戶承歲課視酒戶納曲錢法”中提到的酒戶[12]。但是在晚唐五代宋初的敦煌地區,被稱為酒戶的有兩種:一是官酒戶,二是寺院中的酒戶。
(一)敦煌的官酒戶
晚唐五代宋初敦煌的官酒戶,如P.3569v《唐光啟三年(887)四月為官酒戶馬三娘、龍粉堆支酒本和算會牒附判詞》記載:
官酒戶馬三娘、龍粉堆。去三月廿二日已后,兩件請本粟三拾伍馱,合納酒捌拾柒甕半。至今月廿二日,計卅一日,伏緣使客西庭、扌祭微、及涼州、肅州、蕃使繁多,日供酒兩甕半已上,今準本數欠三五甕,中間緣有四五月艱難之(乏)濟,本省全絕,家貧無可吹食坐,朝憂敗闕。伏乞仁恩,支本少多,充供客使。伏請處分。牒件狀如前,謹牒。光啟三年四月日龍縣丞牒。付陰季豐算過。廿二日、準深押衙陰季豐。右奉判令算會,官酒戶馬三娘、龍糞堆,從三月廿二日于官倉請本貳拾馱,又四月九日請酒本粟壹拾伍馱,兩件共請粟叁拾伍馱,準粟數合納酒捌拾柒甕半,諸處供給使客及設會賽神,一一逐件算會如后(后略)。[3]622-623
本件文書是唐光啟三年(887)官酒戶馬三娘、龍粉堆二人上書歸義軍府衙要求支付酒本的狀憑。作為官酒戶,馬三娘、龍粉堆二人需要為歸義軍出使西庭、扌祭微,以及來自涼州、肅州、蕃等地的使者提供酒水。但由于歸義軍提供給二人的酒本較少,釀酒的原料入不敷出,故二人向歸義軍府衙提出補充酒本,以此充供使者。從歸義軍支付給他們的酒本35馱,即歸義軍府衙需要向官酒戶支付大量的酒本,可知歸義軍時期確實存在著官酒戶。
(二)敦煌寺院中的酒戶
吐蕃統治時期敦煌寺院中的酒戶。如沙州寺院有隸屬的酒戶,S.0542《戌年諸寺丁口車牛役部》第44旱記載:“(大云寺)安寶德:煮酒一日。”第146行:“(靈修寺)何伏顛:酒戶。”[13]可知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的寺院有酒戶,他們隸屬于寺院,是寺戶的一部分,但是也承擔官府的勞役。
晚唐五代宋初歸義軍政權統治下敦煌寺院的酒戶。如S.1519(1)《辛亥年(891或951)某寺諸色斛斗破歷》第9行載:“油貳升,酒戶郭沒支節料用。”[3]177P.4906《年代不明(10世紀)某寺諸色破用歷》第6至7行記載:“油壹升,與酒戶安富子寒食節料用。”[3]233寒食節時,寺院的酒戶郭沒、安富子各從寺院支取節料油2升、1升。對于二人的性質,姜伯勤指出,他們已經擺脫了對寺院的隸屬性,從寺戶酒戶轉到以領取寺院酒本為寺院供酒的酒戶。作為小生產者和小商品生產者,他們的身份具有雙重性:一方面,他們作為當時開店投榷的酒戶,在買官榷或交榷錢后取得賣酒資格,并以零售的形式向寺院發售,這種經營方式屬于封建社會商品生產性質;另一方面寺院以預付酒本的方式向酒戶發放安家酒本,這種酒本在酒戶經營困難時有某種貸款式的性質,酒戶按照寺院的要求釀酒、供酒,從而形成了在一定時期對寺院的依賴,并使寺院得到低于時價水平的供酒,對酒戶形成某種超額的剝削[8]255。姜先生依據的是《通典》的記載:“廣德二年十二月,敕天下州各定量酤酒戶,隨月納稅,除此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8]254廣德二年是764年,唐代宗的第二個年號,但是到吐蕃統治敦煌時,由于吐蕃的制度與中原王朝不同,吐蕃統治下的敦煌是否也實行酒榷制度,作者并沒有直接的證據來說明。
對于歸義軍政權下的官酒戶,馮培紅指出,官府榷酒制度下有“官酒戶”的稱呼,既冠有官字,相對應的應該有寺院酒戶的存在。馮培紅對姜伯勤提到的“敦煌諸寺供酒的酒戶又稱為酒司”這一說法,他認為姜先生誤解了酒司的含義,“既混淆了酒司的性質,否認酒司是歸義軍官府的酒業管理機構,而認為其屬于寺院性質;同時又混淆了酒司與酒戶之間的關系,否認兩者是互為從屬的關系,而認為彼此等同”[14]。張議潮建立歸義軍政權以后,曾經對部分寺戶進行放免,但是張議潮死后,其政策被改變。當時的寺院為了保護財產,“千方百計地把寺院對地產和人戶的占有保存下來”[8]128,如寺戶被以“常住百姓”的名義保護下來,寺田被稱為“廚田”,等等。在此情況下,吐蕃時期出現在敦煌寺院中的寺戶酒戶,或寺戶酒戶的一部分應該也是以常住百姓的形式被保存下來。因此,筆者同意馮先生的意見并認為歸義軍時期隸屬于寺院的酒戶繼續存在。而被保存下來的這部分酒戶,他們作為歸義軍時期敦煌寺院的隸屬人戶,在節日期間也從寺院領取節料。
由此可推測酒戶安富子、郭沒兩人與其他在寺院領取酒本的經營者如馬家、寒苦家、羅家店、丑子店等不同:酒戶安富子、郭沒完全是隸屬于寺院,從寺院領取節料,而馬家、寒苦家、羅家店、丑子店等酒店應該是姜伯勤先生在其著作中提到的從寺院領取酒本,依附于寺院,但是又向官府交納酒榷的酒戶、小生產者或者小商品生產者。同時,筆者也在敦煌文書中多次發現寺院從以上酒店沽酒的記載①,這也從一定程度上說明后者雖然與寺院聯系密切,但是他們并不隸屬于寺院,他們與寺院應該是一種合作關系。
從敦煌寺院支付給郭沒、安富子二人的節料可看出,歸義軍時期的敦煌寺院繼續存在著從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的寺戶酒戶轉化而來改稱為常住百姓并與之身份相差不多的寺院隸屬酒戶。這些酒戶同寺院常住百姓或寺奴婢一樣,過節時從寺院領取節料,而且還極有可能從寺院領取月糧或春秋糧。
四、敦煌寺院領取節料人員的特點
晚唐五代宋初從敦煌寺院領取節料人員的身份有以下特點。
其一,附屬于寺院的人員,他們的身份略等同于寺院的奴婢,但是卻比一般的奴婢身份要高,如恩子、黑女等人,他們在節日期間從寺院領取的節料是麥、粟、面、油等。此外,領取節料的人員還有隸屬于寺院的酒戶,他們從寺院領取節料以及酒本,所釀造的酒歸屬于寺院,基本上不能對外出售。這與那些獨立開店的酒戶不同。
其二,敦煌佛教教團的僧官以及寺院的僧眾也在節日期間領取節料,如僧錄、法律以及寺院的眾僧、諸和尚或徒眾等。他們領取或享用的節料有酒、麥、粟、白面等。
其三,從敦煌寺院領取節料人員的身份看,寺院的附屬人員幾乎很少有酒,然而敦煌寺院或佛教教團的僧官或諸和尚等人從寺院領取的節料里有酒。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寺院在發放節料時的等級性。
唐代佛教繁榮,中間雖然經武宗滅佛影響,但是佛教仍然深入人心。晚唐五代宋初的敦煌雖然處于當時中西交通的要道之上,然而它并沒有受到武宗滅佛的打擊,佛教仍然在此地流行,寺院的僧人除了參加一些必須的生產勞動外,還經常參加或舉行各種宗教活動,在宗教活動中獲得外界的布施。與中原地區佛教寺院不同的是,敦煌寺院平時并不提供本寺僧人的日常飲食,但是在節日期間,僧人可從寺院領取或享用節料:酒、麥、粟、面、油等食品。此外,寺院的隸屬人口也可在節日期間獲得寺院下發的節料。但是他們的節料與僧官、普通僧人相比,仍然存在著等級性。
注釋:
①敦煌諸寺馬家、寒苦家、羅家店、丑子店等酒店沽酒記錄:S.4649+S.4657拚合《庚午年(970)二月十日沿寺破歷》S.4657第7行“□月十七日,粟壹碩貳豆斗,員昌店沽酒石眾井……”(第215頁);S.6452(1)《某年(981—982)凈土寺諸色斛斗破歷》第1—2行載“十四日,粟壹豆斗,就氾家店沽酒”(第222頁);S.5039《年代不明(10世紀)諸色斛斗破用歷》第26—27行“麥陸斗,就丑子店沽酒沋都頭亡看都官用”,第29—30行“麥陸斗,扵史盈子店沽酒屈曹僧正陰都頭用”(第229頁);P.2049V《后唐同光三年(925)正月沙州凈土寺直歲保讓手下諸色入破歷算會牒》第234—235行“粟柒斗,寒苦及馬家沽酒三日交庫用”(第360頁)。S.5050《年代不明(10世紀)某寺諸色斛斗入破歷算會牒稿殘卷》第14—15行“粟伍斗,趙家店沽酒迎磑車師僧用”(第535頁)。以上均來自唐耕耦、陸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3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印中心出版,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