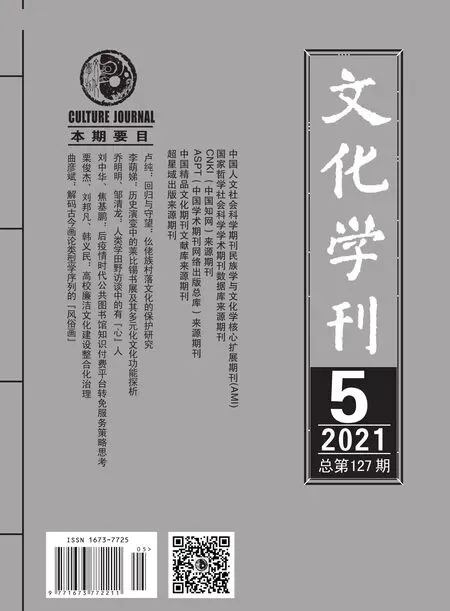認知隱喻視角下中英禁忌語動因對比研究
張 穎
語言作為人類思維的工具和文化成果的載體,在社會和歷史的長河里傳承人類文明的果實。語言作為一個音義結合的符號系統隨著社會的變遷而發生變動,既穩定又變化。社會變遷影響語言系統的同時,語言系統變化也反映社會變遷,對社會具有反作用。其中,不同語言中禁忌語異同就體現了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個性與共性。
一、認知隱喻視角下禁忌語研究綜述
據《說文解字》記載,“禁”是“吉兇之忌”之意,“忌”是“憎惡”之意。“禁忌”一詞指被禁止或忌諱的言行,一般作動詞或名詞。英文中“禁忌”一詞為taboo,來源于湯加詞匯,一般作名詞、形容詞或動詞。人類從無知中產生恐懼,對自然現象抱有崇敬之心,依靠主觀臆想創造出看似合理的解釋,將自身愿景、祝福寄托于神靈之上。在日常生活和交際過程中也體現這種崇敬和尊重,將一切神明相關看作不可侵犯之物。人類這種靈物崇拜的社會現象和主觀思維逐漸反映在語言系統中,形成了禁忌語。
20世紀80年代,語言與社會文化、認知之間的關系引起研究者注意,從禁忌語異同探討文化異同。萊考夫(Lakoff)和約翰遜(Johnson)曾從認知隱喻的角度解釋了禁忌語所反映的認知機制,從認知語義學角度提出“隱喻”[1]。該理論主張人們的生活和隱喻密切相關,不可分割,主要解決意義的性質、意義的生成等問題。該理論還認為隱喻是不同認知域的映射,從一個具體的概念域向一個抽象的概念域的系統映射,反映人類思維方式和認知手段。中國語言學界對禁忌語的提出較早,但開始系統性研究相對較晚。陳原對語言禁忌全面引入和分析[2]。陳建民從語言與社會的關系角度對禁忌語研究有所探討[3]。在20世紀80年代之后,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到禁忌語研究的價值,研究成果逐漸增多。但是,目前從認知語言學隱喻角度進行中英禁忌語認知異同對比研究不多,仍存在較大研究空間。
二、中英禁忌語共性及個性對比分析
(一)神靈圣人名稱謂類禁忌語
褻瀆性禁忌語是禁忌語中的一大類,中英語言國家都有忌諱直呼神靈圣人名諱的現象。二者在人名稱謂方面有相同之處,但也有不同之處。
西方國家宗教信仰信奉基督,因此,信徒是不能隨意直呼上帝的名稱的。例如,在日常正式交際場合會避免直呼God(上帝)。西方國家人們信奉人人生而平等,一般會直呼人名,不論對方是長輩還是同輩、上級還是下級,一律直呼名字。打招呼時,使用“Mr.”“Mrs.”“Miss”加姓氏[4]。而且在取名字時,有時傾向于給孩子使用祖父和祖母的名字,表示紀念和尊敬。
中文也有類似的禁忌語現象,但是中文的稱謂類禁忌語類型比英語更多,分類更細致。中國長期處于封建專制統治之下,受傳統儒家文化影響,講究嚴格的等級秩序,宗法制度的沿襲塑造“家國統一”的思想,因此,古代忌諱直呼君主、圣人的名字。生活中避免直呼長輩、父母、上級領導的名字,否則會被認為沒有禮貌。取名字時也十分忌諱使用同音或諧音長輩親屬的名字。而且中文中有家族式稱呼語用分為擴展的現象,時常會使用稱呼非親屬關系,例如“食堂阿姨”“看門大爺”“警察叔叔”等。
(二)生老病死類禁忌語
生老病死類的禁忌語反映了人們從出生到死亡整個生命軌跡中的各種客觀生理狀態的禁忌現象。中英具有很多共性,“生”不是指“出生”,而是指個體的生命狀態、身體形態等方面。交際時會用“聾啞人”代替眼睛、耳朵殘障人士。英語中也有類似用法,如用physical handicapped代替cripple、lame。“病”代表一種不幸、災禍。中英都會避免談論疾病、死亡等話題,如用terminally ill或the big C代替cancer,用縮略詞避免疾病名稱,如AIDS。“死”指“死亡”,但人們表達時會主動避免對“死”的描述。中英避諱描述死亡的方法有很多,中文根據“死”不同的語義特征有兩百多余種委婉表達方法,比如“犧牲”“仙逝”“與世長辭”等。英文中也有很多委婉表達方法,如pass away、go to a better world等。
中西國家對于“老”的態度存在差異,這種態度也體現在中英禁忌語中。中國傳統美德講究尊老愛幼,一個成年人年齡越大,意味著經驗越多,是年輕人學習的對象。老人代表一家之長,是具有智慧、經驗的人,因此,不存在年齡對于夢想或生活的限制,中文中有“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老當益壯”等用法。“老先生”“老壽星”之類稱呼中的“老”表示尊重、尊敬之義。而歐美等西方國家更崇尚年輕活力,衰老是尷尬和敏感的話題,一般表達年齡大也會用委婉的詞匯或用法代替,如advanced in age、getting on years等。
(三)特色文化傳統或民俗相關的禁忌語
在中文和英語中很多與特色文化傳統或民俗相關的禁忌語有所差異,有很多方面的體現。例如動物禁忌語、數字禁忌語、顏色禁忌語等。如動物有關的禁忌語,如歐美文化中的dragon與中國文化中“龍”的形象完全不同,歐美文化中的dragon是一種強大但邪惡的象征,而中國文化中的“龍”是九五之尊、吉祥、權力、尊貴的象征,如“龍鳳呈祥”“龍馬精神”“生龍活虎”等。
三、中英禁忌語認知隱喻動因分析
(一)認知隱喻的普遍性與特殊性
隱喻是一種認知方式,是一種源域向目標域映射的系統性的認知過程。在隱喻關系產生之前,目標域僅僅是一個未知的空白區域,源域的事物特征對于空白的目標域來說至關重要,因為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兩者是否能形成隱喻關系,以及將會形成什么樣的隱喻關系。例如對于“死”的映射,死亡對于每個人都有客觀物理世界生命終結的意義,這來源于人對于客觀世界的體驗,這種認知經驗使人們會不由自主地回避死亡這個話題。為了達到交際和諧、得體、禮貌等目的,人們傾向于不談及一切與“死”相關的負面概念,所以中英禁忌語中對于“死”的禁忌現象是具有隱喻普遍性的,都有類似“死亡”是一個旅程(Death is journey)、“死亡”是休息(Death is rest)等概念隱喻結構[5]。但是,中英禁忌語中也有些隱喻結構是不同的,同一個源域在中英中映射了不同的目標域,或者同一個源域在中英中凸顯了不同的目標域,進而產生特殊性。例如中文中存在“警察叔叔”“食堂阿姨”等親屬稱謂詞匯外化現象,這種隱喻結構的投射關系是成立的;而英語中沒有這種現象,因為源域親屬稱謂無法投射到與自身沒有血緣關系的陌生人身上,源域與目標域之間的投射關系是不成立的。
(二)認知隱喻環境
一種語言中,話語隱喻結構的源域與目標域之間投射關系成立與否與使用該語言的民族的文化認知環境有關,為語言系統內部的隱喻結構提供認知隱喻環境。
不同民族文化價值觀的建立,是以地理環境、歷史條件等客觀條件和文化基因、意識形態、社會習俗等主觀條件為基礎的。這些主客觀條件時時刻刻影響著民族文化價值觀,民族文化價值觀又反作用于主客觀條件,二者是一種互構關系。一方面,對于一個國家或民族來說,民族文化價值觀的塑造離不開這些主客觀條件;另一方面,作為一種國家或民族思考世界和實踐于世界的指導,民族文化價值觀影響了這個國家或民族的思考方式、認知機制和實踐方法的塑造。因此,這些主客觀條件以及民族文化價值觀共同形成了一個龐大且變動的民族認知環境。在這種獨具特色的認知環境下,民族語言系統也受到一定影響,認知隱喻的結構受到塑造,即影響源域與目標域之間成立映射關系與否。它為民族語言系統提供獨特的認知路徑、心理聯想語境等,構成認知隱喻的基礎知識結構和基本經驗,進而使民族語言系統展現其普遍性和特殊性。
中英禁忌語中很多共性和個性也展現了雙方民族認知環境的共性和個性。例如宗教信仰方面影響禁忌語的異同,如中國古代對皇帝、圣人、長輩名字的忌諱,英文中對基督教中的上帝、惡魔、“13”“5”等忌諱。中文對于上帝、“13”等源域沒有像英語那種宗教隱喻的概念隱喻。再如政治歷史方面,中國古代長期受到君主封建專制統治制度和儒家思想的影響,遵循等級制度,因此,產生對皇帝、圣人、長輩名字的忌諱。而西方文化受古希臘和古羅馬文化的影響,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從解放人性到解放個性、追求理性,一直處于宗教和人性的角逐中,英語中稱謂的直呼或名字的繼承都表達了西方追求平等、自由、個性的思想,在稱謂隱喻結構中沒有中文那種等級隱喻的概念隱喻。
四、結語
中英禁忌語之間存在很多異同,體現了兩種語言背后深層認知隱喻的異同。從中英語言認知對比的角度看禁忌語的異同發現:一方面,中英禁忌語認知隱喻存在普遍性和特殊性;另一方面,中英塑造禁忌語的民族認知隱喻環境存在異同,這主要是從主客觀條件與民族文化價值觀互構的關系中而產生的異同。除此之外,可以從更多不同的認知視角看待中英禁忌語異同,如從原型理論、概念整合理論等入手挖掘更多的深層動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