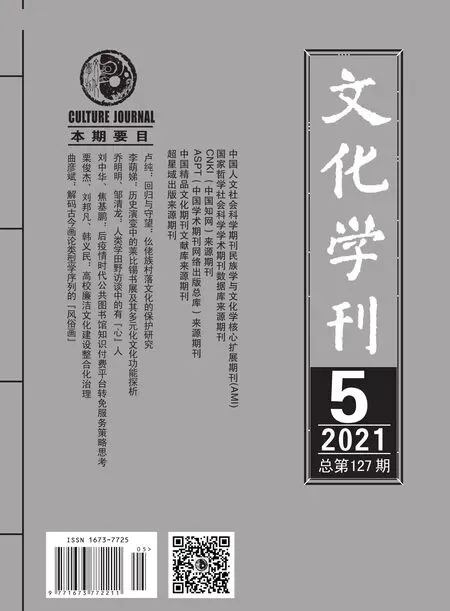異化論視角下《吶喊》中文化負載詞的英、日譯研究
楊雨時 黃成湘
魯迅作為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文壇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辛辣諷刺的文筆曾喚醒了部分同時代民眾的憂患意識。目前,我國正大力支持中華文化“走出去”,對于同屬于漢字文化圈的日本來說,異化翻譯策略是讓日語讀者最大限度了解我國文化的一種策略。而且,日本一流的魯迅研究專家井上紅梅在翻譯《吶喊》時使用的異化策略也與魯迅提倡的“硬譯”不謀而合,這種看似“硬”的翻譯方法下的“語言產物”或許對于早期目的語讀者來說難以理解,但是,隨著中日交往的不斷深入,這些原本帶有濃厚異域色彩的文化負載詞會逐步被理解和接納,甚至成為兩國文化的“共識”。
一、異化與歸化之爭
“異化”與“歸化”這對翻譯術語是美國翻譯理論家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譯者的隱形》一文中提出的。他認為:“異化翻譯是不透明的,它避免流暢,傾向于在譯文中融入異質性話語,異化翻譯在解釋原文時同樣具有傾向性,但異化往往是彰顯這種傾向,而不是將其藏匿起來。”[1]進而指出異化主要以源語文化為中心,強調譯文要有別于目的語;而歸化主要以目的語文化為中心,強調譯文要同于目的語。許淵沖是“歸化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張充分發揮漢語優勢,揚長避短,重視譯文的通順,還提出了“優勢競賽論”[2]。王育倫贊同魯迅在翻譯中所指的“削鼻剜眼”,指出“翻譯作品必須有別于中國的文學作品,不僅在內容上使讀者想到這是外國的,而且應該在語言形式的某些方面使讀者想到這是‘外國貨’”[3]。葉子南指出:“只有當表達同一概念時,原語(如英語)與譯入語(漢語)的表達法有差別時,才會出現西化。……極度的歸化譯法會抹去許多風格、文化、藝術的特征,從而影響譯文的真正價值。”[4]總的來說,絕對意義上的歸化與異化都是不存在的,兩者相輔相成。孫致禮認為:“異化和歸化兩個相輔相成的翻譯方法,任何人想在翻譯上取得成功,都應學會熟練地交錯使用這兩個方法。”[5]孫致禮首先肯定了歸化在一定時代條件下所起的重要作用,并認為能異化時盡量異化,在難以異化的情況下,應當退而求其次,進行必要的歸化處理。也就是說,孫致禮把異化擺在了第一位。進而,孫致禮從泰特勒的“翻譯三原則”談起,認為原作的“思想”和“風格”都帶有濃厚的異國情調。如果不使用異化的翻譯方法,就很難再現原作的思想,而要讓原作和譯作一樣流暢,又必須采取歸化的翻譯方法。
二、《吶喊》英、日譯本的先行研究
短篇小說集《吶喊》真實地描繪了辛亥革命至五四運動時期的社會生活,表達了魯迅強烈的憂患和變革意識,彰顯了人道主義精神。時至今日,魯迅作品英譯本之間的對比研究和日譯本之間的對比研究已基本成熟,但其兩種外譯本之間的對比研究,如英、日譯本的對比研究寥寥無幾。本文選用的英譯本是1990年夏威夷大學出版的美國學者威廉·萊爾的譯本(Dairyofamadmanandotherstories),日譯本是1932年改造社出版的日本魯迅研究專家井上紅梅的版本(收錄于《魯迅全集》)。萊爾是耶魯大學有名的魯迅文學作品研究員,他翻譯的魯迅作品具有簡潔、流暢的特點;而在日本,井上紅梅熟知中國民間風俗,有“中國通”之稱,是日本最先翻譯魯迅作品的人。上述兩個譯本的譯者均比較精通魯迅作品及中國文化,這是本文選擇這兩個譯本的主要原因。
關于《吶喊》的日譯研究,冉秀對《吶喊》的井上紅梅譯本和丸山升的譯本進行詳細分析得出,兩位譯者基于各自的時代背景和讀者要求,分別采用“魯迅化”和“本土化”的話語方式進行跨時空翻譯對話。20世紀30年代的井上紅梅譯作滿足當時日本讀者了解中國社會和中國民情的愿望。相比而言,丸山升的譯作讓日本學界更好地理解了魯迅文學的“神韻”,即與原作極其“神似”[6]。也就是說,井上紅梅作為第一個翻譯魯迅作品的人,對中國文學在日傳播作出的貢獻不容忽視。相比之下,冉秀對丸山升的譯作評價更高。藤井省三在魯迅文學日語翻譯思考中寫道:“拙譯《故鄉/阿Q正傳》,并未將魯迅本土化即現代日語化,而是通過日語譯文的‘魯迅化’來努力傳達生存于時代巨大轉換時期魯迅的深層苦惱。……因此,拙譯許多文章與明快的格調相去甚遠”。[7]藤井省三在翻譯魯迅作品時只是盡可能地還原魯迅的寫作風格,因此存在不少晦澀難懂之處。而本文通過對比威廉·萊爾譯本(以下簡稱“萊爾譯本”)和井上紅梅譯本(以下簡稱“井上譯本”),總結兩本譯作各自體現的異化或歸化傾向,在我國大力倡導中華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或許能為我國文學作品的譯介提供新的思路和啟示。
三、《吶喊》中文化負載詞的英、日譯本比較
文學作品中最關鍵的就是對文化負載詞的解讀。準確翻譯文化負載詞既可以減少文化損失,讓外國讀者更好地認識中華文化,又能促進不同文化間的交流。文化負載詞能體現出語言包含的文化信息,反映一定時代的社會生活現狀。美國學者尤金·奈達對文化因素進行了分類,具體為生態、物質、社會、宗教、語言文化五大類。筆者參考尤金·奈達對各類文化負載詞的定義,劃定了各類文化負載詞的具體范圍。
(一)生態文化負載詞
生態文化負載詞包括地理環境、天氣、氣候、動植物、季風等相關詞匯。
例(1):
原文:秋天……只剩下一片烏藍的天。(選自《藥》)
萊爾譯本:The second half of ... leaving nothing butthe dark blue sky.(選自Medicine)[8]49
井上譯本:亮るい月は日の出前に落ちて、寢靜まった街の上に藍甕のような空が殘った。[9]39
此處,萊爾和井上都采用了歸化的翻譯策略。“烏藍”這一漢語詞匯是“黑里泛藍”的意思。萊爾根據“烏藍”的漢語釋義,將其譯為the dark blue sky(黑藍的天),而井上選擇使用比喻的手法,將其比喻為“藍甕のような空”。“藍(あい)”是“濃く深い青色”(深藍色)的意思,而“甕(かめ)”指的是“液體などを入れる、底の深い陶器”(盛放液體的深底容器)。經查,日本網站上有很多關于制作“藍甕(あいがめ)”的視頻資料,雖然井上沒有直接告訴讀者,“烏藍的天”是“黑藍色的天”,但他引入了“藍色瓷罐”這一物品,讓讀者對“烏藍的天”有了初步認識。
(二)物質文化負載詞
物質文化負載詞包括具體的實物、表示貨幣、時間、重量、距離等度量信息的單位。
例(2):
原文:第二是夏三爺賞了二十五兩雪白的銀子,獨自落腰包,一文不花。(選自《藥》)
萊爾譯本:And right after him comes Third Master Xia. Without spending a single copper, that one ended up pocketing a reward oftwenty-five ounces of snowy white silver.(選自Medicine)[8]54
井上譯本:第二は夏三爺から出る二十五両の雪白々々の銀をそっくりおれの巾著の中に納めて一文もつかわねえ算段だ。[9]46
例(3):
原文:溫兩碗酒。(選自《孔乙己》)
萊爾譯本:Warmtwo bowls of wine.(選自KongYiji)[8]43
井上譯本:酒を二合燗つけてくれ。[9]34
原文的“雪白的銀子”,萊爾譯為snowy white silver,而井上譯為“雪白々々の銀”,在日語中,這一表述不會造成理解上的困難,但這樣的用例非常少。原文中的“夏三爺賞了二十五兩雪白的銀子”指的是因為夏三爺舉報自己的親侄子夏瑜,官府賞了他二十五兩銀子,并不像井上理解的,夏三爺賞了“我”(康大叔)二十五兩銀子。“我”(康大叔)在這段話中闡述的是夏瑜死了,有兩個受益者,一是華老栓,他得了夏瑜的血制成了人血饅頭,二是夏三爺,而自己卻一分好處沒撈著。因此,井上的翻譯也屬于誤譯。“二十五兩”中的“兩”這一貨幣單位被萊爾譯為“盎司”,井上則直接譯為“兩”,并未加特殊說明。中國古代“二十五兩”與萊爾翻譯的“二十五盎司”并不等值,但考慮到清朝的物價、貨幣換算,這也是一種翻譯的“權宜之計”。此外,書中還有一處孔乙己要溫“兩碗(酒)”的情景,其中,“兩碗”被萊爾譯為“two bowls of (wine)”,而井上譯為“二合”。“合”是日本特有的計量單位,一合為180毫升。可以看出,井上翻譯得更為精確,而萊爾翻譯得比較模糊。
(三)社會文化負載詞
社會文化負載詞包括歷史人物、地名,象征身份地位的頭銜,娛樂與禮儀傳統,社會機構、娛樂場所等相關詞匯。
例(4):
原文:我……在鎮口的咸亨酒店里當伙計。(選自《孔乙己》)
萊爾譯本:I got a job as a waiter inThe Prosperity For All...(選自KongYiji)[8]42
井上譯本:わたしは十二の歳から村の入口の咸亨酒店の小僧になった。[9]32
例(5):
原文:竟偷到丁舉人家里去了。(選自《孔乙己》)
萊爾譯本:Went and stole fromDing the Selectman's house!(選自KongYiji)[8]46
井上譯本:ところもあろうに丁挙人の家に入ったんだからな。[9]37
“咸亨酒店”創建于1894年,取名“咸亨”寓意為酒店生意興隆,萬事亨通。萊爾譯的The Prosperity For All就比井上譯的“咸亨酒店(かんこうしゅてん)”更能充分展示其深刻含義。對于文中提到的“秀才”“舉人”等頭銜稱呼,萊爾在注釋中有明確解說:中國古代科舉考試分為秀才、舉人、進士三個等級;井上則使用了直譯的翻譯方法。“秀才”“舉人”是明清科舉制度中的稱呼,即便日本與中國同屬漢字文化圈,為了更準確地傳遞這類詞匯的意義,筆者認為也有解釋的必要。
(四)宗教文化負載詞
宗教文化負載詞包括佛緣詞匯、中國古代封建迷信等相關用語。
例(6):
原文:化過紙,呆呆的坐在地上。(選自《藥》)
萊爾譯本:Having done with her weeping and havingburned her paper money, she now sits blankly on the ground.(選自Medicine)[8]56
井上譯本:やがて銀紙を焚いてしまうと地べたに坐り込み…[9]49
例(7):
原文:華大媽……化過紙錠。(選自《藥》)
萊爾譯本:Mother Hua... andburns the paper money.(選自Medicine)[8]55
井上譯本:華大媽…泣いて銀紙を焚いた。[9]48
對于“化紙”這一概念,萊爾譯本和井上譯本都沒有格外解釋。甚至,萊爾譯本將“化紙”和“化紙錠”都翻譯成了burn the paper money,井上譯本將兩者都翻譯成了“銀紙を焚く”。其實,“紙錢”和“紙錠”是兩個外形完全不同的東西,“紙錢”是供死者享用的冥幣,多為鈔票或銅錢狀;而“紙錠”是用錫箔糊制成銀錠狀的冥錢。可以看出,兩譯本在此處均未注意到“紙錢”和“紙錠”的差異。
(五)語言文化負載詞
語言文化負載詞包括諺語俗語、歷史典故、名言、成語,以及方言、臟話等。
例(8):
原文:多乎哉?不多也。(選自《孔乙己》)
萊爾譯本:Hath the gentleman many? Nay, he hath hardly any.(選自KongYiji)[8]46
井上譯本:多からず、多からず、多乎哉、多からざる也。[9]36
例(9):
原文:他還要老虎頭上搔癢!(選自《藥》)
萊爾譯本:Then the Xia kid’s gotta gorub salt in the woundby talking that kinda stuff.(選自Medicine)[8]54
井上譯本:あいつが虎の頭を掻いたから堪らない。[9]47
在例(8)中,井上和萊爾都在句式和詞匯使用上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孔乙己“書呆子”的氣質。正如萊爾譯本中的Hath、Nay,分別用Has、No的舊體形式來體現孔乙己的說話風格;井上譯本則采用了古典日語的表現形式來體現孔乙己“儒雅書生”的形象。在例(9)中,日語中形容“不自量力”的慣用語有“身の程を知らない”等,而井上選擇了“虎の頭を掻いた”的表達方式,目的是告訴目標語讀者,在漢語中形容一個人“不自量力”可以說“在老虎頭上搔癢”。但由于該譯本是日本第一個《吶喊》日譯本,為了便于日本讀者理解原文的意思,筆者認為此處應該在譯文后用括號加注說明,這是漢語中“不自量力”的比喻。
綜上所述,井上譯本在文化負載詞的翻譯過程中,較大程度保留了源語的文化色彩,使讀者體會到了中國風情。但他在對原文的理解方面稍有欠缺,對日語中存在但少見的名詞沒有進行特別的解釋說明。萊爾譯本較多地站在目標語讀者的立場,對文化負載詞大多采用注釋的翻譯方法,甚至用從句來解釋、定義文化負載詞。兩譯本對極具中國特色的文化現象都存在歸化、模糊的翻譯傾向,但在文化的解釋方面,萊爾譯本更勝一籌。
四、結語
近年來,我國大力倡導中華文化“走出去”,日本與中國同為漢字文化圈,在文化方面存在不少相通之處,或許可以采用異化為主、歸化為輔的翻譯策略,在充分傳達原作大意的基礎上,讓日本讀者多了解原汁原味的中華文化與地道的中文表達。而英語國家與中國存在較少的文化共通點,或許可以采用歸化為主、異化為輔的翻譯策略,讓英語國家的讀者在理解譯作表達的基礎上,實現文化層面的輸出,進一步逆轉中國大量輸入外國文化的局面。
隨著我國綜合國力日益提升及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力的逐漸擴大,西方社會對我國的關注度也與日俱增。現階段,以我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訴求被越來越多的國家聽到,我國在國際事務上的發言也越來越擲地有聲,正是中華文化“走出去”的大好時機。勞倫斯·韋努蒂的“異化論”無疑為中華文化“走出去”提供了一個新思路。這種以源語文化為中心的、彰顯“異質性”元素的思想正好符合中華文化融入世界文化的需求。在歷史的洪流中,“異質”的部分或融入目的語國家文化,被目的語讀者接納,或遭到目的語國家的抵觸和排斥,引發“文化沖突”,在“沖突”中實現文化的相互交流、碰撞。